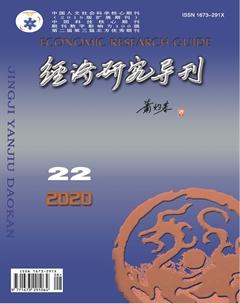資源型城市城鎮用地增長邊界劃定研究
徐宏娟 耿哲 徐巖



摘 要:城鎮用地增長邊界(UGB)劃定對資源型城市土地利用規劃和管理具有重要意義。以徐州市中心城區為例,構建地理加權元胞自動機(GWR-CA)模型,在對該模型進行校準和驗證的基礎上,考慮資源型城市生態環境約束條件,設定未來城鎮用地需求情景,基于“反規劃”理念,對2030年UGB進行劃定。結果表明:GWR-CA對2015年城鎮用地增長模擬的精度較高,可用于模擬未來城鎮用地擴張;兩種情景下,2030年分別新增城鎮用地106.75km2和273.25km2,前一種情景更為合理,在生態約束下2030年UGB面積為441.02km2,城鎮空間主要向東部及東南部緊湊式擴張。研究考慮了資源枯竭型城市生態環境約束,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和引導城市空間有序發展。
關鍵詞:資源型城市;GWR-CA模型;城鎮用地增長邊界
中圖分類號:F299.27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0)22-0115-06
引言
城鎮用地擴張一直是土地利用/覆蓋變化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城鎮用地不斷擴張,但城鎮用地無序蔓延給區域社會經濟及生態環境帶來了許多問題,如耕地過度非農化、森林砍伐、生態環境破壞等[1]。如何有效引導城市合理擴張,協調城市發展和資源及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2]。特別是在資源型城市,由于礦產資源的開采,資源型城市出現沉降塌陷、液化災害等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嚴重制約著城市建設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因此,綜合考慮其生態環境約束,引導其城市用地有序增長,成為這類區域轉型過程中面臨的重要課題。
城市增長邊界(Urban Growth Boundary,UGB)作為目前控制城市無序擴張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之一,其最早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開展研究和實驗[3]。UGB不僅是城市建設用地和非建設用地的分界線,也是城市在某一時期城市擴張的邊界線[4]。有效劃定城市空間增長邊界可遏制城市“攤大餅”式無序蔓延,倒逼土地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城市用地利用效率,從而降低城市增長的資源消耗成本[5]。我國在UGB研究與應用方面相對較晚,2006年《城市規劃編制辦法》首先提出要進行UGB的劃定,同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將剛性邊界和彈性邊界的概念引入北京市城市邊界之中[6]。然而,UGB一開始主要根據研究人員的經驗劃定,科學性相對不足,后來學者們綜合考慮空間因素(如交通、地形),采用基于元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CA)的城市用地增長模型[7~8]、CLUE-S[9]、CA-Markov[10]及FLUS[11]等模型劃定UGB,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已有研究大多針對非資源型城市開展UGB研究,而對資源型城市UGB劃定研究相對較少。同時,在已有模型中,地理加權回歸(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GWR)能可有效探索空間異質性影響因素[12],因而將其與約束性CA模型進行耦合的GWR-CA城市用地增長模型[13]可更有效地為UGB劃定提供依據。
為此,本研究以資源枯竭型城市徐州市的中心城區為研究區域,運用地理加權回歸(GWR)模型對其2005—2015年城鎮擴張驅動力進行分析,構建GWR-CA城鎮用地增長模擬模型對研究區2030年城鎮用地擴張進行情景模擬,進而劃定其UGB,以求為研究區城鎮土地利用規劃與管理提供決策依據。
一、研究區概況及數據
(一)研究區概況
徐州市位于江蘇省西北部,其地處東經116°35′~118°66′,北緯33°71′~34°97′。徐州是中國第二大鐵路樞紐,交通發達,區位優勢明顯,有“五省通衢”之稱,也是華東地區重要的老工業基地之一。作為資源型城市,徐州市歷史上依資源而興、靠資源發展,然而,隨著礦產資源逐漸枯竭,一系列生態問題陸續凸顯,如礦產開采造成的地面塌陷與沉降、水體污染等,嚴重制約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當前,徐州市正處于轉型關鍵時期,并正著力打造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導致近年來徐州市特別是其中心城區(包括賈汪區、泉山區、銅山區、云龍區、鼓樓區6個區)城鎮用地快速擴張。因此,徐州在生態環境問題、地理位置、交通區位、社會經濟及土地利用變化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將其作為研究區可為資源型城市城鎮用地增長邊界劃定提供參考。本研究以徐州市中心城區作為研究區(見圖1)。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的數據包括土地利用數據、DEM數據、城市規劃數據、交通區位圖及社會經濟發展數據等。其中,土地利用數據采用2005年、2015年的Landsat TM遙感數影像圖進行解譯,土地利用類型分為7類:城鎮用地、水域、耕地、草地、林地、其他建設用地及未利用地。影響徐州城鎮用地擴張的潛在因素分為地形因素、可達性因素和自然環境因素,其中地形因素包括高程和坡度,主要通過30m分辨率DEM(地理空間數據云)處理而來;可達性因素包括到高速公路的距離、到一般公路的距離、到市政府的距離、到區政府的距離、到鄉鎮政府的距離、到水域的距離及到景點的距離等,這類因素通過ArcGIS中的歐氏距離工具分析得到;自然環境因素主要包括河流、未穩定塌陷區、山林保護區、洪水淹沒區、嚴重液化區、風景名勝區、濕地保護區、自然保護區、二級水源保護區等,主要來自《徐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7—2020年)》等資料。以上所有因素都統一處理為30m分辨率的柵格數據,城鎮用地規模預測中所用的人口數據來源于2005—2015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徐州統計年鑒》。
二、研究方法
(一)GWR-CA模型
CA模型因具有自組織性、“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和從時間、空間兩個維度反映城市發展變化的能力而被認為是模擬復雜城市系統非常有效的模型之一[14],CA中元胞(土地單元)具有兩種狀態:城鎮用地和非城鎮用地,每個元胞都在特定步長t下按已設定的轉換規則進行轉換[15]。元胞i在t+1時刻的狀態轉換概率Pgi,t受其當前的狀態Si,t、空間變量影響下的土地利用轉換概率Pdi、周邊鄰域影響Pni、限制性因素Con和隨機因素Sto的綜合作用[16]。Pgi,t的表達式為[13]:
采用GWR-CA模型進行分析時,首先計算研究時段需轉換的元胞數量num,并設定每次迭代轉換數量k,本文在模型驗證時主要通過獲取研究時段內城鎮用地變化數量來求得num,而在未來城鎮用地模擬時通過城鎮用地需求預測獲取num;然后選擇具有最大Pgi,t的k個非城市用地元胞進行轉換,并更新土地利用圖層,重新計算Pgi,t,重復上述迭代過程,直到所轉換的元胞數量等于num為止[8]。
(二)模型校準及驗證
本文采用2005—2015年數據對GWR-CA模型進行校準。根據研究區實際,選取以下潛在驅動因素:到水域的距離(X1)、到高速公路的距離(X2)、到一般公路的距離(X3)、到鎮政府的距離(X4)、到區政府的距離(X5)、到市政府的距離(X6)、到景點的距離(X7)、高程(X8)和坡度(X9)。同時,作為資源型城市,研究區城鎮用地擴張的絕對限制因素包括未穩定塌陷區、山林保護區、洪水淹沒區、嚴重液化區、風景區、濕地保護區、自然保護區、二級水源保護區、湖泊、河流、水庫以及坡度大于25度的土地單元,對于這些絕對限制性因素,將其Con值設置為0,其他區域設置為1。
為獲取模型各變量的參數,本文分別提取1 250個發生城鎮用地轉換的元胞(Y=1)和1 250個未發生城鎮用地轉化的元胞(Y=0)共2 500個樣本點用于GWR模型分析。首先,基于SPSS軟件對各因素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并以方差膨脹因子VIF<10為標準剔除具有顯著共線性的潛在因素,再將保留的因素納入GWR4.0軟件中進行GWR回歸分析,并采用ROC檢驗(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回歸分析結果,ROC越接近1,模型有效性越高。在此基礎上通過克里金空間插值法對各驅動因素回歸系數進行空間插值,從而獲取各驅動因素在各個柵格處的作用系數。
模擬模型精度驗證主要采用總體精度、Kappa系數、FOM指數(Figure Of Merit)等方法[19],其中,總體精度介于0~100%之間,Kappa系數、FOM都介于0—1之間,以上指標值均越大越好。對于Kappa系數,當其大于等于0.75時,模型具有較好的準確性,0.5 (三)資源型城市城鎮用地增長邊界劃定思路 “反規劃”理念認為,城市規劃應先將城市生態基礎保護起來,從而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要[20]。基于“反規劃”思想,本文通過參考《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2005年)和《武漢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第224號)初步劃定生態控制線,主要包括山林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濕地保護區、自然保護區、二級水源保護區,再結合徐州資源枯竭型城市和自然環境的特點,將未穩定塌陷區、洪水淹沒區、嚴重液化區、湖泊、水庫、河流以及坡度大于25度的區域也納入控制線范圍,在此基礎上對城鎮用地進行布局。本文目標年城鎮用地擴張邊界劃定具體思路為:首先,根據上述過程劃定生態控制區并將其作為GWR-CA模型的絕對限制因素;其次,結合歷史土地利用數據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預測目標年的城鎮用地需求量;最后,在采用歷史數據對GWR-CA模型進行校準和精度驗證后,將生態控制區作為絕對限制性圖層,采用GWR-CA模型對未來城鎮用地擴張進行情景模擬,并選擇合適的情景劃定城鎮用地邊界[11]。 本文設定兩種未來發展情景:情景一,基于綜合增長率的城鎮人口及城鎮用地預測,情景二,基于馬爾科夫模型的城鎮用地預測。其中,情景一主要是考慮近年來研究區城鎮人口年均綜合增長速度,進而預測2030年城鎮人口數量,并根據《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確定人均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標準,進而預測2030年城鎮用地規模。情景二采用廣泛用于土地利用數量變化預測的馬爾科夫模型[21]對城鎮用地規模進行預測。分析時,本文以2005年為基期年,2015年為驗證年,土地利用類型的轉移概率公式為[22]: 三、結果分析 (一)模型校準與驗證結果 首先,在GWR分析前對自變量進行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9個潛在變量均不存在顯著共線性,進而將其全部帶入GWR進行分析。結果表明,GWR模型的赤池信息準則(AICc)為1 163.182,而全局Logistic回歸的AICc為1 412.293,GWR的AICc結果小于全局回歸模型,表明采用GWR模型可獲得最優帶寬。對模型進行ROC檢驗,結果表明,GWR和全局Logistic模型的ROC分別為0.968和0.902,表明兩者的擬合效果均很好,但GWR模型擬合效果更優,因此研究區城鎮用地擴張驅動力應考慮空間異質性特征。 從回歸模型結果來看(見下表),在其他因素不變的前提下,到高速公路距離(X2)、高程(X8)、坡度(X9)對研究區城鎮擴張影響均為正向,回歸系數分別在0.146~0.402、0.013~0.085、0.013~0.059之間,到一般公路距離(X3)、到鎮政府距離(X4)、到區政府距離(X5)對城鎮擴張影響均為負向,回歸系數分別在-3.392~-0.972、-0.706~-0.076、-1.037~-0.326之間,而其余因素的影響既有正向也有負向,這表明各變量在不同區位對城鎮用地擴張有著不同的影響效果。進而,采用克里金空間插值法對以上各變量回歸系數進行空間插值,從而得到各元胞各變量對城鎮用地擴張的影響系數。 將以上空間插值得到的結果帶入式(2)和式(3)求得各變量作用下非城鎮用地城鎮化的概率圖層,進而基于2005—2015年數據采用GWR-CA模型進行模擬,并將2015年模擬結果與實際土地利用現狀進行對比,采用前述精度驗證指標進行分析,結果(見圖2)表明,GWR-CA模型的總體精度為96.52%,Kappa系數為0.82,FOM為0.58,Kappa和FOM值分別大于0.75和0.5,且FOM大于已有研究中的FOM值[23~26],說明校準后的GWR-CA模型能較好地反映研究區城鎮用地擴張過程,該模型可信度較高,可用于對研究區未來城鎮用地擴張的模擬。 (二)目標年城鎮用地增長邊界劃定 本文根據前述兩種情景進行未來城市用地擴張模擬:情景一,基于綜合增長率的城鎮人口及城鎮用地預測,預測出2030年研究區城鎮人口為383.38萬人,按人均建設用地115m2/人計算,可得2030年城鎮用地面積為441.02km2,比2015年增長106.75km2;情景二,基于馬爾科夫模型的城鎮用地預測,將2005年與2015年作為預測基期年,利用不同地類之間面積數量或比例關系進行概率轉換[22],預測出2030年研究區新增城鎮面積273.25km2。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政策與規劃起著重要作用,我國對城市建設用地實行建設用地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堅持底線思維和紅線意識[27]。因此,未來城鎮擴張速度與以前相比會有所減緩。2018年徐州榮獲聯合國人居環境獎,成為宜居城市中的翹楚,自2015年以來,徐州一直致力于舊城改造工作,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戰略位置,打造生態宜居的樣板城市,這就要求徐州節約集約用地,遏制城鎮的粗放擴張,加快資源型城市的轉型,故此徐州2015—2030年主城區的城鎮擴張面積不宜過大。因此,本研究中馬爾科夫模型在未來城市用地擴張模擬方面可行性不強,而情景一預測結果更符合未來發展情況,故將情景一作為城鎮用地增長邊界劃定的依據,故需轉換的城鎮用地柵格數為118 469個,進而確定城鎮用地增長邊界(見圖3)。 從情景一下城鎮用地增長邊界模擬圖來看(見圖3),新增城鎮用地主要分布在銅山區、云龍區和鼓樓區,而賈汪區、泉山區相對較少,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城鎮用地擴張要求地勢平坦,連霍高速與淮徐高速的交匯加速了附近城鎮的發展,徐州經濟開發區與銅山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帶來的經濟增長促進了開發區附近城鎮規模的擴大。城鎮用地增長邊界劃定結果表明,2015—2030年新增城鎮用地約106.75km2,城市空間出現向東部和東南部的擴張趨勢,同時生態約束控制使城鎮用地增長更為緊湊,有利于倒逼已有城鎮用地的集約高效利用,保護耕地,提升城市發展質量。同時,由于在城鎮用地擴張模擬過程中綜合考慮了采礦塌陷地等生態敏感區域對城市建設的影響,劃定的城鎮用地增長邊界更有利于協調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因此,以上結果不僅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要求,也遵循了城鎮用地擴張的客觀歷史規律。 四、結論與討論 針對已有研究較少對資源型城市城鎮用地增長邊界進行研究的問題,本文以徐州中心城區為研究區域,在“反規劃”理念下運用GWR-CA模型來劃定2030年其城鎮用地增長邊界。研究表明:首先,GWR-CA模型模擬結果的總體精度、Kappa系數、FOM分別為96.52%、0.82和0.58,表明模型具有較高的準確性,可用于對未來城鎮用地擴張進行模擬。其次,基于綜合增長率的城鎮人口及城鎮用地預測結果更符合研究區發展實際,在“反規劃”理念下劃定2030年徐州市中心城區的城鎮用地增長邊界,新增城鎮用地面積為106.75km2,城市空間有向東部和東南部擴張趨勢,城鎮用地集約水平將會提高。 限于數據可獲取性,本文在驅動因素選擇方面不夠全面,如缺少基本農田這一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同時,本文采用遙感解譯數據進行研究,在用地規模上可能與實際城鎮用地會有一定差異。因此,未來需綜合考慮以上問題,進一步提升研究區城鎮用地增長邊界劃定的準確性。 參考文獻: [1] ?叢佃敏,趙書河,于濤,等.綜合生態安全格局構建與城市擴張模擬的城市增長邊界劃定——以天水市規劃區(2015—2030年)為例[J].自然資源學報,2018,(1):14-26. [2] ?Xia C.,Zhang A.,Wang H.,et al..Predicting the expansion of urban boundary using space syntax an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9,(86):126-134. [3] ?張韶月,劉小平,閆士忠,等.基于“雙評價”與FLUS-UGB的城鎮開發邊界劃定——以長春市為例[J].熱帶地理,2019,(3):377-386. [4] ?劉偉玲,張育慶,楊俊.不規則鄰域CA的城市增長邊界研究——以大連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例[J].測繪通報,2018,(8):93-96. [5] ?Liang X.,Liu X.,Li X.,et al..Delineating multi-scenario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with a CA-based FLUS model and morphological method[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8,(177):47-63. [6] ?張振廣,張尚武.空間結構導向下城市增長邊界劃定理念與方法探索——基于杭州市的案例研究[J].城市規劃學刊,2013,(4):33-41. [7] ?龍瀛,韓昊英,毛其智.利用約束性CA制定城市增長邊界[J].地理學報,2009,(8):999-1008. [8] ?舒幫榮,劉友兆,張鴻輝,等.集成變權與約束性模糊CA的城鎮用地擴張情景模擬[J].武漢大學學報:信息科學版,2013,(4):498-504. [9] ?Huang J.,Liu T.,Huang D.Delimiting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using the CLUE-S model with villag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J].Land Use Policy,2019,(82):422-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