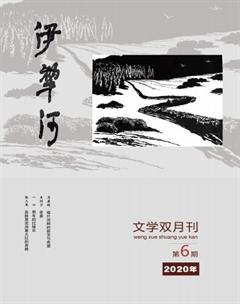老宅
去年五月,我曾獨自回到察布查爾縣的老宅,待了不足半日。彼時,是我時隔三年后第一次來看老宅。今天,多半是在我的主張下,退休已有些時日的父親陪著我,時隔不多不少又一年再次來到了這里。我們在一扇嶄新的紅色大門前停下腳步,門的外側,一條陌生的柏油路直淌而過,透過側旁的圍墻,我看到院內的屋頂上有幾個伙計正忙著拾掇,鋪設彩鋼。父親敲門兒,呼叫里頭的伙計,一邊扭過頭興致勃勃地向我介紹這段時間來他翻修老宅的“大業”。
“咔嗒”一聲,鐵質的雙開合大門從內推開,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精瘦男子給我們開了門,父親叫他“小田”,是這次翻修作業的負責人。我跟著父親一進入院內,便立即明白先前他所說的“大業”絕非吹噓。去年來時,大門還是乳白色,經十余年,斑駁可見,院內雜草叢生,林果敗落,屋舍外墻上的瓷磚和房內的涂料稀稀拉拉,多有凋落,就連屋頂也長滿了野草,此番前來,著實大變樣。小田師傅翻新了大門,重刷了涂料,貼了瓷磚,整飭屋頂鋪上了彩鋼,而父親,則親自將院內的雜草拔除清掃完畢。
我對童年的回憶,不管在何時、以何種方式開啟,總是繞不開這座神奇的院落,這里的一花一木、一事一物,都固執地占據著各自的邊界,納藏著一段段秘密與回憶。
馕坑里的火
一進門右側,幾團灰白的余燼堆在墻角,與下方的土層混出灰白相間的模樣,那是前幾周母親燒掉我不穿的衣物留下的灰燼。恰在此處,曾經坐落著一口馕坑。在兒時的印象里,當時的馕坑是高出我頭的,盛夏里,外婆和母親都曾坐在上頭,前后忙碌數小時,為一家人打出數周的口糧。新打出來的馕是我最熱衷的美食,外婆和母親總是會特地打幾個摻了羊油和雞蛋的小馕,她們遞給我時的神情,就我記憶所及,是有一些區別的。外婆更多的是嚴肅,或許因為那時她已經五十多歲,如此高強度的作業,身體已開始吃不消,加之需要專心,早點打發我也便于她集中精力;至于母親,更多的則是一種喜悅,那種笑容,怎么說呢,在烈焰的灼烘和馕坑的炙烤下,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紅彤彤、還帶有幾絲煙漬的笑臉,其實并不好看,說到底,那不過是一個初嘗生命喜悅的年輕母親的笑臉。那時我不過四五歲,妹妹也躺在襁褓中。她生下我們,親手打出熱乎乎的馕,養育著我們,并沉浸于其中。
往日如昨,如今多少年過去了,我依舊會不時想起小時候的馕,其實味道早已模糊,只是那神情、笑容和熱乎乎的感覺,從那個酷暑的熱浪中掙脫,成為一種無論何時都溫暖的回憶。
后來,大概是在十三年前,外婆和母親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再上馕坑,它的宿命便也走到了盡頭。然而在它的遺址上,火焰卻從未熄滅。
正如前面所說,時至今日,母親都會定期在這里燒些東西,不是什么特別的,不過是些我廢舊的衣物和書本罷了。母親燒我東西的習慣,一直可以追溯到我記事起。或是受了外婆的影響,母親聲稱并始終堅信,但凡我穿過的衣物、留有字跡的書本,都必須燒為灰燼,倘若不小心被別人污損,勢必將給我帶來不幸。母親為了我,就這樣荒唐又執著地燒了二十多年,在老宅的爐灶里燒,在火盆里燒……終于在馕坑拆掉后沒多久,開辟了這處新位置。如今,即便我們已搬往伊寧市十多年,母親依舊保持著這個習慣,定期收集好我的廢舊衣物和書本,拿到老宅馕坑的遺址,點燃那團熟悉的火焰。
我曾多次想著阻止母親,但又一次次作罷。因為我知道,無論是馕坑里烤出我和妹妹食物的火,還是在她看來能夠庇佑我平安的火,母親都不容熄滅。
磚石與野草
父親拍了拍我,我才晃過神來,小心地移開腳步,避免灰燼沾上鞋子。從這個角度,恰可以看到老宅前院的全貌,三棟老房沉默地駐守于斯,其中一棟最大的,初建于1999年,貼滿紅、白兩色的瓷磚瓦片,偶有幾片殘破的已被父親換上了新的,明顯區別于其他兩棟未貼瓷磚的房子。從建成到2005年,這棟房一般都是空置的,只有家中來了借宿的客人才會住人,直到后來家里安鍋爐,通暖氣,我們才搬離燒煤爐的房子住了進去。另外兩棟則蓋得更早些,時間雖已模糊,但我清楚地記得,當時蓋這兩棟房子余下的磚塊,被父親拿來砌滿了前院的地面。
小時候,每逢大雨,鋪滿棕紅色磚塊的庭院都會煥然一新,散發出一種特別的光澤,之前泥濘不堪的地面不復再現。鋪磚自然是大有裨益,但每逢酷暑時節,外婆總要在庭院里撒上好幾桶水,給滾燙的磚塊降降溫,否則灼熱難耐。這時候,我總要責怪外婆一番,認為她浪費了水資源,曉之以“最后一滴水將是人類的眼淚”等等大道理,而她總是耐心地聽完,回復道:“這水流入地下,成為地下水,或者蒸發掉又變成雨水降下來,怎么會是浪費呢?”三言兩句便使我語塞。如今回想起這段往事,不禁唏噓感慨其間的規律。老去枯死、自然倒下的樹木,從一處流向另一處的水,蒲公英被吹散的種子……自然中的一應萬物,只要不加以人類過多的參與,因循各自的路徑循環往復,又何曾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死去”“浪費”呢?
去年來時,庭院里長滿了齊膝深的野草,遠不是此刻經父親修整后的光景。因老宅長久閑置,院落的地面長年無人踩踏,野草便順勢抓住機會,一個個從磚塊間的縫隙中竄出,肆意生長、蓋滿了庭院,讓人不禁喟嘆這野蠻的生長力。即便是今日,依舊有幾束野花或高或低、星星點點地點綴著庭院。低頭細看,還能發現好幾處螞蟻穴,偶有幾支密密麻麻的“行軍蟻”部隊井然有序地前進著,似是在搬運著什么……說來,人和自然的關系真是奇妙,有時相依相存,但只要人類稍加缺位,自然往往會在一瞬間恢復原貌,悄無聲息間抹去人們加諸其上的印記。
睜眼看世界的地方
說來神奇,回顧往昔的二十余年,如果說哪個階段對于培塑現今的我開放包容的世界觀、文化觀有過裨益,倒非那些在大城市甚至異邦所見的世面和經歷,而恰恰是在這方宅之內。我稱之為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地方”。
而后兩年,我正式步入校園開始接觸先前幾未接觸過的國語。對那時的我而言,在學校里呆的一整日,無論是上課,寫作業,還是課間游戲,交朋友……多半都是在學國語,以致我一度認為學習是一件頗為費力的事兒。入學后沒幾個月,我開始在那棟我和外婆、妹妹常住的偏房外墻上記刻拼音和新學的漢字,每日如此,樂此不疲。除了鞏固學習的目的,當時還有另一層考慮,彼時熱播的香港僵尸劇里,林正英總會用一些寫著紅色漢字的黃紙符咒,一貼上去,便讓各路僵尸鬼怪動彈不得,以至我深信所有的漢字都擁有莫測的力量,足以守護我家的老宅。那幾年,我在院內所有能刻寫的墻面上都留下了這樣的字符,從早期的拼音、漢字到完整的句子,悉數有之。時至今日,兒時刻寫的個別拼音和漢字依舊醒目,靜靜地躺在墻壁上……
誠如先前所言,老宅是我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地方,換言之,我的成長便是在這一過程中的成長,人生最劇烈的變化、最豐富的體驗、最精彩有味的生活,基本都集中在那十幾年。打我記事起,我置身成長的就不只是一種背景和語境:父母和外婆都掌握三門以上的語言,英雄史詩里的巴特爾,《天方夜譚》里的飛毯,金庸古龍筆下快意恩仇的江湖,每晚必看的港臺劇和日漫,裘伊·西柏導演的《霹靂舞》中炫酷的舞姿,以及數不清的各類各國譯介的電影、音樂、電視劇。那會兒的娛樂資源或許是稀缺的,科技也不可與今日語,但快樂從未稀缺。鄰里街坊不僅操著各種語言和方言,更有各式各樣的人們,有能說會道的幽默家、吟詩彈唱的阿肯、手藝精湛的木匠……有打得一手好馕的師傅,偶爾拿著和好的面過去,只消留下幾個馕便可作報酬;有利索老成的屠夫,上門宰羊,收拾,在半推半就中欣然拿著主人送的一塊肉告別……那些有趣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生活,工作,朝夕相處,他們常常是搖搖腦袋哼幾句便是詩,長吁短嘆唱幾句便是歌。
或許是因為那時大家相對都閑適,又或是因為和外部世界的直面與對比也不多,在我腦海中,生活樂趣的匱乏,彼時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種有閑階級創造的快樂,頗有點兒古典主義的意味。
如今回想起那段往事,就好似昨天,但將之描述出來,用的,似乎又是未來的語言,恍如隔世。
后院中的游戲和死去的麻雀
在前院的右側,有一條幽長的通道直通后院,這是連接前后院的唯一樞紐。通道左面,是瓷磚瓦房的右側,有一面高達四米的磚塊墻壁,右面則是鄰居房舍的左側墻壁,全由草泥打造,當年我刻寫于此的字符早已風蝕殆盡。我走過通道移步后院,映入眼簾的是一大片齊腰深的雜草,乍看上去,羊圈和廁所似是長在了這些雜草上,漂游不定,輕易找不到下腳的地方。我久久佇立,腦海里逡巡著往昔在此的種種回憶,正是在這塊長滿雜草的地方,曾種過土豆、西紅柿、辣椒,養過雞和鴨,短暫地圈養過幾只綿羊,還有幾株蘋果樹、梨樹和杏樹留存至今。不過在兒時,這里更多的是我和妹妹游戲的地方。有時是我陪著她玩過家家,用手帕裹上幾塊兒馕和干果,往水壺里倒滿奶茶,一般來說,我們都更青睞用那種墨綠色的軍用水壺,這會讓我們接下來的“荒野旅途”多一分身臨其境的感覺。當然,更多時候多半是在我的強迫下,妹妹會和我排演一些具體的故事,由我負責構思具體的情景、場景,進而共同演繹。比如一次激烈的戰斗,我虛構出眼前的敵人和數量,然后我們倆揮舞著父親用鋸子和小刀制作的木劍,和不存在的敵人展開一番惡斗,那時的我如此癡迷這類游戲,以致常常在后院消磨了大半天,全然不顧早已餓得發慌的妹妹。
說到最喜歡的玩具,自然要提到彈弓。在過去,彈弓是男孩子們最常見的玩具之一,打靶的目標從靜物到動物,不勝枚舉,鳥兒自然是其中最受男孩們青睞、借以證明自我的選擇。而我,便曾在后院打死過一只麻雀。
在那次命中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有過無數失敗的嘗試,在樹上歇息的、飛著的、偶爾到地上覓食的鳥兒,都是我屢試不爽的射擊目標。直到那個微涼的夏日午后,離晚飯還有些時間,我拿著彈弓來到后院,正巧看到幾只麻雀在稍高些的楊樹枝干上歇息,瞄準、射擊,隨著石籽兒“嗖”的一聲射出,其中一只應聲直落,在擊中的剎那,久違的勝利喜悅涌上心頭,甚至一度左右張望,希冀著能有旁人見證我的成功。但隨著鳥兒“噗通”墜地,以及隨后短暫卻異常醒目的掙扎、呻吟,這種喜悅轉瞬便煙消云散,轉而被一股刺骨的恐懼和負罪感攝住全身,一度動彈不得。從那以后,我再沒有以活物做過彈弓試射的靶子,同時,也讓我過早地陷入對死亡的探究與思索。
過去的哈薩克老人們常愛說:“我身體的一半已埋進土里了”,頗有幾分看淡生死的哲理意味,以及對生命、生活的知足和謙遜。兒時每晚入眠前的時刻,伴隨我的必定是外婆的故事,以及她不厭其煩的嘮叨。她總是一邊捻著飛轉的紡錘,做些打毛衣、毛襪用的羊毛線,一邊給我講哈薩克人口耳相傳了數百年的英雄史詩。而每當她放下手中的紡錘,我便知道她要開始那些諄諄教誨了,大體是些這樣的話:日后在她的葬禮上應怎樣拄著木棍哭泣,以怎樣的音調說出那些悼念的詞語。當時的我并不以為然,直到后來我去參加某個親戚的葬禮,因一時疏忽了哈薩克人參加葬禮時的禮節,而感到羞愧和自責,我才明白那叮嚀并非只關乎逝者的體面和尊嚴,也關乎生者和死亡本身,關乎你如何看待死亡、是否尊重死亡。
人們從對死亡的陌生到漸漸熟悉,多半是因為葬禮。過去,我家附近有一處墳地,我時常好奇那土堆下的世界,每當送葬的卡車滿載站立的人們行經路口,父親便會告訴我,若想真正理解生命的意義,便得去參加一次葬禮。生者的哭泣總是提醒著每個人,多年來,死神從未放棄對我們的窺伺,在它面前,我們不過是尚在此生羈旅的人。
一次又一次,我撇下許多迫在眉睫的事務,于忙碌間趕到這里,漫無目的。一次又一次,當我披著夕陽褪去的最后一絲余暉,轉身告別這里,便像在縈繞的霧色中凝望一個熟悉卻又漸行漸遠的、沉默的故人背影。
我的老宅,我回憶的精神血脈,無論它流注、置身于何種空間、時間,我祝福它永遠年輕且流動。我也相信并期待,誠如楊煉先生所說——永遠出發,卻永無抵達,無論何時我都能鼓足勇氣上前,輕輕敲一敲那扇紅色大門,“嘿,我來了”。
·作者簡介·阿依奔,哈薩克族,新疆作家協會會員,現居伊寧市。在《青年作家》《西部》《民族文匯》等刊物發表小說、散文、詩歌三十余篇(首),出版有個人文集《窗里窗外》。曾獲第四屆“中華情”全國詩歌散文聯賽金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