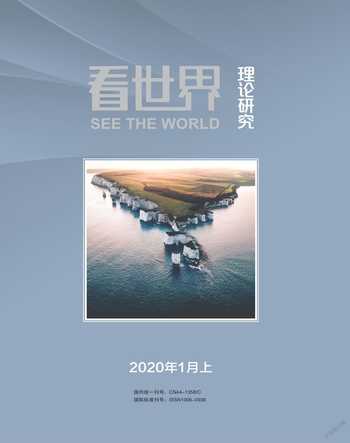論《邊城》中的民俗事象
摘要:《邊城》是沈從文筆下呈現(xiàn)出的最美麗的“湘西世界”,湘西的山山水水和巫楚文化氛圍養(yǎng)育了沈從文,而沈從文又通過(guò)自己的筆把湘西故土神秘的風(fēng)姿和噴涌的原始生命力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邊城》的成功之處在于沈從文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放在了民俗事象之中,將意蘊(yùn)深厚的民俗景觀作為寫作的背景,將小說(shuō)的人物和事件融于民俗學(xué)語(yǔ)境的框架中,使民俗獲得了一種媒介的作用。因此,對(duì)民俗的理解成為了對(duì)《邊城》理解的一把鑰匙。
關(guān)鍵詞:《邊城》;民俗;事像
歌謠在苗族人的生活中,特別是在各種儀式中,占著很重要的地位。苗族人不但平素能隨時(shí)隨地信口唱來(lái),表達(dá)當(dāng)時(shí)的情緒或敘述當(dāng)?shù)氐氖录颐慨?dāng)舉行某種儀式或集會(huì)時(shí),男女對(duì)歌更是日夜不休。而對(duì)歌也成為了男女婚戀過(gu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huán),青年男子是否能尋到理想的伴侶、抱得美人歸,就要看他唱歌的本事了。《邊城》中的天保和儺送兄弟二人為情所困,也正是通過(guò)唱歌的形式來(lái)公平地在愛(ài)情中一決勝負(fù)的。儺送動(dòng)人的歌聲在夜色中飄蕩,讓翠翠在睡夢(mèng)中感受到了這“又軟又纏綿”的情意,她對(duì)會(huì)唱歌的儺送生出了少女的情愫,“靈魂為一種美妙的歌聲浮起來(lái)了。”一曲曲歌謠讓這場(chǎng)沒(méi)有硝煙的愛(ài)情之爭(zhēng)變得愈發(fā)溫婉,同時(shí)也顯露出苗族人樸素自由的情愛(ài)觀念——無(wú)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沒(méi)有金錢、門當(dāng)戶對(duì)的限制,優(yōu)美的情歌發(fā)自人的肺腑,又以全部的生命來(lái)歌唱,怎能不叫人為之傾倒呢?青年男女完全以情愛(ài)為中心進(jìn)行自由交往和戀愛(ài),不受封建禮教的束縛與影響,他們的縱情放歌既是健康、優(yōu)美又不悖于人性的自由的生命形式,同時(shí)更是狂熱地追逐著生命本真意義的激情沖動(dòng)和個(gè)體生命自由意志的證明。沈從文如行云流水般自由的筆觸為唱山歌這一苗家風(fēng)俗作了美麗動(dòng)人的展示,展現(xiàn)出他對(duì)民歌的傾心和深刻的理解力,也展現(xiàn)出這種民俗中隱含的一種原始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機(jī),“沈從文將這種生命力的有無(wú)上升到了一個(gè)民族整體生命力之有無(wú)的象征的高度。”這種在唱歌民俗中體現(xiàn)出的熱情智慧的生命與自然和諧的情韻正是沈從文強(qiáng)調(diào)的意旨所在。
在時(shí)序、季節(jié)的變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傳統(tǒng)的節(jié)日,這些節(jié)日最易顯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端午節(jié)中的劃龍船、捉鴨子,是一種湘西特有的民俗文化。這種文化不受外來(lái)文化的影響,保存的是自己民族固有的風(fēng)俗習(xí)慣。《邊城》中四次寫到了端午節(jié)劃龍船比賽,而翠翠、儺送,天保三人的情感糾葛都是因端午節(jié)而引起的。端午節(jié)將一切的悲歡離合、人事命運(yùn)都串接在一起,成為了小說(shuō)敘事過(guò)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端午日,當(dāng)?shù)貗D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額角上用雄黃蘸酒畫了個(gè)王字”,“約上午十一點(diǎn)鐘,全茶崛人就吃了午飯……莫不倒鎖了門,全家出城到河邊看劃船。”在這樣一個(gè)全城出動(dòng)的節(jié)日里,沈從文把人與人的交流與來(lái)往順理成章地放在了人頭攢動(dòng)的河邊,為青年異性的結(jié)識(shí)和交往提供了一個(gè)寬松自然的環(huán)境,讓愛(ài)情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自然地出場(chǎng)了。翠翠在小說(shuō)第二次的端午節(jié)描寫中與儺送相識(shí),她用輕輕的一句“你個(gè)悖時(shí)砍腦殼的”表達(dá)了少女嬌羞矜持之態(tài),也使得她對(duì)儺送單純的誤會(huì)成為第三次端午節(jié)的伏筆。因“不能忘記那件事”,翠翠在來(lái)年又同祖父去看了半天船,但卻因儺送在“六百里外沅水中部青浪灘過(guò)端午”,所以未能相見(jiàn),卻結(jié)識(shí)了天保和順順。經(jīng)過(guò)四次端午節(jié),翠翠從由祖父陪同到獨(dú)自趕節(jié),在節(jié)日民俗的啟迪下,其復(fù)雜微妙的內(nèi)心活動(dòng)在端午節(jié)的氣氛中孕育成熟,情愛(ài)意識(shí)也發(fā)生了由無(wú)知到蒙朧的變化。《邊城》不但為我們?cè)敿?xì)展示了端午節(jié)的熱鬧場(chǎng)面,彰顯了湘西人民的粗獷放達(dá)的性格和心理,敘寫了端午節(jié)這天人們以一種近乎虔誠(chéng)的心態(tài)、激動(dòng)的心情來(lái)感受這節(jié)日的美妙之處,我們由此知道端午節(jié)在湘西邊民的心中占有著怎樣的地位,湘西人快樂(lè)、激動(dòng)與幸福的體驗(yàn),是如此真實(shí),如此單純,如此打動(dòng)人心。同時(shí)也為我們展示了湘西青年男歡女愛(ài)中飽含著生命的自由與熱力,在他們生命能量的盡情釋放中表達(dá)的是對(duì)活著的喜悅和生命存在的禮贊。
“賽船過(guò)后,城中的戍軍長(zhǎng)官,為了與民同樂(lè),增加這個(gè)節(jié)日的愉快起見(jiàn),便派兵士把三十只綠頭長(zhǎng)頸大雄鴨……放入河中……不拘誰(shuí)把鴨子捉到,誰(shuí)就成為這鴨子的主人。”捉鴨子這一端午節(jié)的附屬民俗,表現(xiàn)出男人本能中的征服欲望。順順年輕時(shí)本是捉鴨子的一把好手,“在任何情形下總不落空”,但當(dāng)次子儺送在十歲便能入水閉氣把鴨子捉到時(shí),順順解嘲似的說(shuō):“好,這種事情有你們來(lái)做,我不必再下水和你們爭(zhēng)顯本領(lǐng)了。”捉鴨子在這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成熟男性顯山露水的手段,同時(shí)也成為了小男孩長(zhǎng)大成人的標(biāo)志。儺送用嫻熟的技巧使自己在水中成為了最受矚目的男子,同時(shí)也贏來(lái)了人們“二老,二老,你真能干”的贊譽(yù)聲,善捉鴨子在此體現(xiàn)了男人對(duì)于征服獵物多多益善的原始欲望。在端午節(jié)這樣一個(gè)男女相會(huì)的時(shí)節(jié),追趕鴨子的民間游戲同時(shí)也包含了男女追逐歡會(huì)的模式和意念,暗含了男子對(duì)女子的征服欲。所以,同伴和儺送開(kāi)著這樣的玩笑:“你這時(shí)捉鴨子,將來(lái)捉女人,一定有同樣的本領(lǐng)。”女人和鴨子一樣,都是成熟男子的戰(zhàn)利品,捉鴨子這一民俗事象同樣顯現(xiàn)出湘西青年男女蒙朧的情愛(ài)意識(shí)的覺(jué)醒。
在《邊城》中,“走車路”和“走馬路”這兩個(gè)婚嫁民俗事象共同建構(gòu)起了一個(gè)深層民間婚俗結(jié)構(gòu)。“走車路”具有堂皇而名正言順的特點(diǎn),婚姻的締結(jié)是雙方長(zhǎng)輩的權(quán)力和義務(wù),而婚姻的當(dāng)事人無(wú)足輕重。在這種婚姻觀念的支配下,夫妻雙方的責(zé)任和義務(wù)勝過(guò)情感,帶有明顯的漢族婚俗特點(diǎn),也被認(rèn)為是帶有包辦婚姻色彩的婚俗。“走馬路”則是一條愛(ài)情勝過(guò)婚姻、情感重于義務(wù)的成婚之路,它可以飛越貧富不均筑成的高墻,喻指自由戀愛(ài),具有典型的苗族婚俗特點(diǎn)。因?yàn)槔洗さ呐畠寒?dāng)年和一個(gè)“營(yíng)兵”私下相愛(ài)受到社會(huì)的非難而徇情死去,所以他擔(dān)心翠翠也“走馬路”重蹈覆轍,就希望愛(ài)翠翠的那個(gè)青年“走車路”,通過(guò)媒人來(lái)正式求婚。老船工一心想把翠翠許配給天保,并對(duì)天保說(shuō):“大老,你聽(tīng)我說(shuō)句正經(jīng)話,你那件事走車路,不對(duì);走馬路,你有份的!”并且在知道了動(dòng)聽(tīng)的歌謠是儺送而非天保所唱時(shí),依舊暗示翠翠“大老也很好”,并且試探性地問(wèn)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婦,請(qǐng)人來(lái)做媒,你答應(yīng)不答應(yīng)?”天保一開(kāi)始就“走車路”,充分體現(xiàn)出他傾向于漢族傳統(tǒng)的婚姻觀,他將自己和翠翠的婚姻完全放在老船工的應(yīng)允點(diǎn)頭上,似乎并不關(guān)心翠翠愛(ài)的到底是自己還是儺送。而翠翠的靈魂是山歌凝成的,她愛(ài)的是要唱一輩子歌給她聽(tīng)的儺送。儺送和翠翠兩人因歌聲而產(chǎn)生愛(ài)情,這種單純的氣質(zhì)使得兩人在性情上能保持和諧一致。在這里,愛(ài)情悲劇的產(chǎn)生就在于這兩種婚俗所體現(xiàn)的觀念的矛盾與對(duì)立。兩種不同的婚俗對(duì)于湘西這個(gè)特定的環(huán)境來(lái)說(shuō),其實(shí)就是苗族生活文化和漢族生活文化差異性的表現(xiàn)。在這個(gè)二元對(duì)立的婚俗結(jié)構(gòu)中,沈從文所展現(xiàn)的這一愛(ài)情悲劇,否定了傳統(tǒng)的婚姻,顯然是有積極意義的。
列夫·托爾斯泰說(shuō),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藝術(shù)因素之一是“基于歷史事件寫成的風(fēng)俗畫面”。在《邊城》中,沈從文之所以傾情于民俗,根本的一點(diǎn)就在于對(duì)原始生命張力的贊美及生命自由意識(shí)的張揚(yáng)。所以當(dāng)他不遺余力充分展示湘西傳統(tǒng)文化的豐富內(nèi)容之時(shí),各種各樣的民俗:神秘的、殘忍的、熱鬧的、活潑的等等,都實(shí)際是作者贊頌美,追求人性美,追求優(yōu)美的人生形式的一個(gè)手法或方法,通過(guò)這些不為人知的湘西風(fēng)情的描寫,作者想借此傳達(dá)的不僅是向世人展示湘西的風(fēng)貌,更主要是對(duì)湘西優(yōu)美、健康、自然,又洋溢著勃勃生機(jī)的人生形式的稱頌和追求。通過(guò)對(duì)理想中的湘西世界的描繪,表現(xiàn)出他對(duì)某種更為健全的民族精神和更為完美的倫理道德的呼喚,以及他對(duì)重建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渴望和決心。
作者簡(jiǎn)介:
高露露(1994—),性別:女,籍貫:甘肅省,學(xué)歷:研究生,單位:西北師范大學(xué),研究方向: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