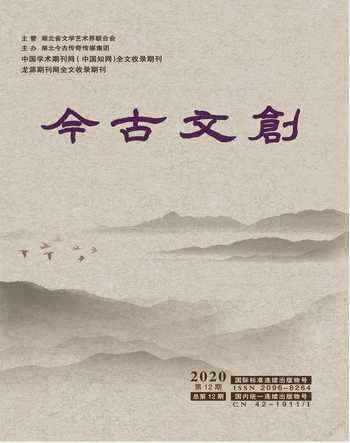探析《世說新語》中的士人人格精神
【摘要】 在我國文學史上《世說新語》是經典筆記體小說,內容涉及漢末到東晉時期士族逸聞趣事,書寫魏晉風流故事,透過風流瀟灑士子生活看到魏晉士人諸多荒唐行為,發現這些知識分子的血淚、痛苦、悲哀、無奈,猶如開在懸崖邊的鮮花,在寒風中掙扎,用特殊的言行風貌表露士人心聲。本文通過探析《世說新語》中士人人格精神,以期深入解讀《世說新語》,從中汲取文學養分。
【關鍵詞】 《世說新語》;士人;人格精神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2-0021-02
魏晉時期屬于歷史上的亂世,這個時代動蕩不安,社會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在此基礎上社會各界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其中知識分子作為思想界領袖,所受沖擊更加強烈。士族文人生活在魏晉時期經歷東漢末年黨錮之禍,親歷司馬氏集團與曹魏政權的權利之爭,在暫時統一西晉后“八王之亂”爆發,士族文人卷入其中,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在動蕩的社會背景下士族文人慘遭幾次打擊,生活體悟隨之發生改變,知識分子感受到世間險惡、生命無常,開始在困境中思考。士族文人建功立業、積極進取的精神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為個性張揚,從自我角度出發消耗人生,由此形成魏晉風度。正如學者研究所指,魏晉風度表面上風流瀟灑,內里卻悲哀、抑郁、苦痛。基于此,為體會魏晉時期士族文人思想,探析《世說新語》中士人人格精神顯得尤為重要。
一、根據神韻之美分析士人人格精神
魏晉時期士人心靈自由,想往自由恬淡的生活,舉止悠閑灑脫且重外貌,更加重視神韻之美,從表面上看是魏晉時期審美風尚影響士人外貌,實則是當時士人高逸絕俗、寧靜淡泊、淳樸自然人格精神對外在美產生深遠影響,《世說新語》通過特異言行針對士人神情氣韻進行短篇幅描寫,為此士人神韻已然并非一般精神風貌,二是排除倫理道德束縛的風采氣度,在才情及精神品格共同作用下予以展現,是魏晉時期士人人格精神深層次追求的外在表現,賦予審美風尚深遠意義,如清奇、自然、才情、骨氣、超詣、飄逸、礦達、風神等,均是《世說新語》描述士人神韻之美的常見詞語,將士人之“神”視為重要內容,同時與審美意識融合在一起,能體現出士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如“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那可便與人隔”等,說明魏晉時期人們在評價對方時用才情神韻取代倫理道德,引領士人追尋生命本真,再用神韻之美予以體現,用外在表現詮釋士人人格精神[1]。
二、根據賞譽篇分析士人精神世界
在古代士族文人是參與皇權統治工作的“主力軍”,肩負治國平天下重任,然而在社會背景動蕩不安情況下士族文人成為統治者的潛在敵人,不可隨意干預政治,為保住性命在亂世全身而退士人不得不選擇退避三舍,在政治時局中無立錐之地的士人暫且將匡扶天下、救濟百姓壯志抱住腦后,將生活重心放在個人人生追求上。通過對賞譽篇內容進行分析可知,淡泊名利、簡約曠達、清高恬淡、質樸率真是評價魏晉時期士人精神品格的常見詞匯,如“王戎目山巨源……真可謂至真至誠!”“謝動輿曰……通達簡約暢快之意”等描寫均可反映出士人精神世界特點。在魏晉時期士族文人名流將更多精力放在修身養性層面,從虛無縹緲的追尋向人生回歸,使士人不再追求虛名浮利,而是個人精神世界的超然與自我,開始塑造人類自然本性,同時士人嘗試放下負累,在原始的生活狀態中升華靈魂,在恬淡的生活環境中釋放樸實無華的內心情感,繼而助力士人精神品格朝著寧靜淡泊、簡約明快、怡然自得方向發展[2]。
三、根據棲逸篇分析士人生存狀態
各個時代人們的精神品格受政治、經濟、科技等諸多因素影響,為此顯現出一定差異。魏晉時期朝局動蕩,爭權奪利讓士族文人看到人性殘酷,在世道黑暗籠罩下士人渺小無助,既無法一抒胸志,又無法改變現狀,為免于殺戮辭官歸隱成為眾多士人的不二之選,如蘇門隱者等,遠離權利旋渦在山林深處生活。棲逸篇記載“二隱分道”故事,故事內容講到汝南周子南與南陽翟道淵少時相交,在潯陽歸隱山林,庾太尉認為周子南應參與當時的政務,為此周子南走上仕途,翟道淵仍留在青山綠水間,兩好友就此分開,后來周子南探望翟道淵仍不予其交談,說明道不同不與謀,正體現出魏晉時期士人心志堅定、不畏權勢、寧靜淡泊精神品格。與翟道淵相比,嵇康更加堅決,在《世說新語》中寫道:“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作為竹林七賢,嵇康還是曹魏皇室姻親,其妻是曹操曾孫女,無論是受傳統忠君愛國思想影響,還是出于個人情感,嵇康與司馬氏道德觀念、政治思想均格格不入,雖如此仍未削弱嵇康在當時名人士族群體中的影響力,為此其成為司馬氏拉攏對象。公元260年,即甘露五年,司馬昭謀殺魏帝,為抹掉弒君惡名,想要拉攏士族獲得輿論支持。基于此,司馬昭請山濤出面邀請嵇康為官,一面是嵇康好友,另一面是政治理念、精神思想均不契合的當權者,嵇康陷入兩難境地,擺在面前有兩條路,一是在威逼利誘下曲意迎合,違背心志入朝為官,二是遠走他鄉傲世獨立,堅守內心的凈土。然而,拒絕封侯拜相就說明與司馬氏公然為敵,得罪即將掌權的篡位之人,也許嵇康命不久矣。盡管如此權衡利弊嵇康仍對司馬氏的行為深惡痛絕,并未選擇茍延殘喘,拂了好友情面,拒絕山濤舉薦,同時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嵇康用剛正不阿、堅毅勇敢、大義凜然的人格精神守住自己的名節與尊嚴,雖最終死在司馬氏集團手中,但魏晉時期士人的人格精神可見一斑。
士人生逢亂世,歸隱之士甚多,之所以選擇歸隱過淡泊致遠的生活主要是為了避免惹禍上身,為此有些士人精神不堅,在發現亂世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后立即放棄清苦的生活,從山林走到權利兼具的官場,還有部分士人看厭世道奸詐,對當權者理念無法茍同,內心想往理想世界,然而卻無法改變現實生活,空有治國平天下豪情壯志,并無一展拳腳良機,更不甘淪為掌權者玩弄在手的籌碼,悲痛之下選擇歸隱,守住內心的純凈,避免靈魂染色,雖為無奈之舉,但只管問心無愧。多數士人過著不問世事的生活,殘酷的現實世界將他們逼入痛苦深淵,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想要過理想的生活何其之難,士人依舊無法擺脫掌權者左右。士人避世情懷及處世哲學正說明魏晉時期士族文人開始探索生命的真諦及人生的價值,對統治階級的暴行不再一味順從,反映其對自我人格及生命的關懷[3]。
四、根據任誕篇分析士人生命抗爭精神
魏晉時期士族文人落拓不羈,這是一種人格精神,亦可體現出士人對現實的反抗,士人外在狂放失常,內里痛苦堅守與堅決抗爭,在任誕篇記載諸多這樣的故事。例如,阮籍喪母,晉文王在座,向其獻出酒肉,司隸何曾同坐說明公孝治天下,阮籍重喪飲酒吃肉,理應流放到荒漠之地以正風教,文王說嗣宗如此勞累哀傷,你不能和我一樣擔憂,還說什么?再說有病還飲酒吃肉,是合乎喪禮的!阮籍繼續吃喝表情淡定。司馬氏掌權后標榜孝道,對于阮籍來講,這不過是司馬氏維護自身政權的手段而已,是借此打壓異己的幌子,是有背禮教的行為,是對禮教的褻瀆。雖然心知肚明,但不好公然指責,阮籍便用自己的方法戳破掌權者謊言,一副鎮定自若、滿不在乎無知孩童模樣,踐踏司馬氏偽禮教、假孝道治國理念,看似漫不經心,實則反映其對統治階級的不忿之情。在封建社會與統治階級叫板并非明智之舉,稍有閃失就會萬劫不復。渴求名利的人們明知司馬氏意圖,拿阮籍綽綽約約的樣子很沒辦法,只能托詞掩飾、閃爍其詞。阮籍自然不會拿著雞蛋磕石頭,其處事圓通可在危險中全身而退,與嵇康的表現不同卻殊途共歸,擺出反抗姿態的同時亦發人深思。通過對任誕篇內容進行分析可知,魏晉時期士人多災多難,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噩夢,同時磨礪知識分子精神品格[4]。
中國古代士人憂患意識與生俱來,具有關心社會現實、歷史使命感、社會責任感等精神,作為文化界、思想界精英,士人普遍存在豪情、才情、自信,尊嚴成為人格精神不可抹殺及侵犯的一部分。魏晉士人憂國憂民,悲天憫人、博大情懷,心想建功立業、改變現狀、報效祖國、濟世救人,期許在匡扶社稷、救濟蒼生過程中實現人生價值,然而現實世界當頭棒喝,理想在爭名奪利、爾虞我詐的政治爭斗中搖搖欲墜,士人在現實生活中碰壁、徘徊,遭受政權斗爭殘酷打擊。士人在體現價值、實現理想過程中不斷受挫,無法自由施展理想抱負,人生夢想化為泡影,內心彷徨、痛苦、失落、迷惘,為紓解苦悶與抑郁之情士人走上抗爭之路,重新思考自身價值與理想信念[5]。
五、結語
綜上所述,在混亂的魏晉時期士族文人受到打壓,遭受現實生活沖擊,在歸隱及與政權抗爭過程中開始找尋生命價值,重新認識自我,獲得全新認知體驗,士人修心養性的成就超過建功立業的成果,期許用超然之姿、神韻之美能敲響統治階級警鐘,同時士人在放縱任情、自我麻醉中表示不滿,用以反抗強權及現實社會,在悲苦、無奈、心酸中淬煉堅強勇敢、恬淡自然、寧靜志遠的精神品格。
參考文獻:
[1]李妍悅.《世說新語》中的“任誕”精神[J].新鄉學院學報,2019,36(7):30-33.
[2]張慧.論《世說新語·雅量》與魏晉士人崇尚的人格美[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7):104-107.
[3]顧紅艷.從《世說新語》看魏晉風度的精神內蘊與美學內涵[J].美與時代(下旬刊),2017,(5):49-51.
[4]岳瑩.論明清世說體筆記小說中士人道德觀對魏晉的繼承[J].昭通學院學報,2018,40(04):80-84.
[5]陳冉,強中華.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士人的生存狀態[J].湖北科技學院學報,2017,(9):62-63.
作者簡介:
劉彩霞,女,漢族,山西呂梁離石人,呂梁學院離石師范分校,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