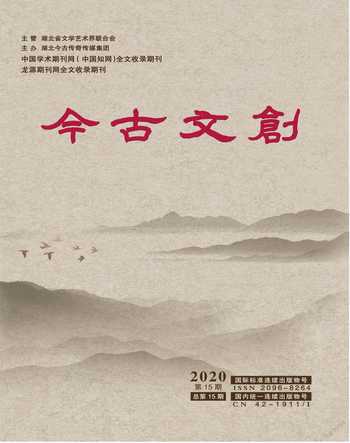用休止換取回響
左怡然
【摘要】 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在其代表作《苔絲》中,對作為全書悲劇基礎的亞雷誘奸苔絲的情節并未展開正面的細致的描寫,而是通過誘奸前大量的環境鋪墊與誘奸后苔絲的境遇的直接拼接來為那個過程留白,卻起到了驚心動魄的效果,給讀者留下了極大的想象空間。
【關鍵詞】 高潮;留白;沉默;意義的召喚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5-0004-02
當讀者懷著緊張的心情,用顫抖的手指翻向下一頁,做好了陪主人公一同面對災難的準備時,卻驚奇地發現:《苔絲》中的高潮成了一段空白,敘事在此處戛然而止。這實在是作者的有意設置。這段誘奸過程實則被安排在第一章節《處女》的末尾,而緊接著第二章節的題目被命名為“失貞”。那么僅憑這點,那些從未耳聞本書且首次閱讀的讀者到這里也大致明白發生了什么。在第一章的末尾,亞雷借著夜色與薄霧的遮掩將苔絲誘致獵苑的密林中,直到苔絲因太過疲倦而入睡。在第二章的開端,苔絲已經不得不離開這個給她造成嚴重心靈創傷的地方,且抱著一種既知道自己“犯下”世俗大忌卻又仍對未來抱有一絲希望的單純又惹人憐愛的心態。但說作者在此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又是完全不準確的。他摒棄正面描寫而用旁觀者抒發哲思的客觀口吻,平和地向讀者評論這一過程的實質和結果。他寫道:“這片美麗的女性織品,就像游絲一樣敏感,又實在像白雪一樣潔白,為什么就像她命中注定要接受的那樣,一定要在上面畫上粗鄙的圖案……”蒼白無力的“子孫償罪”與“宿命論”,不過是作者的一種無奈,且反映了本書的時代主題,即農民階級在社會倫理道德的深重影響與社會演變的洪流的雙重夾擊下被迫改造自身。
哈代省略高潮部分具體情節的做法,可以看作文學創作中的“留白”。留白最主要的效果應當是給讀者想象與思考的空間,但在這里絕不僅僅于此—它引發的想象不過是一個開端,為接下來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親手揭開生活血淋淋的面紗時獲得循序漸進的痛感,并最終陪著苔絲一起徹悟做鋪墊。由最初的旁觀者,到角色的參與者,再到徹悟后從角色中升華以俯視社會,讀者真正經歷了這一完整的過程。倘若作者按部就班地將誘奸的全過程展現出來,盡管讀者可以較早地得到完整的信息,那份本能的恐懼和代入感就會流失,難以使讀者與主人公苔絲的情感認知同步發展,也無法達到心理隨著情節推進產生的階梯式落差。1979年電影版《苔絲》即為一例。由于體裁自身的差異及受眾需求的不同,電影選擇將誘奸過程直接展現。于是一切都變得理所當然起來,觀眾像早已預知一切的一樣做出評論與感嘆,卻難以全身心地投入。這樣對特殊過程的直白處理與原著中的留白處理相對比,極大地降低了作品的深刻性與藝術性。
對留白片段的起點與收束點的設置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地方。所謂“留白片段的起點”其實也就是其上文的結尾。《苔絲》選擇了議論式的哲理的抒發,從風格上來說,哈代通過直接議論的方式,使用平靜如宗教語言的文字來推進情節,一方面是歐洲本土文化特色與敘事傳統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滿足了同時代同地域讀者的心理接受需求,同時有助于作品主旨層次的上升:作為現實主義小說本應起到地對社會現象的充分解讀和評述,以帶給時代一些提示。
讀者在留白的空間中通過想象,與苔絲一同度過了那個罪惡的夜晚。等到與苔絲再次相遇,她已稍稍平復了心情,為亞雷誕下了孩子,在特蘭里奇又過了一段時間后決心要永遠離開這里。顯然,這里省略的不僅是一個時間的跨越,更是主人公心理狀態的跌宕回轉以及精神上的飽受折磨。在對全書的反復及仔細閱讀后會發現,這種類似于電影中蒙太奇效果的大跨度不僅沒有讓讀者不知所措而難以接受,反而起到了兩點作用:一是有助于讀者帶著疑惑和興趣繼續閱讀,并在接下來的重重暗示、渲染、揭發、議論中逐漸深入主題,將浮于表面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二是當情節出現的空白超乎尋常時,本文之前所提及的那段來自作者的帶有宗教憐憫與宿命意味的議論在讀者的心中顯得更加重要,在全書中的地位也才真正凸顯出來。
無論在美術、電影還是文學等多個領域,留白手法的體現都不過是整個作品中一個部分的空白,但絕不是孤立的。它需要前文埋下充足的伏筆,使情節盡管有所空缺也能順理成章,再加上后文不斷地予以補充,使讀者得以真正體悟到“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美感。
由于《苔絲》中苔絲被亞雷誘奸的片段在第一章的末尾,因而前文所占的篇幅不算大。然而就在這短短的一章里,每一個角色都在推動這一事件的發生。首先是那位冒充德伯家族后裔的亞雷·德伯先生。在與苔絲初次相遇時,他在心里已經種下了情欲和不軌的種子:“真是一個叫人饞涎欲滴的小姑娘啊”,苔絲走后他說道。這是作者的一個“殘忍”之處:讓讀者看清亞雷背后的丑惡面孔,為一無所知的單純的苔絲干著急。隨后亞雷像一個幽靈般仿佛能夠隨時隨地出沒在苔絲周圍,偷窺她的一舉一動,并用假借母親名義的一封信以及物質回報迷惑苔絲的家人。這樣,這張“蓄上了仔細修剪過的黑色胡須,胡須的尖端向上翹著,膚色黝黑,兩片后嘴唇紅潤光滑,雙眼滴溜直轉”的臉即便沒有扮演施暴者的角色,也足以成為年輕的女性讀者的噩夢。至于他的奸詐狡猾,亦足以將孩子般純真的苔絲玩弄于股掌之間。最終他選擇制造這場不幸的時間地點都“恰到好處”,如同提前做了巧妙的設計和預算,也是十分合理的。其次,苔絲較于遇見亞雷更為不幸的,莫過于那個頂著祖先的光芒悲慘地來到這個世界上又注定悲慘地瓦解的家庭:極度愛慕虛榮的父親,愚蠢荒唐的母親以及一群年幼無知的弟妹。重拾祖先榮耀的渴望、對金錢和名譽的極度需要幾乎蒙蔽了這個家庭所有成員的雙眼,苔絲成了他們換取理想物質生活的工具。哪怕苔絲投奔“親戚”的心有絲毫動搖,孩子們就“咧嘴大哭”,母親也在一旁幫腔,認為苔絲不去則成了家里的負擔,給苔絲造成不可抗拒的心理壓力。父親為了“慶祝女兒出門”,喝醉了酒而無法前去送行。一切都推動著苔絲“自投羅網”,讓人心生凄涼。再次,苔絲自己也有難以推脫的責任:初次體驗異性大膽直接的愛慕,在應當果斷拒絕或明辨是非之處優柔寡斷。她總是后知后覺,在被亞雷的網死死裹住時才做無力的反抗。“她心里想,被玫瑰花刺了,這不是一個好兆頭—這是那天她注意到的第一個預兆”,然而她依舊無法下定決心摘下被亞雷半推半就戴上的那些花兒。
在中國,留白是藝術作品創作中常用的一種手法,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學的典型載體,原指書畫藝術創作中為使整個作品畫面、章法更為協調精美而有意留下相應的空白,以存想象空間。美術的留白使整幅作品的氣韻更為生動,是藝術家們含而不露的情感抒發,也是筆觸上自然而然的流露。較為經典的要數馬遠的《獨釣寒江圖》:通過大幅度的留白,把江之寒氣和釣之獨韻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音樂中,留白是“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詮釋方式。無論是紅極一時的神曲《忐忑》,還是約翰凱奇的《四分三十三秒》,歌詞或旋律的留白,可以使人們從聽覺到內心深處產生無窮的愉悅快感與審美享受,聽眾與藝術家也真正做到了心靈上的交流。陶淵明有“但識琴中趣,何勞紙上音”,大概就是音樂留白最古老的佐證了。
相對于“留白”這個飽含中國韻味的名詞,許多學者在論及文學作品中類似現象特別是西方文藝作品時,更多地傾向于使用“空白”與“沉默”來表達。西方文論中“空白”觀念的提倡者主要是波蘭“現象學美學”的權威英珈登和德國“接受反映論”的創始人之一伊瑟爾。在英伽登看來:“文學作品描繪的每一個對象、人物、事件等等,都包含著許多不定點,特別是對人和事物的遭遇的描繪”。對于接受理論而言,文學空白需要讀者帶入自己的情感體驗去不斷猜測與增補。這種增補不僅是一種心理上的移情,更是一種身份與價值上的認同。正因為如此,一千個讀者,才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有學者將空白分為“哲理性空白”“修辭性空白”“結構性空白” 。其中的“結構性空白”與其被看作一種意義的傳達,不如說是意義的召喚,作者的“沉默”意味著讀者的解放,文本將解釋權賦予了讀者,鼓勵讀者充分參與并積極創造。這樣,“空白”作為一種欲擒故縱的引誘,帶來的是更加深入的窺探。“這同樣是一個隱秘的沉默在詮釋與過度詮釋中不斷去魅的過程。”
文本中的沉默與空白的還原揭示了文本背后人物的無言、語言的隱喻、詩歌的意境、視角的遮蔽;發現了在結構斷裂、標點停頓、段落劃分中蘊含的深刻意義,擁有穿透語言表象的強大力量。尼采在1883年的遺稿中寫道:“最好的沉默者不是把自己的面孔遮掩住,把水攪渾,以致人們看不清底細。相反,最好的沉默者是明白之人,誠實之人,看得透的人。 他深邃,以至于最透明見底的水也不會使之顯露。在他們那里,沉默不是以沉默的方式顯露的。”哈代將“哲理性暗示”與“大幅度留白”巧妙融合,竭力避開了對最骯臟的場面的正面描寫,卻絲毫沒有淡化事情的嚴重性,反而使讀者從沉默背后的隱喻里感受到內心對文本更高的認同與契合,作者的價值取向、作品的價值基調及創作背后真正的目的,均得到了有力的表達。
參考文獻:
[1]托馬斯·哈代.苔絲[M].王忠祥,聶珍釗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50-97).
[2]張愛玲. “半生緣”.張愛玲全集(第二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12-174).
[3]司同.“文學‘沉默’的本體論意義”[J].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09,(23):6.
[4]金艷.藝術作品中的留白之美[J].文藝評論,2013.1.
[5羅曼·英珈登.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8.
[6]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尼采稿遺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