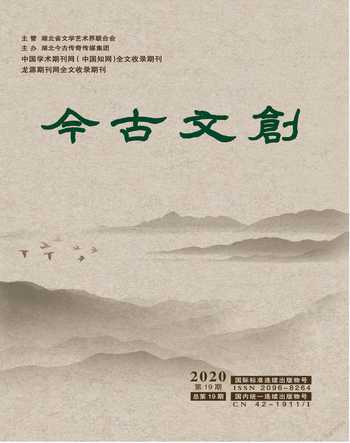弗洛姆異化理論視域下的《變形記》和《砂女》的比較研究
【摘要】 “異化”主題在卡夫卡的《變形記》和安部公房的《砂女》中都有鮮明的體現,作家在作品中表現了人在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中被異化的現實,揭示了現代社會中人的生存困境。但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被“異化”后卻有不同的價值取向,體現了作家個人的人生理念。因此,本文將以弗洛姆的異化理論為基礎,通過對兩部作品中“異化”的比較,感知兩位作家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關注和不同的人生觀。
【關鍵詞】 變形記;砂女;異化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9-0027-02
“異化”,在西方的辭書中是一個多義詞,焦慮、悲觀絕望和寂寞孤獨等都可視作其含義。“馬克思把異化十分近似地明確描述為意義和自我價值的缺乏。他說,異化的工人是‘喪失了一切現實生活內容’的,同時表現為沒有價值、缺乏體面的人們。”而弗洛姆則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他在《健全的社會》中認為:“所謂異化就是一種認識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人把自己看作一個陌生人。”
弗洛姆把剖析人的本質作為自己的理論核心,并由此形成了人道主義異化理論。因此本文將采用弗洛姆的異化理論,從異化的社會環境、異化的人際關系和個體面對異化的不同價值取向三方面入手,對《變形記》和《砂女》中的異化現象進行比較,從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兩部作品對人存在的關注,為人生樹立一個正確的引導方向。
一、異化的社會環境
人不僅生存在社會中而且社會環境又會反過來作用于人,對人的健康發展起著一定的影響。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中認為:“人精神是否健康,這并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取決于所處的社會結構。”在健全的社會結構下,每個人的身心都能得到全面而健康的發展,而在不健全的社會中,人往往會成為社會發展的犧牲品,身心都遭受到巨大的損害。
《變形記》中格雷戈爾的異化,離不開其生存的社會環境對他的損害。他生存在一個金錢至上唯利是圖的社會中,在這種社會環境的主導下人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制于金錢,人往往淪為金錢的奴隸。格雷戈爾的異化表現在他由人變成蟲的荒誕情景中:“一天清晨,格雷戈爾·薩姆沙從一串不安的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一只碩大的蟲子。”“不安的夢”說明格雷戈爾一直生活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中,即使在夢中他的精神也得不到片刻寧靜,而這種不安來自于物欲橫流的社會環境對他的壓迫。為了維持生計償還家庭的債務,他必須努力工作賺錢。他就像一臺發動機,每日不停地工作直至機器損害才能停下來。高強度的工作以及得不到良好的休息早已使他身心俱疲,但是為了賺錢,他只能忍受社會對他的壓榨和損害。他就像甲蟲一樣背負著沉重的壓力,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看似堅硬實際上卻飽受摧殘,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惡劣的社會環境和沉重的工作重壓使格雷戈爾猶如行尸走肉一般,他變得萎靡不振,喪失了生活的激情,在這種狀態下他早已在不知不覺中被異化。卡夫卡通過對生活在社會中的小人物被異化的現實的描寫,來反映人的“存在”處境,揭示了不健全的社會對人的異化和傷害。
《砂女》發行于日本戰后的重建時期,這一時期日本的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問題也在日本社會顯現。在現代物質文明社會的沖擊下,各階層社會矛盾加劇,人們忽視了對精神世界的關注,久而久之個體在都市生活產生了迷惘和孤獨的情緒,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問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砂女》中的男人從都市“逃離”到偏僻落后的鄉村,實際上是對都市世界的反抗,都市的環境給了男人強烈的孤獨感和壓迫感。安部在《砂女》中表現了在資本主義社會高速發展時期,社會環境對人的戕害以及人與社會不斷異化的關系。
二、異化的人際關系
人生存在社會環境中,自然要與社會中的人發生聯系。這種聯系必須是有效的,人能夠從人際關系中得到情感的慰藉。但正如弗洛姆所言:“在我們今天的人際關系中,幾乎找不到多少愛多少恨,這是一種表面的友好,一種更虛偽的花言巧語,背后是疏遠、冷漠和難以覺察的不信任。”所以,當人在人際關系中得不到溫暖時,他的心理就容易受到傷害,人與人的關系就會變得緊張、疏離直至異化。
《變形記》和《砂女》中的主人公都遭受了人際關系的異化,格雷戈爾面對的主要是親情關系的異化,而《砂女》中的男人則是因為在各種人際關系中找不到自我存在自感,產生了孤獨迷惘的情緒以致被異化。
在《變形記》中,格雷戈爾的家庭原本是比較和諧的,因為那時他是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全家人都要依靠他生活。但是當他變成蟲子長時間不能為家里掙錢,并且他的存在成了家庭的負擔后,這個家庭內部的關系開始出現了巨大的分裂,親情在這個家庭中成為冷漠的存在,格雷戈爾遭受了至親之人的排斥和冷漠。母親由于害怕他的樣子而疏遠他,父親則用蘋果對他進行攻擊,并使他受了重傷。妹妹也漸漸地對他產生了厭煩心理,主張要把哥哥送走。家庭本是避風港,親情原本是最親密的情感,但格雷戈爾卻得不到親人的理解和關愛。卡夫卡通過格雷戈爾變形的遭遇,以及家人對他的冷漠態度,描寫了在金錢沖擊的社會下,人與人的關系只能靠金錢來維系,最親密的感情也抵不過人們對金錢的追求,揭示了現實社會中人與人關系異化的現狀。
《砂女》中的男人雖有體面的工作,健全的家庭,與同事們相處也沒有太大的矛盾,但在他的精神世界,他依然是一個孤獨的存在。因為夫妻關系早已到了熱情退卻的倦怠期,而生活中又沒有真心實意相處的朋友。可見無論是在夫妻關系還是人際交往中,他都找不到自我的存在價值,在與人相處中他感受不到自己是被需要的一員。他獨自來到偏遠的村莊收集昆蟲的目的就是要享受“發現”的樂趣。“只要你有所發現,那你自己的名字也就能和昆蟲長長的拉丁學名放在一起,用花體羅馬字寫進昆蟲大圖鑒里去呢。而且,恐怕還能半永久地保存下來。”有了這種新發現,自己的名字就會長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人的存在就不會因為生命的終結而結束,于是男人希望借此在社會上找到自我存在的永恒價值。安部通過《砂女》反映出現代人在生存中的困境,揭露了在現代社會人際關系的異化下,人們找不到自我價值的孤獨感和喪失了自我的失落感。
三、個體面對異化的不同價值取向
在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的雙重異化下,《變形記》和《砂女》中的主人公都面臨著嚴峻的生存處境。但是二人面對異化后荒誕的人生卻有不同的價值取向,格雷戈爾在家人對他異化后態度的巨大轉變中逐漸絕望而后走向死亡,而《砂女》中的“男人”一直為了能夠逃出砂洞而不斷反抗,最終通過發現儲水裝備重新找到了生存的意義,獲得了新的希望。
在《變形記》中,當格雷戈爾發現自己變成甲蟲后,他沒有放棄對生活的希望并努力接受自己變成蟲子的事實。但家人的冷漠與憎惡卻打破了他的幻想與一線希望。他的內心無比悲涼,想到自己的存在令所有人痛苦,他認為自己應該消失,不要再成為家人的累贅和負擔。他被至親的家人所拋棄,在社會中成了一個孤獨的存在。內心的孤寂與對未來生活的厭倦,使他對這個世界深感絕望,最終在徹底絕望中走向了死亡。在《砂女》中,當男人被困于沙洞無法離開時,逃出沙洞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標,他用盡了各種辦法想要逃離這里。一次次失敗后男人并沒有放棄,反而立志要做第一個逃出去的人。“一天,男人在屋后的空地上,架好一致捉烏鴉的陷阱,把它叫作‘希望’。”
可見,即使身陷于極端的生存環境中,且每回都以失敗告終,但他仍對逃離沙洞充滿希望。在經歷了絕望和失敗后,男人不僅并未意志消沉,反而研制出了儲水設備。通過儲水設備的發明,男人重新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后來,當男人終于有了逃跑機會時,他卻暫時放棄了回歸到正常生活的機會,選擇留在砂穴生活來追尋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種態度的轉變在于既在于想要通過儲水設備得到村民的認可,又在于男人愿意向全新的未來發起挑戰,而這一點比回到都市繼續做一個孤獨的人更有吸引力。安部對男人態度轉變的書寫,是他面對人的異化問題后所提出的一種解決之道,即積極接受并正視“異化”,從而以此實現對自我的超越。
四、結語
本文以弗洛姆的異化理論為研究視域,通過對《變形記》《砂女》中異化的社會環境、異化的人際關系和個體面對異化的不同價值取向的比較分析發現,在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的異化下,格雷戈爾與“男人”在現實生活中面臨著嚴峻的生存環境。但是《變形記》和《砂女》中的個體在面對異化后呈現出了不同的價值取向,格雷戈爾在異化后由希望走向了絕望和死亡,而“男人”則在對絕望的反抗和斗爭中找尋到了新的希望。這種不同與作者本人的個人經歷和自我選擇有關,格雷戈爾的絕望其是卡夫卡內心深處的悲劇意識的反映,這種悲劇意識的形成和積淀,既源于其不幸的家庭成長經歷又源于其對自己猶太身份的不安,在“反猶主義”運動下,卡夫卡既看不到未來的出路,又無力反抗不公正的命運,對現代主義的悲觀失望,使他絕望于人的存在處境。相反安部公房不僅有相對健全的成長環境而且敢于與現實相抗爭,作為日本戰后存在主義的大家,安部深受存在主義的影響,而存在主義的觀點之一就是自由選擇。因此面對絕望的處境,安部的選擇是正視絕望并努力超越絕望。這種超越在當下的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即給處在困境中的人提供了一種選擇,選擇直面苦難,用希望來抵抗絕望,在困境中不斷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從而以樂觀的心態面對人生中的每一個困境。
參考文獻:
[1]陸梅林,程代熙編選.異化問題(下)[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
[2]安部公房.砂女[M].楊炳辰,張義素等譯.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
[3](美)卡夫卡.卡夫卡小說全集[M].韓瑞祥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4](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會[M].歐陽謙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3.
作者簡介:
李宇晴,女,遼寧大連人,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