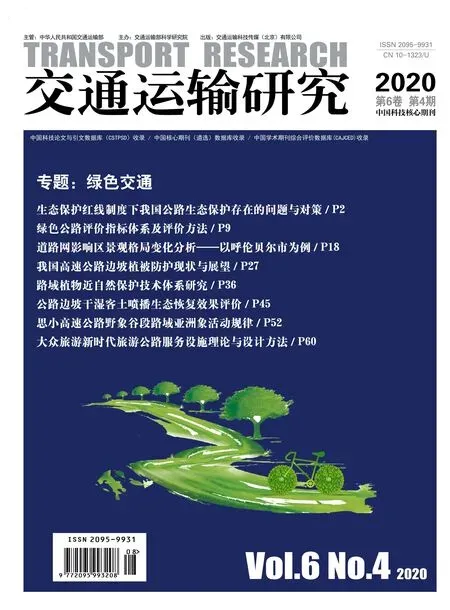道路網(wǎng)影響區(qū)景觀格局變化分析
——以呼倫貝爾市為例
楊艷剛,崔慧姍,柳雁玲,王 云,關(guān) 磊,黃山倩
(1.交通運輸部科學(xué)研究院,北京 100029;2.吉林省高等級公路建設(shè)局,吉林 長春 130024)
0 引言
道路是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的重要組成部分[1]。道路網(wǎng)的形成加劇了土地利用的強度,對周邊生態(tài)系統(tǒng)產(chǎn)生了累積性、復(fù)雜性、不可逆的影響[2-3],是導(dǎo)致野生動物死亡、棲息地質(zhì)量下降、種群割裂、生境和景觀破碎化及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驅(qū)動因素[4-7]。
國內(nèi)外學(xué)者就道路網(wǎng)對景觀生態(tài)系統(tǒng)影響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8-9]。20 世紀(jì)90 年代以來,隨著3S 技術(shù)的發(fā)展,有關(guān)道路網(wǎng)的研究逐步深入,研究領(lǐng)域也拓展到路網(wǎng)對生態(tài)系統(tǒng)過程及功能的影響[2],以及路網(wǎng)變化過程中景觀格局變化[10]、路網(wǎng)影響區(qū)土地利用變化[11]等方面。國外研究主要關(guān)注道路網(wǎng)生態(tài)累積影響、景觀破碎化影響等方面[12],如Forman 研究了道路網(wǎng)對景觀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累積影響效用[13];Saunders 探討了道路建設(shè)對景觀結(jié)構(gòu)及土地利用的影響[14];Forman 提出了不同等級道路影響域[15]。整體上,基本明確了路網(wǎng)對景觀生態(tài)的影響,但還缺乏有關(guān)道路網(wǎng)景觀影響程度及時空尺度的研究。
國內(nèi)對路網(wǎng)景觀生態(tài)影響的研究多集中于不同等級道路網(wǎng)的尺度效應(yīng)[16]、道路網(wǎng)與生態(tài)系統(tǒng)破碎化的關(guān)系等方面[17],且道路網(wǎng)景觀生態(tài)效應(yīng)研究多在省域尺度[18]、市域尺度[19-22]上開展。這些研究基本明確了道路網(wǎng)對景觀生態(tài)影響的性質(zhì),但關(guān)注路網(wǎng)對景觀格局影響的時間尺度和空間范圍的較少,沒有在景觀尺度上明確不同道路網(wǎng)規(guī)模對周邊景觀的影響及道路網(wǎng)對路側(cè)景觀的影響范圍,導(dǎo)致在開展路網(wǎng)生態(tài)影響評價時,影響范圍確定困難,難以提出針對性保護措施。
景觀格局指數(shù)高度濃縮景觀格局信息,是反映其結(jié)構(gòu)組成和空間配置某些方面特征的定量指標(biāo)[23-24],用于量化表達(dá)不同路網(wǎng)布局形式下景觀格局的變化及特征,是識別路網(wǎng)作用景觀機制、分析其生態(tài)效應(yīng)的重要前提。本文將應(yīng)用景觀格局分析法,分析呼倫貝爾市1988—2015 年間4 個時期道路網(wǎng)及其影響區(qū)內(nèi)景觀格局的變化,研究道路網(wǎng)形成和加密過程中,鄰近道路網(wǎng)區(qū)域內(nèi)景觀格局的時空變化,進(jìn)而確定不同規(guī)模路網(wǎng)對景觀格局影響的空間范圍,以期為在區(qū)域尺度上確定路網(wǎng)適度規(guī)模、合理規(guī)劃路網(wǎng)布局提供科學(xué)依據(jù)。
1 研究區(qū)域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qū)域概況
呼倫貝爾市地處東經(jīng)115°31′~126°04′、北緯47°05′~53°20′之間,總面積25.28 萬km2;氣候類型屬于溫帶大陸性季風(fēng)氣候,地區(qū)年均溫度為-3~0℃,年均降水量250~380 mm,年蒸發(fā)量1300~1900mm[25];地形總體呈西高東低并緩慢過渡形態(tài)。從大興安嶺西麓到呼倫貝爾草原的西端植被與土壤類型發(fā)生明顯的區(qū)域分異。區(qū)域東部為山地,分布著粗骨性土壤,植被類型以森林及山地草原為主,向西延伸逐步過渡到森林草原、草甸、草甸草原,土壤類型為黑鈣土。再向西延伸,氣候逐漸干旱,土壤類型以栗鈣土為主[26]。
截至2016 年底,呼倫貝爾已形成了以2 條國家高速(G10 綏滿高速公路和G5511 集阿高速公路)、3條國道(國道111,301和332)和5條省道(省道201,202,203,301,302)為主骨架,以縣鄉(xiāng)、邊防、專用公路為脈絡(luò)的公路網(wǎng)[27]。
1.2 數(shù)據(jù)獲取與處理
研究區(qū)行政邊界數(shù)據(jù)來源于中國科學(xué)院資源環(huán)境科學(xué)數(shù)據(jù)中心(http://www.igadc.cn)。根據(jù)研究目的,結(jié)合研究區(qū)內(nèi)的實際土地利用與分布情況,按照《土地利用現(xiàn)狀分類》(GB/T 21010—2017) 二級分類標(biāo)準(zhǔn),將該區(qū)土地利用類型劃分為林地、草地、耕地、建設(shè)用地、水域及其他用地,共6 個一級分類20 個二級分類。選取1988年、2000 年、2012 年和2015 年空間分辨率為30m×30m 的Landsat TM 數(shù)據(jù)為數(shù)據(jù)源,成像時間在8~9 月間,云覆蓋率均低于0.1%。研究所用各期道路矢量數(shù)據(jù)分別來自對應(yīng)年份發(fā)布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交通圖,其中2015年度道路矢量數(shù)據(jù)來自1∶25萬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公路電子地圖。
利用遙感圖像處理軟件ERDAS 2010,對遙感影像進(jìn)行幾何校正、輻射定標(biāo)、大氣校正、多波段圖像合成和裁剪等預(yù)處理;建立解譯標(biāo)志,利用野外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和Google Earth 近期影像數(shù)據(jù)選取訓(xùn)練樣本和驗證樣本;采用常用的最大似然監(jiān)督分類法對4 期影像數(shù)據(jù)分別進(jìn)行分類處理,并對分類結(jié)果進(jìn)行后處理,確保分類結(jié)果的總精度達(dá)到80%以上。
1.3 景觀指數(shù)篩選
景觀指數(shù)能定量表示景觀格局信息[28],主要可分為景觀斑塊水平、景觀類型水平和景觀水平3 個層次,且各層次內(nèi)部景觀指數(shù)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guān)性[29]。景觀指數(shù)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冗余性,在運用景觀格局指標(biāo)時,應(yīng)根據(jù)研究需要與指標(biāo)的實際意義,結(jié)合生態(tài)學(xué)過程慎重選擇[30]。本文針對道路建設(shè)、道路網(wǎng)形成過程中對生態(tài)因子影響及景觀格局的作用方式,重點研究不同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水平上景觀格局的變化,為此篩選了斑塊密度(Patch Density,PD)、平均斑塊面積(Average Patch Area,AREA-MN)、景觀形狀指數(shù)(Landscape Shape Index,LSI)、邊緣密度(Edge Density,ED)、蔓延度指數(shù)(CONTAG)及多樣性指數(shù)(Shannon's Diversity Index,SHDI)共6 個景觀指數(shù),用于反映景觀組成、結(jié)構(gòu)及分布特征。各指數(shù)生態(tài)學(xué)意義如表1所示。

表1 景觀格局指數(shù)及其生態(tài)學(xué)意義
1.4 道路網(wǎng)提取與緩沖區(qū)生成
首先,收集1988 年、2000 年、2012 年和2015 年呼倫貝爾市交通圖并進(jìn)行數(shù)字化,生成路網(wǎng)矢量數(shù)據(jù)并統(tǒng)一進(jìn)行投影轉(zhuǎn)換。然后,利用ArcGIS 10.3 軟件包中的緩沖區(qū)分析(Buffer)功能生成緩沖區(qū)。由于距離公路越近的區(qū)域,受公路建設(shè)的影響越大,根據(jù)《環(huán)境影響評價技術(shù)導(dǎo)則 生態(tài)影響》(HJ 19—2011)[31],公路建設(shè)生態(tài)影響范圍一般為兩側(cè)500m 以內(nèi),而公路對景觀的影響一般略大于此范圍,因此本文分別提取道路兩側(cè)0~100m,100~200m,200~300m,300~500m,500~1000m 共5 個緩沖區(qū)。接著,將上述緩沖區(qū)與景觀類型解譯數(shù)據(jù)進(jìn)行疊加,運用Frag?stats 4.2 分別計算不同緩沖區(qū)內(nèi)的景觀指數(shù)。最后,對各景觀指數(shù)進(jìn)行兩個層面的對比:①對比不同年份路側(cè)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格局指數(shù)變化,分析路網(wǎng)密度由疏至密變化過程中,路側(cè)景觀指數(shù)的變化;②對比路網(wǎng)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指數(shù)的變化,分析路網(wǎng)對路側(cè)景觀格局影響的距離。
2 路網(wǎng)影響區(qū)內(nèi)景觀組成及格局變化分析
2.1 區(qū)域路網(wǎng)變化特征分析
呼倫貝爾市1988 年、2000 年、2012 年、2015 年道路網(wǎng)長度變化情況如圖1 所示。對比各階段路網(wǎng)里程可看出,在1988—2015 年近30 年間,區(qū)內(nèi)路網(wǎng)長度逐步增加,由1988 年的2 662km 增加到2015 年的4 138km,增長55.44%;路網(wǎng)密度也由0.011km/km2增大到0.016km/km2。

圖1 不同時期呼倫貝爾市路網(wǎng)規(guī)模柱狀圖
2.2 路網(wǎng)影響區(qū)景觀類型組成及變化分析
研究區(qū)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類型均以草地景觀為主,在1988 年、2000 年和2012 年,0~100m,100~200m,200~300m 緩沖區(qū)內(nèi)農(nóng)田景觀比例高于森林景觀,隨著緩沖區(qū)距離的增大,森林景觀面積比例增加,占比超過農(nóng)田景觀(見表2)。總體來看,在1988 年和2000 年,路網(wǎng)兩側(cè)各緩沖區(qū)距離內(nèi)景觀比例主要以草地景觀和農(nóng)田景觀為主,道路網(wǎng)主要分布于地勢相對平坦的草原和農(nóng)田地帶。隨著道路網(wǎng)的延伸,至2015年道路進(jìn)入研究區(qū)北部林地,兩側(cè)森林景觀和其他類型景觀(沙地、濕地等)逐漸增多,草地景觀、農(nóng)田景觀占比下降。

表2 研究區(qū)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類型比例
2.3 不同路網(wǎng)密度下道路網(wǎng)兩側(cè)景觀格局變化分析
比較不同年份路側(cè)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指數(shù)的變化情況,發(fā)現(xiàn)1988—2015年間,隨著路網(wǎng)密度逐年增加,斑塊密度(PD)均呈現(xiàn)先下降后增加的趨勢,2000 年路側(cè)斑塊密度較1988 年下降,其后逐漸上升;路側(cè)各緩沖區(qū)距離內(nèi)平均斑塊面積均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即隨著道路網(wǎng)密度的增加,路側(cè)景觀中平均斑塊面積下降,在0~100m、100~200m 緩沖區(qū)內(nèi),平均斑塊面積在1988—2000年間出現(xiàn)小幅增加。
邊緣密度(ED)反映景觀中異質(zhì)斑塊間物質(zhì)、能量、物種及其他信息交換的潛力及相互影響強度[32]。遭受擾動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在恢復(fù)過程中,異質(zhì)斑塊增加,邊緣密度增加,景觀異質(zhì)性進(jìn)一步提高。隨著恢復(fù)進(jìn)程的推進(jìn),初始的小斑塊進(jìn)一步擴展、合并,邊緣密度下降,并逐步趨近于周邊未受干擾的景觀異質(zhì)性格局。在1988—2015年間,隨著路網(wǎng)密度的增加,0~100m 緩沖區(qū)內(nèi)邊緣密度增加,大于100m 緩沖區(qū)內(nèi)各時期邊緣密度差異不大。
景觀形狀指數(shù)(LSI)綜合反映景觀斑塊的異質(zhì)程度。在耕地、林地、人工斑塊類型占比高或草地、濕地、水體等自然形成的斑塊面積占比小的景觀中,空間結(jié)構(gòu)復(fù)雜,景觀形狀指數(shù)(LSI)較高。在1988—2015 年路網(wǎng)加密過程中,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形狀指數(shù)均隨著路網(wǎng)的加密而出現(xiàn)明顯增加。
蔓延度指數(shù)(CONTAG)用于描述景觀里不同斑塊類型的團聚程度或延展趨勢。一般來說,高蔓延度指數(shù)表明景觀中的某種優(yōu)勢斑塊類型形成了良好的連接性[33],反之則表明景觀具有多種要素的密集格局。在1988 年、2000 年、2012 年、2015 年4 個階段內(nèi),道路網(wǎng)兩側(cè)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蔓延度指數(shù)均呈“先略上升,而后逐漸下降”的趨勢。
景觀多樣性指數(shù)(SHDI)反映景觀組分?jǐn)?shù)量和比例的變化情況。由多個組分構(gòu)成的景觀中,當(dāng)各組分比例相等時,多樣性指數(shù)最高。就本文研究結(jié)果來看,在1988—2015年間,隨著路網(wǎng)的加密,路側(cè)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多樣性指數(shù)增加。
2.4 道路網(wǎng)不同距離內(nèi)景觀格局變化分析
對比路側(cè)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的斑塊密度(PD),發(fā)現(xiàn)0~100m 緩沖區(qū)內(nèi),由于道路這一相對連續(xù)完整的斑塊的存在,斑塊密度很低;在100~200m 和200~300m 緩沖區(qū)內(nèi),路側(cè)景觀斑塊密度明顯增加;在300~1000m 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斑塊密度逐漸下降。
隨著與道路距離的增大,緩沖區(qū)內(nèi)平均斑塊面積(AREA-MN)先減小后增加,0~100m 緩沖區(qū)內(nèi)平均斑塊面積較大是由相對完整單一的道路斑塊嵌入造成;在100~300m 緩沖區(qū)內(nèi),平均斑塊面積出現(xiàn)了較明顯的下降;在300~500m 緩沖區(qū)內(nèi),平均斑塊面積有所增加;在500~1000m緩沖區(qū)內(nèi),平均斑塊面積出現(xiàn)了明顯增加。
在0~100m 緩沖區(qū)內(nèi)道路與其周邊景觀斑塊間存在明顯且較為平整的邊緣,邊緣密度(ED)較高;隨著與道路距離的增加,在100~200m 和200~300m緩沖區(qū)內(nèi)邊緣密度出現(xiàn)下降;在300~1000m緩沖區(qū)內(nèi),邊緣密度增加。
在0~100m 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形狀指數(shù)(LSI)較低;在200~300m 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形狀指數(shù)增大,可能因為該距離內(nèi)受道路建設(shè)及路網(wǎng)形成影響,異質(zhì)性增加,因而導(dǎo)致形狀指數(shù)增大。在大于300m 的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形狀指數(shù)呈下降趨勢,說明路側(cè)景觀結(jié)構(gòu)由復(fù)雜變得相對簡單,即由破碎化的景觀格局逐漸向具有相對完整平滑邊緣的近自然斑塊類型變化,反映出該緩沖內(nèi),道路建設(shè)對景觀格局影響較小。
在100~200m,200~300m 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蔓延度指數(shù)(CONTAG)增大,即距離道路越遠(yuǎn),景觀優(yōu)勢斑塊的連接性越好;在500~1000m 緩沖區(qū)內(nèi),蔓延度指數(shù)卻呈下降趨勢。
在1988年、2000年、2012年3個階段,景觀多樣性指數(shù)(SHDI)均隨著與道路距離的增大而逐漸增大,即距離道路越遠(yuǎn)的地方,景觀越多樣。在2015年,多樣性指數(shù)則隨著與道路距離的增大而降低,但總體來看同距離緩沖區(qū)之間多樣性指數(shù)值差異不大。
以上各指標(biāo)在不同年份的大小和變化情況如圖2所示。
3 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及不同路網(wǎng)密度下景觀格局變化分析
3.1 不同路網(wǎng)密度下景觀格局變化分析
本文應(yīng)用ArcGIS 空間分析工具和景觀指數(shù)分析工具,分析了呼倫貝爾市1988—2015 年近30年間路網(wǎng)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的景觀格局變化,發(fā)現(xiàn)景觀斑塊的演變趨勢受路網(wǎng)密度增加的顯著影響。隨著路網(wǎng)密度的增加(1988—2015 年),區(qū)域景觀整體呈現(xiàn)一定程度的破碎化,具體表現(xiàn)為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斑塊密度均增大,平均斑塊面積減小,陳輝對青藏鐵路不同距離緩沖區(qū)生態(tài)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影響研究也發(fā)現(xiàn)了這一規(guī)律[34]。究其原因可能是,這一時期研究區(qū)內(nèi)增加的多條貫通道路對區(qū)域景觀產(chǎn)生了顯著影響,如省道203、國道232 等,同時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持續(xù)發(fā)展,研究區(qū)內(nèi)路網(wǎng)持續(xù)加密,道路沿線人類活動強度增加,這都會造成區(qū)內(nèi)斑塊密度的增加。
隨著路網(wǎng)密度的增加,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形狀指數(shù)、景觀多樣性指數(shù)增大,表明區(qū)域內(nèi)景觀類型增加,景觀結(jié)構(gòu)變得復(fù)雜,異質(zhì)性增加,破碎化程度加深。景觀多樣性指數(shù)增大的可能原因是道路網(wǎng)延伸至原本沒有道路的景觀類型中,新建道路路側(cè)景觀類型增加(見表2),因此造成了景觀多樣性指數(shù)增大。蔓延度指數(shù)呈先上升而后逐漸下降的趨勢,究其原因是這一時期內(nèi)路網(wǎng)加密并未引起路側(cè)景觀中不同斑塊類型間團聚程度發(fā)生變化,或路網(wǎng)對區(qū)域景觀格局影響程度并未增加,因此景觀斑塊間的連接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fù),而在2000—2015年間,路網(wǎng)持續(xù)加密造成研究區(qū)內(nèi)連續(xù)分布的景觀持續(xù)被切割,蔓延度指數(shù)下降。
景觀格局變化的驅(qū)動因子主要有人為因子和自然因子,驅(qū)動力主要有城鎮(zhèn)化作用機制、水資源約束機制、技術(shù)進(jìn)步機制及人口增長促進(jìn)等[35]。就研究區(qū)而言,在近30年內(nèi),區(qū)內(nèi)路網(wǎng)逐漸加密,即便新增加的道路主要為省道、縣鄉(xiāng)道等低等級道路,其仍然造成生態(tài)系統(tǒng)破碎化,這與李雙成有關(guān)道路網(wǎng)與生態(tài)系統(tǒng)破碎化關(guān)系的研究結(jié)果相似[17],即路網(wǎng)增加造成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破碎化。
3.2 路網(wǎng)不同距離內(nèi)景觀格局變化分析
各景觀指數(shù)在100~300m 緩沖區(qū)內(nèi)均發(fā)生顯著變化。
(1)在100~200m,200~300m 緩沖區(qū)內(nèi),斑塊密度明顯增大、平均斑塊面積顯著減小,區(qū)域景觀破碎化程度加大;在300~1000m 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斑塊密度逐漸下降,平均斑塊面積增大,破碎化程度有所降低。
(2)在100~200m,200~300m 緩沖區(qū)內(nèi)邊緣密度、形狀指數(shù)增加,表明在這一距離內(nèi)斑塊形狀變得簡單,景觀異質(zhì)性降低;在300~1000m緩沖區(qū)內(nèi)邊緣密度增加、形狀指數(shù)下降,表明斑塊間邊緣鑲嵌形式變得復(fù)雜,景觀異質(zhì)性增加,斑塊類型及鑲嵌格局更趨近于自然景觀類型。
由此可推測,路網(wǎng)對周邊景觀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影響距離范圍可能在道路兩側(cè)300m 范圍以內(nèi),這與王云等得出的“道路對景觀格局的影響距離為單側(cè)200m”[36]結(jié)果相似。
4 結(jié)語
本文以呼倫貝爾市為例,通過分析其1988—2015 年間4 個時期道路網(wǎng)及其影響區(qū)內(nèi)景觀格局的變化,探討了道路網(wǎng)形成和加密過程中,不同距離緩沖區(qū)內(nèi)景觀格局的時空變化。研究發(fā)現(xiàn),隨著路網(wǎng)加密,路側(cè)空間結(jié)構(gòu)變得復(fù)雜,斑塊密度增大,平均斑塊面積減小,破碎化程度加深,原有相對單一的景觀類型由于路網(wǎng)形成而變得多樣。
受遙感數(shù)據(jù)回訪周期、空間分辨率、云遮擋等的局限,在多期遙感數(shù)據(jù)中獲取時間完全一致且無云條件下的影像難度很大,另外該研究涉及數(shù)據(jù)量大、分類分級復(fù)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分析精度[37]。由于道路影響域是一個不等寬且不連續(xù)的區(qū)域,且寬度受分析尺度影響,為進(jìn)一步明確道路影響域及影響機理,還應(yīng)采用不同時空分辨率的多源遙感數(shù)據(jù)進(jìn)行綜合分析判斷,同時考慮不同分析尺度間的轉(zhuǎn)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