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肢骨科手術(shù)中采用舒芬太尼和羅哌卡因腰硬聯(lián)合麻醉的效果
吳 忠 湖南省岳陽(yáng)市二人民醫(yī)院麻醉科 414000
腰硬聯(lián)合麻醉是目前臨床用于下肢骨手術(shù)的主要麻醉方式,主要通過(guò)羅哌卡進(jìn)行麻醉,具有鎮(zhèn)痛效果好、循環(huán)系統(tǒng)穩(wěn)定等優(yōu)點(diǎn)[1]。但臨床發(fā)現(xiàn)僅用羅哌卡因進(jìn)行蛛網(wǎng)膜下腔阻滯麻醉需要較大的劑量,會(huì)帶來(lái)一定的不良反應(yīng),如惡心嘔吐、皮膚瘙癢、低血壓等。羅哌卡因和阿片類藥物聯(lián)合使用不僅能提高麻醉效果,且安全性好[2-3]。近期,我院使用舒芬太尼和羅哌卡因用于下肢骨麻醉,效果較好,現(xiàn)報(bào)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18年7月—2019年7月間收治的行下肢骨手術(shù)的患者80例為觀察對(duì)象,使用隨機(jī)數(shù)字法隨機(jī)分組:對(duì)照組40例,其中男23例,女17例,年齡20~60歲,平均年齡(43.8±3.9)歲;體質(zhì)量指數(shù)(BMI)20~28,美國(guó)麻醉醫(yī)師協(xié)會(huì)(ASA)分級(jí) I~I(xiàn)I 級(jí)。觀察組40例,其中男21例,女19例,年齡20~60歲,平均年齡(42.9±3.8)歲,BMI20~28,美國(guó)麻醉醫(yī)師協(xié)會(huì)(ASA)分級(jí) I~I(xiàn)I 級(jí)。組間基本資料比較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
1.2 納入標(biāo)準(zhǔn) 本研究所有患者均自愿參與,且簽署知情同意書,符合以下條件:(1)所有患者均為臨床確診且需要進(jìn)行下肢骨手術(shù)治療的患者;(2)排除有其他系統(tǒng)嚴(yán)重器質(zhì)性或功能性病變的患者;(3)嚴(yán)格術(shù)前檢查,排除手術(shù)禁忌證;(4)排除認(rèn)知功能障礙患者;(5)排除在2年內(nèi)接受過(guò)下肢骨手術(shù)及術(shù)前1d內(nèi)使用過(guò)鎮(zhèn)痛藥物的患者。
1.3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術(shù)前均進(jìn)行圍手術(shù)期護(hù)理,完善各項(xiàng)術(shù)前檢查,護(hù)理人員對(duì)患者進(jìn)行健康宣教和心理輔導(dǎo)。患者入室后開(kāi)放靜脈通路,30min內(nèi)輸注乳酸林格液6ml/kg,連接心電監(jiān)護(hù),監(jiān)測(cè)患者各項(xiàng)生理指標(biāo),面罩吸氧3L/min。本研究80例患者由我院麻醉科同一組麻醉醫(yī)生實(shí)施腰硬聯(lián)合麻醉。患者取左側(cè)臥胸膝位,術(shù)前常規(guī)消毒鋪巾,選擇L2~3間隙作為穿刺點(diǎn),正中入路椎管穿刺,穿刺針達(dá)到硬膜外腔后置入腰麻針,若有腦脊液流出則可注入局麻藥物,注射速率為0.1ml/s。對(duì)照組用7.5mg 0.5%的羅哌卡因(耐樂(lè)品)作為局麻藥對(duì)患者使用,觀察組使用6mg 0.5%的羅哌卡因聯(lián)合舒芬太尼5μg。在硬膜外間隙向頭端置管3~4cm,固定后患者平臥。嚴(yán)格監(jiān)測(cè)患者情況,若有心動(dòng)過(guò)緩、低血壓等癥狀出現(xiàn)立即使用麻黃堿或去氧腎上腺素處理以及阿托品等藥物進(jìn)行處理,保證患者生命體征穩(wěn)定。
1.4 觀察指標(biāo) 觀察比較兩組患者不同時(shí)刻的平均動(dòng)脈壓(MAP)和心率(HR)情況,分別記錄為麻醉前、麻醉后5min、麻醉后20min和麻醉后1h。使用視覺(jué)模擬評(píng)分(VAS)比較患者術(shù)后鎮(zhèn)痛情況,選擇麻醉后3h、9h和24h三個(gè)時(shí)間點(diǎn)進(jìn)行。觀察比較兩組患者麻醉相關(guān)指標(biāo),采用針刺法測(cè)試,包括最高感覺(jué)阻滯平面以及到達(dá)該平面的時(shí)間、痛覺(jué)退至T12的時(shí)間以及痛覺(jué)阻滯持續(xù)時(shí)間(腰麻藥注射完畢至切口開(kāi)始疼痛的時(shí)間)。患者下肢骨運(yùn)動(dòng)阻力采用改良Bromage評(píng)分進(jìn)行評(píng)估,記錄運(yùn)動(dòng)恢復(fù)時(shí)間(從蛛網(wǎng)膜下腔注藥結(jié)束至下肢運(yùn)動(dòng)完全恢復(fù)的時(shí)間)和評(píng)分,0~3級(jí)分別為無(wú)運(yùn)動(dòng)阻滯、無(wú)法直腿抬起、無(wú)法屈膝、無(wú)法屈踝。最后比較兩組不良時(shí)間發(fā)生情況。

2 結(jié)果
2.1 不同時(shí)刻兩組患者M(jìn)AP和HR比較 所有患者手術(shù)均順利實(shí)施。觀察組患者M(jìn)AP和HR在麻醉后5min至麻醉后1h時(shí)刻均較對(duì)照組高(P<0.05),這表明觀察組患者整個(gè)麻醉前至麻醉后1h過(guò)程中MAP和HR較對(duì)照組更平穩(wěn),見(jiàn)表1。

表1 不同時(shí)刻兩組患者M(jìn)AP和HR比較
注:與對(duì)照組比較,*P<0.05。1mmHg=0.133kPa。
2.2 兩組患者術(shù)后鎮(zhèn)痛情況 觀察組患者麻醉后9h和麻醉后24h時(shí)VAS評(píng)分顯著低于對(duì)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jiàn)表2。

表2 兩組患者VAS評(píng)分比較分)
2.3 兩組患者麻醉相關(guān)指標(biāo)比較 觀察組患者的最高阻滯平面高于對(duì)照組,且到達(dá)最高阻滯平面用時(shí)更短,痛覺(jué)退至T12時(shí)間更慢,痛覺(jué)阻滯持續(xù)時(shí)間更長(zhǎng),且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兩組的運(yùn)動(dòng)阻滯情況(包括時(shí)間和評(píng)分)無(wú)差異(P>0.05),見(jiàn)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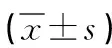
表3 兩組患者麻醉相關(guān)指標(biāo)比較
2.4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yīng)比較 不同麻醉方案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比較無(wú)差異(P>0.05),見(jiàn)表4。

表4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yīng)比較
3 討論
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各種原因?qū)е碌南轮遣∽兓騽?chuàng)傷越來(lái)越多,臨床下肢骨手術(shù)的技術(shù)也得到飛速發(fā)展。麻醉是整個(gè)手術(shù)的關(guān)鍵步驟,臨床多采用腰硬聯(lián)合麻醉,該麻醉方法鎮(zhèn)痛效果好,具有易操作且對(duì)患者循環(huán)系統(tǒng)影響小的優(yōu)點(diǎn)[4]。麻醉藥物的選擇是麻醉成功的關(guān)鍵,需要麻醉醫(yī)師根據(jù)患者情況做出合適藥品和劑量的選擇。
羅哌卡因是純左旋體長(zhǎng)效酰胺類局麻藥,可逆的阻滯沖動(dòng)傳導(dǎo),有麻醉和鎮(zhèn)痛雙重效應(yīng),具有感覺(jué)、運(yùn)動(dòng)組織分離的特點(diǎn),且不會(huì)對(duì)心血管和中樞系統(tǒng)造成較嚴(yán)重的影響[5]。使用大劑量羅哌卡因的情況下可產(chǎn)生外科麻醉效果,而小劑量的羅哌卡因則有良好的鎮(zhèn)痛效果,且有局部的運(yùn)動(dòng)神經(jīng)阻滯效果[6]。舒芬太尼是阿片類局部麻醉藥物,在不增加交感神經(jīng)阻滯的情況下可以明顯增加對(duì)感覺(jué)神經(jīng)的阻滯。舒芬太尼為脂溶性藥物,可以通過(guò)和脊髓表面的μ受體結(jié)合而產(chǎn)生麻醉鎮(zhèn)痛效果[7-8]。舒芬太尼易通過(guò)血腦屏障,其血漿蛋白結(jié)合率高、分布容積小,因而鎮(zhèn)痛強(qiáng)效且持續(xù)時(shí)間長(zhǎng)。當(dāng)羅哌卡因和舒芬太尼聯(lián)合使用效果更好,在椎管內(nèi)注入舒芬太尼,能縮短羅哌卡因的感覺(jué)和運(yùn)動(dòng)神經(jīng)阻滯的起效時(shí)間[9-10]。
從本研究結(jié)果來(lái)看,從麻醉后5min到麻醉后1h,使用羅哌卡因聯(lián)合舒芬太尼的患者M(jìn)AP和HR都高于單用羅哌卡因患者,而兩組患者M(jìn)AP和HR從麻醉前至麻醉后1h過(guò)程是下降趨勢(shì),這說(shuō)明兩藥聯(lián)合使用對(duì)患者血流動(dòng)力學(xué)影響更小,麻醉過(guò)程更平穩(wěn),筆者認(rèn)為這是由于兩藥聯(lián)合使用舒芬太尼的使用降低了羅哌卡因的劑量,起到了穩(wěn)定血流動(dòng)力學(xué)的效果,而舒芬太尼與羅哌卡因聯(lián)合應(yīng)用還可通過(guò)調(diào)整心排出量,使血流動(dòng)力學(xué)更趨于平穩(wěn)。
本研究中觀察組患者的最高阻滯平面高于對(duì)照組,且到達(dá)最高阻滯平面用時(shí)更短,痛覺(jué)退至T12時(shí)間更慢,痛覺(jué)阻滯持續(xù)時(shí)間更長(zhǎng),這表明兩藥聯(lián)合使用有更好的麻醉阻滯效果,起效更快,吸收更平穩(wěn)。而兩藥聯(lián)合使用患者術(shù)后9h和24h疼痛較輕,這提示舒芬太尼聯(lián)合羅哌卡因能夠延長(zhǎng)鎮(zhèn)痛效果,筆者認(rèn)為這可能和舒芬太尼的高脂溶性有關(guān),較高的脂溶性使得藥物能夠穿過(guò)血—腦屏障,更易達(dá)到有效濃度并保持;同時(shí)脂溶性也是得其更易被人體吸收,對(duì)循環(huán)系統(tǒng)影響小,避免循環(huán)負(fù)荷,抑制交感神經(jīng)和大腦中樞興奮,從而降低應(yīng)激反應(yīng)。綜上所述,舒芬太尼復(fù)合羅哌卡因使用在下肢骨科手術(shù)腰硬聯(lián)合麻醉中效果較好,值得臨床推廣。
- 醫(yī)學(xué)理論與實(shí)踐的其它文章
- 多點(diǎn)反饋管理在醫(yī)院感染管理中的應(yīng)用
- 基于自主學(xué)習(xí)的課程評(píng)價(jià)體系在組織學(xué)與胚胎學(xué)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
- 綜合康復(fù)護(hù)理措施對(duì)骨結(jié)核患者生活質(zhì)量及預(yù)后的影響
- 健康信念模式護(hù)理對(duì)老年糖尿病足的預(yù)防作用
- 九步口腔操聯(lián)合間歇經(jīng)口置管在腦卒中中度吞咽障礙患者的應(yīng)用及護(hù)理
- 2018—2019年長(zhǎng)葛市疑似預(yù)防接種異常反應(yīng)監(jiān)測(cè)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