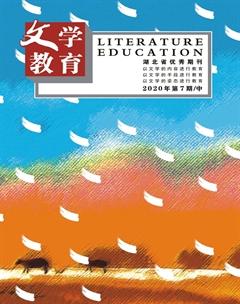以《嬰寧》為例談《聊齋志異》的藝術特色
內容摘要:作為寄寓蒲松齡“孤憤”之意的“才子之書”,《聊齋志異》呈現出異于同時代其他小說的鮮明的藝術特色。收錄于《聊齋志異》卷二的《嬰寧》篇,是蒲松齡描寫女性的典范之作,為“他者”的小說人物皆含有作者“本我”的精神氣質,也是一篇表達作者隱喻、精微之意的小說。筆者將以《嬰寧》為例,從藝術手法、敘事話語方面,看蒲松齡如何描繪人物、組織情節、抒發本我“孤憤”之情,以此來分析《聊齋志異》的藝術特色。
關鍵詞:《聊齋志異》 《嬰寧》 蒲松齡 藝術特色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先生指出:“《聊齋志異》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意在說明《聊齋志異》以“傳奇”為敘述方法,“志怪”為小說性質。
《嬰寧》以象征、以小見大等藝術手法將婦女自由的新觀念和新思想、社會批判思想寄予在小說故事之中,蒲松齡以嬰寧為自己理想化的人格,將個人情感注入嬰寧身上,發嬰寧被封建社會所同化的憤懣之聲,從嬰寧中可以看出他的影子,《嬰寧》整個故事也是蒲松齡所在時代的縮影。
一.通過語言、行動塑造人物
《嬰寧》中通過語言刻畫人物,主要以嬰寧和鬼母體現得最為明顯。蒲松齡著力刻畫一個貌美愛花又純真得近乎癡憨的嬰寧,嬰寧一登場,他就以十分傳神的筆法,勾勒出她不同凡俗的形象:她“容華絕代”,手拈梅花,姍姍行走在上元節的郊野。當她發現王子服死死盯住自己的目光后,“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開篇起勢,蒲松齡就以簡潔的筆觸,將嬰寧愛花、愛笑、貌美和純真的特點鳥瞰式勾畫地寫出。
后文中,蒲松齡對嬰寧愛笑的性格,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嬰寧人未到而笑聲先聞,在相見過程中,她時而“嗤嗤笑不已”,時而“笑不可遏”,受到母親斥責后“忍笑而立”,但轉瞬“復笑不可仰視”。這一系列關于笑的描寫,聲態并作,簡潔又鮮明的刻畫出了嬰寧愛笑的性格特征。
蒲松齡將嬰寧嬌憨近癡的天真,也通過她的語言表現的生動自然。當王子服拿出上元節嬰寧遺落的梅花示以相愛之意時,嬰寧說:“待郎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捆負送之”。當王生告訴她:“非愛花,愛拈花之人耳”,嬰寧依然全然不解其中的繾綣之情,說:“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當她得知王子服所說的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愛時,俯思良久仍然了無所悟,說:‘我不慣與生人睡。”甚至還告訴母親“大哥欲我共寢”。幾句對話,就將嬰寧如癡似憨、天真爛漫的性格特點表現得栩栩如生。
鬼母的精明和智慧也體現在語言和行動中,甚至很多時候體現在她的耳聾和不言中。在王生初見鬼母時,“媼聾聵不聞”就寫了鬼母時而耳聾,為后面鬼母再次耳聾作了鋪墊。后來鬼母久等嬰寧與王生吃飯不至,追問他們在院子里談什么耽誤這么久,嬰寧說:“‘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這里鬼母的耳聾明顯是故作未聞,以此避免了王生的尷尬。鬼母的聰慧則在她的聞與未聞、說與不說之間了。
蒲松齡把鬼母作為母親的善良、無私,對嬰寧的寵愛,通過鬼母的幾句簡短話語體現出來。如王生來到嬰寧家里時,鬼母介紹嬰寧說“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我言少教誨,此可見矣。年已十六,呆癡如嬰兒”。看起來是貶嬰寧,實際上,這句話體現了鬼母把嬰寧當做自己的女兒一樣,如千千萬萬個母親,對嬰寧既有著管束,在外人面前又忍不住引薦和謙遜的嗔怪。之后,嬰寧和王生見面,大笑不止,鬼母“媼瞶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語言中有對嬰寧的溺愛和對嬰寧人前失禮的嗔怪。并且,作為母親,鬼母至始至終都沒有向嬰寧提出過要求。即使死后和嬰寧見面,也再三叮囑嬰寧“勿驚郎君耳”,言語之間可見鬼母的無私以及其對嬰寧深沉的母愛。
二.《嬰寧》的敘事話語藝術
1.語言“詩化”的特征
《嬰寧》呈現出明顯的蒲松齡個人視角,在客觀敘事過程中滲透進作者的主觀感懷。蒲松齡長于借前人詩歌意象充當小說引子或“造端”生事,創造出悲歡離合的敘事意趣。如《嬰寧》中所寫嬰寧居住的南山風光以及她若不經意的笑,其意趣脫化自蘇軾的詞《蝶戀花》:“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將前人詩意轉換為小說敘事意趣,或借前人詩意生發妙趣橫生的故事,使《嬰寧》敘事寫人余韻繚繞,飽含詩情畫意。
《嬰寧》故事還在蒲松齡的詩中出現類似的意境,蒲松齡在其詩《贈妓》中寫道“為尋芳跡到蓬萊,怪道佳人錦作胎。柳線叢中聞笑語,杏花深處見門開。”“尋芳”“佳人”“笑語”“杏花”等文辭閃爍其間,這與《嬰寧》所敘王子服獨訪嬰寧、門外聽笑聲那段文字非常逼近。除《嬰寧》之外,蒲松齡面對某個階段的某種人生感受,經常會分一題兩做,別將其寫成詩詞與小說,至于孰先孰后,有時就難于辨識。蒲松齡喜于一題多做,小說敘事內容上多有與詩歌意象、詞句、思想互滲的情況,所以這使《嬰寧》以及《聊齋志異》,語言上有著揮之不去的詩韻。
在《嬰寧》中,多用借景抒情、移情于景的手法,從而創造出詩畫一體的優美意境:蒲松齡多次描寫嬰寧家中的環境,將想要表現的嬰寧、鬼母的性格特點寓在環境描寫中,用環境來展現人物的性格。如嬰寧和鬼母的家“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墻內桃杏尤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院內“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啟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鬼母能于“空翠爽肌”的“亂山合沓”之中,營造一個恬靜、優美、充滿詩意的居所,充分說明了鬼母勤勞能干、聰慧大氣的人物性格;而嬰寧自小生活在意境修雅、詩情畫意的環境中,又有鬼母的寵溺和教育,如何不具有天真善良、率性樸質的性格呢?
2.敘事中抒發“孤憤”之情
《嬰寧》一文中,可以看見作者的主觀傾向和主觀理想,蒲松齡的自我抒情常常化身為小說中的嬰寧或附體到嬰寧身上,完成了小說中由作者抒情到敘事的轉換——將“抒我情”翻轉為“敘他事”。嬰寧的憨態可掬,象征著蒲松齡本人企慕自由的心境與性情,是小說文本外部的作者與文本內在人物在精神上的融合。與《嬰寧》類似,《聊齋志異》中蒲松齡通過多篇塑造美好狐魅形象的狐妖小說,來展示他的美好愿望和理想,以此對當時的黑暗社會做出批判。
蒲松齡在《嬰寧》中塑造了兩個世界,通過兩個世界的對比,道出蒲松齡的人生幻滅之感。一個事是“莒之羅店”的現實世界“此界”,一個是“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綠柳,墻內桃杏尤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的幻境“他界”,“他界”是具有烏托邦性質的詩意世界,結納了自然的光亮、男女的柔情、人際往來的溫馨,洋溢著濃厚的樂園氣,蒲松齡凸顯嬰寧生活世界和王生生活世界的反差,反映了現實世界的世俗。到后來王生“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通過消解“他界”,反襯此生易逝的哀感,也揭示出現實的“此界”一如“他界”,終乃“幻夢之空花耳”,為文本結尾處的感喟與嬰寧性格轉變作鋪墊。
眾所周知,《聊齋志異》是一部“孤憤之書”,蒲松齡在書中主要借人物以寄寓“孤憤”之情,《嬰寧》中嬰寧被寄予了蒲松齡飽經世事挫磨而謹慎處世和超然于世俗的態度。嬰寧由一個混沌未開、率性憨態的少女,被封建社會同化為態度莊肅、無笑無戚的少婦,從愛笑轉變為不笑,嫁人前后兩個時期的嬰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蒲松齡刻意制造嬰寧性格的反差,將嬰寧融入了現實世界“正常”婦女的形象中,仿佛是終于回歸正常的喜劇,但顯然她沒有真的正常,嬰寧最終是被世俗社會吞噬了童真的笑容,其實是更高層次的悲劇。這個悲劇不單屬于嬰寧,還屬于封建社會中廣大受壓迫的婦女,由此《嬰寧》一篇中可以看出蒲松齡對封建禮教窒息女子天性的憤懣之情,看出蒲松齡向往超然于世俗的理想。
狐妖是蒲松齡筆下最常出現的主要形象之一,她們被蒲松齡賦予了人的思想感情和音容笑貌,具有超凡的美貌、善良而純情的品質,象征著作者理想化了的人格和良知。蒲松齡與他小說文本人物不斷交融化合,他筆下的狐妖們,很多都是他精神或本體的象征。蒲松齡在狐妖的悲劇里,抒發著自己的“孤憤”之情,與前代文人“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艷情”創作同理。
三.總結
《嬰寧》一篇可以看作《聊齋志異》狐妖篇中的代表性作品,其中寄托了蒲松齡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同時也抒發了他的遺憾和憤慨。除表達的“本我”思想之外,《嬰寧》還成功的塑造出了性格特點鮮明的人物:通過語言、行動、環境的描寫塑造出嬰寧憨直天真的個性;通過其他的輔助人物來側面烘托出嬰寧的獨特;通過轉換型的情節突出嬰寧嫁人前后的性格變化,增強嬰寧被封建社會所同化的悲劇感和無奈感。可以看出蒲松齡運用象征、對比、烘托等多種藝術手法,將人物塑造得豐滿生動,將故事敘述得有情感有節制,多處懸念推動情節發展、伏筆為結局作鋪墊,足以見蒲松齡的寫作技巧高超和其超越時代性的創新。
蒲松齡愛寫狐妖,狐妖在《聊齋志異》中約占六分之一的篇幅,他多通過與嬰靈類似的狐妖,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蒲松齡借用傳奇的敘述特長,他筆下的狐妖,不強調其“靈異性”,而是著重賦予她們人性化的特點,其品性往往髙于常人,使小說內容精彩充實,情節離奇而生動,展現出極其迷幻曲折的色彩,借此來寄托蒲作者的“本我”之情。從《嬰寧》中可以看出,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多通過寫狐妖來反映社會現實,給予了狐妖深層次的社會現實意義,通過狐妖的經歷和悲劇,來抒發自身的“孤憤”情感。
參考文獻
1.李桂奎.詩稗互滲與《聊齋志異》意趣創造[J].文學評論,2019.3
2.熊江梅.《聊齋志異》的詩性敘事[J].中國文學研究,2019.2
3.蘭蓓蓓.《嬰寧》人物性格分析[J].蒲松齡研究,2017.4
4.李暉.《聊齋志異》中的“人鬼戀”研究[D].西北大學,2016
(作者介紹:肖博瑤,湖北大學中文國家基地班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