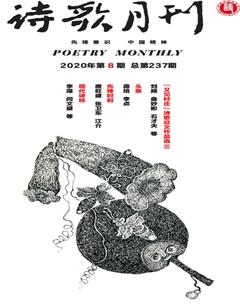作為教師的詩人
【美】理查德·艾伯哈特 劉康凱/譯
五年前,我坐在波士頓的一家商務辦公室里,接到一個電話。有時人們說人受到一次召喚(雙關語,同時有接到一個電話之義——譯者注)。生活選擇他們走上一條路。這個電話問我是否愿意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做駐校詩人。
當時我有一種觀念,認為詩歌是不能教的,它的神秘本質是逃避解釋、拒絕分析的。我認為詩歌不能由詩人來教。我不懷疑這門課可以由教授來教。我不是在達特茅斯、劍橋、哈佛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什么嗎?
然后我把這認作是一個挑戰(zhàn)。為什么要把自己的思想封閉在既有的觀念上?為什么不在教詩的過程中體驗生活呢?事實上,為什么不應該是詩人最適合教詩呢?帶著一種油然而生的冒險意識,我們穿越整個國土來到西雅圖。
在談到詩人作為教師或教師作為詩人的一些問題之前,應該說一下,我前面提到的那個電話,在隨后的四年里,又令人驚奇地跟來了另外四個,這是有記錄的。概括地說,有兩所大型州立大學:華盛頓大學和康涅狄格大學,它們的問題特別而生動。接著是被惠頓學院(馬薩諸塞州諾頓市),一個有百年歷史的女子學院,召去擔任一個新的訪問教授職位。然后是實行導修制的普林斯頓大學,在那里除了教詩之外,我還做了一系列的克里斯汀·高斯講座。現(xiàn)在是達特茅斯學院,這是一次出道三十年后的還鄉(xiāng)。“歲月是什么?”是瑪麗安·摩爾一本書的書名,人活的越久,這個問題就變得越尖銳。
實際上,我大約15歲時就受到了詩歌的第一次召喚。
詩歌正在被重新發(fā)現(xiàn)。歷史又回到它古老的魔力。詩人可以教詩的想法開始付諸行動。在作為一門知識學科、一種情感方式、一種對生命神秘意義的直覺的詩歌,與所謂的真實世界的真實事件之間,人們感到需要融合。這一行動已讓我們的大學和學院安置了一打或更多詩人作為駐校詩人、教授或講師,造成了一個有趣的美國現(xiàn)象。
類似地,現(xiàn)在這種需求融合的感覺促使企業(yè)和基金會將資金投入到了學院和大學,在加州、賓州,以及今年夏天在達特茅斯,讓企業(yè)高管們在40多歲時從人文學科中學習到他們在20歲時可能學不到的東西。或者學會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舉例來說,如果不能將商業(yè)理解為國族文化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它就是貧困。三十年前,商業(yè)和文化是兩極分化的。現(xiàn)在我們看到,雙方互相依賴,并且他們負有共同的責任。如果我們的大學和學院能夠回饋贊美之情,把大學教師送進商業(yè)辦公室和工廠,擴大他們的視野,那將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最近我偶然發(fā)現(xiàn)一本舊筆記本,里面有達特茅斯早期或達特茅斯之后的詩歌。有一頁出現(xiàn)這樣一句話,很可能是我1926年畢業(yè)后不久寫的:“生活應該是在思想和運動中消耗能量,而不是在人身上。”我一發(fā)現(xiàn)它時,就已記下了它。首先,一句批評的話。“和運動”中有一處含混,暗示著某種社會行為,但我顯然有意將其嚴格地與“思想”并置,并意味著智力生活本身。
我可以在引用這句話時向我那時的達特茅斯致敬嗎?我從我的教授那里得到了對智性事物的最高尊重。在求知欲達到頂峰時,幾乎是一種無限的審美愉悅。但請注意這句話。它孤零零地站立在小筆記本上,仿佛我曾試圖表達大學教育的精髓。重要的是,在災難之前,在衰退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美國人是安全的。沒有人愿意把精力花在人民身上。到現(xiàn)在為止,我們有了更深刻和更真實的民主意識。也許一個去年班上的畢業(yè)生會把那句話寫得幾乎相反。如果你把一個新的電動洗衣機放在你的房子里,它不會動(我可以證明這一點),除非一個工人正確地連接和調試它。如果清潔工和垃圾工不來,一個月后會發(fā)生什么?社會是一個綜合的事件連續(xù)體,這些最后提到的社會成員和大學教授或銀行行長一樣重要。我至少花了20年才學到這一點。
詩歌也適于這一圖景。
但在我回憶往事的時候,讓我重提一下榮退的霍普金斯校長的一句話,在我那個時代,這句話成了一句名副其實的口號,那就是“一個有頭腦的貴族”。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擺在我們面前,作為年輕人,我們要用智識去征服世界。這是一句很吸引人的話,它用模糊但強大的雄心激發(fā)我們。現(xiàn)在看來,它與某些國家口號一樣恰當?shù)貙儆谧约旱臅r代,就如“新政”和“公平交易”屬于它們的時代一樣。歷史進程的運動是復雜而神秘的。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人類并不是單靠腦力生活,這一觀察使我回到詩歌上來。
詩歌位于生活的中心,如果我早有才智,我本該使用一個術語,這個術語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一直被各種批評學派應用。我應該采用“一個感性的貴族”。這樣才能承負起整個人性,它與世界全面的、潛在地豐富的融合。它將解釋各種各樣的經(jīng)驗,并包含矛盾和作為思想行為模式的說教這兩者的邊界。
現(xiàn)在,在我自己的領域里,一個真實而麻煩的問題存在著。詩是貴族的還是民主的?
我希望能處理好這個問題,并帶著對另一個主要問題,即對詩歌與科學關系的接受進一步思考它。
詩歌是貴族的還是民主的?
就此我想問的是,是詩人,就是說偉大的詩人,或一群主導性詩人,主宰了這個時代,把文化提升到詩人的水平(這可以說就是本世紀上半葉的艾略特,或是任何一個你可以命名的領導群體,如果你同意這個主張的話);還是說,詩歌本是民主的,因此最終由所有讀者通過時間來評判,故此實際上是一種人民意志的表達,一種民主的設定?
讓我再詳細說明一下。我想知道這個困擾我多年的問題的答案。保持詩歌水準的主要是在大學里培養(yǎng)出來的詩人和讀者嗎?人們能做出這么大的有效概括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意味著詩歌是貴族的東西,因為社會大眾中的才智之士很少有人受過足夠的訓練,去寫出或理解最好的詩歌。
我現(xiàn)在想站在辯論的立場上。這不是一個總體信仰的問題。智識越高,詩就越偉大,就變得越深奧。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死于1889年,享年44歲,生前只發(fā)表過三首詩。在1918年他的朋友羅伯特·布里奇斯出版了他的作品之后,人們認識到了他的價值,隨后的二十多年,關于他的書籍層出不窮。現(xiàn)在,關于霍普金斯的書籍和文章的泛濫已經(jīng)平息。他向這個世紀親密說話,但夠不到最后一個世紀的耳朵。
我非常喜歡他的詩,還有布萊克的詩。然而,我仍認識到,即使在現(xiàn)在,盡管霍普金斯在教科書和批評性的評價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可能只有數(shù)千讀者在閱讀他。這樣在我看來,他還是一位貴族詩人。他吸引訓練有素的讀者和復雜的性格。這是他身上的一個局限,還是一個如此民主以至于不在乎他說什么的社會的局限?
再舉一個例子。卡爾·桑德堡在20年代有很好的天賦。他似乎直接為可能是大多數(shù)美國人說話,并置身于我們民主文化的核心。桑德堡代表了與艾略特對立的一極。在大學里,他沒有被有信心地閱讀,也沒有被有學問的人評論,因為他太簡單,不能激發(fā)想象力,而且他的語言也很平淡。相反我們崇拜的是已故的華萊士·史蒂文斯,他碰巧是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險公司的副總裁。現(xiàn)在,如果你承認桑德堡是真正民主的,并且在美國我們有民主文化,那么你就不用把桑德堡和他的同類,大眾藝術的實踐者,提升到一個他們目前達不到的層次嗎?
恰恰相反。史蒂文斯那無定形的、閃爍的、燦爛的、難解和微妙的想象使許多人著迷。微妙而難解的詩人們在今天贏得了勝利,但正如我們所知,趣味是一只蹺蹺板,改變是不可避免的。
我不排除提出的問題,但不接受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限制。相反,我為之聲辯的是一個我們在這個國家里所擁有的充滿活力的詩人的萬神殿,一種趣味的普遍性,它通過鑒別力擁抱廣泛的互不相同的思想和風格。
另一個關注點是作為一種藝術范例的詩歌和科學的關系。它們看似截然不同。似乎科學造就了我們這個世界,并且控制了它。科學讓事情發(fā)生。相反地,用奧登的話說,詩歌似乎“無所事事”,它結束于沉思,可能常常是一個美麗、淡漠的沉思,似乎遜于科學。
藝術,或者還是讓我們保留“詩”這個詞,表達一個時代的本質。一個人不太了解十九世紀的情況,他通過書本,去了解在巴拉克拉瓦戰(zhàn)役中有多少士兵排成行彼此對壘。一個人可能通過閱讀濟慈、布萊克、丁尼生、惠特曼、愛默生來感受這個世界。我們從邏輯學角度理解不了內戰(zhàn),但通過例如斯蒂芬·克蘭的《紅色英勇勛章》,可以揭示它的主要特征。這是一個男人寫的故事,他讀過有關戰(zhàn)爭的書,但沒有參加戰(zhàn)斗。他的想象力在藝術上保留了那場戰(zhàn)爭的意義。
在藝術和科學的關系上沒有次等或高等的問題。這些名詞無需采用。歸根結底,它們代表著同樣的智識的運用,即想象力。
在卡爾·邁克爾森編輯的一本新書《基督教與存在主義者》中,我在第61頁讀到,愛因斯坦“向我們保證,科學只能處理物質的功能和相互作用,但永遠無法了解或深入物質的本質” 。他還在某處說,在發(fā)明一種新的宇宙理論時,大腦“跳過了一條溝”。在某個很棒的時刻,他的大腦跳過一條溝,從當時已知的東西跳向某種新的東西。他以一種新的方式看待事物,提出了他的相對論和場論。現(xiàn)在似乎很容易把時間想象成第四維度。我們的祖父輩沒有一個能這樣想。這本質上是一種詩的想象。
艾略特先生在寫作后來出版于1922年的《荒原》時,實際上把十九世紀拋在了腦后。他發(fā)明了一種新的詩歌,他以一種新的方式看待事物。
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話,在他們的巔峰時期,科學的和詩意的想象也被等同于智力—感受力的運用。它們是同一棵樹的樹枝,它們有我們共同人性的普遍根源。
科學基于理性,它僅限于測量。詩歌往往基于直覺,直覺有著深厚的、古老的資源,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為它取決于一個人的偏好,即是否感覺到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世界觀,以及這種世界觀是否吸引了自己。許多聰明人從出生到死亡完全與藝術無緣。
我只提出了兩個詩歌教師能解決的問題。如果一個大學生能夠在他想象力的范圍內,運用年輕人頭腦中所有的靈敏性來學習,并且能夠用一系列學術觀點令人滿意地回答這些問題,那么他不僅可以盡情享受,而且還可以走向教育的一端,那就是自我認知。
上面的公式我不太滿意。人們希望避開詭辯,但仍請允許我采取一種懺悔的姿態(tài)。奧登最近在某處說了些話,大意是他在科學家面前感到自卑。在這些世界的統(tǒng)治者面前,他感到格格不入。這是一種聰明的態(tài)度,但這句話里有一種古怪的、狡猾的味道,好像他不是這個意思。如果科學僅僅是通過理性,對二十世紀負責的話,而這個世紀的一半就有兩場戰(zhàn)爭,一次大蕭條,以及準備向他們和我們所有人彈回的鈷彈,那么科學家應該感到最原始的愧疚。毫無疑問,他們中的一些人是這樣做的,但他們在自己的感情面前是無助的。
在科學家面前,作為一個詩人,我本能地感到優(yōu)越。我已經(jīng)在引用愛因斯坦時宣告了他們的局限性。我在前面公平地說過,科學和藝術之間沒有爭論,想象力在兩者中起著同等的作用;然而,我不得不說,大多數(shù)詩人都褒揚人類(有時甚至是在譴責、諷刺或嘲笑人類時——人們可能會想到波德萊爾、斯威夫特),長久流傳的詩歌必然具有道德的價值,贊同人類的善,它在意識深處的狀態(tài)使它與宗教直覺相結合,它為心靈和頭腦說話的能力賦予它塑造真理的無限潛力。
失去這一視野的人又重新開始看到它了。人不能單單靠管理收益為生,靠對物質的實際控制為生,靠對實利主義的驕傲自夸為生。他必須靠內心的強迫,靠深層的自然動力,靠敏感的直覺,靠精神的現(xiàn)實,靠對無法言喻的事物的關心,靠虔誠,靠祈禱,靠謙卑,靠所有那些使靈魂在斗爭中充滿活力并穿透幻覺面紗的生生不息的力量生活。這一現(xiàn)實的大部分都可能被嵌入了潛意識。正是從這些區(qū)域里,藝術誕生了,在這里我只談到一種藝術——詩歌。
對詩歌的研習,從莎士比亞的時代到迪倫·托馬斯的時代都是嚴肅而光榮的事,我看不出它會傷害人,我能看到它的道德力量豐富人的生活質量。因此,我認為學習和教授它是正當?shù)摹R粋€人必須寫詩那就寫吧。
我想把這些概括結束于一個關于批評的札記上。直接的印象,未經(jīng)圖式化的、個人的直覺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類型,可能比大多數(shù)或任何類型都好。
比如說,研究者傾向于反抗葉芝在《幻象》中來之不易的圖式化,盡管這種圖式很迷人,但由于武斷和緊張而無法令人滿意。很少有人真正喜歡它。許多人可以佩服它的圓錐形的精雕細琢,但它不知何故沒有接受所有的生命,當它在假裝這樣做的時候。他們給予它欽佩,以及理解,但不給予它愛,對此它也并不要求。羅伯特·弗羅斯特的宏富天才是我所高度贊許的,他所做的相對較少、有點不守規(guī)矩,但完全符合人性的和令人信服的離題話,偶然的看法,和尖銳的評論,可能代表了最好的詩歌批評,這種批評不是針對一個流派,也不古怪,而是幾十年來(保守地說)被輕易拋棄的真理的智慧閃光。
例如,去年春天在普林斯頓,弗羅斯特突然說:“所有的科學都是馴化科學。”這跳過了一條溝。我們很喜歡它。這說明了上述論點之一。他以顯著的機智和深邃的智慧,即對真理的崇高熱愛,將那些冷冰冰的科學人、原子鈷夢想家、地球撼動者,與街上的男人、廚房里的女人聯(lián)系起來,表明科學家畢竟只是盡其所能馴化宇宙。這是一種機智、簡練、最人道、最可愛的表達,聽了這話,滿屋的人咯咯笑,隨后又哄堂大笑起來。
我們用做來逃避“是”。科學家是實干家。商人是實干家。我真正關心的是“是”。詩歌關心“是”。它建構“是”的狀態(tài)。這是一種對“是”的方式的探索。我們都在努力去“是”。科學通過做使我們害怕“是”。詩歌,以及其他藝術,鼓勵我們“是”。讓我們不要被做的重負所累,以致忽視了“甚至路旁的荊棘叢也因神的榮耀而燃燒”。
本文初刊于1956年11月份的《達特茅斯校友雜志》, 后收入作者的詩歌隨筆集《談詩歌與詩人》(伊利諾斯大學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