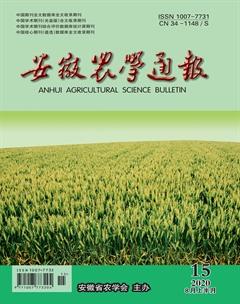珠海市“三生”空間格局演變及其驅動因素研究
陳楚 陳士銀 馬智宇



摘 要:“三生”空間的協調發展是當前國土空間規劃中探討的熱點話題之一。通過構建“生產-生活-生態”的空間分類體系,以粵港澳大灣區的節點城市珠海為研究對象,采用地理空間信息分析、土地利用動態轉移、“三生”空間重心遷移等方法,對珠海市1980—2015年35年間“三生”空間的時空格局及其驅動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1)從面積變化上來看,生活空間面積變化較為顯著;生產空間持續減少,大量的轉出面積流入了生態空間;生態空間面積變化情況最小。(2)從重心遷移的角度上來看,“三生”空間重心相對集中,均分布在斗門區和香洲區,僅生產空間在2015年重心逐步向東南方向遷移。(3)“三生”空間的格局演變與頂層政策和區域的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密切相關。
關鍵詞:“三生”空間;重心遷移;格局演變;驅動因素
中圖分類號 F301.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7-7731(2020)15-0102-07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tial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discussed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building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Production –Living–Ecological”, choosing Zhuhai city, an important note cit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r, as the research area, using the geographical spatial information analysis, the transfer of land use dynamic, migration of “Production –Living –Ecological”, to analyse its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ea change, the living space area changes significantly; The production space continues to decrease, and a large amount of off-site area flows into the ecological space. The ecological space area changes the least.(2)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er of gravity migration,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Production –Living –Ecological” space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all of which are distributed in Doumen District and Xiangzhou District. Only in 2015,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production space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southeast direction.(3)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Living –Ecological” is closely related to top-level polici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growth.
Key words: “Production –Living –Ecological” Spatial; Migration; Pattern evolution; Driving factor
近些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城鎮化、工業化的加速推進,引發人地關系緊張、生態環境惡化、空間結構失衡等問題,我國國土空間規劃出現布局重復混亂、結構配比不均、集約利用程度低等負面現象[1,2]。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過于注重土地的生活功能和生產功能,對土地生產、生活的利用開發度大,而疏忽了對生態功能的保護[3],導致生產生活用地不斷擴張,生態用地遭到擠占,加劇了不同土地利用類型間的沖突與爭奪,最終造成國土空間規劃紊亂。識別與劃分“三生”空間是優化國土空間的基礎[4],實現“三生”空間的高效利用,既能穩步推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又能協調土地資源的合理分配,是當前我國關注的熱點話題,也是世界各國發展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
“三生”空間體現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對土地利用與開發的影響,基于對“三生”空間的時空格局及其演變規律分析,為土地利用規劃和可持續發展規劃提供參考依據。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人口激增,人地關系日趨緊張,優化“三生”空間格局有利于保護自然生態系統,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人居環境。
19世紀末期,國外學者首先提出了“帶形城市”“田園城市”“有機疏散”等經典規劃理論[5-9],但這些理論大部分是應用于城市規劃中。2013年以來,我國規劃師們逐步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是新時期國土空間規劃的核心思想,“三生”空間、“三生功能”等概念相繼出現在一些政府報告與政策文件當中。“三生”識別與分類成為當今學術界探討的熱門話題。我國學者主要從不同尺度對“三生”空間的分類、識別方法、空間演變及驅動因素進行了分析與討論。縱觀相關研究,現階段我國“三生”空間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為此,本研究主要圍繞“三生”空間劃分、演變趨勢、重心遷移等內容展開分析,為國土空間規劃的編制、空間資源的保護與可持續開發提供。
1 研究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珠海市地處珠江三角洲腹地,位于廣東省南部的珠江口西岸,位于113° 03'~114°19' E、21°48'~22°27' N之間,北接中山市,東倚江門市,瀕臨南海,與澳門半島相連,是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圖1)。自改革開放以來,珠海市土地利用結構與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而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珠海作為節點城市之一,在面對巨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有限國土空間資源規劃的挑戰。因此,分析珠海市“三生”空間的時空格局演變及其驅動因素,不僅可以為珠海市編制土地利用規劃提供依據,也為粵港澳大灣區涵括城市的國土空間布局優化與可持續發展規劃建設提供指導。
2015年,珠海市地區生產總值為2024.98億元,同比增長10.0%。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46.63億元,增長3.0%,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0.6%;第二產業增加值1006.01億元,增長10.2%,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4.8%;第三產業增加值972.34億元,增長10.0%,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44.6%。三次產業的比例為2.3∶49.7∶48.0。在服務業中,現代服務業增加值562.86億元,增長10.1%,占GDP的 27.8%。在第三產業中,批發和零售業增長6.3%,住宿和餐飲業增長9.1%,金融業增長14.8%,房地產業增長 10.8%。民營經濟增加值685.20億元,增長7.8%,占GDP 的33.8%。2015年,珠海市人均GDP達12.47萬元,按平均匯率折算為2.0萬美元,同比增長8.5%。分區域看,香洲、金灣和斗門3個行政區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329.02億元、420.10億元和275.86億元,分別增長9.3%、12.5%和 9.1%。全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1.7%。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土地利用類型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空間分辨率為30m×30m。由于研究期時間跨度較大,出現參考標準在不同時期不一致的情況,均以2015年為基準。最終得到珠海市1980、2000和2015年3年期的土地利用現狀圖和基礎空間數據庫。社會經濟數據從以下途徑:國家數據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廣東省人民政府(http://www.gd.gov.cn/zwgk/szfgb/index.html)、中國珠海政府(http://www.zhuhai.gov.cn/sj/)等途徑,獲取《廣東統計年鑒》《珠海統計年鑒》以及珠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有關資料。本文中廣東省行政區劃界線圖、珠海市行政區劃界線圖等矢量數據從城市數據派(https://www.udparty.com//)下載獲取。部分公式、參數來源于其他學者的參考文獻資料。
1.3 珠海市“三生”空間分類體系構建 對于“三生”空間的劃分原則,本文主要遵循主導功能性和單一性原則、生態空間優先原則、系統性原則,將“三生”空間分類與土地利用分類相銜接,構建基于地類的“三生”空間分類指標體系。由于目前暫無統一的評價標準體系,在梳理相關文獻后,本文將參考劉繼來、劉彥隨[10]等的研究成果,根據研究數據中珠海市的土地利用類型,對20個二級地類進行評分。采用1、3、5級賦分制,功能缺失為0分,最低功能得1分,最高功能得5分,構建珠海市土地利用”三生“空間分類體系(見表1)。由表1可知,珠海市生產空間包括水田、旱地、河渠、其他建設用地;生活空間為城鎮用地、農村居民點;其余用地均劃為生態空間。基于“三生”空間分類體系,通過Arc GIS軟件對珠海市土地地類進行重分類,繪制出1980年、2000年和2015年珠海市“三生”空間現狀圖(見圖2)。
1.4 三生”空間格局測度分析方法
1.4.1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是馬爾可夫模型在土地利用變化方面的應用,可用于研究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方向。采用矩陣的形式,將土地利用變化所產生的面積轉移進行表達,能直觀展示出研究區域“三生”空間類型變化,其表達式為[11]:
利用ArcGIS軟件分別對1990年和2015年珠海市“三生”空間按柵格數據進行交叉空間分析,并結合柵格計算工具,建立各期土地類型轉移矩陣和轉移強度空間分布圖。使用 Excel 數據透視表對分析數據加以處理,導出珠海市“三生”用地轉移矩陣。
1.4.2 土地利用動態度(LU) LU分為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和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通過計算土地利用動態度可分析出在某一時間段內土地空間類型總體或單一土地空間類型發生轉變的速度,計算數值越大,表明變化速度越快,程度越劇烈,其表達式為[12]:
式中:LC為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LUi-j 表示在T時期內i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轉為j土地利用類型面積的絕對值,LUi 為研究初期第 i 類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T 為研究時段,L表示單一土地利用類型的動態度,Ua表示研究初期和Ub 表示研究末期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
1.5 “三生”空間重心遷移分析 重心遷移用于研究一定區域內,相對平衡點發生變化的遷移軌跡。本研究運用重心遷移模型,分析在不同時間內人口重心遷移情況,結合土地利用數據,繪制出“三生”空間重心遷移軌跡圖,研究分析人口重心遷移與各空間類型分布間的內在聯系。
其定量表達式為[13]:
式中:[Xt]表示第[t]年“三生”空間重心的經度坐標,[Yt]表示緯度坐標。Cti為第[i]個斑塊該種“三生”空間類型的面積,[Xi]、[Yi]分別為第[i]個斑塊重心的經緯度坐標。
2 結果與分析
2.1 “三生”空間格局演變
2.1.1 數量分析 1980—2015年,珠海市“三生”空間轉移面積變化為516.06km2,占土地總面積的35.29%。其中,生活空間的轉出面積和轉入面積分別為27.18km2、148.63km2,相差121.45km2,轉出為生產空間、生態空間各占比為42%、58%,由生產空間和生態空間轉入均約為50%;生產空間、生態空間的轉出面積分別為259.05km2、229.83km2,轉入面積分別為148.63km2、200.59km2,2類空間均有較大占比的面積轉為生活空間(表2)。
運用綜合土地利用變化動態度(LC)公式計算1980—2015年珠海市“三生”空間綜合動態度為0.50%。分時段計算LC值,得出1980—2000年珠海市“三生”空間LC值為0.42%,2000—2015年珠海市“三生”空間LC值為0.91%。從LC值的計算可以分析出自2000年來珠海市“三生”空間類型演變速度愈加劇烈。
1980—2015年,珠海市生產空間減少較為明顯,面積由685.99km2減至573.48km2,動態度為-0.47%;生活空間擴張快速,面積變化更為顯著,動態度達5.25%,面積增加128.47km2;生態空間由706.24km2減少至690.28km2,動態度為-0.06%,面積相對保持穩定(見表3~表5)。
2.1.2 空間轉移 根據1980—2015年3期的土地利用分類數據,結合表1中的“三生”空間分類體系結果,進一步探討珠海市“三生”空間的格局演變特征。為更直觀了解珠海市“三生”空間在不同時期的分布變化,利用ArcGIS 10.2對1980年和2015年兩個時期的生產、生活、生態空間進行空間疊加分析,導出1980—2015年珠海市“三生”空間演變分布圖,分析各空間類型在不同年份的增加或減少情況(見圖3)。“三生”空間演變分布中,藍色圖例表示該空間類型在1980年存在,而在2015年發生減少,轉化為非原空間類型;紅色圖例表示在2015年該空間類型面積新增。總體來看,生活空間面積變化方向以增加為主,生產空間和生態空間面積變化相對較均衡地進行減少與新增交替。從不同類型空間變化的動態圖斑來看,生產空間圖斑出現較為完整大面積的從中部減少往東南部增加,同時在斗門區北部呈現碎片化空間類型增加減少變換;生活空間面積增加圖斑以片狀成集聚型為主,其中,增加圖斑集聚度最明顯的為香洲區主體部分,以中部為核心向南北靠東邊延伸。在斗門區生活空間面積增加圖斑從中部呈帶狀南下向西延伸。金灣區生活空間增加區域主要分布在東南面兩端,有小部分分布在西北面與斗門區相接;生態空間演變圖斑顯示出在東南部呈較大面積片狀減少,東北部零碎較為分散減少,同時,在中部往東北方向生態空間呈現出從片狀至碎片化均勻分布狀增加,而香洲區西部分散地塊生態空間面積以增加為主。
2.2 “三生”空間重心遷移分析 基于重心遷移模型計算公式,利用ArcGIS軟件的空間分析工具和幾何計算器工具,分別計算得出1980年、2000年和 2015 年珠海市“三生”空間重心坐標(見表6)。
珠海市“三生”空間重心位置,在不同時間的遷移方向和遷移距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總的來看,1980—2015年期間,珠海市生產空間重心與生活空間重心分別在斗門區與香洲區內遷移,生態空間重心在1980年和2000年在斗門區與金灣區交接附近,2015年則較為明顯遷移至斗門區內。對不同類型空間重心遷移而言,生產空間重心在1980—2000年間在往西南遷移一小段距離,而在2015年,生產重心明顯往東南遷移較遠距離;研究期間生活空間重心先向東南方向遷移再向西方向遷移,生活空間重心呈現不斷向南遷移的態勢,主要由于在1980—2015間,生活空間集中在香洲區出現較大片區的增加;生態空間重心遷移距離最小,同時呈現整體細微向北遷移的狀況,說明珠海市生態空間在研究期間增長或者減少較為均勻(見圖4)。
通過土地利用變化動態度(單一、綜合)、轉移矩陣、空間疊加分析、重心遷移模型等研究方法,對珠海市“三生”空間格局時空演變進行分析可知:
(1)從時間推移變化分析結果看,1980—2015年,珠海市“三生”空間發生變化面積為516.06km2,占土地總面積的35.29%。且自2000年以來珠海市“三生”空間類型的演變速度明顯加快。生活空間的擴張快速,面積變化最為顯著,生產空間面積持續減少,生態空間面積變化最小。生產空間轉出面積占比最大,其轉出轉入均已生態空間為主。生活空間面積轉入轉出差異最大,空間類型轉入由生產、生態空間各占比50%。
(2)從空間轉換變化分析結果看,1980—2015年,珠海市生產空間呈片狀在中部減少在東南部增加,呈現碎片式在西北部增減交替,其重心在3時期均落在斗門區,但在2015年出現較長距離從中南部往東南方向遷移;生活空間面積增加在各區以片狀集聚型為主,增加量與集聚度最為明顯位于香洲區主體部分,其重心在3時期均落在香洲區;生態空間在東南部較大面積片狀減少,在西北部呈片區或碎片化增加。
2.3 “三生”空間格局演變驅動因素
2.3.1 公共政策因素 國家政策文件的頂層設計對國土空間布局優化具有宏觀調控作用。近年來,“‘三生空間”成為熱點詞,相關概念或以其為理念的國土空間布局優化設計頻頻在政府相關工作報告或政策文件中出現(見表7)。
一系列國家政策文件都對土地利用的變化、城市開發(增長)邊界的明確以及“三生”空間的劃定和布局起著決定性的影響[14]。同時,珠海市在《廣東省珠海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2020年)》確立“生態優先、保障發展、節約集約、區域協調”的土地利用戰略;《珠海市生態文明建設“十三五”規劃》《珠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年)》等對珠海市的土地開發利用與布局優化具有指導作用,影響著“三生”空間類型演變。
2.3.2 人口增長因素 人口是城市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其數量增長、分布、素質以及遷移都會對土地利用的變化產生影響[15],人口增長必然導致生活空間擴張。根據珠海市1980—2015年年末,常住人口及生活空間變化情況(圖5)可知,珠海市的年末常住人口在1980—2000年快速增加,從36.53萬人增長至123.65萬人,年均增長4.36萬人。2000—2015年年末,常住人口保持相對穩定的持續增長,從123.65萬人增長至163.41萬人,年均增長2.65萬人。1980—2000年間,人口迅猛增長,生活空間也加速擴大,從69.98km2擴增至168.61km2,年均擴增面積4.93km2。2000—2015年間,人口增長放緩,生活空間擴張步伐也放慢,從168.61km2擴增至198.45km2,年均擴增面積1.99km2。從《珠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年)》可知,到2020年珠海市全市人口預計將達 245萬人,而市區建設用地規模也將擴張至210km2。人口快速增長形成巨大住房需求,推動生活空間不斷地擴張,同時不可避免地占用生產或者生態空間,最后驅動“三生”空間格局的演變。
2.3.3 經濟發展因素 在人口大幅度增長的同時,珠海市的經濟也在快速發展,成為珠海市“三生”空間類型變化的另一重要驅動因素。通過查找翻閱珠海市歷年統計年鑒繪制出其地區生產總值以及第一、二、三產業產值變化圖(見圖6)。由圖6可知,珠海市地區生產總值在1990年開始逐步增長,在2000年后呈現出直線上升的狀態,產業結構以第二、第三產業為主,兩者貢獻率高于90%。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珠海市生產空間愈發注重集約高效,斗門區與金灣區部分片區更多向生產空間轉型,部分區域生產性增強,宏觀上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產業園區、工業園區、商業綜合題等參與進城市空間布局與建設。生產空間在斗門區和香洲區高效集約,香洲區的生活功能和生態功能增強,致使珠海市空間格局發生變化。
3 結論
本研究選取我國最早的經濟開放城市之一,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的節點城市——珠海市為研究對象,提取珠海市1980年、2000年、2015年三期的遙感影像解譯圖,基于地類構建“三生”空間的分類指標體系并進行評分,利用GIS空間分析、重心遷移等方法,對珠海市1980—2015年的“三生”空間格局演變進行分析,并對演變的驅動機制進行了系統梳理,主要結論如下:
(1)由時間推移變化分析可知:1980—2015年,珠海市“三生”空間發生變化面積為516.06km2,占土地總面積的 35.29%。且自2000年以來珠海市“三生”空間類型演變速度明顯加快。生活空間擴張快速,面積變化最為顯著,生產空間面積持續減少,生態空間面積相對保持穩定。生產空間轉出面積最多,其轉出轉入均以生態空間為主。生活空間面積轉入轉出差異最大,空間類型轉入由生產、生態空間各占比50%。
(2)由空間轉換變化分析可知:1980—2015年,珠海市生產空間呈片狀在中部減少在東南部增加,呈現碎片式在西北部增減交替,其重心在3時期均落在斗門區,但在2015年出現較長距離從中南部往東南方向遷移;生活空間面積增加在各區以片狀集聚型為主,增加量與集聚度最為明顯位于香洲區主體部分,其重心在3時期均落在香洲區;生態空間在東南部較大面積片狀減少,在西北部呈片區或碎片化增加。
(3)國家政策文件的頂層設計對國土空間布局優化具有宏觀調控作用,地方政府依據國家頂層設計制定符合城市發展要求的規劃部署,因而頂層設計與地方規劃共同推動“三生”空間格局的演變發展。
(4)人口增長、經濟發展與“三生”空間格局演變具有密切關系。人口快速增長形成巨大的住房需求,推動生活空間不斷地擴張,而人類群居習性也會使生活空間呈現片狀擴張;珠海市經濟發展迅猛,同時在城市規劃方面注重高效集約,因而生產空間成片狀向城市外圍圈發展。生活空間、生產空間的發展,也勢必會造成生態空間的擠占。
參考文獻
[1]李科,毛德華,李健,等.湘江流域三生空間時空演變及格局分析[J/OL].湖南師范大學自然科學學報,2020(02):9-19[2020-04-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3.1542.n.20200330.0847.004.html.
[2]張磊,陳曉琴,董曉翠,等.三生互斥視角下工業用地空間布局優化——以天津市為例[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19,35(03):112-119.
[3]張紅旗,許爾琪,朱會義.中國“三生用地”分類及其空間格局[J].資源科學,2015,37(07):1332-1338.
[4]黃金川,林浩曦,漆瀟瀟.面向國土空間優化的三生空間研究進展[J].地理科學進展,2017,36(03):378-391.
[5]郝晉偉,李建偉,劉科偉.城市總體規劃中的空間管制體系建構研究[J].城市規劃,2013,37(04):62-67.
[6]Morris, K.I., Chan, A., Ooi, M.C., et al. Effect of vegetation and waterbody on the garden city concept:An evaluation study using a newly developed city, Putrajaya, Malaysia.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2016,58:39-51.
[7]Sharifi, A. From Garden City to Eco-urbanism:The quest for sustainable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16,20:1-16.
[8]Kharchenko, N.N., Moiseeva, E.V.,Prochorova, N.L.,et al, Ecosystem functions of forest park green belt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a fact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ving standards in conditions of sparsely wooded regions.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ngineering and Earth Sciences: Applied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ISEES 2018)[M]. Atlantis Press,2018.
[9]Xing Y. Brimblecombe P. Role of vegetation in deposition and dispersion of air pollution in urban park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19,201:73-83.
[10]劉繼來,劉彥隨,李裕瑞.中國“三生空間”分類評價與時空格局分析[J].地理學報,2017,72(07):1290-1304.
[11]付秋祺.天津市大寺鎮城鎮土地動態變化研究[J].海峽科技與產業,2019(05):157-158.
[12]于志磊,秦天玲,王剛,等.川江流域土地利用時空格局動態變化特征[J].南水北調與水利科技,2016,14(02):38-43,61.
[13]郭慧麗,李巧云,關欣,等.湖南桃源縣土地利用動態變化研究[J].湖南農機,2012,39(03):136-137,141.
[14]楊永強.土地利用規劃環境影響評估在環境保護與國家政策實施中的作用[J].化工設計通訊,2016,42(03):211,214.
[15]姚安坤,張志強,郭軍庭,等.北京密云水庫上游潮河流域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3,20(02):53-59.
(責編:張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