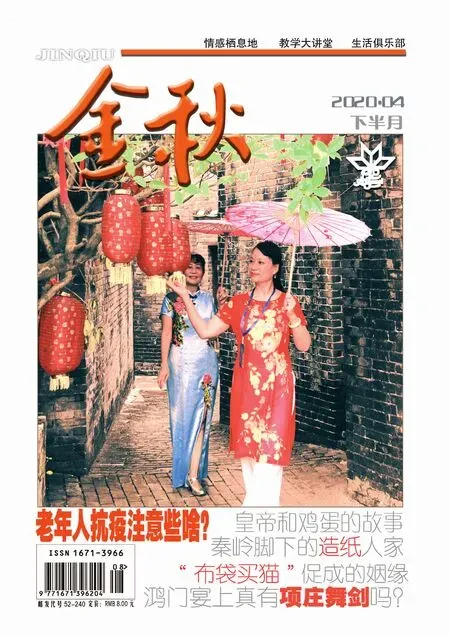文人墨客與老北京的風(fēng)沙
◎文/臺灣·邱仲麟

撲面沙塵滾滾來
近代以前,北京城肆虐的風(fēng)沙大概是所有到過這里的士人的共同記憶。弘治十八年(1505),剛考上進(jìn)士的倪宗正駐足在北京的街頭,一陣大風(fēng)挾帶著塵土迎面而來,他開始領(lǐng)略到北京的風(fēng)沙,于是留下了“長安路,長安路,塵埃十丈如煙霧”的詩句。明末,袁中道(1570-1623)在感懷舊事時,也曾有“燕市多飆風(fēng),常吹陌上塵。一層塵已去,一層塵又生”的描寫。
北風(fēng)肆虐,沙塵蔽日,這一自然現(xiàn)象成為在北京生活的士人難以磨滅的記憶。萬歷末年,俞彥回憶起在北京的點點滴滴,作了《憶長安十首》,其第一首寫道:“長安憶,最憶是灰塵,地有寸膚皆著糞,天無三日不焚輪,并作十分春。”俞彥系南直隸太倉人,萬歷二十九年(1601)考上進(jìn)士,授職兵部主事,升兵部員外郎,后官至光祿寺少卿。走過這段在北京不算短的歲月,最讓他忘不了的竟是那漫天的沙塵。
說起來,北京的風(fēng)塵之多,著實令南方士人感到不習(xí)慣。萬歷年間,來自福建的謝肇淛(1567-1624)談到:“燕、齊之地,無日不風(fēng);塵埃漲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為苦,土人殊不屑意也。”又說風(fēng)大到什么程度呢,“不減于海颶,而吹揚黃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見,歲恒一二云。”根據(jù)學(xué)者研究,北京地區(qū)在明朝276年當(dāng)中,共有95個年份出現(xiàn)過春夏時節(jié)大風(fēng)連日、沙土飛揚的風(fēng)霾天氣,即每三年就有一次。據(jù)記載,北京風(fēng)沙最為頻繁的時期為成化、正德、嘉靖、萬歷以及天啟至崇禎年間。這些從蒙古高原南下的風(fēng)霾,有時可連續(xù)數(shù)十日或上月。
如天順八年(1464)二月至三月,史書載“黃塵四塞,風(fēng)霾蔽天,沙土迭雨,所括之風(fēng)從西北來,且呼呼有聲”。又如成化四年(1468)三月,風(fēng)沙累日,天壇、地壇的外墻,“風(fēng)沙堆積,幾與墻等。”而嘉靖二年(1523)二至四月,“風(fēng)霾大作,黃沙蔽天,行人多被壓埋”,“黃沙著人衣,俱成泥漬”。崇禎十三年(1640),陳龍正(1585-1645)在家信中談到:“自二月十九以后,屢大風(fēng)霾,或連三四日,或間一二日”;三月初三清晨,“黃土彌天”,接著風(fēng)大作;初五夜,“狂風(fēng)尤甚,徹旦及申,飛瓦拔樹,人馬迎風(fēng)者,皆不能前,且?guī)子写刀拐摺薄?梢韵胍姰?dāng)年風(fēng)霾之可怕!
如此惡劣的氣候,令長年在北京生活的南方人常深以為苦。明中葉,薛蕙(1489-1541)寫詩詠道:“長安城中不可留,風(fēng)塵日日使人愁。”而對謝肇淛來說,雖然北京冬季嚴(yán)寒,但他卻是“不患寒而患塵”。北京這種無孔不入的風(fēng)沙,在狂風(fēng)吹襲之余,常造成室內(nèi)不論是窗戶或是幾案,到處都是“飛埃寸余”。而大風(fēng)一起,“塵沙豈似瀾”的情景,“飛沙澀齒牙,霧眼揮酸淚”的滋味,也都在南方文人的詩文中表露無遺。等到退職鄉(xiāng)居,遇見北京來的人,依然是“怕說東華十丈塵”。直至清代,北京的風(fēng)塵一如往昔。清代后期,《燕京雜記》曾云:
黃河以北,漸有風(fēng)沙,京中尤甚。每當(dāng)風(fēng)起,塵氛埃影,沖天蔽日,覿面不相識,俗謂之刮黃沙。月必數(shù)次或十?dāng)?shù)次,或竟月皆然。

紙糊窗來擋風(fēng)沙
又云:“風(fēng)沙之起,觸處皆是,重簾疊幕,罩牖籠窗。然鑚隙潛來,莫知其處,故幾席問拂之旋積。”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要保持室內(nèi)清潔幾乎是不可能的。由于風(fēng)塵可憎,故李慈銘(1829-1894)曾在同治三年(1864)說,都中有“三苦多”:“天苦多疾風(fēng),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貴官。”在這三多之中,除了貴官多之外,就是風(fēng)與塵了。也就因為這令人苦惱的風(fēng)與塵,住戶多半以紙糊窗來防阻沙塵的侵入。然而整個室內(nèi)的空氣,隨著這一層紙的糊上也隔絕了對流的機(jī)會。清季,陸費達(dá)在《京津兩月記》中提到:
北京因患蚊蠅、塵砂之故,窗欞皆不能啟,窗心糊紗,四周糊紙。天空空氣,因地勢高爽,甚為清鮮。室中則異常悶苦,頗害衛(wèi)生,一日不外出,輒如患病。北人無論男女,無不外出嬉游。南人來者,眷屬每不喜出外,終日蟄居家中,婦女之病而死者比比皆然,此亦居京者不可不知之事也。
由此可知,北京由于多風(fēng)塵等因素,房屋的窗戶多不能開啟,因此室內(nèi)的空氣異常污濁,對居住者造成傷害,這是風(fēng)塵對北京居家生活所造成的另一不良影響。
短短一尺絹,占斷長安色
在明清時代的北京,人們?yōu)榱吮苊怙L(fēng)沙對眼睛造成傷害,出門總戴著一種特殊的面紗。此種景況,即徐渭(1521-1593)所謂的“長安街上塵如煙,葛布眼眼風(fēng)難度”。而王世貞(1526-1590)的《戲為眼罩作一絕》,亦述及了“短短一尺絹,占斷長安色;如何眼底人,對面不相識”的情形。萬歷末年,利瑪竇在北京也見到這種特殊的景觀。他寫到:
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磚或石鋪路的,也很難說一年之中哪個季節(jié)走起路來最令人討厭。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塵同樣使人厭煩和疲倦。由于這個地區(qū)很少下雨,地面上分離出一層灰塵,只要起一點微風(fēng),就會刮入室內(nèi),覆蓋和弄臟幾乎每樣?xùn)|西。為了克服這種討厭的灰塵,他們就有了一種習(xí)慣,那或許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這里在多灰塵的季節(jié),任何階層的人想要外出時,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條長紗,從帽子前面垂下來,從而遮蔽起面部。面紗的質(zhì)料非常精細(xì),可以看見外面,但不透灰塵。
透過利瑪竇的這段描述,我們可以了解,外出戴面紗,乃是帝國都城的一大景觀。據(jù)屠隆(1542-1605)自述他在北京的體驗云:“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fēng)起飛塵滿衢陌,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看來即使眼睛不會受到風(fēng)沙侵入,但鼻孔滿是沙塵卻是難以避免,生活在北京,出門需要充足的準(zhǔn)備,回來不僅要洗臉,還得清理鼻腔。
北京居民這種以紗覆面的習(xí)慣,一直到近代猶然。乾隆年問,汪啟淑曾說:“正陽門前,多賣眼罩,輕紗為之,蓋以蔽烈日、風(fēng)沙。”民初,雷震亦云:“京師塵土蔽天,風(fēng)大時,耳目皆為之閉塞,路上行人,往往以手巾覆面。”

為了減少街道的灰塵,清代官方?jīng)]有“潑水卒”,專責(zé)潑灑街道,這也是北京令人記憶的一景。“潑水卒”在明代雖未見記載,但清代這一制度有可能是繼承明代的。清初,周長發(fā)(1696~?)在《燕臺新樂府·潑水謠》中云:
沿衢喚潑水,怒馬華軒塵四起。老兵健卒聲喧闐,汲泉貯桶排門前。瞥見密云愁不雨,白龍手幻飛濺濺。一車百錢辦不易,即論苦水猶煩費。寶此惟供馬足清,瓶盆涓滴休輕棄。饑者獨擔(dān),勞者弗替。敢辭蘊隆日日劬,不則里正申申詈。
從詩當(dāng)中可以看出,街上有兵丁專責(zé)灑水,但由于北京水貴,一車需要銅錢百文,故兵丁責(zé)成里正,要百姓將用過的水省下,屆時用以灑街。由于定時潑灑,北京城內(nèi)的御道,據(jù)說是潔凈如拭。乾隆年問,蔣士銓(1725-1785)在《京師樂府詞·潑水卒》中曾云:
城內(nèi)天街凈如拭,老兵潑水有常職。軟塵不飛帶余潤,風(fēng)伯揚之無氣力。汛掃反道見禮經(jīng),負(fù)土抱甕兼守更。司寤掌夜比都候,宵行夜游分以星。街心除掃如鏡平,驅(qū)馳但許官車行。微風(fēng)細(xì)雨真堪樂,坐對軍持怕久睛。
這一首詩述說了潑水卒的職務(wù)與心酸,他們除了平常灑水之外,還得負(fù)責(zé)整理道路、掃除街心。也就因為他們的辛苦,街道中央的官道與御路,才得以平整而干凈。一般而言,灑水多在黃昏,故凈香居主人《都門竹枝詞》云:“馬蹄過處黑灰吹,鼻孔填平閉眼皮。堆子日斜爭潑水,紅塵也有暫停時。”
這個制度,直至清末猶在。民初,陳師曾(1376-1923)在《北京風(fēng)俗圖》中就畫有潑水夫,并賦詩曰:“風(fēng)伯揚塵起,素衣化為緇。勺水勿嫌少,功澤勝雨師。”不過,灑街的水可能不盡然是清水。19世紀(jì)之末,英人Henrv Norman曾記道,北京每當(dāng)傍晚時分,會以城里溝渠的溝水灑街,這些溝水多含有泥巴,這樣一來,灑街的效果大打折扣:等到泥干了,又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