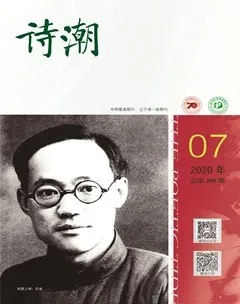好像出席假面舞會 [組詩]
楊河山
馬從不睡覺
我發現馬從不睡覺,
那年我七歲,當夜里去撒尿,
看見它們站在馬棚子里,
咀嚼,鍘刀切割麥秸的聲音。
紅色的舌頭舔著木頭槽子,
紫色的眼睛,像冰燈。
后來的很多個夜里我去撒尿它們仍然站著,
咀嚼,鍘刀繼續切割,
紅舌頭滴著涎水。
以至于我總在想馬為什么不睡呢?
睡覺多好,它們的冰燈,
會沒有油嗎?我心疼它們總是不睡,
當我長大,失眠的時候,
它們總是浮現在我的眼前,
狹長的河床般的頭顱
朝向我,貼近我注視著我,
紅舌頭舔我,像久已離世的母親親切的撫慰。
你活著的每一個瞬間都是你的
你活著時候的每一個瞬間都是你的,
你已經度過了它們。
無論那些幸福的時光,
還是痛苦悲傷的日子,
好的壞的,你都在一起度過。
以及所有的辛勞和奔波,
煎熬——這個世界已沒有任何東西屬于你,
包括你的軀體,它屬于塵埃。
(你的靈魂屬于上帝)
只有你活著的時候所度過的每個瞬間
屬于你,它們是你的。
(佩索阿:你是真的活了一萬多天,
還是僅僅生活了一天,
卻重復了一萬多次?)
那嚓嚓嚓行走著的生命的時針和秒針
所承載的事物,誰都拿不走,
它們屬于你,它們才是你天然的財富。
喂——
我想對著墻壁喊一聲:喂——
沒有人回答。我想對著禁閉的大門喊一聲,
喂——沒有人回答。
我想對著敞開的窗戶喊一聲,
喂——沒有人回答。
我想對著封閉時期空無一人的街道喊一聲,
喂——沒有人回答。
我想對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高喊一聲,
喂——是我,沒有人回答。
我想對著無邊的時空黑暗中那無比明亮的部分,
對著無限浩渺的空虛高喊,
喂——我是誰?此刻我在哪兒?
我要去哪里?沒有人回答。
我高喊:喂——喂——其實我呼喚的
是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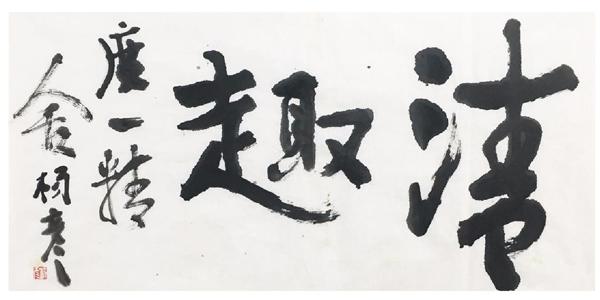
楊彥作品
我是我父親的孩子
我是我父親的孩子。
我父親是我父親的父親的孩子。
我父親的父親,是他的父親的孩子。
我們曾經都是孩子。
而我也將有許多孩子,
我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們,
這意味著什么?
我從未見過我父親的父親,
相信他也會如此,而未來某個時刻,
我的后代們也不會見過我。
(或許將在詩中重逢)
這一切其實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我們都曾經年輕,
然后不可避免地衰老,
重逢,或離別,然后遺忘,
我們每個人都是中間的媒介,
我是我父親的孩子,
我是孩子,但現在我已經接近老年。
秩 序
女孩的學習桌上有一盞白熾燈,白熾燈上
方的屋頂上有一盞更大的枝形吊燈,枝形
吊燈的上方是月亮和星空,星空上方是更
加深邃的星空。
聽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彈奏舒曼《童年即景》
好像在夢里,我是否還能重新變成
一個孩子?在田野上飛奔,
在泥濘的土道上滾動一個鐵圈,
在散發著稻草氣味的
脫粒機里睡覺,在鐵路小站追逐一輛
綠皮火車,在小河釣魚,
在玉米地捉迷藏,在那個唯一的場院
放飛一只綠色絲線的耗子風箏,
在山坡上騎馬,騎牛,騎豬,
與一只母雞賽跑,在冬天的院子里
升起一盞紅燈……
這些深情溫暖的回憶令人惆悵又悲傷,
時間過去太久了,
我走得太遠,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