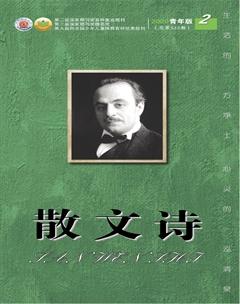希區柯克《后窗》:以電影窺視電影

柒姑娘,重慶市渝中區人。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
上世紀50年代希區柯克導演的電影《后窗》 (Rear Window,1954),之所以被當成經典的驚悚懸疑類型片而不直接稱為犯罪片,是因為全片并沒有出現犯罪的過程,只是通過其他信息加以暗示,讓觀眾自行揣摩。一個摔斷了腿的人在百無聊賴之中對著窗口發呆,無意間發現對面一戶人家,丈夫貌似把妻子分尸。一直到影片最后,希區柯克也沒有揭示謎底,犯罪是否成立,但整個過程足以讓人捏一把汗。希區柯克式“作者電影”讓他幾乎成為驚悚懸疑片的代名詞,善于制造懸念并超越現實地創造出一個充滿懸念的世界,把驚悚懸疑片提到了藝術的新高度。作為一名極為敏感且從未接受科班訓練的導演,希區柯克用電影傳達出他內心對世界某種失控的恐懼、焦慮和脆弱感,甚至接近精神病患者。他嘗試用電影喚醒我們每個人內心的希區柯克,就像走進一個彌漫著窒息般黑色氛圍的房間。
《后窗》有意思之處在于,它巧妙運用電影去揭示了電影是什么。一直以來電影是以電影作為畫框、以電影作為窗口兩種觀點來進行闡釋的。二者主要區別在于對電影取鏡所產生的遮擋關系的理解:畫框是封閉的,窗戶是開放的。人的眼球觀察到的世界是立體的,世界就是自己的影像(在己影像)。而電影給人的立體感(三維空間感)其實是建構于屏幕(二維平面)之上的,這樣的真實感并不等于真相,只是一種幻覺,電影即造夢。人對世界的觀察是處在散亂、偶然的廣闊時空之中,生活本身的流動并不是連續排列的戲劇性事件。而一個電影鏡頭,其時長和鏡框都是有限的,它就像是對世界的一個動態橫截面,導演要把這些截面作為材料組合成戲劇化的事件,這就是電影所謂的場面調度。
在被稱為“一部柏格森式電影”《畢加索的秘密》(1956)中,影片撇開畢加索,而讓畢加索筆下的線條、顏色成為畫布上的演出,成為一種懸念迭代的生成過程。德勒茲認為,電影是唯一可以感知時間的藝術。在《運動一影像》與《時間一影像》兩本書中,德勒茲獨辟電影哲學的分析:當時間附著于空間,則是“運動——影像”;當空間附著于時間,則是“時間——影像”。電影的存在依托于記錄影像的物質材料,但電影作為純視——聽影像的情動(affect)是超越儲存介質的,和所有藝術形式一樣,它能夠實現自我保存和自我感知(percept),在人的大腦屏幕實現感覺(sense)的重生。觀看:人的眼睛在面部就形成類似黑洞——白墻,我們透過“黑洞”去觀看并被宇宙的黑洞吸引。人的面部包含著非人的成分,當我們閉眼也并非看不見,我們能看見黑暗。
作為驚悚懸疑類型片,有意思的是,《后窗》的魅力不在于其情節有多么復雜,也不是訴諸人物情感上的波瀾起伏,它用懸念激起觀眾的驚悚是純電影式情動(affect)的直接作用,它是——心智的,非語義的。此時,我們對于自然時間的感知已變成對于電影時間的感知,即日常所說的“扣人心弦”,隨著情節推動,越發沉浸其中。演員在表演時,攝影機如同觀眾的眼睛,演員處于假想的“被窺視”狀態。在電影《后窗》中,第一個窺視——被窺視鏡頭是對面穿比基尼的金發女郎在屋內跳舞,女性及后來的女性貌似被害作為被觀看的客體,代表著電影處于被觀看的客體地位。這個相對歡快、美艷的場景就像是電影開場或戲劇序幕。觀眾沉浸或者疏離,更多的,則是兩種狀態兼而有之。當窺視者(男主人公)獨自觀看對面時,是處于沉浸狀態,他與保姆、女朋友聊天的時候是處于抽離狀態。接著,窺視者(男主人公)聽到對面的鋼琴聲,得出婚嫻不幸福產生孤獨感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是否可靠我們不得而知。對面的男人爬上樓梯,回家,把大箱子搬運到外面,時時在窗口張望,收拾刀具、繩子,而他的妻子再也沒出現過。籃子裝著小狗從樓上到樓下,狗是嗅覺靈敏的動物,影片用它暗示不尋常的氣息,后來犯罪嫌疑男想要殺死小狗。窺視者(男主人公)的情緒隨著對面的人的動作發生波動,他與女友討論,與警探爭辯,試圖去發現真相,通過看到的不完整的畫面去推測:被害者可能埋在樓下花園里。事實上,窺視者(男主人公)看見的就是希區柯克導演精心安排的場面調度,這些可見和可聽的電影引起觀眾(也是劇中的男主人公)腦海里另一部電影,一部暗流涌動的電影,它構成了心智上的懸念和情感上的驚悚,所以那個犯罪的結論不是觀眾或窺視者(男主人公)看到的,而是被讀出來的或者存在于欲望里的。
《后窗》用電影中的窗口很好地揭示了電影作為窗口、作為畫框、作為吸引力的“黑洞”的特點。《后窗》所呈現的過程,即在半遮半閉的窗口觀看,試圖去猜想沒有看見的部分(畫外空間,蒙太奇)。對于驚悚懸疑電影而言,最精彩的不是揭曉謎底的一瞬,而是懸而未決的瞬間,腦海中的血腥比看見的血腥更加血腥。于是希區柯克選擇不揭開謎底,讓觀眾持續處于緊張狀態。 《后窗》中,磚紅色的房子,藍天、黑夜、窗子、樓梯、窺視、陰影、電話,各種服裝、道具的使用,激進背景音樂的選用,都讓這變成一場視聽盛宴。這需要對這些影像表征足夠講究,耳聰目明,并且精準剪輯,才能激發觀眾“視覺上的欲望”。這種視覺上的欲望和危險表現為窺視欲,躲在暗處而對別人的生活產生好奇,窺探別人的隱私。盡管現在到處充斥的監控影像,是出于保障安全或者監督等各種目的,但監控仍就像無處不在的鏡頭或眼睛。希區柯克可謂是監控影像的先驅,只不過,在當下是作為控制與服務社會的監視,而在希區柯克那里則是發明了一種窺視電影。電影《后窗》中50個窗口的場景就像是監控畫面,由無數個小屏幕并置。因此,可以認為監控也是電影概念的擴大。值得一提的還有我們的隨手拍攝,近乎于《工廠大門》《火車進站》等電影的最初形態。影片呈現,當窺視者試圖去干涉對面那戶人家,就會發生危險。這意味著,屏幕(窗口)是一重阻隔,一旦跨越,就可能出現某些意想不到的情況。“電影”就像影片中表現的,觀看者拿著望遠鏡透過窗戶去觀看,望遠鏡的形狀極像電影圓鏡頭。不同于戲劇,電影可以放大一切需要放大的細節,種種技術手段更是增加了其可能性。而另一部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放大》則戲謔地告訴我們,放大之后的一切也不一定是可信的。
《后窗》描述的狀態更接近于電影默片時期,觀看者聽不見對白,只能看見動作,影片人物穿著也充滿舞臺感。對于觀看者摔斷腿的設置為故事發生增加了合理性,同時也像皮下注射論所認為的,電影是強制性觀看,讓人注意力集中。在家對著電腦看電影與在電影院看電影的觀影感受是不相同的,就像是受干擾與排除干擾;反催眠與催眠。電影之美是什么?這是電影美學探尋的基本問題。約翰·福特的電影《搜索者》(1956)告訴我們電影就像門,瓦爾達則在《一百零一夜》(1995)中將電影擬人化表現。任何藝術門類,其審美途徑都是經過感官抵達思維,電影更是對感覺的全方位包裹。于是,湯姆·提克威電影《香水》(2006)能夠實現嗅覺的視覺呈現;就像語言有內在圖像性和音樂性一樣,詩歌也能讓語言出現味覺效果。電影本內在于我們,當我們開始看電影,視——聽世界由潛在變為存在,得以重新呈現。電影不僅僅是媒介,電影就是思維。當我透過電影看向一扇窗,那扇窗也在看向我這邊。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電影在看著我們,正如印象派畫家莫奈說“花朵在看”。亦如中國現代詩人卞之琳的短詩《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