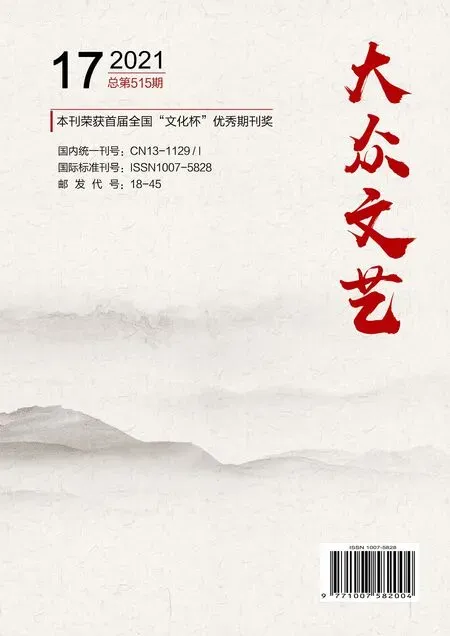情理交融中的明暗魅惑
——試論話劇《雷雨》的語言趣味
李 佳
(河南大學音樂學院,河南開封 475000)
有學者說,從我國劇作家曹禺創作的《雷雨》中看到了《俄狄浦斯王》的影子。的確,《雷雨》在藝術精神上受古希臘悲劇的影響,在創作中遵循西方戲劇藝術理論“三一律”。曹禺雖學習借鑒西方戲劇藝術手法的成果,但更重要的是將其成功的“中國化”。[1]《雷雨》是一首敘事詩,語言有著獨特的朦朧魅惑力,語言文字明暗變化的鮮明對比,理性中流露著難以控制的情緒化傾向等。有人問“《雷雨》是怎么寫的”,曹禺曾這樣說“現在回憶起三年前提筆的光景,我以為我不應該用欺騙來炫耀自己的見地,我并沒有明顯的意識著我是要匡正諷刺或攻擊著什么。也許寫到末了,隱隱仿佛有一種情感的洶涌的流來推動我……”①就是將這樣一種復雜又原始的情感宣泄凝注于筆尖,才使得《雷雨》在語言文字上的成就尤為突出,本文將從劇本創作出發談談其語言趣味。
一、明亮與黑暗——語言的清純明凈與污穢氣息的鮮明對比
在《雷雨》縱橫交錯的戲劇矛盾沖突里,周沖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作者對他性格與命運的描摹有著十分重要的戲劇意義。劇本中他的語言時時刻刻無不流露出他的天真爛漫、美好活潑與積極樂觀的人生向往,他是黑暗中一抹明亮的光芒。一個僅17歲又洋溢著無限青春與活力的男孩兒,懵懂的內心有著對一切事物博愛的幻想,純真的靈魂蕩漾在虛無縹緲的幻想之中。周沖向四鳳講述的臆想中的世界是最能表現他性格的極其純凈的戲劇語言:“對了,我同你,我們可以飛,飛到一個真正干凈、快樂的地方。那里沒有爭執,那里沒有虛偽,沒有不平等……沒有……你說好么?”②如詩如畫般的幻想與丑惡污穢的現實形成強烈對比,在那樣黑暗的社會環境中,美妙純真的幻想注定要被殘酷的現實撞個粉碎。在勸母親喝藥時,他才真正意識到了父親威權的不可挑戰;謙卑善良的他在同魯貴的交談中,才發現二人之間有著一層無法突破的透明隔膜;當母親蘩漪歇斯底里的吼他發怒時,他才看到母親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樣慈愛溫柔。“你真是沒有點男子氣,我要是你,我就打了她,燒了她,殺了她……你不是我的兒子”“(指周萍)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個的人,可是他現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③看到他眼里最慈祥聰慧的母親也這樣丑惡地為情愛痙攣地喊叫,他才徹頭徹尾的認識到現實的污穢粗惡。
“周沖是這煩躁多事的夏天里一個春夢。在《雷雨》郁熱的氛圍里,他只是一個不調和的諧音,有了他,才襯出《雷雨》的明暗。”④《雷雨》中的周沖擁有清純明凈的靈魂,話語言辭中透露著單純、青春的懵懂與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就是這樣一個心靈純凈的人卻置身在污穢黑暗的社會環境中,魯貴如污水泥濘中的蛆蟲啃噬著丑惡虛偽的生意經,代表著維護封建秩序的周樸園,不顧一切、瘋狂而近乎變態地追求自由之愛的蘩漪等等。他是這黑暗現實中的一束明亮的光,盡管他的理想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是一種空想,但他與全劇其余讓人沉悶壓抑的人物形象相比是獨特的存在。作者用不同風格的語言刻畫出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語言中的清純明凈同污穢黑暗形成鮮明的對比,給人以思想與情感的雙重沖擊,也讓我們對周沖這樣一個可愛的生命的消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如若周沖不死,在那樣一個難以打破的黑暗環境中,他就會像周萍一樣回歸到周樸園的秩序中來,這將是比死更悲劇的悲劇。[2]
二、朦朧魅惑的語言“魔”力
《雷雨》中的又一大語言特色是潛臺詞與模糊語的大量使用。潛臺詞是“臺詞中所包含的或未能由臺詞完全表達出來的言外之意。”⑤劇本中大量使用潛臺詞和模糊語,越是這樣看似朦朧模糊的語言表達,越是在無形中透露著無盡的犀利與尖銳,越是這樣的字眼,越是激發讀者探求其言外之意與隱藏在背后的故事。
蘩漪是劇中最具“雷雨”性格的人,“她的生命交織著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⑥,不是愛便是恨,不是恨便是愛,一切都走向極端,要如電如雷般轟轟烈烈的燃燒一場。劇中她走向極端的語言指引,依附在看似朦朧模糊的言辭中,更顯得尤為尖銳。從戲一開始,作者就告訴我們蘩漪只有一個心思:報復。她會無所顧忌地揭露一切,揭露她自己的罪惡。她時時在恫嚇,她警告周萍:“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個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來的。”周萍另有所愛,不把她放在心上,于是她宣布:“好,你去吧!小心,現在(望窗外,自語)風暴就要起來了!”她說是自然界的暴風雨,但是我們感受到的是她心里的暴風雨。她從一出場內心就是狂躁的,“樓下也這么悶”,“我簡直有點喘不過氣來”,她言語中的“悶”傳達出的是難以言傳的精神痛苦,這是一種超常態的欲望和對欲望超常態的壓抑,有著近乎瘋狂的情緒力量。“(把窗戶打開,吸一口氣)熱極了,悶極了,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變成火山的口,熱烈的冒一次,什么我都燒個干凈,那時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凍成死灰,一生只熱熱地燒一次,也就算夠了……”⑦滿蓄著受壓抑的力,必然要隨時隨地尋求一個缺口,以便沖決而出。話語間,她在強壓著內心燃燒的熱情欲火,給讀者帶來持續的緊張感。愛到嫉妒變成破壞,朦朧的話語尖銳到讓人覺得可怕,她也在一步步預謀的破壞中享受著報復帶來的極端快感。
像這樣給人以緊張感、極具戲劇性和的潛臺詞和模糊語還有不少,再以第一幕為例,魯貴向四鳳訴說周家屋子過去“鬧鬼”的一段對話:“哦,這屋子有鬼是真的”“可不是?我就是乘著酒勁兒,朝著窗戶縫,輕輕地咳嗽一聲。就看見這兩個鬼颼一下分開了,都向我這邊望……這我可真見了鬼了。”他故弄玄虛,制造緊張氣氛,說見到“鬼”,又不立馬說出實情,給四鳳造成心理壓力,也給觀眾設置懸念。魯貴的訴說推動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四鳳的心被提得緊緊的,我們的心也跟得愈緊,欲探究竟。像這樣表面含糊不清、不知所指的言辭,愈發顯得犀利尖銳,更勾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想要努力探求言語背后事情的真相,為劇情發展做了很好的鋪墊。[3]
三、情感的爆發與理性的思考——語言的感性呈現與理性表達
在《雷雨》中,看似平靜實際暗藏洶涌的場面比比皆是,從故事拉開帷幕到結束雖只有一天時間,但他的導火索已埋下三十年,由過去的事件不斷推動現在的事件,在不斷揭開事件真相的過程中,感情這座火山也在一點點的積蓄升溫,而后終于爆發。曹禺曾說“苦熱會逼走人的理智。在一定意義上,他在蘩漪身上所著力發掘的,正是人的非理性的情欲,以及人的魔性方面,蘩漪的內在魅力,實出于此。”⑧蘩漪:“(向周沖、半瘋狂地)你不要以為我是你的母親。你的母親早死了,早叫你的父親壓死了,悶死了。現在我不是你的母親,她是見著周萍又活了的女人,她也是一個要一個男人真愛她,要真真活著的女人……”這是積蓄多年郁熱苦悶的情感大爆發,沖破傳統倫理道德的束縛,她不惜放棄以至褻瀆最為神圣的母親的尊嚴,赤裸裸的在孩子面前展現著自己對情欲的渴望,確實驚世駭俗、震撼人心。這樣情緒化的人物語言的爆發能夠迅速將故事推向高潮。
曹禺說“《雷雨》的降生是一種心情在作祟,一種情感的發酵……”⑨是的,作者將他的情感帶入到了劇本創作中。所以,他整部作品的語言文字,或隱或顯地都在呈現著一種感性的情緒化傾向,這種感性情緒也為劇本注入了充沛的生命力。但僅靠感情的傾注與流露是寫不出《雷雨》的,我們也絕不能忽視曹禺劇本創作中深潛的理性因素的存在。[4]
曹禺對《雷雨》的理性把握,首先體現在學習和借鑒西方戲劇藝術手法的優點,并結合中國文化、民族戲劇、民族生活等,使外來的西方戲劇藝術形式扎根中國土壤,將其成功的“中國化。”讀書期間,他大量接觸了希臘三大劇作家和莎士比亞、契訶夫、奧尼爾等人劇作,領悟到世界戲劇發展的本質趨勢即詩與現實的結合。[5]他站在中國民族的土壤上,將領悟到的西方戲劇觀念進行有益吸收與革新,形成他創新性的中國戲劇觀念,寫出了中國現代第一部真正的悲劇。扣人心弦的敘事語言、熱熱鬧鬧的環境描寫、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個性化人物塑造,在他的作品《雷雨》中都得到了完美體現。其次,表現在曹禺長遠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出色的對文字的把握能力,使《雷雨》語言的嚴謹性和完整性堪稱中國話劇史上的典范。作者采用鎖閉式的結構,巧妙地從“過去”和“現在”兩條線索出發,構成了一個嚴謹且完整的整體,環環相扣,又精巧合理。
四、結語
曹禺《雷雨》的戲劇語言充滿著趣味,它能抓住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經,不斷撩撥你的心弦。語言擁有如此魔力,除了曹禺具有深厚的文學素養以外,更重要的是他情感的流露,賦予《雷雨》以靈魂。他的戲劇語言源于對生活的敏銳洞察,同時也反映出了人靈魂深處的掙扎。通過這些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情感洶涌下不乏理性思考、朦朧魅惑中盡顯犀利、明暗對比鮮明的戲劇藝術語言,塑造出一個個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同時,也讓讀者感受到朦朧魅惑的語言魔力,給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注釋:
①曹禺.《曹禺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01.第182頁.
②曹禺.《曹禺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01.第118頁.
③曹禺.《曹禺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01.第169頁.
④劉子凌.《話劇與社會——20世紀30年代中國話劇文獻史料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3.第233頁.
⑤《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⑥曹禺.《曹禺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01,第184頁.
⑦曹禺.《曹禺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01,第71頁.
⑧錢理群.《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第21頁.
⑨曹禺.《曹禺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01,第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