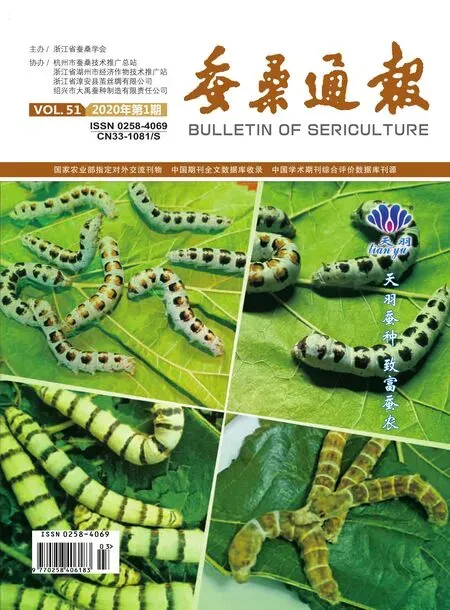湖州桑基魚塘系統“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能值分析*
楊 眈,呂凱倫,王皓琪,周浩瀾,吳宇航,金航峰*,金佩華,2,黃凌霞
(1.浙江農林大學 動物科技學院 動物醫學院,浙江 杭州 311300;2.湖州師范學院,浙江 湖州 313000; 3.浙江大學 動物科學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桑基魚塘是遺存于我國南方太湖流域和珠江流域蠶區的一種傳統的循環農業生態系統,并在國際上享譽盛名。上世紀90年代,聯合國糧農組織曾將它盛贊為“世間少有美景、良性循環典范”[1]。浙江省湖州市桑基魚塘系統現存面積1.40×108m2,其中包括4×107m2桑地和1×108m2魚塘。該系統相對完整地保留了傳統桑基魚塘系統“桑—蠶—魚”循環共生的生產模式,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2017年,聯合國糧農組織正式將其確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作為循環農業生態系統的典范,桑基魚塘系統除提供桑葉、桑果、蠶繭和魚等動植物產品外,還具有保持土壤、調節氣候、涵養水源和觀光旅游等多方面的價值,在保護湖州地區生態環境和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王靜禹等[3]對湖州桑基魚塘系統的各項生態服務功能的價值進行了貨幣化計算,發現在超過100億的總體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中,休閑旅游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遠遠高于提供產品的價值。這說明桑基魚塘系統需要以一個生態整體的形式存在,才能為社會提供更高的服務價值。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傳統農業的生產模式也在不斷變化。桑基魚塘系統中,蠶業生產效益開始低于水產效益,“重養魚、輕養蠶”的生產觀念逐漸形成并占據主導地位,傳統“桑—蠶—魚”生產模式的整體性遭受破壞,桑基魚塘面積逐年下降,嚴重影響地方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發展[4]。同時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該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工作面臨的另一大難題就是農村地區普遍缺乏勞動力。近年來,家庭農場模式的出現和推廣,使得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兼業、副業農戶轉變為專業農戶,這為做好該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創新發展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5]。
湖州市南潯云豪家庭農場位于湖州桑基魚塘系統核心保護區內,是一家以桑基魚塘為主體,實行“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生產模式的家庭農場。“跑道養魚”是指跑道養魚技術,是一種集成了循環流水養殖、集中排污和生物凈水等技術的生產模式,與傳統水產養殖方法相比,具有更高的工業化、智能化和生態化水平[6];“機械化養蠶”包括小蠶共育、機械伐桑和大蠶立體化飼養等環節,可以有效減少蠶業生產對勞動力資源的需求[7]。為了客觀評價“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的推廣價值,我們對該模式的生態性和經濟性開展研究。
上世紀80年代,美國生態學家Odum H.T.提出了能值理論,并逐漸發展稱為評價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重要方法。該理論以太陽能值為標準,將生態系統中的所有能量和資源進行換算,定量分析各種自然資源和人類經濟投入資源的價值,從而實現對系統可持續性的客觀評價[8]。能值分析在國家[9]、區域[10]和地方[11]生態系統的應用十分廣泛,同時也適用于農業生態系統的研究。對于種養結合的復合生態養殖系統,朱冰瑩等[12]對“秸稈—羊—田”循環系統進行了能值評估,結果表明,系統終端產品的能值利用效率得到了顯著提高,同時緩解了部分環境壓力,但是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有所降低;高承芳等[13]利用能值理論對馬尾松低效林林下種草養雞的種養結合模式進行了評價,結果表明該模式的產出效益明顯大于傳統模式,經濟活力更強,環境負載更低,有顯著的推廣價值。而對于桑基魚塘系統,國內僅有劉少慧等[14]曾用能值理論對桑基—蠶—魚塘的傳統經營模式進行了可持續性評估,認為由于基塘比例的嚴重失調導致傳統桑基魚塘系統穩定性較差,并提出了適應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桑基—蠶—魚塘—大球蓋菇和油基—魚塘—湖羊兩種新型模式。
本文利用能值理論對南潯云豪家庭農場的“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生產模式進行能值的統計和分析,同時與傳統桑基魚塘生態系統的能值指標進行比較,評價該模式的生態性和經濟性,并提出相關發展建議。
1 研究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文以湖州市南潯云豪家庭農場為研究對象,該農場位于東經120.12 °北緯30.71 °附近[3],包括桑園子系統、養蠶子系統和養魚子系統。其中桑園子系統中有桑園面積48000 m2,桑樹品種為農桑14和大十,主要用于生產養蠶所需的桑葉;養蠶子系統包括小蠶共育室和立體化養蠶設備,建設費用為59萬元;養魚子系統中有魚塘面積52000 m2,其中包含3條由水泥鑄成的長25 m、寬5 m、深2.5m深的長形渠道,實現了“跑道養魚、池塘養水”,渠內主要飼養品種為草魚,系統建設費用為38萬元。
1.2 研究方法
根據能值分析理論,可以將系統輸入資源分為可再生當地環境資源(renewable local environmental resources,RE)、不可再生當地環境資源(non-renewable local environmental resources,NE)、可再生投入有機能源(renewable purchased organic energy,RO)和不可再生工業輔助能源(non-renewable purchased industrial auxiliary energy,NI)[8]。參照劉少慧[14]的研究方法,在“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中,可再生當地環境資源主要是雨水化學能;不可再生當地環境資源主要是表土損失能;可再生投入有機能源包括養蠶子系統中的蠶卵、養魚子系統中的魚苗,以及系統整體的電力、勞動力和機械設備租金;不可再生工業輔助能源包括桑園子系統中的復合肥和農藥、養蠶子系統中的蠶藥、養魚子系統中的飼料和魚藥,以及系統整體的基建折舊。輸出產品主要是蠶繭和鮮魚。根據以上分類,繪制“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能值流動圖,如圖1所示。
1.3 數據采集
于2019年3月對南潯云豪家庭農場“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生產模式進行詳細調研,調研內容包括:管理模式、養殖規模、基建費用、電力支出、人工費用,以及購買蠶卵蠶藥、農藥化肥、魚苗魚藥等費用。參照孟祥海等[15]的計算方法,將系統中的基建和設備投入按照15 a經營期進行分攤。同時根據 Odum[16]和藍盛芳[17]提供的數據,對于貨幣值統計的項目,直接由貨幣能值轉換系數9.86×1012Sej/$計算得到能值;對于非貨幣值統計的項目,需要先根據能量折算系數計算得到該項目的能量值,再經能值轉換系數計算得到對應的能值。其中雨水化學能和表土損失能的計算方法參考喻鋒等[18]的方法,具體如下:
雨水化學能=土地面積×年降雨量×2.82×106。由《2018年湖州市水資源公報》中得知該地區2018年度降雨量為1681.3 mm。因此,雨水化學能=(48000-52000)×1.6813×2.82×106=4.74×1011J。
表土損失能=耕地面積×3.18×106,其中耕地面積即系統中桑園面積48000 m2,因此,表土損失能=48000×3.18×106=1.53×1011J。
2 結果與分析
2.1 能值輸入與輸出結構
“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各項目的能值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該系統的總輸入能值為1.10×1018Sej。其中可再生當地環境資源RE能值為7.30×1015Sej,占比為0.66%,主要是環境資源中的雨水化學能;不可再生當地環境資源NE能值為9.72×1015Sej,占比為0.88%,主要是環境資源中的表土損失能;可再生投入有機能源RO能值為7.47×1017Sej,占比為67.91%,主要為勞動力資源的能值(占系統總輸入能值的44.82%);不可再生工業輔助能源NI能值為3.41×1017Sej,占比為31%,主要為魚塘子系統中飼料的能值(占系統總輸入能值的19.18%)。總輸出能值Y為3.45×1018Sej,其中蠶繭的能值輸出為1.59×1018Sej,占比為46.09%;魚產品的能值輸出為1.86×1018Sej,占比為53.91%,兩者比較接近。
2.2 能值評價指標分析
根據 Odum[16]和藍盛芳[17]的論述,本文選用能值投入率(emergy investment ratio,EIR)、能值收益率(emergyyield ratio,EYR)、環境負荷率(environmental loading ratio,ELR)和能值自給率(emergy self-sufficiency ratio,ESR)4個指標對“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進行能值評估,并與劉少慧[14]對傳統桑基魚塘系統的評估結果進行比較,計算公式和結果如表2所示。
2.2.1 能值投入率
當系統運行主要依靠人類投入資源,對環境的依賴程度較低時,能值投入率的值較大。從表2可知,“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的能值投入率為63.92,是傳統桑基魚塘系統的6.96倍。這主要是因為與傳統桑基魚塘系統相比,“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中包含小蠶共育、立體化養蠶和跑道養魚等項目,工業化和集約化水平較高,生產過程中受溫度變化、自然災害等環境因素的影響較小。目前跑道養魚和小蠶共育的生產技術相對比較成熟,可以通過提高桑園管理過程中的科技化水平,改進立體化養蠶的自動化水平,來進一步提高系統的能值投入率。
2.2.2 能值收益率
當系統具有較高的生產能力和經濟效益時,能值收益率的值較大。從表2可知,“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的能值收益率為3.17,比傳統桑基魚塘系統高53.14%。考慮到傳統桑基魚塘系統幾乎沒有基礎建設費用,而“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在基建投資較大的前提下,依然收獲了更高的經濟效益,說明該模式具有較好的經濟性。
2.2.3 環境負荷率
系統在運行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大量廢棄物,給環境帶來較大的壓力時,環境負荷率的值較大。從表2可知,“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的環境負載率為0.46,比傳統桑基魚塘系統低28.12%。這可能是因為在傳統桑基魚塘系統的養魚子系統中,容易發生塘泥淤積、殘餌腐爛和藥物污染等問題,可能會對當地的生態環境特別是水質造成破壞。而在“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中,養魚子系統產生的廢棄物被集中收集和處理,降低了環境壓力。根據Cavalett Otávio等人[19]的研究,系統環境負荷率小于2時,在生產過程中不會對環境造成明顯的壓力。所以“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具有較好的生態性,而傳統桑基魚塘系統也遠優于環境負荷率為5.88的單一魚塘養殖系統[14]。
2.2.4 能值自給率
當系統內部資源循環利用程度較低時,能值自給率的值較小。從表2可知,“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的能值自給率為0.02,比傳統桑基魚塘系統低77.78%。主要原因是傳統桑基魚塘系統中,桑葉用于喂蠶,蠶沙和桑葉殘渣用于喂魚,塘底淤泥一部分用于肥桑,系統內部資源得到了充分的循環利用,可以減少從市場購入桑園復合肥、養魚飼料等生產資料。而“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的桑園子系統中,養魚產生的排泄物及吃剩的餌料會用作桑樹生長的肥料,但養魚子系統的飼料等生產資料幾乎全部由市場購入,系統整體購入的市場資料相較于傳統桑基魚塘系統更多。說明與傳統桑基魚塘系統相比,“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對內部可利用資源的開發比較不足。
3 結論
本文以2018年云豪家庭農場的運營數據為標準,運用Odum H.T.的能值理論原理和方法,定量計算了反映“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生態性和經濟性的能值指標。結果顯示:該系統的能值投入率(EIR)為63.92,比傳統桑基魚塘系統高5.96倍,科技水平更高,運行過程受環境影響更小;能值產出率(EYR)為3.17,略高于傳統桑基魚塘系統,經濟效益優勢不明顯;能值自給率(ESR)為0.02,低于傳統桑基魚塘系統,系統內部資源的利用水平較差;環境負載率(ELR)為0.46,低于傳統桑基魚塘系統,對環境的保護效果更好。這些指標表明,“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是典型的生態農業生產新模式,具有顯著的推廣價值。
4 討論
從系統內資源利用配比來看,“機械化養蠶—跑道養魚”模式的機械化養蠶子系統中,目前小蠶共育室提供的小蠶和桑園提供的桑葉數量過剩,可以適當增加立體化養蠶設備;跑道養魚子系統中,目前水塘面積能承擔更多的生物凈化工作,可以適當增加養魚跑道。蠶繭和魚產品的生產技術相對成熟,生產規模的擴大能夠顯著提高經濟收入。
從系統結構來看,根據劉少慧[14]的研究結果,通過引入大球蓋菇子系統,充分利用農作物的副產品,形成桑—蠶—魚—大球菇模式,在系統能值投入基本不變的前提下,能值總產出比桑基—蠶—魚塘模式顯著提高。可以在原系統中養蠶子系統和養魚子系統的基礎上,適當增加其他子系統:如果桑子系統,通過合理密植葉桑來增加果桑種植面積,配套桑椹鮮果的加工設備,生產桑果汁、桑果酒等產品,延長產業鏈;食用菌子系統,利用桑園廢棄物桑枝進行食用菌栽培,實現系統資源的充分開發;家禽養殖子系統,利用桑園的土地和剩余的桑葉、桑椹進行桑園養雞,糞便可以增加桑園土壤有機質含量。目前云豪家庭農場已經開拓多種渠道對桑樹資源進行綜合利用,但是產能有限,輸出產品的能值相對較低,需要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才能增加系統結構的穩定性,同時提高整體經濟效益,在市場中獲得更強的生存和競爭能力。
從技術集成水平來看,將物聯網技術應用于跑道養魚生產模式中,可以實現各項水質指標的實時監控和遠程調節,可節約大量人力和物力;機械化養蠶生產模式是對傳統養蠶技術的改革和創新,實現了養蠶過程的半自動化,但是系統中勞動力資源的能值占比依然過高(占總輸入能值的44.82%),可以將物聯網技術結合溫室大棚應用于桑園的種植管理中,實現溫濕度的實時監控、水肥一體化的遠程控制、桑樹病蟲害的快速診斷等功能,有利于進一步減少勞動力,節約成本。
從系統生態服務價值來看,根據王靜禹等[3]的研究結果,桑基魚塘系統每年的休閑旅游價值為82.92億元,占總生態服務價值的77.50%,說明可以結合養蠶科普、果桑采摘、魚塘垂釣、新農村建設等內容,對該系統的休閑旅游價值進行深度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