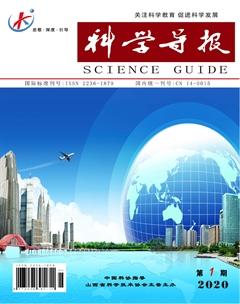云南少數民族風俗
竇澤杰
(一)摩梭走婚習俗的概況
我國的摩梭人作為一種民族下的獨立人種而存在,其在少數民族地區稱納日人,在我國其主要分布于四川與云南兩省交界的瀘沽湖地區。云南的摩梭人屬主要居住于云南北部,屬于納西族,走婚習俗是摩梭人特有的一種事實婚姻狀態。
納西族摩梭人的婚姻形式比較復雜,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正常的婚姻關系,二是“阿肖同居”,三是“阿肖婚”。最為典型的是“阿肖婚”。這里所說的“阿肖婚”意思是“共宿的朋友”的意思。當地的摩梭人把這個形式稱之為“走婚”,摩梭人一般在十九周歲以后,就會開始進行“走婚”,等到女方有了孩子后,便可以正式走婚了。傳統的走婚表現在摩梭男子主動搶女方身上的一件東西,若摩梭女子明確表示愿意接受,這便是流露出相愛之情,這就能說明彼此已經接受對方成為自己的“阿夏”。隨后,摩梭族的男子便開始走訪女子,在走訪女子時必須帶上先前找好的媒人或帶上關系較親密的朋友到女方家中。女方家中會提前備好酒菜,盛情款待男方。同時女方家長會通知其本村的親族,表示自己的女兒已經有了“阿夏”。到入睡時,由女方母親或姊妹將男子送到女子的花房。同時,摩梭男子在頭三次走訪女子時都要回避女子的舅舅、兄弟等。總而言之,這種民族婚姻可以總結為男不娶、女不嫁,男女雙方不進行家庭的實質性組合,而是摩梭男子到女子家中居住,天亮后又回到自己家中,所生的子女由女方撫養,雙方除這種關系外并沒有經濟上的聯系,也不要承擔義務,完全是一種“母系婚姻”。但這種走婚習俗并不是隨意性的,男女雙方從走婚開始就有著對應的義務,走婚的同時是絕對不允許走婚男女與多人同時保持走婚,一旦違反這一原則,便會受到民族內部的譴責。
摩梭人的這種走婚習俗,其最初的目的無非在于保證摩梭人的繁衍生息、理清兩性倫理。同時,摩梭人通過這種習俗達到了理順家庭私有財產關系和穩定社會生活秩序的目的。在這種民族狀況下的走婚習俗中,作為女方的家族功能凸顯出來。走婚的男子建立婚姻關系后,可以對其子女不承擔任何的責任,他們的子女生活完全依托于女方的家庭。女方家庭承擔了家庭中的子女撫養的全部責任。
(二)走婚習俗的法律沖突問題
依照納西族摩梭人的走婚習俗,雙方不存在形式上的婚姻,走婚制中婚姻和財產繼承的內容幾乎不涉及國家的婚姻法和繼承法的實質內容,它有自己的一套規則來約束摩梭人的相關行為,這套內容沒有得到國家的認可,沒有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在婚姻方面體現了極大的自由,財產方面也毫無爭議的指出了屬母系家庭所有。一般而言,其由女方家庭單獨承擔子女撫養義務,與男方并無撫養上的爭議,同樣,在女方家庭內成長的子女對男方(父親)也無相應的贍養義務。同時子女對男方的財產也無相應的繼承權。
這樣的民族習俗很顯然與會讓我們聯系到民法、婚姻法和繼承法等一些具體的法律規定,很顯然,走婚的習俗與實體法的規定是相沖突的,如在司法實務中法官遇見諸如此類的問題,則很難以實體法規定判斷其事實,更難以作出判決,這就需要法官重視民族習俗這一非正式法源。
(三)走婚習俗的司法適用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納西族的走婚習俗是在國家法之外維持的,其“走婚式”的婚姻關系也不是依靠國家強制力來管制的。因而可以將其歸于民族習慣法范疇之內,然而我們所說的民族習慣法,其又不屬于國家制定法,并不能作為法官司法審判的依據。從外國的經驗來看,大多數的民族習慣法也都是通過法官自由裁量,由個案審判法官根據相關民族習慣法與現行法是否沖突進行判斷。可以說該種實現途徑就是通過法官來適用法律的一種自由裁量權,特別是在現行法律存在漏洞或不足時,讓民族習慣法基于其原生性和傳統性等特征自然的作為司法審判的評價規范。但是,從基本分類而言,民族習慣法和國家法確是直接對立的,國家法屬于正式法源,可直接由法官將其作為司法審判的評價規范,而民族習慣法是非正式法源,只能借助于法官在訴訟中享有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適用,將其間接的作為司法審判的依據。概括來說,民族習慣法并不是國家制定的成文實體法,其進入司法審判必然要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
摩梭人的走婚習俗屬于民族習慣的一種,但這種習俗卻與婚姻家庭繼承法等實體法規定相左,在此情況之下,法官完全可以依據其掌握的法理進行基本判斷和事件調查,通過調查可以看出走婚習俗由來已久,且已經成為該地區普遍遵循的一種行為習慣。其能傳承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應屬于少數民族無害的習俗,我國憲法規定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因而法官可以據此進行說理,將該非正式法源引入裁判之中,使判決結果實現一種區域內的公正。當然法官也可通過報請程序,將此類案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予以確認抑或是充分利用少數民族地區立法權單獨進行實體性立法的方式解決,但這些程序僅限于事后,對紛繁復雜的司法實踐仍有賴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