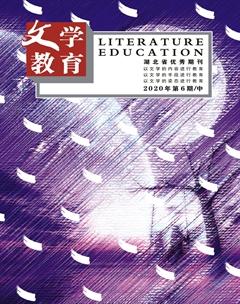新寫實小說研究:以《鐘山》為中心
內容摘要:一個文學實踐成為一種話語實踐,其發生時的起源往往會因而被遮蔽,新寫實小說也不例外。盡管,眾多當代文學研究普遍都指出《鐘山》雜志是新寫實小說的發源地,但對這段歷史的敘述存在著被簡單化、本質化的傾向,對其從發源到消亡的全過程,缺乏必要的探究。因而,本文意在通過《鐘山》(1988-1991)對新寫實小說倡導、組織和策劃的全過程,厘清該思潮內部紛繁蕪雜的文學現象,探究歷史祛魅后,新寫實小說在當時文學場域內產生轟動效應的內在動因,并將《鐘山》對新寫實小說的成功策劃作為切入點,探究文學期刊對文學生產的巨大影響力。
關鍵詞:新寫實小說 《鐘山》 蕪雜 內在動因 影響
一
新寫實小說是先鋒小說后出現的一種新的創作傾向,經由《鐘山》宣傳策劃,在當時沉寂的文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從文學史的角度而言,新寫實小說不但在當時寂靜的文壇引起了轟動,而且其創作理念的影響延續至今:“‘寫生存本相或者‘特別注重現實生活原生態的還原的‘寫實主義,在新世紀也獲得了切實的內涵,有兩個關鍵詞是與之密切相關的,一個是‘底層。另一個是‘日常生活。”[1]298因而,研究新寫實小說,具有現實與歷史的雙重意義。程光煒等學者提出的“重返八十年代”,無疑更是將八十年代的文學實踐重新納入研究者的研究視野,成為文學研究的熱點。新寫實小說作為八十年代中后期的重要文學思潮,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語境下自然又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以《鐘山》雜志作為研究的中心,有利于重返文學現場,厘清新寫實小說從發生到衰微的動態發展過程。
《鐘山》初步擬定籌辦“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專欄的構想,產生于1988年3、4月間,編輯部徐兆淮、范小天和作家周梅森的一次偶發性討論。其后,《鐘山》編輯部為了將這一設想付諸實踐并取得較好效果,做了大量的組織與宣傳工作:“在文藝界廣泛征求意見,并作適當思想發動與組織發動。”[2]247編輯部徐兆淮和范小天于1988年7月先后拜訪了作家、評論家、報刊編輯、文化界和新聞界人士,為“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專欄的順利開展打下了堅定的基礎,獲得了廣泛的支持。1988年10月,《文學評論》編輯部與《鐘山》編輯部聯合召開了“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此次研討會涉及到文壇上相繼出現的一批“新寫實主義”作品,引發了與會者的討論。1988年第6期,《鐘山》刊登一則文訊,表明將于1989年第1期舉辦“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從最初的構想到最終刊發文訊,前后不過7、8個月,但卻獲得了廣泛的響應。由此可見,《鐘山》前期的宣傳策略無疑是成功的:研討會的舉辦,成功地將這些具有新質的文學作品納入評論家的評論視野;“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欄目和評獎活動,調動了作家的創作積極性;同時,以“新寫實”命名此次文學活動,使得讀者在先鋒小說消解意義、打破常規閱讀習慣后,看到了小說向現實主義回歸的傾向,獲得了閱讀興趣。新寫實小說在期刊雜志、評論家、作家、讀者的共同推動下,成為轟動一時的文學創作和評論的潮流,并在文學史上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從整體進程來看,《鐘山》并未如期舉辦刊發新寫實小說作品(1988年在文訊中表明“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將于1989年第1期舉辦)。1989年第1期,僅刊發了1988年10月召開的研討會簡記,1989年第2期,刊發由丁帆、王干等六位學者的觀點組成的《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筆談》,直到1989年第3期,《鐘山》才首次開辟“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專欄。雖然《鐘山》把握時機,及時總結文壇創作動向,并搶先號召、組織、命名這一潮流,但是從構想到實施,時間略為倉促。因而,《鐘山》無法如約刊發新寫實作品也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鐘山》在未有充分稿源準備的情況下,倉促舉辦“新寫實小說大聯展”,背后有其深層原因。自1984年頒發《國務院關于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期刊無法獲得政府撥款,再加之商品經濟的沖擊、大眾文化的盛行,純文學期刊的發行量驟減,這使得本就艱難的文學期刊直接面臨生存危機。一些文學期刊不得不刊登廣告謀求期刊的生存,《鐘山》雜志顯然也在其中。《鐘山》先后刊登過雙洋酒廠、南京裝飾材料廠、電子人體增高器、丹陽市染料化工廠等廣告,有時會將廣告巧妙地嵌入在文學作品之中,如在1989年第5期的報告文學一欄中發表《醉猿的后裔——來自雙洋酒廠的報告》為雙洋酒廠宣傳,在1989年第1期散文《小鎮秋色》為丹陽市染料化工廠宣傳等。這些都彰顯了《鐘山》謀求期刊生存的努力。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鐘山》會在準備不夠充分的情況下,依然將“新寫實小說大聯展”的時間定于1989年第1期,因為此次策劃若取得成功,無疑是一次絕佳的宣傳機會,既能夠提升其在文學期刊中的地位,同時也能夠吸引讀者、增加銷量,謀求更多的發展機會。
二
《鐘山》自1988年第3期開創“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專欄到1991年新寫實小說落潮,共刊登新寫實作品30篇,評論性及理論討論文章15篇。通過細讀刊發的文學作品和相關文章。不難發現這一思潮內部的蕪雜。
在《鐘山》“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欄目下刊登的30篇小說中,風格、技法均呈現出一定的差異。以1990年第2期刊登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的五篇獲獎作品為例:趙本夫的《走出藍水河》通過野孩——徐一清——編筐老漢的身份結構了野孩“一出一入”藍水河的人生歷程,充滿了象征和隱喻的意味。朱蘇進的《絕望中誕生》將大量的自然科學語言放置于小說敘述之中,通過孟中天的構想,完成對整個社會歷史的哲學剖析。范小青的《顧氏傳人》表面是講述蘇州城顧氏大家族幾代后人的命運,實則暗含著對人性和歷史的思考。高曉聲的《觸雷》以孩子的視角完成了對文革的敘述與反思。《逍遙頌》相較于其他四篇,則顯示出了明顯的荒誕意味。劉恒以貌似無深意的細節和語言,展現文革背景下一幢封閉教學樓內學生的人性扭曲,意在挖掘人性之惡,寓意深刻。這五篇作品并未聚焦于對現實生活的原生態還原,相反作家們借鑒了先鋒小說的種種技法,力圖讓小說的形式與內容完美融合,增強小說的審美意蘊。其中,《逍遙頌》則更偏向于先鋒小說那種對寫作技巧和人物心理的探索,可讀性較弱。綜合其它刊登于“新寫實小說大聯展”下的小說,不難發現《鐘山》刊登的新寫實小說更像是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的“中間物”。這些作品與后期被公認為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的《煩惱人生》《一地雞毛》等相比,更為關注小說技法,減少了對瑣碎現實的描寫。除此之外,被收錄于“女作家小輯”的池莉的《太陽出世》,在其后的文學研究中,往往被歸于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之中。這顯示出《鐘山》在組稿過程中,并未對新寫實小說的創作特征有一個完整而清晰的概念界定。因而,《鐘山》雜志“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欄目下的小說,從一開始就呈現出迥異的創作風格。
對新寫實小說創作傾向的模糊界定,是貫穿此次思潮宣傳策劃始終的。在《鐘山》的推動下,新寫實小說已然成為文壇上爭論不休的熱點話題,但從發軔到落潮,“新寫實”的概念、特征等相關問題,始終是“眾聲喧嘩”。在1988年9月召開的研討會上,評論家對文壇上出現的“新寫實主義”作品的評價就呈現出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這是現實主義的回歸和復興,一種截然相反,這是對以往現實主義的反動和叛逆。”[3]不論是在當時《鐘山》召開的研討會上,抑或是在之后刊登的相關的理論探討文章中,都顯示出對“新寫實”這一創作傾向的不確定性。重返當時的文學現場,當時的主要觀點主要歸納為以下三種:一是認為新寫實小說是自然主義的回歸,二是認為新寫實小說是現實主義的回歸,三是新寫實小說是融合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創作技巧的產物。事實上,從當時的相關作品和評論文章來看,新寫實小說具有豐富的審美意蘊,并不像后來一部分文學史所敘述的那樣“在追求生活表現的原生態和‘零度情感的同時,敘述的過于沉悶、單調也導致了小說藝術魅力的喪失。”[4]276新寫實小說在當時呈現出“多重面孔”,即便是在《鐘山》這一場域內,也呈現出不同的美學品格。
在《鐘山》1989—1991年刊登的相關文章中,既有對這一思潮的肯定、鼓勵,也有對這一思潮的否定和懷疑。肯定者在剖析文壇、新寫實小說的創作傾向后,往往對新寫實小說的前景寄托了美好的祝愿。而懷疑者則針對其定義的模糊等方面,給予溫和的提醒并對其前景表達隱憂。在新寫實小說筆談中,黃毓璜就指出這種具有不確定性的倡導有其危險所在:“其一,‘新寫實多少滲透了由現狀而激發的互補意識,而互補意識到了庸人心理上,最容易孵化出絞殺個性的調和與失落自我的皈依……其二,已經出現的、可以歸入‘新寫實范疇的小說,創造精神和表現手段上多具備靈動的開放性和廣泛的包容性。它并不排斥而且經常吸收、兼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及現代主義的諸多因素,而從此類作品概括出這樣一個共名反過來律之創作時,就有可能因為名稱和概念自身超范疇的涵蓋,導致其不確定指向亦即其自身意義的消亡。”[5]從《鐘山》刊登評論的策略來看,《鐘山》的編輯不僅刊登贊同的觀點,也會選用一些質疑的觀點。一方面,意在營造出眾聲喧嘩的討論氛圍,彰顯出《鐘山》兼容并蓄的辦刊理念,另一方面,意在通過批評家對這一新的創作傾向的深入思考以及以溫和的質疑,引導新寫實小說創作健康發展的意愿。
三
從《鐘山》推動新寫實小說的整體情況來看,盡管新寫實小說的推動過程顯露出倉促性,且命名爭議大、界定模糊、創作傾向不一,但它能夠獲得評論界的廣泛支持,并使商品經濟沖擊下的文學重新煥發活力,有其深層的歷史原因。首先,當時的文壇經歷了商品經濟和東西文化的雙重撞擊,文壇一時間失去了轟動效應,純文學的讀者數量驟減,這一新創作傾向的出現符合當時文學發展的規律。盡管新寫實小說創作傾向各異,但較之先鋒派小說更具有可讀性,同時呈現出不同于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創作技法。新寫實小說緩和了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的兩力角逐,是具有過渡意義的產物,它吸收了先鋒派文學創作的種種技法融入寫實之中,呈現出獨特的審美品格,為文壇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新寫實小說作為一種新的創作傾向,引起了文學期刊、作家和評論家的關注。在《鐘山》舉辦“新寫實小說大聯展”之前,即有文學刊物和評論者發現這一新的創作傾向:《上海文學》的編者于1987年刊發對池莉的《煩惱人生》的評論,評論家吳秉杰、雷達等對這即將出現的文學傾向作出了評論。待到1988年《鐘山》高舉“新寫實”的大旗,招徠了更多的作家、評論家。從文壇的整體氛圍而言,《鐘山》開辟“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專欄并舉辦評獎活動,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作家創作具有新質的文學作品。對于評論家而言,聚焦這一新的創作傾向,通過討論、界定以及對具體文本的批評賞析,是獲取文壇的話語權的最佳路徑。因而,評論家們更加積極地投入新寫實小說的種種討論之中。最后,新寫實小說轟動效應,離不開《鐘山》雜志的成功策劃。《鐘山》雜志把脈文壇,及時將這一新的創作傾向形成一種號召。盡管其刊登的“新寫實”作品與這一號召并不完全貼切,但卻能夠獲得其他文學期刊的廣泛響應。一時之間,《文藝報》、《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等文學期刊紛紛刊登相關作品、評論,與《鐘山》的推介一起形成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文學場。文學期刊、評論家共同將新寫實小說的影響力擴展到了最大值。新寫實小說的出現與期刊的辦刊策略和制造文壇熱點的想法密切相連,是商業思維進入純文學領域的一個表征:“文學期刊與大眾傳媒對文學思潮發展的‘推波助瀾作用開始顯現,開始由‘幕后走向‘前臺,成為推動文學思潮形成的主導性力量。”[6]129
正如當時在《鐘山》刊發大量“新寫實”相關的評論性文章的王干所言:“‘新寫實的出現,是文學期刊介入當代文學的一次成功范例。”[7]17從《鐘山》雜志的整體發展情況而言,新寫實小說的成功策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策下的生存困境,提升了它的期刊地位。《鐘山》在創作傾向不夠明晰的情況下,以極具開放性、包容性的號召,開啟了此次文學策劃,顯示出期刊自覺的策劃意識。《鐘山》在文訊中表明:此次“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力圖倡導一種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當代意識、歷史意識和哲學意識,又貼近生活關注現實的小說創作傾向。顯然,《鐘山》極具概括力的號召,獲得了普遍的認可,招攬了大批作家、評論家,也吸引了更多的讀者,一舉打響了期刊的知名度。盡管在此之前,當代文學史上也有文學期刊想要發揮對新的文學創作傾向的推動作用,“文化‘尋根成為熱點,《作家》和《上海文學》成為‘尋根文學的幫手……《收獲》《花城》與先鋒作家攜手合作,為本土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8]但是,不論是從這些期刊媒介所造成的影響力還是文學熱度,都遠不及《鐘山》對新寫實小說的宣傳策劃。當這段文學史成為過去的時候,再次提及“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文學思潮時,很難直接指出哪個期刊雜志介入并推動它們的發展。然而,文學史已經將新寫實小說與《鐘山》緊密纏繞成為一個共同體,提及新寫實小說,就不可避免地提及其發生的文學場域——《鐘山》雜志。更為值得一提的是,《鐘山》成功推動新寫實小說成為轟動一時的創作潮流,使得越來越多的文學期刊積極介入文學場域,發揮大眾傳媒對文學思潮的推動作用。
《鐘山》于1991年第3期后停止對“新寫實”小說的推動,昭示著“新寫實”思潮的落潮,但并不意味著這一創作傾向的消亡。“新寫實”所涵蓋的豐富的創作特征,在其后的文學創作中仍有所體現:如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寫實基礎上融入新的創作技法、對哲學意識的顯現等。《鐘山》對“新寫實”推動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為當時的文壇增添了活力,也對以后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期刊的發展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1]王慶生,王又平主編.中國當代文學 上 第2版[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徐兆淮著.作家 編輯 讀者 編余叢談[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3]李兆忠.旋轉的文壇——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簡記[J].鐘山.1989,(1):181-184.
[4]朱棟霖,龍泉明,朱曉進著.中國現代文學史 1949-2000[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5]黃毓璜.虛實相生與總體意蘊[J].鐘山.1990,(1).
[6]張永清主編.新時期文學思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7]王干著.邊緣與曖昧[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8]曹瑞杰,王青.《鍾山》雜志四十年發展變遷研究[J].出版發行研究.2019,(3):54-58,53.
[9]《鐘山》:1988-1991年.
(作者介紹:李慧,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