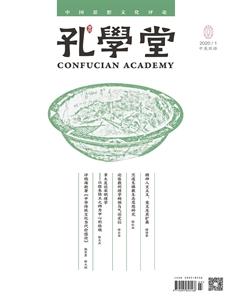奉天法古與西漢儒生的更化善治運動
姜喜任
摘要:西漢初年,以賈誼、董仲舒為代表的儒生通過批判秦政與法家,掀起了一場以“奉天而法古”為號召的更化善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根據學術取向的不同,可以把當時的儒生分為兩派:一是好言災異的奉天派,借助災異占驗探究天人之際神秘而又可畏的感應關系,本天道以立人道,批判君主專制,限制君權;一是好言禮制的法古派,通過古今對比揭示王朝更迭、治亂興衰的歷史規律,以古禮準今制,確立禮教先行、刑罰為輔的治理模式,抨擊時弊,移風易俗。西漢末,王莽利用奉天派的災異論取代劉氏政權,推行新政,將法古派的禮制論付諸政治實踐,從而將西漢儒生的更化善治運動推向高潮。由于王莽一朝對災異論的濫用以及對禮制論的拘泥不化,在導致新朝覆滅的同時也宣告了復古更化運動的失敗,但這場運動為此后中國的政治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關鍵詞:奉天法古? 西漢儒生? 更化善治? 災異? 禮制
秦漢之際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段非常關鍵的時期,正是在這段歷史時期,中國結束了分封制,建立了郡縣制,從此奠定了兩千多年大一統封建帝制的政治社會治理模式,這就是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周秦之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訴求之下,對于周秦之變以及秦漢之際政治與思想的深入研究顯得尤為必要,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言:“漢以后二千余年之局,實自漢人開之。凡論社會、政治與文化及學術者,皆不可不著重漢代也。”結合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梳理《史記》《漢書》,可以發現以賈誼、董仲舒等為代表的西漢儒生在“奉天法古”的大旗之下,通過反思秦政、批判漢制,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更化善治運動。因此,對于這一歷史現象的深入研究,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揭示秦漢之際政治社會治理的些許真相,為當前的國家社會治理提供有益啟示。
一、過秦與正韓:更化善治的起因 [見英文版第77頁,下同]
秦朝興亡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奇特而又顯著的現象,漢承秦制而起,整個漢代的儒家學者都熱衷于對秦制以及作為秦制指導思想的法家學說進行反思和批判。正如單純先生所說:“因為‘焚書坑儒引起的‘秦火之痛,儒家的批判在制度層面直接指向秦帝國,是所謂‘過秦,即秦帝國作為一種制度上的過失;在思想層面卻指向秦帝國的思想基礎——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是所謂‘正韓,即糾正法家的思想謬誤。”過秦與正韓成為漢儒批判現實政治、構建宏大王道理想的邏輯起點,也是引發西漢儒生更化善治運動的最初誘因。
漢初,最先反思秦亡教訓的是陸賈。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在陸賈看來,秦亡的關鍵在于沒有根據取、守之間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施政方略,而湯、武所建立的商、周之所以國運長久,原因就在于他們“逆取而以順守之”,即取之以暴力而守之以仁義。秦以嚴刑峻法、獎勵耕戰迅速強大起來,但統一天下之后仍然“任刑法不變”,所以難免滅國之運。有鑒于秦亡的教訓,漢雖以馬上得天下,但還須以儒家《詩》《書》仁義治天下,文武并用方是長久之道。實際上,陸賈的觀點其來有自,《商君書·開塞》曰:“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商鞅反對法古修今,主張因時制宜,武王逆取天下而以順守之,即取之以暴力守之以仁義,所以能夠長久。秦雖以法家作為指導思想,卻忽視了商君“取之以力,持之以義”的訓誡,其亡國自不待言。
陸賈之后,批判秦政與法家的繼起者是賈誼。賈誼《過秦論》曰:“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曰:“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顯然,這種觀點與上述陸賈的觀點相一致,都著眼于攻守之間的政策調整,并在過秦的同時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漢承秦制”,為更化善治埋下了伏筆。據《漢書·賈誼傳》載,賈誼在上書文帝的《治安策》中對秦政及法家的流毒進行了全面深刻的清算與抨擊。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并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余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商鞅變法,以法的強制性與功效性取代仁義禮樂等倫理價值,視百姓為耕戰的工具,驅之以刑罰而誘之以爵祿,將人趨利避害的獸性完全激發出來,因而導致社會風俗的敗壞,尤其表現在對宗法家庭制度的破壞。張金光先生指出:“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對家庭制度嚴厲推行分戶析居的改革政策,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按照《儀禮·喪服傳》所說,在宗法制度下,原是‘昆弟之義無分的。秦政府推行最小型家庭政策,強令分析,把家庭單位析到骨肉之間已無可再析的地步為止,這是對宗法制度的徹底否定。”分戶析居的政策對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倫理造成了致命打擊,父子姑婦之間唯利是圖,毫無恩情可言,因而與禽獸無異。賈誼批判的重點在于“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即秦朝風俗敗壞的余毒對漢朝的影響猶在,由此自然導出移風易俗的更化課題,賈誼說:
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奸人并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
秦朝以法家立國,法家工具主義的價值觀對禮義廉恥等社會倫理規范有莫大的殺傷力,從家庭的角度講,“六親殃戮”,親親之情不再;從社會的角度講,“君臣乖亂”,尊尊之等泯滅,儒家所倡導的“尊尊”“親親”的理想社會秩序遭到全面破壞,這也是風俗敗壞的根本原因所在。賈誼認為,漢興至孝文二十余年,“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被暴秦破壞掉的禮義廉恥等社會倫理規范尚未恢復健全,奸人尚存僥幸之心,百姓疑惑不知所從,因而治理國家的當務之急在于“定經制”,顏師古注曰:“經,常也。君為君德,臣為臣道,共為忠信也。”也就是說,確立儒家仁義禮智信等常理常道對社會的價值引領,規范君臣父子等社會家庭秩序,在下可以美俗,在上可以美政,賈誼的這種主張可以說開西漢儒生復古更化之先聲。
經過陸賈、賈誼的思想鋪墊,董仲舒第一次明確提出借更化以求善治的觀點。對于秦政與法家,董仲舒同樣有著激烈的批判,比如他說:“(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并起……”這種批判與陸賈、賈誼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代表了漢代儒生的一般意見。在過秦與正韓的基礎之上,董仲舒對承秦而來的漢政表達了深沉的憂慮與殷切的期望。
董仲舒曰:“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認為,秦政與法家的遺毒余烈對于漢代國家社會治理影響至深,因而他提出通過更化以求善治的主張。所謂更化,即更秦之化,也就是摒棄秦政與法家的工具理性與嚴刑峻法,代之以儒家的價值理性與禮樂教化,“在仲舒之意,乃求以學術文化領導政治,以政治控制經濟,而進企于風化之美,治道之隆。”董仲舒認為,只有更化才能達成善治的目的。漢興至董仲舒時已七十余年,通過陸賈、賈誼等儒生對秦政與法家的不斷反思與批判,董仲舒終于提出更化善治的理念,隨著歷史的演進,這一理念還將被此后的西漢廣大儒生所繼承與踐行。
總之,正如李若暉先生所說:“漢代儒學始于陸賈、賈誼等人的過秦,然而不幸的是,其時國家制度上恰恰是漢承秦制,所以漢儒名為過秦,其實質卻是過漢,于是復古更化便一直是漢儒不懈的追求。”西漢儒生的更化善治運動便在過秦與正韓的呼聲中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二、奉天而法古:更化善治的路徑 [79]
奉天法古這個觀念是董仲舒提出來的,他說:“《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董仲舒認為,通過更化以求善治必須遵循一定的規矩準繩,他根據春秋公羊學提供的規矩準繩推出其就是“奉天而法古”。何謂“奉天而法古”?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春秋》是孔子通過“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表達王道理想的書,書中所記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隱含著治亂興衰的微言大義。(《史記·太史公自傳》)《春秋》所講的治亂興衰之道是被兩百多年的歷史證明有效的,從中也可以驗證天道與人事之間神秘而又可畏的交互關系。因而,所謂“奉天而法古”實際上就是效法《春秋》所褒揚的先王之道進而順應《春秋》所揭示的天意與天道。
董仲舒奉天法古的觀念為西漢儒生的更化善治運動提供了根本遵循,不同學者對這一觀念做了不同向度的發揮,從而建構了西漢一朝更化善治的兩種路徑,即奉天的路徑與法古的路徑。前者重在探求天意,以天意正定人事;后者重在探求古制,以古制規范今制。錢穆先生指出:“時學者可分兩派:一好言災異,一好言禮制。言災異,本之天意。言禮制,揆之民生。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之徒言災異,貢禹、韋玄成、匡衡、翟方進、何武之徒言禮制。”好言災異的儒生所走的就是奉天的路徑,試圖通過災異占驗警誡人主,達到更化善治的目的;好言禮制的儒生所走的就是法古的路徑,希望通過恢復禮制革新漢政,達到更化善治的目的。當然,不論是言災異還是言禮制,不管是奉天還是法古,都不是截然二分的。正如漢武帝策問董仲舒時所說“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天人、古今互文現義,在漢人的頭腦中宇宙意識與歷史意識是交織在一起的,只不過不同學者側重點不同罷了。
漢儒言災異始于董仲舒,《漢書·五行志》曰:“漢興,承秦滅學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仲舒之后,推陰陽言災異在漢代形成一種風氣,一時言災異者蜂起,“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
言災異作為漢儒更秦之化的重要路徑之一,它所指向的現實問題主要是秦政與法家所確立的君主專制政體。清代學者皮錫瑞指出:“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進諫。以為仁義之說,人君之所厭聞,而祥異之占,人君之所敬畏。”秦始皇踐行法家尊君卑臣的集權思想,否定儒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的雙向度倫理,而代之以“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史記·李斯列傳》)的單向度倫理。漢承秦制,權力日益集中到君主手中,并且君主在政治上獨斷專行,不接受任何制約。比如,漢宣帝“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漢武帝任用宰相多人,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后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余盡伏誅云”。為了革除秦弊,限制君權,漢儒言災異主要集中在兩個關鍵點上:
一是倡言天命轉移,不私一姓,糾正人主以天下為自家產業的私心。秦始皇以天下為私有,“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秦二世“專用天下適己”,“愿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史記·李斯列傳》)。漢高祖以天下為自家產業,他曾戲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史記·高帝本紀》)黃宗羲尖銳地指出:“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有鑒于此,西漢儒生借助災異論闡發了天命轉移、不私一姓的觀點。
眭孟根據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柳自生等災異建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翼奉根據孝武園白鶴館災建言:“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京房《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寬饒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劉向上書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天命轉移的觀念早在西周時期就已形成,《詩經·大雅》曰:“天命靡常”,《尚書·皋陶謨》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書·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夏商二代之所以滅亡,原因就在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所以周公總結夏商二代的教訓,提出敬德保民的觀念,通過敬德保民來“祈天永命”。周代天命轉移與敬德保民的思想為儒家所繼承,但是秦朝以法家立國,不信天命,蔑視道德,妄圖以暴力把持天下,時至漢朝其遺毒余烈猶在。所以西漢儒生借助災異論證明天命轉移的有效性,以此警誡人主天命“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讓君主明白“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二是倡言天人感應,認為人主行為失正必然招致災異,只有反躬修德、施行仁政才能消除災異,以此達到限制君權的目的。對于天人相與之際神秘而又可畏的感應關系,漢儒有詳明的闡述,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谷永曰:“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也就是說,災異是上天對人主行為失正的嚴厲譴告,人主只有反躬自省、畏懼敬改才能消除災異,重獲天心。
漢儒言災異的重心并非災異本身,而是人主的行為失正以及補偏救弊的措施。京房后學郎引《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也就是說,完整的災異論建構必須包括四個環節,即“第一環節是人事失正,第二環節是災異現象,第三環節是在對災異現象不采取任何救治措施的情況下將要發生的事件,第四環節是在救治災異現象的情況下所應當采取的措施。”而四個環節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與第四兩個環節,以京房易學災異論為例:
君無仁德,臣懷叛戾,華飾虛舉,薦賢名實不相副,內為蘇秦之行,外似夷齊之行,故致五谷多無實。朝廷無賢,害氣傷穡,不收,國大饑。其救也,選明經,舉茂才,改往修來,退去貪狼,施恩行惠,賞賜勞臣,此災消矣。
法家主張以陰謀權術駕馭臣下,君主對于臣下毫無仁愛之德,臣下對于君主常懷叛逆之心,君臣之間沒有信任只有虛偽,因而導致上下欺瞞、浮華不實的政風。漢承秦制,漢廷君臣之間依然存在“內為蘇秦之行,外似夷齊之行”等表里不一、名不副實的不良風氣,比如汲黯批評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又如公孫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京房認為,漢廷君臣的這種名實不副的行為會導致“五谷多無實”的災異。如果任其發展不做任何反思修正的話,則會導致“國大饑”的災害。為了避免災害發生,必須采取相應的救災措施,那就是“選明經,舉茂才,改往修來,退去貪狼,施恩行惠,賞賜勞臣”。由此可見,在漢儒借更化以求善治的訴求之下,承秦而來的紕政以及補偏救弊的措施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而災異論只不過是為了達成這一訴求而借助的形式。
漢儒言禮制雖始于叔孫通定禮儀,但叔孫通所定之禮儀無非是尊君卑臣之事,漢高祖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叔孫通也因此見譏于齊魯之士。真正闡發禮制精神,倡言以漢禮取代秦法的是賈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李若暉先生指出,賈生所為“是悉草具漢禮,欲以‘悉更秦之法,即草擬一部全面的漢代禮儀制度,試圖完全更改取代秦法”,由此可見,“漢儒最初對于秦漢律令的基本態度及其作為,即徹底廢除秦法,制定一部全面的漢禮取而代之”。賈誼之后,董仲舒提出復古更化的觀念,即效法古之王者以禮樂教化治天下,革除秦政與法家任刑罰不任德教的暴政。但是董仲舒理論的側重點在于據《春秋》公羊學言災異,即在更化善治的問題上,他走的是奉天的路徑,但是他所提出的復古更化理念已然開啟了法古的路徑,為此后的儒生如王吉、貢禹、韋玄成、匡衡、翟方進、何武乃至于劉歆、王莽等所繼承和踐行。
言禮制作為漢儒更秦之化的另一條重要路徑,它所指向的現實問題主要是由秦政與法家確立并沿襲至漢代的鄙棄禮樂教化、惟任嚴刑峻法的治理方式。《漢書·刑法志》:“至于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懸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承秦制,“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漢文帝時,雖然廢除肉刑但實際上卻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漢武帝時,任用酷吏張湯、趙禹等條定法令,以至于“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與暴秦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漢宣帝時路溫舒上書說:“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為了革除秦弊,更新漢制,漢儒言禮制主要涉及兩個層面:
在更化善治運動中,漢儒言災異的理論本旨是批判君主專制、限制君權,倡言“漢歷中衰”也只不過是為了警誡君主反躬修德、延續天命,結果卻為王莽篡漢提供了可乘之機。錢穆曰:“甘忠可、夏賀良之徒方以推運數見誅,而永言又如此,此自元、成以來一時學者意見,鼓蕩蘊積,遂召莽篡。”《漢書·王莽傳》:“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于漢三七九世之后……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于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于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于新室也。”王莽正是利用了漢儒言災異的這股風氣,以天命轉移、去漢與新為借口,在德祥符瑞的掩蓋之下名正言順的篡奪漢政,這與漢初儒生論證劉氏政權合法性的理路如出一轍。
王莽自專漢政以來,遠紹漢初賈誼、董仲舒,近宗元、成貢禹、韋玄成、匡衡、翟方進、何武等,改革漢制,興復古禮,將西漢儒生言禮制一派的倡議統統付諸實踐。譬如,平帝元始三年(3),王莽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此事宣帝時王吉已言之;又奏“立官稷及學官”,此事賈誼、董仲舒已言之。平帝元始五年(5),王莽奏請改易祭祀天地之禮,“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所以正承天順地,復圣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此事匡衡已言之。居攝二年(7),王莽改革幣制,“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并行”;始建國二年(10),又造寶貨五品,此事晁錯、貢禹等人已言之。始建國元年(9),王莽下詔革新井田制度、稅制、禁止買賣奴婢等,此事董仲舒已言之。始建國二年(9),王莽“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此事賈誼、晁錯、董仲舒已言之。天鳳元年(14),王莽改革官制,“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此事何武、翟方進已言之,等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錢穆曰:“莽之創制立法,亦皆遠有端緒,當自元、成以下漢廷諸儒議論意態推跡之。”又曰:“莽朝一切新政莫非其時學風群議所向,莽亦順此潮流,故為一時所推戴耳。”實際上,王莽之所以能夠篡漢成功,除了利用漢儒言災異的風氣之外,關鍵就在于他能順應漢儒言禮制的潮流,信古敢為,扮演了儒生興復古禮的踐行者,因而獲得了當時儒生的一致擁戴,從而在新莽改制之中將西漢儒生的更化善治運動推向高潮。
歷史總是充滿吊詭,王莽大刀闊斧的改制,將漢初以來儒生的更化措施付諸實行,結果卻并沒有達成善治的目的,相反,新朝很快在內憂外患之中走向覆滅,王莽也在絕望中被殺。反思西漢儒生的更化善治運動以及新莽的興衰歷程,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漢儒的災異論在西漢末年的政治活動中被嚴重地濫用。漢儒言災異的本旨是鑒于暴秦與法家所確立的君主專制政體,借助災異天象警誡君主,限制君權。但這一理論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卻逐漸淪為漢廷君臣政治斗爭的手段。譬如,漢元帝時,京房妄圖通過災異占驗斥退弘恭、石顯、五鹿充宗等權佞,結果卻被對方反咬一口,慘遭棄市。漢成帝時,綏和二年(前7)春熒惑守心,天象異常,為應天象,成帝責令丞相翟方進自殺。王莽本身以符命篡漢,當時投機者紛紛制作符命,以為進身之階。譬如,甄豐之子甄尋“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陜,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更可笑的是,梓潼人哀章見莽居攝,即作銅匱,上書包括自己在內的十一人姓名,“皆署官爵,為輔佐”,王莽竟然遵照哀章銅匱上所書的姓名封拜輔臣,其中有一人名王興,是“故城門令史”,另一人名王盛,是賣餅之人。“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流風所及,人人“爭為符命封侯”,以至于不屑此道的人相互戲謔曰:“獨無天帝除書乎?”當時司命陳崇諫言王莽說:“此開奸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于是王莽“遂使尚書大夫趙并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也就是說,宣告私人制作的符命為非法,只有“五威將率所班”,也就是王莽自己授命制作的符命才是合法的。盡管如此,漢儒借以更秦之化的災異論被新莽一朝濫用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迷信虛妄的非理性因素充斥著新莽朝廷,這是王莽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漢儒的禮制論在實行過程中存在嚴重泥古不化、不達時宜的弊病。漢儒言禮制的本旨在于用儒家的禮樂教化取代法家嚴刑峻法的治理方式,用仁義道德引領社會價值,移風易俗,導民向善。事實上,漢宣帝早就尖銳地指出儒家的缺陷所在,他說:“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譬如,漢元帝時,貢禹認為錢幣制度導致奸邪叢生、百姓貧困,因而建議元帝廢除幣制,效法古代以物易物之俗。后來,漢哀帝時又有人上書建議改革幣制,效法古代以龜貝為貨幣的制度,認為可以救民貧苦。由此一事即可見漢儒在興復古禮方面的泥古不化、不達時宜,王莽新政卻將這一弊病發揮到極致。《漢書·王莽傳》:“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制度與現實政治社會治理之間是存在距離的,王莽迷信禮樂制度,錯把制度的象征意義當成實用意義,犯了“制度浪漫主義”的錯誤。所以桓譚《新論》批評王莽說:“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漢武帝曰“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司馬遷曰“通古今之變”。王莽改制可以說是知古而不知今,泥古而不知變,將儒家禮治的空想性與非理性因素發揮到極致,這大概是新朝覆亡的關鍵原因所在,正如錢穆先生所說:“莽拘古紛更,最為致敗之端。”
表面上看,西漢儒生的更化善治運動隨著王莽新朝的覆滅而宣告失敗,但如果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會發現這場歷時兩百年的運動有著偉大的歷史意義。閻步克先生指出:“秦用法術,漢初用黃老,漢武帝、漢宣帝‘霸王道雜之,直到全力貫徹儒術的王莽‘新政,其間各種政治學說此起彼伏,王朝意識形態顯示了大幅度的動蕩搖擺。”正是在這種動蕩搖擺之中,西漢儒生立場鮮明地批判秦政與法家,貶斥黃老之學,高揚儒家禮樂教化的治理方式與仁義道德的價值取向,他們以天道與古制為標準批判社會現實,構建宏大的王道理想,并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與法家融合,最終在東漢時期形成傳統中國以“外儒內法”為特征的政治社會治理模式,影響著此后中國近兩千年的歷史。
(責任編輯:楊翌琳? ?責任校對:羅麗娟)
- 孔學堂的其它文章
- Xu Qi: The Imprint of Thought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Cultural Issues
- Qian Hai: The Modern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Serving Heaven and Emulating the Ancients: Western Han Confucians’Movement to Reform Regulations and Improve Governance
- Early Modern Guangdong Academies and Their Academic Ethos: A Case Study of Zhu Ciqi’s Early Education Experience
- Nationalism and Spirit of Freedom: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Carsun Chang’s New Confucian Thought
- Ming–Qing Ritual-Based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Zhu Xi’s Doctrineof Ritual: The Dimension of Outer Kingliness in Neo-Confuci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