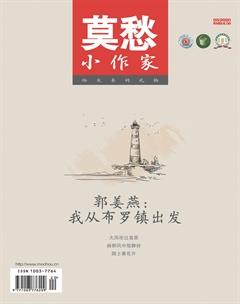《農場疑案》續寫
坐在走廊長椅上的四個人齊齊側頭,看向阿元探長。
柳行看起來酒已醒了大半,只是臉上依然浮著紅暈,“探長,我可以走了吧?今天累了一天,我想快點回去睡覺。”
黃鵬點頭應和。
阿元探長搖搖頭,說道:“現在恐怕還不行,還有一些問題沒弄清。”說完,他向胡強招了招手,“胡師傅,麻煩你帶我到后面轉轉。”
二人先到了辦公室后面柳行的屋子,屋子里暖黃的燈光還亮著,茶幾上歪歪倒倒放著幾個啤酒瓶。從房間的窗戶看出去就是農場中間的路,如果有人經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假如柳行并沒有如他所說的睡著,那么他很有可能在包庇犯人。
此時已經是凌晨三點,路的兩旁間隔幾米才有一盞小燈,在黑夜的映襯下完全沒有白天的生機勃勃。
“你知道農場里的這些人都是什么時候來的嗎?”
胡強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在下巴上摩挲了兩下,緩緩開口:“我是三年前來這里做保安的,那時候柳老板、黃老板和張志都在,只有程斌是一年前才接管橘子園。”
“接管?那之前是有另外的人在管理橘子園嗎?”
“是啊,之前是侯方圓在管理,但是一年前他過世了。”
“因為生病去世的嗎?”
胡強搖了搖頭說:“不,他是晚上喝了酒,走路時不小心從臺階上滑下去摔死的。”
“其實柳老板一開始和場長的關系很好。”胡強繼續說道,“侯老板去世以前,他們三個人經常一起喝酒。只是后來,兩個人的關系忽然就淡了。”
阿元探長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突然想起張志對程斌的評價,問道:“你覺得程斌是個什么樣的人?”
胡強擺了擺手,“我和他不太熟,沒什么共同話題。”
“他和黃場長的關系好像很好。”
“那倒是,他和黃場長經常在房間里,一聊就是一下午。”胡強笑了,“我還懷疑過他是場長的私生子呢。”
阿元探長挑了挑眉。
“不可能啦,廠長的老婆和兒子經常來場里呢。”胡強笑著說。
又走了幾步,大約五十米開外的地方能看到幾棟房子的形狀。
二人先到的是張志的屋子,屋子里很亮堂,還有一個巨大的保險箱。
阿元探長指著保險箱問,“你知道張志都往保險箱里放什么嗎?”
“不清楚,不過應該不是什么值錢貨。張志今年沒賺什么錢,只是裝闊罷了。”
隨即他們轉身向程斌的屋子走去。
“喲,很高端嘛!”程斌的屋子里有好多高科技產品。
“可不是嘛。”胡強咂咂嘴,“他后面那園子里也全是這種高端的東西,除了他,我們都弄不來。”
阿元探長環顧四周,看見還有一扇通往外面的門,“那道門是通向哪里的?”
“那個啊,是到后院的,程斌堅持要一個后院。”
院子不算大,探長走了一圈,站定在一個角落。這里應該是準備播種,土還很新鮮。
這時,突然電話響起,是醫院打來的。
“好,我知道了。謝謝,麻煩你們了。”阿元探長對電話那端的人說。
胡強湊上來,“他們說什么?”
“沒什么重要的。”阿元探長搖了搖頭,“不過黃場長應該沒有生命危險了。”
最后是黃鵬的屋子,一張電視節目表放在茶幾上,看起來黃鵬沒有說謊。
“走吧,我已經清楚了。”
“你知道兇手是誰了?”胡強好奇地問。
阿元探長點點頭,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兩人往辦公室走去。
見到阿元探長回來,四個人先后起身,“現在可以說出兇手是誰了吧?”黃鵬問。
“當然。”阿元探長正了正頭上的帽子,“傷害場長的人是他自己。”
聽到這個說法,四人似乎都驚呆了,七嘴八舌地討論起來。阿元探長靜靜地等待他們安靜下來。
“廁所里的磚頭確實是場長自己放進去的,只不過,他是為了陷害某個人。”
“陷害?”程斌的聲音拔高了些,“陷害誰?”
阿元探長抬了抬眉,“如果黃場長被人傷害,你們第一個想到的是誰?”
“張志?”柳行猶豫著開口。
“沒錯,就是張志。”
“不可能。”胡強反駁,“我看到場長流了好多血,而且他根本不可能自己把磚頭放那么遠。”
“那么晚了,大燈都暗了,況且張志腳受傷了,說是他也沒人相信吧。”柳行說。
“所以,這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探長頓了頓,“胡師傅,還記得我剛才接的電話嗎?”
“記得,你在程斌院子里接的,說場長已經沒有生命危險了。”
“沒錯,醫生同時還告訴了我另一件事情。”阿元探長掃視一遍面前的眾人,看著他們各不相同的表情頓了頓說:“醫生說場長頭上受到了兩次撞擊,較為嚴重的是第二次。頭發里也有兩種不同的磚頭碎屑。除了廁所里發現的磚頭之外,還有一種,剛好在程斌的花園里見過。”
所有人的目光齊齊望向程斌。
程斌的臉上霎時布滿震驚,“你的意思是說,我用磚頭打了場長?你有什么證據嗎?”
阿元探長沒接他的話,目光慢慢轉移,一直移到柳行的臉上停下。
“柳老板,我想你應該看到了什么吧?”
柳行低頭說:“好吧,我確實看到程斌在天黑以后往場長那邊去了。”
程斌臉色驟變,連呼吸也變得粗重起來,紅著臉說:“我怎么知道場長會先砸自己?而且我也沒有動機啊,我和場長的關系那么好,怎么會做出這種傷害他的事情?”
“是啊,程斌和場長的關系真的很好呢。”胡強補充。
“我剛才在你院子里看到了新翻的土。”阿元探長慢條斯理地說,“我本以為是用來種花的——如果那個時候我沒有踩到土底下的部分,沒有看到后門縫里沒有清理干凈的東西。我是說那些海洛因。”
阿元探長接著說道:“你和場長經常一個下午待在房里,還有房間里明顯超出你收入的高端家具,都是因為它們吧。張志發現你們偷運毒品,進行勒索,所以場長設下圈套想讓張志成為嫌疑人。而你知道了場長的計劃,因為與他有矛盾,所以將計就計,在場長砸傷自己后,進行了加害。”
程斌雙腿開始顫抖,額頭上也冒出了黃豆大的汗珠。
程斌終于承認,下午他們爭吵是因為場長要他補上他丟失的那袋毒品。此前,張志也已經前前后后勒索了他上萬元。
趙警官帶走了程斌和張志。
“但是柳老板,你為什么要包庇程斌?”胡強不解地問。
柳行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是因為去世的侯先生吧。”阿元探長說。
柳行瞟了阿元探長一眼,“是。老侯去世之后,一次我和黃場長喝酒,他喝醉了。黃場長說老侯發現了他做過的壞事,要他自首,他就把老侯推了下去。他說的壞事應該就是這個吧。”
醫院里,黃場長從昏迷中醒來,除了輕微的腦震蕩,并無大礙。只是,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制裁。
李漪如:江蘇省南京市第十三中學高一(8)班學生
編輯 巴恬恬 36558426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