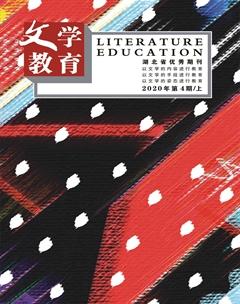“逃離”:時代基因的果實
鄭小驢筆下的“逃離”已成為一種主題和現象,有評論家指出,《可悲的第一人稱》《沒傘的孩子跑得快》等作品中的“疏離”“游離”都呈現出“生活在別處”的渴求。主人公因厭倦于當時當地的生活而不斷地出走,甚至去到刀耕火種的原始叢林。但最終,這些渴求都因現世的請求或意外而中斷。
如果將《一屋子敵人》放到這一主題下進行考察,小說在“逃離”的行為趨向和心理取向上表現得并不激烈。男主人公“我”和女網友黎安相約,分別從北京和武漢出發,準備在昆明長水機場會合,然后開車經大理和臨滄抵達南傘。“南傘”并非虛構而實有其地,這個位于臨滄市的小鎮西鄰果敢,緬北戰事之后國門關閉,不少緬甸難民涌來。這一現實的戰亂背景為和平年代的“80后”提供了具有冒險性和戲劇性的寫作場域。
“我”和黎安并不知道去到南傘之后怎么辦。黎安咨詢知乎的網友怎樣出境,回答是“偷渡”。小說的主題雖為“逃離”,主體卻是“逃離”的方式和過程。他們首先面對的是要在昆明借輛車。無奈之下,家在昆明的黎安只好騙自己母親說要和同事休假出行,借用家里的帕薩特。他們的“逃離”從“家”開始。
當他們到達南傘時,正逢雨夜,飯店老板驚訝于他們的“旅游”目的,因為南傘并非風景秀美之地。南傘的“對面”在戰事之前“遍地黃賭毒”,很多人有去無回,戰事之后則少人涉足問津。老板找朋友老李來帶他們“偷渡”,價格比往常高出數十倍。“逃離”于是就此擱淺。
事實上,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注定無法完成的“逃離”。鄭小驢借用“南傘”這個充滿戰事危機和誘惑的邊陲小鎮,無非是在表達一種“逃離”的愿望。作為“80后”,鄭小驢從寫作伊始便一直在追問,“改革開放后長大的一代人,今天怎么辦?”他們不同于在“后革命”或“革命后”時期成長起來、對歷史進行追憶和記錄的“70后”,也不可能像父輩那樣以介入和在場的姿態去寫知青、寫斗爭史、寫革命建設。他們出生、成長的環境平靜無波、乏善可陳。鄭小驢對自己提出的問題無法給出答案。也可以說,他一直在尋找答案。他的寫作和生活互為呼應地形成了同構:永遠在路上。
鄭小驢是名副其實地將讀書、寫作和“遷徙”結合起來的作家。他愛旅游,愛跑步,愛戶外運動,愛長途自駕。阿乙稱呼他為“游擊隊員”。2014年,28歲的鄭小驢結束了在長沙的生活,將自己放逐到了海南。他在異鄉依然保持著跑步的習慣:沿著美舍河兩岸跑,沿著南渡江的江堤跑,他在跑步時看到河流、漁火、星光,想到曾經的天涯孤旅和危崖巨濤。孤島上的跑步由此構成了一種生命的隱喻。
《一屋子敵人》中的男女主人公為什么會選擇“逃離”?對于這個問題,小說隱約透露了些許原由。男主人公有過體面的工作,一次酒后將酒吧里的女孩帶回家,后被告強奸罪而服刑六年,妻子離婚帶走了孩子。他在獄中學會了縫紉,出獄后落下了抖腿的毛病。女主人公的現實生活表明,她來自于一個破碎的原生家庭。職業不明的父親喜歡喝酒,喝醉后喜歡打罵人,后遇“車禍”身亡。車沒事,他的頭被撞得像顆西瓜。母親忙著照顧小兒子,一個未曾與父親謀面的遺腹子,一個癡迷于扮演奧特曼的小男孩,而無暇顧及于她。男女主人公的生活都遭遇了巨石的重擊而留下了深刻的凹陷。
毫無疑問,這是兩位失敗者,也是一代人的失敗典型。不是戰死、凍亡、餓病,而是被平凡生活一點點地纏繞和吞噬。就連他們的結伴同行同住,都未能給生活增添半點詩意和慰藉,反而讓他們想起了各自深淵般的困境。這樣的人物在鄭小驢的《去洞庭》等小說中都可見到:男人遭遇事業與婚姻的雙重失敗,女人被生活碾壓得沒有還手之力。他們確實沒有歷史的負擔,但生活并沒有因此而對他們撒手。比起父輩,這種磨盤般慢悠悠的絞殺更讓人發瘋。孤獨、漂泊、疏離、困惑、迷惘是這一代人的主題。“逃離”于是成了一種抵抗的姿態和方式。《一屋子敵人》這個題目也逸出了小說內容,彌漫為意義更加廣闊和形而上的所指。
相對于體質孱弱的文壇,鄭小驢的獨特性在于,他的身體和心性互補性地建構起了寫作的格局。長跑的習慣健康著他的身體,他蓬勃結實得不像個作家。內向的性情滋養著他的筆觸,他的寫作安靜且豐饒地貼著時代和心的內里。就這樣,他在“逃離”中寫“逃離”,在“遷徙”中寫“遷徙”,提供了一代人精神肖像的側面,由此呈現了時代基因的果實: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講述主題和方法,由此形成了一代人的美學、價值觀和話語譜系。
曹霞,著名文學評論家,現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