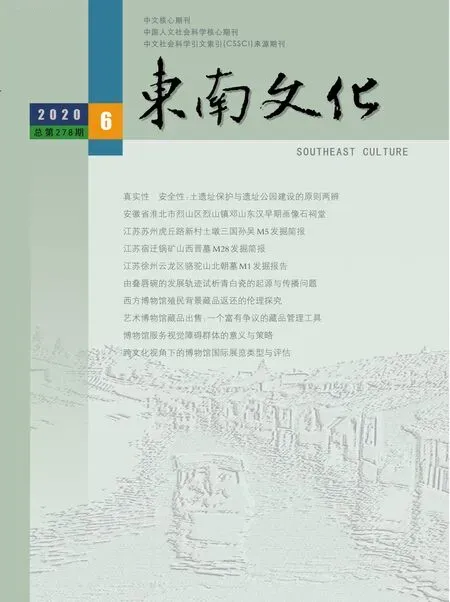西方博物館殖民背景藏品返還的倫理探究
楊 謙
(上海大學歷史系 上海 200444)
內容提要:西方博物館應對殖民背景藏品返還訴求的倫理體系,由之前直截了當地拒絕返還,逐漸轉向當下的提倡雙方溝通與對話,鼓勵在協商過程中加大殖民背景藏品的“來源研究”力度。這種轉變一方面得益于在博物館去殖民化運動的影響下,以非西方視角對殖民背景藏品價值和流轉方式的再認知,以及各博物館職業道德準則等的實踐推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經歷了多種博弈方式之后,博物館意識到返還訴求的應對得當可以讓其轉危為機的利益導向。盡管當下西方博物館表現出坦誠地面對過去、反思不正當殖民歷史的態度,但在倫理上并沒有無條件地支持返還,藏品的直接返還并非博物館應對之下的首選之舉。
法律訴訟與調解通常被視為解決流失文化財產的強硬途徑,但由于各個國家和地區法律體系的不同,難有可以普遍適用的財產法等,而目前已有的國際公約自身適用性又十分有限[1],且對象主要為非法流失文化財產,如1954年《關于發生武裝沖突時保護文化財產的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主要針對戰爭、武裝沖突或被占領期間被轉移的文化財產,效果有限。對于殖民時期因權力、不平等交易等原因造成的文化財產流失,相比法律返還途徑,近些年倫理道德壓力在殖民背景藏品返還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比如加拿大博物館與第一民族委員會(The Task Force on Museums and First Peoples)在處理原住民物品返還時,考慮定制類似《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與返還法案》(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的立法方式,但鼓勵博物館采用“由道德、倫理和專業職責指導的各方平等合作模式”[2]。
殖民背景藏品不僅包括實際殖民統治期間基于暴力等方式獲得的物品,也包括反映殖民意識、話語、知識體系、審美和視角等的物品,其類別有宗教物品、自然歷史物品、藝術品、人工制品等。本文將分析殖民背景藏品返還的倫理道德體系構建歷程及形成原因,以期為探討殖民背景藏品返還的倫理途徑拋磚引玉,不足之處懇請方家斧正。
一、問題的提出:“去殖民化”運動與殖民背景藏品返還
許多西方博物館的形成與殖民主義活動密不可分。來自世界各地的自然標本、文物、藝術品等以戰利品的形式被帶回西方宗主國,而宗主國的官員、商人、傳教士、學者等也在殖民地扮演起收集者的角色,絕大部分所得物品后被收入宗主國的相關博物館中,成為完善世界知識體系和表征異文化的標本[3]。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洲以民族學、自然史、歷史、藝術史、考古學、人類學、科技等為主題的博物館,都或多或少地藏有殖民背景藏品,或得益于當時的殖民擴張。僅以德國的民族學博物館為例,1862年慕尼黑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Fünf Kontinente)建立之后,萊比錫、柏林、漢堡、科隆和法蘭克福等地就先后建立民族學博物館。截至1919年,絕大多數的德國城市都建立起民族學博物館[4],這與當時歐洲殖民擴張活動的興盛以及在此背景下民族學學科的輔助作用密切相關。
伴隨著二戰后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許多原殖民地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在經濟上卻依然高度依附于前宗主國,且在文化上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影響[5]。這一階段殖民主義逐漸走向衰落,進入其發展的最后一個階段,即戴維德·費爾德豪斯(David K.Fieldhouse)所謂的“非殖民化進程”[6]。勒芬·斯塔夫羅斯·斯塔夫里揚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總結這一階段的特點:在外緣地區呈現一種由革命、非殖民化和新殖民主義相互交織的狀況[7]。此處的“非殖民化”或“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概念,狹義上原指殖民國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給予殖民地獨立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旨在盡可能維護自身利益的各種行動[8];而廣義的“去殖民化”則側重于歷史文化視角,意指從各方面擺脫殖民主義的遺產、摒棄殖民主義價值觀的過程[9]。
“去殖民化”運動也影響了博物館界,許多歐洲博物館實行博物館的去殖民化(Decolonizing Museum),在博物館定位與名稱、展覽敘述和藏品來源等方面淡化其殖民主義的色彩[10]。具體而言,在博物館定位與名稱上將原名中的民族學、民俗學等敏感詞進行更換,如2014年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in Leiden)、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 in Amsterdam)與貝赫達爾非洲博物館(Afrika Mu?seum in Berg en Dal)三家博物館,整合為荷蘭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以抹去原名中的“民族學”及原殖民地“非洲”等字眼。在博物館陳列展覽中,則重新審視具有殖民主義觀點、忽略反抗殖民歷史的敘述方式,通過另類的敘事與記錄,力圖客觀與中立地呈現殖民主義、博物館與藏品的歷史。比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在舊有的常設展廳解說文字旁另立新的獨立展板,將博物館的專業觀點和被殖民者、少數族裔與弱勢群體等的另類敘事觀點并置呈現給觀眾[11]。在藏品來源方面,西方博物館圍繞藏品來源的合法性和所有權問題進行反思,且對原殖民地提出的希望返還本國或本民族流失物品的訴求作出回應。這些返還訴求取得了一些國際社會的聲援,如1973年聯合國大會第3187號決議名為“返還各國被掠奪的藝術品”(Restitution of Works of Art to Countries Victims of Appropriation),其導言對“往往作為殖民或外國統治的結果,藝術品幾乎無代價地從一國整批移至他國”這一現象予以譴責,聲稱“返還此類藝術品,是對其因轉移而蒙受重大損失國家的補償”[12]。
盡管第三方國際社會表現出了對殖民背景藏品應當返還給原屬國的倫理支持,但對于涉事的西方博物館而言,其自身卻經歷了一個明顯的態度轉變和返還倫理構建的過程。
二、持有與返還之爭:拒絕返還的倫理尋求
對層出不窮的殖民背景藏品返還訴求,相關西方博物館一開始并非像如今的國際社會一樣予以支持,而是持或明或暗的拒絕態度。事實上博物館要徹底去殖民化似乎并不容易,因為這些博物館的早期發展史已經深深烙下了殖民主義的印記,況且殖民主義思想體系的根除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對西方博物館而言,“去殖民化”是對曾經的殖民歷史的批判性思考,是確保類似的事情不會在當今社會重蹈覆轍,但并不意味著就一定要將殖民背景藏品物歸原主。為了繼續持有殖民背景藏品,這些博物館努力尋找或提出拒絕返還的倫理依據。
首先是所謂“普世性博物館”的提出與質疑。2002年18家歐洲和北美的知名博物館發表了《關于普世性博物館重要性及價值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Museums,以下簡稱“《普世宣言》”),宣稱這些博物館繼續持有藏品對所有民族的利益來說都很重要,因而其藏品不應在返還之列。毫無疑問,彼時的這一提法是拒絕將包括殖民背景藏品在內的藏品歸還給原屬國,而這在當時也引發了一場巨大的倫理之爭,代表了以持有為導向的國際主義與以返還為導向的民族主義兩種聲音的對立,以及殖民與被殖民、帝國和民族國家之間對于藏品歸屬的倫理爭論[13]。質疑者首先認為這些博物館對“普世性”存在曲解,事實上所有博物館都有普世價值[14],殖民背景藏品的流失過程通常與國家和民族情感密切相關,拒絕返還是對原屬國民族情感的再一次踐踏[15]。其次,“普世性博物館”也并非藏品保護和展示的最佳選擇,這一提法忽視了藏品的特殊性,即藏品與創造它的民族緊密相連,脫離了這種原生環境,藏品也就失去了其最重要的價值,對藏品的研究和保護都十分不利[16],比如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對《女史箴圖》修復時所造成的損壞。現在看來《普世宣言》的倫理依據已完全不再有力,但在當時它的提出成為西方博物館拒絕返還的一種辯護方式[17]。
相比于直截了當拒絕返還藏品實物的《普世宣言》,近些年出現的數字返還則激起了對實物返還替代模式的倫理討論。數字返還(digital repatria?tion)理念最初來自于美國的原住民藏品返還實踐。美國1990年頒布《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與返還法案》后,部分原住民遺骸及物品得以歸還,然而由于舉證困難、法律程序復雜、原住民部落社區文保設施落后等問題,大部分原住民藏品并未真正實現歸還。但博物館與原住民群體在返還過程中的合作空前增強,并在2000年由美國國立印第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與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合作,對美國原住民物品進行數字化,以期找到實物歸還途徑之外的另一種途徑[18]。之后數字返還的理念被部分綁上了政治因素,一度被標榜為博物館藏品返還的新選擇[19]。
數字返還的本質是將數字化信息共享給原屬國或社群,包括圖片、文獻、文件、研究成果、知識體系等,然后基于信息再進行藏品的復制、展示等,幫助原屬國重新獲得流失之物的知識,并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藏品知識的全球共享。但數字返還只是解決了藏品的利用問題,并未觸及藏品的所有權問題,而且對于原屬國或社群而言,依附于藏品而存在的民族情感與自我認同等精神價值也未得到慰藉[20]。
換句話說,“數字返還”應當視為實物返還過程中雙方合作的一種產物,是實物返還的一個先前步驟。數字返還只不過是基于博物館對藏品的日常數字化工作,是在實物返還之前實現藏品信息共享或在藏品返還實在無法開展的情況下所進行的暫時性舉措,不應視為實物返還的替代方式。
三、認知與理解:非西方視角下的藏品再認知
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博物館在處理原住民物品返還時與原住民重啟協商與對話,允許有不同聲音來解讀物品,甚至向原住民文化學習、邀請原住民為自己文化代言等[21],這為博物館處理殖民背景藏品倫理道德提供了借鑒。
西方博物館之前在闡釋殖民背景藏品時,大多通過展示他者來呈現自身的敘事方式,強調自身文化的光榮與認同,體現出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以及脫離原生情境的藏品闡釋方式[22]。博物館去殖民化也意味著博物館應擺脫西方世界對藏品認識的價值體系,從非西方的視角來重新審視藏品,包括藏品的重要性、目錄與分類等,這也與后殖民時代文化遺產保護理論強調藏品的原生情境相契合[23]。2007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以下簡稱“國際博協”)大會主題說明在對遺產含義的闡釋中提到:“作為一種整體存在的方式,遺產既包括一個民族在環境、科學、技術和藝術等方面的知識與態度,也包括一個民族固有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后者主要體現在世界觀闡釋、個體和團體的認知活動及其生活方式等方面。”[24]
在西方藏品認知體系下看待藏品,會導致與訴求者提出的返還意愿并不一致的情形,而部分藏品通過回歸原先的語境可以深化自身的意義,因此對藏品價值的重新闡釋是促成雙方有效對話的前提。蘇格蘭格拉斯哥博物館(Kelvingrove Art Gallery and Museum in Glasgow,Scotland)“鬼神舞衣”(Ghost Dance Shirt)的返還案例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傷膝谷幸存者協會(Wounded Knee Survivors Association)對格拉斯哥博物館藏“鬼神舞衣”的第一次返還訴求于1995年提出,但被時任館長朱利安·斯伯丁(Julian Spalding)拒絕;又于1999年第二次提出返還訴求,得到了新館長馬克·奧尼爾(Mark O’Neill)的同意。第二次返還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鬼神舞衣”原生文化情景的再認識。訴求方的代表律師馬里奧·岡薩雷斯(Mario Gonzalez)在返還訴求中闡釋道:“拉科塔的傳統是需要將死者著衣而葬,因此‘鬼神舞衣’應當被視為和人體遺骸具有同樣重要性的物品。”[25]在這之前博物館一直認為這件藏品既非其非法而得,也非神圣物品或人類遺骸,因此不應在返還之列,這一陳述顯然為“鬼神舞衣”提供了一種新的認識。與此同時,為了給博物館和返還方公正的陳述機會,格拉斯哥博物館還為此舉辦了公眾聽證,訴求方代表馬塞拉·勒博(Marcella Lebeau)和格拉斯哥博物館館長馬克·奧尼爾在聽證會上分別向公眾作了報告。這種雙邊陳述可以讓雙方就自己的觀點和證據進行陳述,原本在書面材料中不適陳述的內容,在口述中可以得到聲情并茂的發揮[26]。
除了藏品原本價值,對這些藏品流失方式的再認知也是一個重要部分,其中比較典型的是“不道德交易”的闡釋。其實早在1943年二戰同盟國為解決納粹劫掠問題形成的《倫敦宣言》(London Declaration)中就提到“不道德交易、威脅、脅迫、非法占有或任何其他侵權行為”獲得的財產,被視為可沒收財產。從中可以看出對藏品交易真實性的強調,包括“形式看似合法,甚至自稱為自愿生效的交易”,因為這些交易背后往往體現了不平等的權力分配。盡管這主要是針對德國占領區強制性、恐嚇脅迫下的借出、捐贈和賤賣等交易,但在之后人們認識殖民背景藏品時很快意識到殖民情形下也有許多類似交易。在殖民時期宗主國掠奪以及在與完全不懂西方市場行情的人交換財物時,這些藏品的“價值”在交易過程中難以充分體現,這些藏品的交易本身也需要重新進行審視[27]。
四、對話與合作:職業道德準則和歸還行為指南的實踐推力
為了更好地為博物館實踐工作提供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各博物館協會紛紛制定了博物館職業道德準則。國際博協、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AAM)、英國博物館協會(Museum Association,MA)等機構的職業道德準則基本都涉及藏品返還的相關內容。此外,英、德等老牌殖民帝國的博物館協會,乃至部分擁有豐富殖民背景藏品的博物館,都出臺了具體的藏品返還工作行為指南。比如2019年荷蘭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公布了本館的《文化物品的返還:原則和程序》(Addressing Claims for the Return of Cultural Objects:Criteria and Process)。這些倫理道德準則和返還行為指南,不僅體現出各機構內的一些具有共識性的道德觀念,而且在博物館實際運營和治理中也發揮著類似行業法規的性質與作用[28],對殖民背景藏品返還倫理體系的構建產生一定的推力。
國際博協于1986年通過了《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ICOM 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以下簡稱“《職業道德準則》”),之后的四次修訂更加關注藏品的合法性和人道關懷。其中有關“文化敏感物質”(culturally sensitive material)收藏,以及“文化財產的返還”條例,都涉及殖民背景藏品在內的藏品處理方式(表一)。此外,英國博物館協會頒布的《博物館倫理準則》(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第2.7條提到“博物館需敏感、合適地處理來自英國及國外的藏品返還訴求”,并在之后頒布的《倫理準則:補充指南》(Code of Ethics:Additional Guidance)第 2.5條中對返還工作作了詳細解釋,指出博物館在處理返還訴求時,需要考慮的因素有:法律,目前對返還的認識,文化繼承者的現實利益,追索者與藏品關系的強度,藏品在科學、教育、文化和歷史方面的重要性,持有和返還對廣大利益相關者的影響等。

表一// 《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中有關殖民背景藏品處理的條例
上述道德準則和行為指南對當下殖民背景藏品返還倫理構建的推力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博物館對相關物品的理解與界定。《職業道德準則》中提到了“文化敏感物質”的概念,指的是人類遺體與具有神圣象征意義的物品。之后德國博物館協會在2018年頒布的《殖民背景下藏品處理指南》(Guidelines on Dealing with Collec?tions from Colonial Contexts)中,將這一概念擴展為“歷史/文化敏感物品”(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 objects)[29]。殖民背景藏品就屬于此類,因為它們的獲取通常包含暴力的使用或高度依附的權力關系,同時這些物品可能反映了某種歧視以及殖民或種族的思想意識。在如何具體界定殖民背景藏品上,德國博物館協會認為只要符合下列三種情況之一,即可視為殖民背景藏品:在正式殖民統治時期獲得的藏品,在正式殖民統治之外區域但受到殖民結構或殖民權力非正式影響獲得的藏品,以及能夠反映殖民主義的藏品。為了更好地解釋每種情況,《殖民背景下藏品處理指南》還給出了具體的案例,對殖民背景藏品的認識已經較為全面。
二是博物館面對藏品返還訴求時應持的態度。《職業道德準則》中提到的“博物館必須準備開始讓文化財產回到其原屬國或人民這一議題的對話”,明確了博物館在面對藏品訴求時應當采取一種比較積極的回應態度,應將返還活動視為一種積極的行為,而不是一個應該盡量回避或避免被卷入的問題,甚至可以將其視為博物館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30]。這種態度與之前《普世宣言》所表現出來的拒絕返還的強硬姿態截然不同,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博物館對原屬國的返還訴求都要同意,而是應立即開展針對性的調查、溝通等工作,由被動轉為主動。比如英國博物館與美術館委員會(Museums and Galleries Commis?sion)在2000年頒布了《返還與遣返:行為指南》(Restitution and Repatriation:Guidelines for Good Practice),為英國博物館在理解和處理藏品返還訴求時提供了切實可循的行為指南,包括具體的考慮返還和決定返還時的詳細步驟[31]。
三是崇尚返還應對工作中的科學性和專業性。《職業道德準則》對博物館返還工作的要求是“必須以公平的態度,基于科學的、專業的與人性的原則去執行”,最為典型的就是博物館對藏品開展系統的“來源研究”(provenance research),即研究藏品從創始到現在之間的持有和所有關系,以確定該藏品是否有殖民背景。專業研究的提出由來已久,早在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國際博協發布的《向原屬國歸還文化財產:孟加拉、馬里和西薩摩亞三國情況初步調查》(Return of Cultural Property to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A Preliminary Survey of Bangladesh,Mali and Western Samoa)報告,就指出了專業研究在藏品返還中的重要性[32]。來源研究將之前的專業研究朝著雙方合作的方向繼續推進,特別強調藏品原屬國的社群或專業人員的參與,因為這種合作可以對藏品的制作、闡釋和收藏史有更為專業的客觀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館職業道德準則和返還指南在倫理上依然沒有無條件支持返還。《職業道德準則》對藏品返還的措辭模糊不清,涉及的內容主要是相關藏品的保存、研究和展示,強調的是對這些藏品的尊重,但并沒有直接表達出贊同返還的態度,對其中8.4條的解讀就更為模棱兩可[33]。《殖民背景下藏品處理指南》中則直接指出,即便“通過專業研究確認了藏品的殖民背景,并不意味著藏品的來源就被定性為有問題的,或者應當考慮返還藏品。相反,這僅僅表明需要提升藏品認識并開展進一步的深入調查”,并一直強調“博物館需要記住返還可能不是唯一或整個的解決方法”[34],藏品的直接返還并非博物館應對之下的首選之舉。
五、結語
目前在殖民背景藏品的返還上,盡管西方博物館并未明確表現出自愿返還的態度,但逐步形成了直面過去殖民歷史、強調雙方對話與溝通并鼓勵在協商過程中加大專業研究力度的倫理體系。這個倫理體系不僅可以讓西方博物館向公眾展現其坦誠面對過去,反思不正當歷史的去殖民化渴望和實踐,也折射出博物館在經歷了多種博弈之后,最終意識到,若返還訴求應對得當,可以讓博物館轉危為機,吸引公眾對博物館事務的參與,甚至提高博物館公信力的利益導向[35]。一方面,博物館可以借此重新審視自身及定位[36],如格拉斯哥博物館在返還工作中對博物館收藏價值的反思:“如果博物館代表了更好的自我和人類價值,那么我們不得不承認,可能還有比持有和保存更重要的價值。……我們對博物館的態度并不是將其視為塵土飛揚的儲藏室,而是可以探索和討論個人和社區意義和身份緊迫問題的地方”[37]。另一方面,博物館可以與藏品原屬國建立起長久的聯系[38],加強雙方對藏品的共同研究、聯合策展等。在大英博物館對雅典衛城帕特農神廟大理石雕刻(The Monuments of Parthenon in Athenian Acropolis)的返還案例中,盡管返還訴求還未達成,但雙方已經開展了實質性合作并共同出版了研究性書籍[39]。
對于藏品原屬國而言,如何通過藏品返還倫理體系向西方博物館施加公共道德壓力,建立新的國際文化話語與秩序,并結合國際公約等法律途徑共同推動返還工作的深入,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目前,已有學者借用保羅·巴托爾(Paul Bator)提出的規范國際藝術品貿易的價值標準,如保護價值、組合價值、為人所知并可接近、國家財物、不可讓與的民族身份認同價值、必不可少的親緣關系等[40],將其應用于殖民背景藏品的價值分析中[41]。這在可執行的法律訴訟請求缺失的情況下,論證為某一藏品返還給原屬國的合理性存在充足的道德和倫理論據提供了一種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