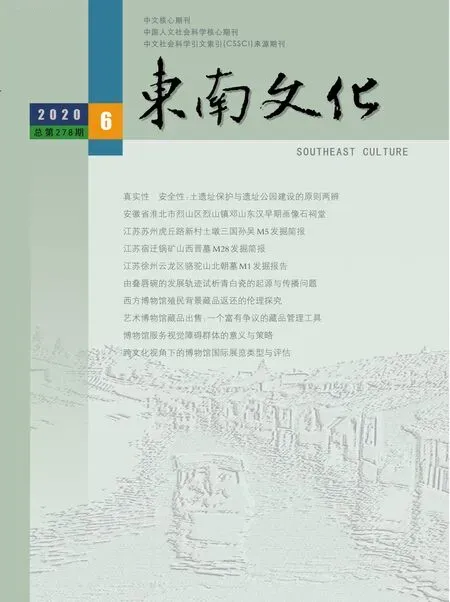唐宋墓葬出土人首魚身俑研究
丁子杰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江蘇南京 210023)
內容提要:人首魚身俑是唐宋墓葬中時有出土的一種鎮墓神怪俑,唐代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區,五代兩宋時多見于南方,分布和使用有著明顯的時代和地域特色。其內涵在唐宋時期亦有不同。在唐和五代,它是鎮墓壓勝、喪葬禮制的一種表現,而在兩宋時,則和道教思想關系密切。
人首魚身俑是唐宋墓葬中時有出土的一種隨葬器物,它們造型獨特,形制多樣,置于墓中有著獨特的意義,為行文簡潔,以下簡稱為人魚俑。目前學界對其已有不少研究,如徐蘋芳和白彬兩位先生主要對其性質進行了分析,前者認為人魚俑是墓葬中名為“儀魚”的隨葬品[1],后者則認為人魚俑實為道教雷神[2]。崔世平則重點論述了人魚俑的分類和葬俗的傳播[3]。本文受教于前輩學者的論述,結合目前為止已出土的人魚俑材料,擬從類型、時代、地區、內涵幾個方面對人魚俑進行研究分析,如有不正,懇請諸位師長不吝批評賜教。
一、人魚俑分類
目前出土人魚俑的墓葬,筆者共收集有40余座(表一)。根據出土的人魚俑造型,本文將人魚俑分為A、B兩型。

表一// 人魚俑出土信息一覽表

續表
A型:人魚俑魚身扁平,人臉轉向身體左側,魚尾右擺,身體中部彎曲,整體輪廓呈“S”形(圖一),魚身下多連有底座,大都也為“S”形。該型不僅造型接近,大小上也十分接近,俑身長度都在20~22厘米之間,高度在8~10厘米之間。

圖一// A型人魚俑
B型:該型人魚俑數量較多,約占人魚俑總數的四分之三。魚身筆直,無彎曲現象,頭尾偶有上翹,輪廓總體呈直線形。身體部位上,除了常見的魚鱗、魚鰭外,還出現有足、角等。B型人魚俑種類較多,根據人面部朝向可分為Ba、Bb、Bc三小型。大小差距也較大,大的人魚俑長30、高13厘米,小的僅長13、高4.8厘米,多數長度集中于15~27厘米,高度在7~13厘米。
Ba型:該型人魚俑臉部均朝上或微向上(圖二︰1),多有魚鱗和魚鰭,在B型中數量最多。

圖二// B型人魚俑
Bb型:該型人魚俑臉部均向下或微向下(圖二︰2),身體部位上除了常見的魚鰭魚鱗外,目前有角的人魚俑也僅見于此型,即太原金勝村唐墓出土人魚俑。
Bc型:該型人魚俑臉部均向前(圖二︰3、4),該型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其魚身前部多設有足部,像范澄墓人魚俑魚身下有雙足,而李昪墓和江西彭澤墓人魚俑則是以鰭為足,雙鰭突出于身體兩側并支撐于地面。
陜西歷史博物館館藏一件人魚俑,長22厘米,臉轉向身體右側。目前為孤例,且這件人魚俑為征集品,具體的背景信息亦缺乏,故本文未加分型,將其列入特例,亦未深入探討。
最后簡要提及各型人魚俑的材質和底座。目前出土的人魚俑多為陶質,其中,A型人魚俑均為陶質,B型人魚俑在唐代均為陶質,而五代兩宋時期質地就較為多樣,如江蘇蔡莊五代墓的木質人魚俑、福建南宋陳元吉墓的石質人魚俑,可見唐代的人魚俑不論何型,均為陶質,而五代兩宋時的南方,人魚俑并不局限于單一材質。至于底座,A型人魚俑由于身體扁平且彎曲,需要底座來保持平穩,故A型人魚俑均有底座;B型人魚俑底部大多寬大平直,對底座要求較低,在唐代不少仍有底座,但五代兩宋就很少見了。底座形狀則大多取決于人魚俑的類型,A型人魚俑多為“S”形底座,B型人魚俑為長條形或長方形底座。
二、人魚俑的使用歷程
人魚俑雖盛行于唐宋,但在唐之前也有發現,目前發現最早的人魚俑時代為隋大業元年(605年),原報告中推測其可能為墓葬中的隨葬品,而有明確紀年的人魚俑中最晚的是浙江云和正屏山宋墓人魚俑,時間為1248年。人魚俑以唐代發現最多,其中又有近半數集中于初唐,時間在650—700年左右,中、晚唐時亦有發現,但數量較少,五代時人魚俑的使用有所回升,僅南唐二陵中就出土有13件人魚俑,后來的兩宋時期時有出土,但人魚俑數量較之之前已經不多。由此大致可以得出,人魚俑在隋朝時就已出現并可能已經被當作隨葬品使用,唐代則是人魚俑盛行的重要時期,其中尤以初唐時最為流行,雖然在五代時使用又有所增加,但不可否認的是,初唐以后直至南宋,人魚俑雖一直有使用,但數量已有明顯減少,南宋以后目前未見有人魚俑出土。
具體到類型上,明確出土有A型人魚俑的墓葬,除天津軍糧城唐墓時代沒有進一步精確,遼寧黃河路唐墓、河北獻縣唐墓時代接近中唐外,其余均為初唐時期,唐以后就不見有A型。因此A型人魚俑僅在唐代使用,初唐時尤為流行,初唐以后數量減少,唐代以后則不再見到。B型共有30余例,唐宋時期均有發現,南方北方都有出土,且目前已知年代最早和最晚的人魚俑均為B型,可見該型使用時間之長,使用地區之廣。不過各小型的發展有一定區別,Ba型、Bc型人魚俑唐至兩宋都有發現,其中Ba型在唐代占據主流,雖然到了五代兩宋仍有發現,但是數量都不及唐代多,Bc型則一直存在,唐宋時數量變化不大,而Bb型只見于唐和五代,兩宋時已不見。
三、人魚俑的傳播和地域特征
唐代人魚俑多在北方地區,主要是河北和山西兩地,遼寧也有相當數量的發現,南方僅見有福建漳浦縣劉坂鄉唐墓和江蘇無錫皇甫云卿墓。五代兩宋時,除了陜西洋縣南宋彭杲墓外,基本都在南方地區,五代時多見于江蘇,兩宋時多在江西、四川等地。人魚俑在北方流行時南方鮮有發現,在南方流行時北方也鮮有發現,因此人魚俑的主要使用地區隨時代發展不斷轉移,不同時代各有不同。在唐、五代、宋三個不同時期,使用的中心地區由河北、山西向南到江蘇,再由江蘇繼續向南至江西、四川等地。而在轉移過程中,A型未離開北方地區,唐以后就不再見到,B型則進入南方地區,五代時流行于江蘇,此時三小型皆有,兩宋時Ba、Bc型向更南的江西、四川等地傳播,Bb型不再見到。
人魚俑除了使用地區不斷向南之外,南北之間的分布也各有特征。從圖三中可以看到北方地區人魚俑分布密集,而南方卻較為分散。先看北方地區,該區人魚俑多屬唐代,主要集中的地區為山西襄垣、長治地區和北京以南的河北大部地區,該區內人魚俑A、B兩型皆有,時代大都在初唐時期,北京地區的大業元年人魚俑更是目前可見時代最早的人魚俑,可見這一地區可能是人魚俑流行的重要地區。而北方另一個特殊地區是遼寧省朝陽市,該市附近出土了數例人魚俑,這是目前所見人魚俑位置最為偏東北的地方,與中原諸地相距較遠且周圍并未再見有人魚俑的發現,顯得較為孤立。該區人魚俑A、B兩型都有,形制上和河北、山西地區的人魚俑也有相似之處,人魚俑年代上以初唐時期最多,也有中唐時期的,因此朝陽地區雖然較為偏遠,但人魚俑類型和流行時間和北方山西、河北地區有很多相似之處,總的來看,北方地區的人魚俑不僅分布密集,使用上也具有相當的統一性。

圖三// 人魚俑出土地區分布圖
和北方相比,南方的人魚俑分布特征則是總體分散,局部集中,總的來看南方人魚俑散布于南方各地,而局部地區又有明顯集中,如東南地區的江蘇,西南地區的四川。這種分布當有不少可以討論之處。第一,五代時期,江蘇是人魚俑使用的重要地區之一,這種現象應和南唐政權有密切關系,江蘇大部分地區在五代屬南唐,南唐建國時吸收借鑒了不少唐代制度和文化,這可能是人魚俑在南方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五代時期南方出土人魚俑的墓葬的墓主地位大都很高,如南唐國主、閩國王室等,可見此時人魚俑應是南方地區上層人士常用的一種隨葬品。而在五代之前,江蘇無錫唐墓和福建漳浦劉坂鄉唐墓就出土過人魚俑,唐代人魚俑主要分布于北方,因此這兩座南方墓葬出土人魚俑是較為特殊的,且劉坂鄉唐墓的人魚俑屬B型,南方地區的人魚俑也只有B型,在人魚俑類型上也是一致的。由此可見,江蘇、福建地區在唐代就已有使用人魚俑隨葬的現象,因而東南地區在人魚俑葬俗上可能有著一定的文化共通性和較為連續的文化淵源,這可能也是東南地區人魚俑分布較為密集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兩宋時人魚俑集中于江西、四川兩地則應和道教關系密切,下文將有論述。而陜西洋縣南宋墓出土的人魚俑為當時唯一一個北方地區人魚俑,洋縣位于陜西西南部,隸屬漢中,漢中為道教起源發展的重要地區,也是通向巴蜀之地的重要門戶,和四川聯系緊密,因此該人魚俑可能和道教有一定關系,也不排除四川地區的影響。
四、人魚俑內涵試探
人魚俑形制獨特,是唐宋時期的一種鎮墓神怪俑,在出土人魚俑的墓葬中,大多還有其他鎮墓神怪俑,不少即位于人魚俑附近,這些神怪俑共同在墓中起著鎮墓辟邪、吉祥壓勝之類的作用。不過雖然唐宋時期的人魚俑性質上均屬于神怪俑,但背后的內涵體現是有所區別的。
唐代墓葬中隨葬陶俑盛行,《新唐書·唐紹傳》中唐紹曾上書道:“比群臣務厚葬,以俑人象驂眩耀相矜,下逮眾庶,流宕成俗。”[46]可見無論是官員大臣還是平民百姓,都熱衷于在墓中隨葬陶俑,而唐代鎮墓神煞、地理風水之說大為流行,對葬俗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新唐書·藝文志》中記錄:“右五行類六十家,一百六十部,六百四十七卷。”[47]而其中和喪葬直接有關的書目就多達幾十卷,如《葬經》《葬書地脈經》《墓書五陰經》等[48]。在這類背景下,唐代不僅陶俑發展迅速,鎮墓俑也得到了充分發展,唐代的鎮墓俑已形成一個統一度很高的體系,以兩件鎮墓武士俑配兩件蹲踞狀鎮墓獸最為常見,同時還見有人魚俑、雙人首蛇身俑、十二生肖俑等神怪俑。唐代出土人魚俑墓葬的墓主大多有一定的身份或地位,身份較高的有五品以上官吏,較低的也大都為中下級官吏,至于五代,墓主身份更加顯貴,像南唐皇帝、閩國王室等,可見這一時期人魚俑的使用更有講究。總的來看,唐和五代,墓主身份差距雖較大,但大都為官員,基本都是具有一定地位或身份之人。而這一時期人魚俑形制的統一程度也很高,唐代人魚俑中,A型人魚俑前文已經提及,造型統一,B型以Ba型為主,五代人魚俑以南唐二陵為代表,雖然出土B型種類多,但除了面部朝向不同外,整體造型、身體特征等基本相同(圖二︰1、3)。所以唐和五代,人魚俑葬俗不僅是鎮墓神煞、地理風水等思想的表現,俑造型較高的統一性、所屬墓主有一定身份等又在一定程度表明人魚俑使用的特殊性,也是當時喪葬禮制的一種體現。
宋代統治者推崇道教,其中尤以真宗、徽宗時期為代表,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49]此后天書屢降,而徽宗時期,一方面和道教保持密切聯系,如政和三年(1113年)“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50],政和六年(1116年)“會道士于上清寶箓宮”[51]。一方面又大修宮觀,比如在茅山建元符萬寧宮,在龍虎山遷建上清觀,增建靖通庵、靈寶觀,又“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圣像”[52]。在統治者的大力推崇下,道教在宋代快速發展,在民間的影響也不斷增強,對當時的葬俗也有重要影響。在兩宋墓葬中,唐代常見的鎮墓武士俑、蹲踞狀鎮墓獸幾乎不見,但造型特殊的神怪俑不僅沒有消失,種類反而更加多樣,宋墓中的神怪俑除了唐代已有的類型,還有四神俑、星宿俑、仙人俑等。出土人魚俑的宋墓規格大多較小,墓主身份也多為平民,墓中的人魚俑造型也更加多樣,各人魚俑的細節特征也互有不同,可見人魚俑的使用在下層更加普遍,造型設計也更加靈活。出土人魚俑的墓葬中也會有其他和道教有關的器物,如湖北羅田汪家橋宋墓除了人魚俑外,還出土有完整的十二生肖、四神、塔式罐,報告中指出這些“正好是一套伴隨著道教盛行而出現的器物組合”[53]。而在江西、四川等地,即使是未出土有人魚俑的墓葬,墓中或有其他神怪俑,或有道教色彩濃厚的買地券、符箓等物,由此可見當時道教在民間的普及以及對當地葬俗的深刻影響。因此在這種大背景下,宋墓中的人魚俑雖然仍屬于鎮墓神怪俑,但它們和道教的關系更加密切,是道教思想對葬俗產生影響的重要表現。
綜上,本文認為,首先,人魚俑實質是一種隨葬于唐宋墓葬中的神怪俑,有著明顯的時代和地方特色,是唐宋時期喪葬習俗、神怪觀念的重要體現。其次,人魚俑的內涵也并非一成不變,在不同時代有不同體現,在唐和五代,它是鎮墓辟邪、喪葬禮制、地理風水影響下的產物,在兩宋,則和道教關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