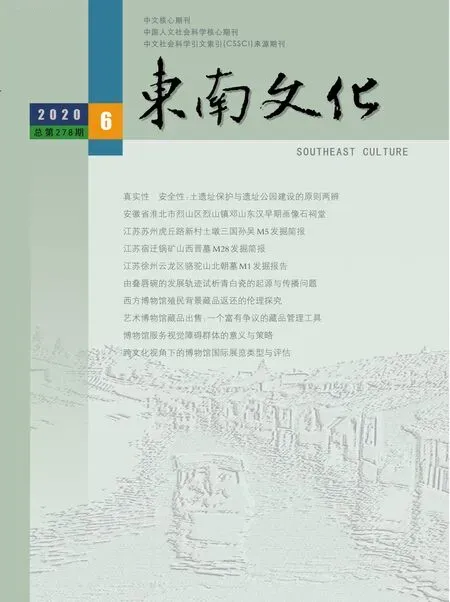江蘇徐州云龍區駱駝山北朝墓M1發掘報告
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 徐州獅子山楚王陵
內容提要:2008年,江蘇徐州云龍區駱駝山附近發現一座北朝時期墓葬。該墓為“凸”字形券頂磚室墓,是徐州地區南北朝至唐初流行的墓葬形制。出土瓷器、陶器、陶俑等多件。據隨葬品特征以及出土銅錢判斷,墓葬年代應為北魏末期至東魏初期。其文化面貌反映出徐州在北魏漢化深入的背景下對于北方政權認可的加強。
2008年5月13日,施工單位在位于江蘇省徐州市云龍區駱駝山腳以東200米的世茂一期建設工地,進行挖掘基坑作業時,發現了一座磚室墓(圖一)。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考古工作人員聞訊趕到現場,立即進行現場保護。經勘察,該墓為磚室墓,墓室上部已被挖土機完全鏟除破壞,墓壙已無法辨認,僅剩磚室墓底。現場散落瓷器殘片若干。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隨即對其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編號為08LTSM1,以下簡稱M1。

圖一// 08LTSM1墓葬位置示意圖
一、墓葬形制
該墓為券頂磚室墓,平面呈凸字形,方向為北偏西40°。墓葬在發現時上部已遭鏟除殆盡,墓室北端殘留券頂跡象。墓長3.94、寬1.32米。墓葬由甬道和長方形墓室構成,墓室內又分為地面和棺床兩部分。甬道長0.91、寬0.87米。前室長0.95米,棺床長2.08米。甬道地面與墓室地面相平,甬道墻殘高51.5厘米。墓壁砌筑方法為三順一丁,甬道和墓室地面為一層立磚加一層人字形平鋪磚,棺床則為三層平鋪加一層立磚,高出前室約13厘米(圖二;彩插七︰1)。甬道殘深51.5厘米。墓磚規格為31.5×16×6.5厘米。棺木已朽,殘存頭骨痕跡和部分腿骨,據之判斷為單人葬,頭向墓門。

1.M1發掘現場(東南—西北)

圖二// M1平、剖面圖
二、隨葬品
該墓共出土文物31件/套(銅錢依出土位置按2件計算)。其中1件銅鏡、若干小銅錢及鐵環銹蝕嚴重。
1.瓷器 3件
青瓷六系蓋罐 1件(M1︰19)。圓形蓋,回字型鈕,鈕的每邊有兩道刻劃豎線,下刻蓮瓣紋。罐圓唇直口,其肩部對稱兩側分別有兩橋形系,另兩側分別有一橋形系,圓肩,鼓腹,最大徑在器中部,平底,肩腹部刻劃蓮瓣紋。外施青釉,釉不及底,灰白色胎質。口徑11、最大徑22、底徑11.8、通高22.3厘米(圖三︰1;彩插七︰4)。

圖三// 出土青瓷器

4.蓮瓣紋青瓷六系蓋罐(M1︰19)
青瓷四系盤口壺 1件(M1︰21)。盤口,細頸,弧肩,鼓腹,平底。頸部有二箍痕,肩部有四系,施綠釉,釉不及底,露出灰白色胎。口徑14、最大徑17.5、底徑10.4、通高25厘米(圖三︰2;彩插七︰5)。

5.青瓷四系盤口壺(M1︰21)
碗 1件(M1︰1)。直口,深腹,餅狀足。所施釉剝落嚴重,灰白色胎質。碗中有三支釘痕跡。口徑9.8、底徑4、通高4.8厘米(圖四︰1;彩插七︰2)。

圖四// 出土陶瓷器

2.瓷碗(M1︰1)
2.陶器
(1)容器 5件。皆為泥質灰陶,素面。
盂 1件(M1︰2)。鼓肩,斜收至底,平底。底部有輻射狀線刻,肩腹部略有殘缺。口徑4.4、最大徑11、底徑5、通高8.5厘米(圖四︰4;彩插七︰3)。
壺 1件(M1︰12)。直口,圓唇,鼓肩,從肩腹部斜收至底,平底。肩上有一對橋形系。口徑3.2、最大徑6.8、底徑3.6、通高8.6厘米(圖四︰2)。
匜 1件(M1︰17)。單側有一個把手,口部分缺失,斜收至底,平底。口徑12、底徑8、通高5.4厘米(圖四︰5)。
托缽 1件(M1︰24)。盞斂口,深腹,與托盤成一體。盤圓唇,斜腹,平底。盞口徑4.4、托盤口徑8、底徑6、通高3厘米(圖四︰3)。
槅 1件(M1︰13)。分為內外兩部分,圓形,中空,內三格,外八格。直徑8.4、通高3.7厘米(圖四︰6;封三︰6)。

6.槅(M1︰13)
(2)俑 5件。皆為泥質灰陶,素面。
侍俑 2件。內穿圓領衣,外罩左衽寬袖外衣,衣裙曳地,體形較清瘦。M1︰5,束發,頭梳雙髻,手被帔帛狀物所遮。通高28厘米(圖五︰3)。M1︰3,頭戴小風帽,雙手拱于胸前扣合。通高27.2厘米(圖五︰4;封三︰1)。

圖五// M1出土陶俑

1.侍俑(M1︰3)
武士俑 2件。面相清秀,內穿圓領衣,外罩右衽寬袖外衣,寬肩,雙手并持一劍,衣擺曳地。M1︰6,頭戴小冠。通高31.8厘米(圖五︰1;封底)。M1︰4,頭戴平巾幘。通高32厘米(圖五︰2;封三︰2)。
人面神獸俑 1件(M1︰7)。泥質灰陶,素面。人面獸身,昂首蹙眉,頭戴雞冠狀帽,前腿直立,后腿蹲踞坐,兩腿略有殘缺。通高17.6厘米(圖六︰10;封三︰3)。

圖六// M1出土陶器

3.人面神獸俑(M1︰7)
(3)陶動物 9件,泥質灰陶,素面。
馬 2件。四腿站立,低頭,尾部朝下。M1︰8,長16.5、通高10.1厘米(圖六︰8)。M1︰9,長23、通高17.4厘米(圖六︰7;封二︰1)。

1.馬(M1︰9)
鴨 2件。腳下均踩一泥質餅狀底。M1︰14,直立,嘴部殘缺。通高6.4厘米(圖六︰5)。M1︰15,作低頭覓食狀。通高3.8厘米(圖六︰3;封二︰2)。

2.鴨(M1︰15)
雞 1件(M1︰16)。為公雞,直立昂首向前,腳下有一餅狀底。通高7.4厘米(圖六︰4;封二︰3)。

3.雞(M1︰16)
狗 2件。M1︰18,呈蜷臥狀。長7厘米(圖六︰2;封二︰4)。M1︰23,前腿直立,后腿蜷臥,臉部殘缺。通高6.1厘米(圖六︰1)。

4.狗(M1︰18)
駱駝 1件(M1︰20)。直立,目視前方,雙駝峰。長24、高19厘米(圖六︰9;封二︰5)。

5.駱駝(M1︰20)
牛 1件(M1︰22)。四腿站立,目視前方,尾部朝下,頭部略為殘缺。長23、通高16.8厘米(圖六︰6;封二︰6)。

6.牛(M1︰22)
(4)模型器 2套3件,均為泥質灰陶,素面。
磨 1套(M1︰10)。磨盤為扁圓形,中間凸起一圈,內有二小孔,磨臺呈圓筒狀,內中空,磨盤與磨臺相連部分及磨臺上有輻射狀線刻。磨臺外徑13.6、高 4、磨盤外徑 7.8、通高6.1厘米(圖六︰12;封三︰4)。

4.磨(M1︰10)
灶 1套(M1︰11)。略呈長方形,火門呈長方形,擋火墻呈階梯狀,灶臺長20.3、高8.2厘米。灶臺上有一灶眼,灶眼內有一釜,與灶臺連為整體。釜上置甑,甑口徑9.4、底3.4厘米(圖六︰11;封三︰5)。

5.灶(M1︰11)
3.銅器
(1)銅鏡 2件。M1︰26,殘為五塊,修復完整后呈圓形鼻鈕銅鏡,鏡面微凸,上有鐵銹痕跡,寬緣斜邊,緣層有一層弦紋。內區飾柿蒂紋相連,銘文僅可辨一字“吉”。直徑9厘米(圖七︰1)。

圖七// M1出土銅器
(2)銅錢 約12件。其中“永安五銖”9枚。M1︰28,圓形方孔,正面有內外廓,銹蝕嚴重。直徑2.2厘米(圖七︰2)。
三、結語
M1出土了較多的永安五銖。永安五銖鑄行于北魏永安二年(529年)。“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1]。墓葬未發現明顯的盜擾痕跡,其上限則可以定為永安二年。《通典》亦載其事,曰“官自立爐,亦聽人自鑄,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2]。永安五銖在發行時當為官民并鑄的情況。
關于永安五銖的廢止,“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以后,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冀州以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奸偽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3]。前世之錢用于后世,其例極多,故墓葬的下限只能以常平五銖的鑄行年代天保四年(553年)為參考。
M1共出土了4件陶俑,其出土時皆位于甬道兩側近墓室處,每側各二,前為侍俑,后為武士俑。這四件陶俑,面目清秀,形體瘦高,不同于鄴城地區所出土的陶俑,而是類似于洛陽傳統,亦或說是南朝影響下云岡風格的延續。宿白先生曾認為中原北方地區在造型藝術上有兩次大的變化:第一次為北魏孝文帝在平城推行漢化改制的時期,受東晉劉宋時期顧愷之和陸探微“秀骨清像”畫風的影響,云岡石窟佛像造型在太和十三年(489年)以后,從曇曜五窟深目高鼻、通肩右衽的西域影響,轉變為摹仿南朝士大夫形體清瘦、褒衣博帶的漢式服裝造型[4]。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遷洛以后,這一風格亦在龍門、鞏縣石窟中繼續流行。M1所出的四件陶俑,便是“秀骨清像”這一風格的典型表現。
如此便需談論徐州在南北朝時期佛學文化中的地位。湯用彤先生在論及北朝佛學時曾提到:“北方義學之淵源,孝文帝時,實為徐州為最著。”[5]在北魏時期,道融、慧義、東阿慧靜、僧嵩等諸位論學大師皆曾授學游歷于徐州及周邊。北魏僧淵的弟子知名者有四人,其中道登、惠紀、曇度等人皆為孝文帝所重,而僧淵初游徐州時,便在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6]。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曾親幸白塔寺憑吊僧嵩居寺,曇度更是“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元)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7],可見孝文帝之推重。孝文崇法,已深入義理,而平城佛教此時又倍受徐州影響[8]。佛學義理研究的繁榮,實際上也是徐州文化、經濟繁榮的一個側面體現。徐州在北魏時期為繁華之地:“(堯)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徹,由是,后更孫絡。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9]且青徐多術藝,其地在皇興三年(469年)入魏以后,不僅高僧北上,文藝亦徙平城,皇信堂、太廟、太極殿等的營建,皆與青徐營戶有關;青齊入魏以后,北方既獲得了南朝術藝,也便利了南北交往,為北魏的漢化的不斷深入提供了重要條件[10]。佛像造型秀骨清像以及褒衣博帶式的服飾,皆是南朝文化影響的結果,徐州便是這一影響路徑的重要節點。徐州長時間位于南朝政權統治下,即使在入魏以后,這一地區的造像風格,相對于平城與洛陽,也當最先受到南朝文化之沁潤。看似M1所出四件陶俑是云岡或洛陽影響下的結果,實乃徐州在前,而云岡在后,更毋論洛陽。
宿白先生所說的第二次變化,便是自南朝蕭衍建梁之后,“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南朝風尚一大變化,反映在造型藝術上便是張僧繇畫派“骨氣奇偉”,變重神骨為“得其肉”,變清瘦為豐壯。這一變化,在南齊已現倪端,南朝蕭梁逐漸發展,大約于梁武帝中期影響及北魏洛陽,并完成于北齊時期。洛陽城內永寧寺塔所出神龜二年(519年)的一批塑像,就與蕭梁人物極為接近[11]。北魏晚期洛陽地區元邵墓[12]、染華墓[13]以及東魏冀州地區高雅墓[14]所出陶俑,就是這第二次變化的直接表現。至東魏北齊時期,這一造型風格的運用更是極盡繁榮。
值得注意的是,永安五銖的發現將墓葬年代上限定為永安二年,其年代也自然晚于元邵墓(武泰元年,528年)和染華墓(孝昌二年,526年)。但M1所出陶俑,明顯屬于更早的流行造型。在洛陽乃至鄴城地區深受“骨氣奇偉”的造型特征影響的時候,徐州地區卻孑然而為一孤島。
M1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陶瓷器也有著明顯的南朝遺風,但其與同時期長江下游地區所流行的多小龕、直欞窗、棺臺之類設置的單室券頂墓[15]有著諸多差別,更似在單室券頂墓的基礎上獨立發展而來。溯尋其跡,可發現其形制與南京王興之夫婦墓[16]、南京劉宋明曇憘墓[17]乃至長江中游湖北枝江姚家港晉墓[18]基本一致,可略窺其對于東晉劉宋時期墓葬形制明顯的繼承關系。
M1所出盤口壺,其形制出現于東晉中晚期[19]。與其類似形制的器物可在枝江姚家港晉墓(M3︰25)、江西九江陶淵明紀念館東晉墓(I式盤口壺)[20]、江西大余元嘉八年劉宋墓(印紋陶盤口壺)[21]中發現,其流行年代大致在東晉中晚期至劉宋早期。與同時期南朝中晚期墓葬所出瘦高的盤口壺不同,M1所出盤口壺與墓葬形制一樣,皆保有著東晉至劉宋以來的傳統,而非同時期南朝齊、梁所流行的文化因素。
M1所出青瓷六系罐將六系橋形鈕、腹蓮結合,形制較為獨特。腹部雕蓮的青瓷罐,南北皆有發現。南朝有江蘇句容西斛村墓[22]、浙江瑞安天監九年墓[23],其制作皆不如M1精細。北朝墓中此類器物發現更多,也更為發達,如河北平山崔昂墓[24]、磁縣茹茹公主墓[25]、河南濮陽李云墓[26]。李云墓出土了青瓷六系罐、黃釉綠彩四系罐各2件,為北朝瓷器的精品,其中一件四系罐亦是將橋形鈕與腹蓮結合,其制作更較M1成熟。
劉宋泰始二年、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劉宋徐州刺史薛安都降魏,北魏始有徐州,自此淮泗之地盡為魏有,淮河以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自此先后被北魏奪去;南方則退守淮陰—壽陽一線,攻守之勢完全轉換。若依魏祚遷鄴的535年算起,期間徐州雖有短暫易手,此時屬魏已有近70年。但M1仍有著相當部分的南朝文化因素,且帶來這種因素的并非是與其同時代的齊梁政權。
如此可見M1所表現出的徐州北魏末至東魏初這一時期的文化,既區別于洛陽、鄴城,也不同于南朝。其墓葬形制、青瓷器乃至陶俑造型,皆繼承于東晉劉宋時期的南朝文化,即便在入魏以后,仍保有著這一文化特征而不作改變。繼續發展變化的南朝文化,在越過徐州影響至洛陽、鄴城時,這一文化特征亦未作改變。
歷來學者在論述北朝墓葬時,多將徐州歸于青齊地區,亦或將其概括為南北文化交流之地。但北魏太和改制之前,徐州已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中心地位。這種獨立的中心地位,日本學者早有關注[27]。徐州地區較具特色的文化特征,有著對于南朝傳統的強烈認可,即使在其入北魏后依然存在。但徐州地區的器物特征,與同時期南朝亦有著相當差異,徐州即使從南朝再受最新的影響,也不立即效仿,而是在汲取中保有著相當的獨立乃至排斥性。
早在漢魏之時,青徐豪霸即是影響政權穩定及北方統一的關鍵問題[28]。劉裕滅南燕后,原居青齊的王玄謨、申宣、垣護之等南遷徐州,劉宋政府亦利用徐州豪族以達到鎮撫青齊的目的[29]。淮北四州入魏以后,曾有大量豪族南遷郁洲,并成為蕭道成篡奪劉宋政權的關鍵力量[30]。但仍不乏諸如彭城劉氏之族留守徐州,并成為北魏政權控制地方的有力力量[31]。叢亭里劉氏在彭城有著龐大的宗族勢力,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南齊豫州刺史裴叔業進攻徐州,北魏即把徐州事務委任劉芳處理,以利用叢亭里劉氏影響,來穩定徐州形勢。劉氏在南北均有居官,且多與鄉里宗族保持聯系,以利觀望,而南北朝廷亦利用其穩定局勢,發展勢力。M1的墓主,或即與斡旋于南北朝之間的徐州豪強有關。
與此同時,青齊地區連帶徐州的豪族,多有騷動不安而意圖南叛者,亦成為南齊對抗北魏的重要陣地。《魏書·張敬叔傳》:“張讜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所勒送。”[32]《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于是徐州民桓標之、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蜂起為盜寇,聚眾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為主。”[33]《南齊書·李安民傳》:“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34]
但蕭齊政權并未與青齊豪族形成“王與馬,共天下”般的密切關系,淮北四州豪族離開桑梓故園南遷后,頗受南齊政權的擠壓[35]。相反的是,北魏太和年間采取漢化政策以后,北魏政權對于淮北四州的安撫頗為緩和。《北史·元鑒傳》:“鑒上書遵孝文之旨,采齊之舊風。”[36]北魏在全國范圍推行漢化政策,無疑會博得處于秦漢魏晉時期文化重心的青齊徐兗地區豪族的好感乃至認同[37]。孝莊帝永安二年,北海王元顥為梁武帝所遣,率兵北上,期間派使者與青齊豪族接觸,皆被其駁斥,且被視作“是作賊耳”[38]。
同時徐州在入北魏以后對洛陽仍有著相當的離心力,在其任者多有宗親。盡管如此,于洛陽乃至鄴城所言,徐州亦是避過良所。《北史·王遵業傳》:“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39]《北史·高乾傳》:“乾因勸神武受禪……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啟神武,求為徐州。”[40]
徐州豪族在接受北魏的同時,仍然保留著對于其所繼承的南朝文化的追求。徐州地區“秀骨清像”造型的存在,當由來已久。在平城以及洛陽通過徐州汲取南朝文化因素的同時,徐州對于洛陽的認可也在隨著北魏漢化的深入而逐漸加強。“秀骨清像”特征的造像,無疑成為這兩者糅合的最好載體。其既滿足了徐州豪族對于其追求的南朝文化,也表示了其對于洛陽政權的認同,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徐州在北魏晚期至東魏早期區別于其他地區的特色文化。這種發展,直到東魏尤其北齊時鄴城對于徐州控制的加強而削弱。
(項目負責人邱永生;發掘葉繼紅、滕雪慧、周波、賈飛;資料整理胡選奇、劉聰、謝琦、劉繹一;繪圖、拍照、拓片王音、賈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