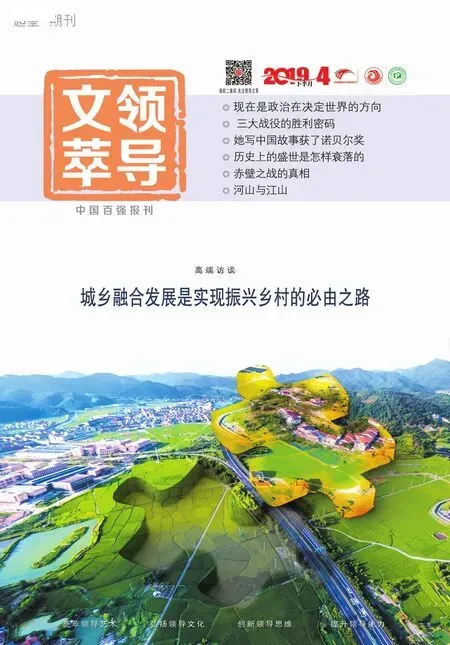和周總理在西花廳過年
周保章是周恩來堂弟周恩彥之子。1961年,周保章第一次到中南海西花廳過年,在與七伯、七媽七天短暫的相處中,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

1961年2月袁周總理與親屬們在西花廳合影袁右一為周保章
自己盛飯、縫被子
我到北京之后,和七伯七媽吃第一頓飯時,我邊吃邊觀察。我看到七伯的飯快吃完了,等他吃完最后一口,我馬上站起來,說:“七伯,我幫你盛飯。”七伯是長輩,我是晚輩,而且飯也不在跟前,我作為晚輩理應去做這些。但是,當我站起來,伸出雙手去拿七伯碗的時候,七伯把手一擋說:“不用,不用,我自己來。”
如此一來,我站在那里有些尷尬,我的手沒有接到碗。看我尷尬了,七媽鄧穎超打了個圓場,說:“保章,你坐下,你坐下。”七伯這時接著說:“自己能辦到的事,為什么叫別人呢?”
后來的一天下午,我從外面回來,一進西花廳內廳,就看到七媽拼著兩張桌子在縫被子。七媽是1904年生人,那時候57歲了,她眼睛不行了,所以我給她穿針上線,和她一起縫。
那時我就想,國家領導人,多么高的職位,身邊工作人員不少,西花廳里有秘書、衛士、醫務人員、炊事人員,還有專門的大師傅做飯,怎么七媽還要堅持自己動手呢?我心生很多感慨:一個是平等的精神,認為大家都是同志,是平等的;再一個就是七伯七媽沒有忘掉那么些年來所堅持的東西,不忘本。
年夜飯不設酒不擺菜
大年三十,總理家也和老百姓家一樣,要吃個團圓飯。這個團圓飯可是大家庭的團圓飯。七伯把北京市的親屬接過來,像周恩壽伯伯一家。另外,七伯還把總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連同他們的家屬都請來,有三四十人。
到了吃團圓飯的時間,桌上光有碟子、碗筷,其他什么都沒有。過了一會兒,我正納悶的時候,衛士通知了,說總理到了。總理從車里出來了,從后廳的側門進來的,工作人員也來了,他們拿來兩樣東西,小米稀飯和包子。就這兩樣東西,上得也很快,小米稀飯是大盆裝的,包子也是大盆大碗端上來的。
這時候,七媽向七伯會心地一看,七伯就站起來了。七伯說話很簡單:“今天年三十,請大家一塊來吃個團圓飯,感謝大家。”他說了以后,又往七媽那一看,七媽也會心一笑。七媽站起來說:
“今天是除夕,總理請大家來吃團圓飯,不設酒,不擺菜,總理請大家吃包子,喝小米稀飯。為什么呢?中國革命是靠小米加步槍取得勝利的,小米對中國革命立下了功,我們在歡樂的時候,不能忘了小米,不能忘了小米那個年代。
小米那個年代是什么年代?艱苦奮斗,英勇殺敵、不怕流血犧牲的年代,所以還是要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為什么能吃到肉包子,因為有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我們翻身做了主人,推翻了三座大山, 成立了新中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們今天才能吃到肉包子,所以我們不能忘了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
總理大年初一的窩窩頭
1961年的時候,七伯才63歲,身體好極了,走路跟一陣風似的,吃飯也很快。他吃完飯就坐在沙發上,小憩一會兒。他看我也吃完了,就把手一招,叫我過去。他問:“保章,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
我說我在青島,在工廠工作,是一名職工。七伯聽了很高興,還給我一些鼓勵。然后,他就問工廠的情況,工廠還能不能正常生產,工人的生活怎么樣,工人每頓飯吃的什么等等,問得很細。我就照實跟他講,沒有東西吃,農村很多人都非正常死亡。能吃到地瓜干就著醬油湯,就是好的了。沒有油水,什么菜也沒有,就是清湯寡水,不扛餓,能吃很多。
七伯聽到這個情況,臉色看起來很不好,很沉重。我知道他聽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年初一的午飯,就七伯、七媽和我三個人一起吃的。我一看,桌上擺放一個小碟子,盛了四個窩窩頭。我心想,大年初一怎么吃窩頭?我拿著筷子去夾窩窩頭。七媽把我的筷子一撥,說:“保章,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那邊有大米飯,你吃大米飯。”七媽沒讓我吃窩窩頭。
這時正是困難時期,糧食都是按照定量的比例來供應的。我意識到總理在國家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一樣,粗細糧搭配吃。后來,我發現他們不只是粗細糧搭配吃,而且也定量、定比例,老百姓怎樣,他們就怎樣,完全沒有特殊待遇。
一晚上一晚上地辦公
七伯的辦公室無關人員是不能進的,七媽一般也不進去,只有他的衛士、秘書等才可以進。我常看到七伯有很多的文件要批閱,一工作起來就不知道休息,常常需要七媽過來提醒他。每次七媽都是先敲敲七伯辦公室的門,然后把門推開,七媽一推開門就說:“恩來,你是不是應該休息一會兒了。”七伯會說:“好,好,好。活動活動。”我遠遠地坐在七伯對面,看到他戴著那個黑框的老花鏡、藍色的套袖在那兒忙著。
當時,用電是很緊張的。比如我們工廠,一個星期就三天有電。電那么緊張,所以當時對電的控制很嚴格,要求人走燈滅。 ? ?我剛到中南海的時候,看到西花廳總理辦公室整宿地亮著燈時,很奇怪,就問成元功叔叔:“怎么對面那四行窗戶老亮燈,一宿一宿地亮?多浪費電!”成叔叔說:“那是你伯伯還在辦公。”我當時還想,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嗎?要一晚上一晚上地辦公。
臨走的當天晚上,吃過晚飯后,我就想早點出發去車站。當天晚上七伯有事,沒在家吃晚飯,就我和七媽在家。吃完飯,七媽說:“保章,不要著急,你伯伯還沒回來。”
等了一會兒,外頭有動靜了,是七伯趕回來了。七伯三步兩步就到了我跟前,主動握著我的手說:“保章,今天晚上我有會,不能送你了。”七伯接著說:“希望你堅持在基層,多寫信來反映基層的情況。”說完這句話以后,他又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轉身就走了。等我回過神的時候,七伯已經出門了。
這個告別很簡短,頂多兩分鐘。但是這兩分鐘對七伯來說,都是要事先安排的。特別是忙的時候,說爭分奪秒也不為過,而且他的行程涉及的不只是他自己,還有好多工作人員。所以,這簡短的道別,對我來說是多么的溫暖和難忘!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