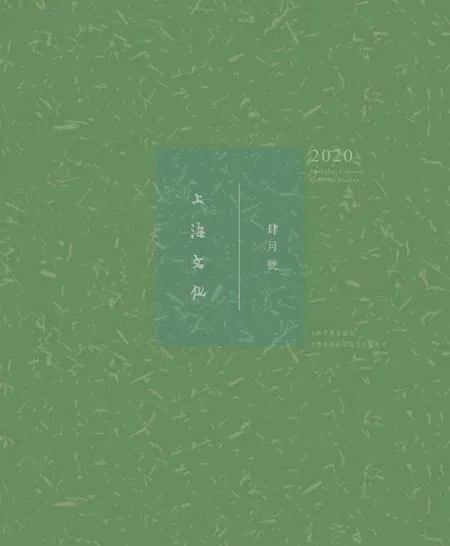明嘉靖《皇帝諭祭》任環碑:滬蘇抗倭真跡刻符
方漢文
古代碑刻的文字記載發現本身是一種“真跡”性的學術創新,這種真跡并不指個體的手寫,而是碑刻的文字,具有真實性與實物性。在比較文明史與文化遺址研究中,這種刻符真跡往往是公認可靠而學術評價較高的記載。但是這種真跡往往與歷史文獻記載存在差異,也引起歷史學家們的一些異議。法國考古學家列德(Michel REDDé)對這一問題的見解顯得相當深刻:“文獻學與考古學研究是和諧一致的,盡管不可避免地存著細節上的差異。但是這種差異是可以用文獻的功能的不同加以解釋的。”①列德(Michel REDDé):《文字記載與考古發現——阿萊西亞遺址給我們的啟示》,《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陳星燦、米蓋拉主編:《考古發掘與歷史復原》,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35頁。而解釋這種差異,更可以看出“發現”作為一種創新的價值在于補充或是校正文獻之不足,這也是一種真跡文本與傳世文本之間的互文性。明嘉靖《皇帝諭祭》任環碑是目前唯一的滬蘇地區明代抗倭御書碑,這種真跡刻符的流傳對于研究明代南北各地沿海進行的規模浩大的抗倭斗爭的歷史,有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
一、嘉靖皇帝真跡抗倭碑
此碑目前收藏在蘇州碑刻博物館,據稱是嘉靖皇帝的書寫真跡摹勒上石(據筆者考察明皇帝書跡,仍有刻碑人王道行等先書丹再上石的可能,碑文字跡與題目相同,體近館閣公文)。碑文題為《皇帝諭祭》,由于碑文內容是明嘉靖皇帝諭祭蘇松兵備、山東布政使任環,追認其領兵抗倭之功的,所以有稱《皇帝諭祭任環抗倭碑》等。
這塊碑刻樹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高185厘米,寬98厘米。碑的形制屬于明清以來在江南普遍流行的條石銘刻,與北方碑額、碑座俱全的漢唐巨碑有所不同。書丹字體秀潤中正,刀法清麗,是典型的江南刻石。碑文如下:

圖1 《皇帝諭祭》碑刻
皇帝諭祭:賜原任蘇松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參政、贈光祿寺卿任環曰:爾執掌兵司,適逢倭變。領眾破敵,保民奠境。建祠加贈,式表忠勞。時維仲春,特修常祀,尚享。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十□日直隸蘇淞□□□王道行等恭刻。
國際化的真跡銘刻研究方法的根本目標在于歷史化,從實物來切入歷史文明語境,而不僅僅是碑刻的解讀。正如美國學者柯馬丁在其近著《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中所說:“我試圖將石刻銘文所運用的表達模式納入周代(多為東周末年)的文學傳統之中……文本的譯注致力于石刻銘文的語境化。對秦代禮儀體系的考察則是為了將石刻銘文歷史化。”①柯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劉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頁。故而首先對石刻所記載的明代抗倭史,特別是任環作為“蘇松兵備”的語境作出分析。
據《元史·阿塔海傳》記載,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軍第二次征日,因遭遇颶風,“遇風舟壞喪師”,②《元史·阿塔海傳》,《二十五史》第7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99頁。元軍全軍覆沒。自此之后元朝雖然仍多次企圖征伐日本,但已經難以形成實質性戰果,直至徹底放棄征服日本的戰略。從此中日間政府外交關系斷絕了100多年,直到明朝建立之后,1404年中日雙方才又恢復政府間的外交關系。其實早自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年)起,中日海上貿易就開始出現危機,據日本學者田中健夫所述:“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元朝官軍不能抵抗。”③田中健夫:《倭寇——海上的歷史》,楊翰球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45頁。延祐三年(1316年)又發生“浙東倭奴商船貿易致亂”事件。《新元史·日本傳》已經開始將日本來犯者稱為“寇”,“惠宗至正中,日本屢寇瀕海州縣。二十三年(1363年),掠蓬州,萬戶劉暹擊敗之”。④柯劭忞:《新元史·日本列傳》,上海:開明書店,1935年,第7073頁。1523年發生了一次日本大名(諸侯)在寧波的“爭貢事件”,大內氏與細川氏兩位大名之間勢力爭奪轉化為動亂,發生焚燒商鋪,殺害明朝官兵的事件。表明“倭寇”進犯已經成為必然趨勢,而嘉靖年間(1522-1566年)被稱為“嘉靖倭患”時期。從1277年到1566年,倭患長達近300年,大小數百戰,山東、江蘇、浙江、廣東、福建沿海展開大面積的抗倭斗爭,這是明代最重要的對外戰爭。史書文獻記載相當多,但是真跡刻石卻并不多,多數碑石都是近年樹立的。明嘉靖《皇帝諭祭》是為數不多的真跡刻石,可能是唯一存世的皇帝真跡,其對于東亞文明之間的歷史關系的研究價值之珍貴,由此可見一斑。
二、任環與蘇松抗倭
任環(1517-1561年),字應乾,號復庵,山西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進士。歷知廣平、沙河、滑縣三縣。據蘇州地方史料記載,任環嘉靖三十年(1551年)遷蘇州府同知處,曾經在當地招募與訓練民兵,發給刀矛火炮、弓弩等,當倭寇進犯時率民兵與之作戰。只要看《明史·兵志三》就可以得知,明海防戰線漫長,“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閩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隸又千八百里,抵山東又千二百里,逾寶坻盧龍抵遼東又千三百余里抵鴨綠江,島寇倭夷在在出沒”。①《明史·兵志三》,《二十五史》第8冊,第238、239、238頁。
明代抗倭戰爭中官軍實力不足,特別是海防力量薄弱,主要采取引進三種兵力對抗兇殘倭寇:第一就是民兵,明太祖定江東后,即命“循元制,立管領民兵萬戶”。②《明史·兵志三》,《二十五史》第8冊,第238、239、238頁。蘇松是江東的核心地區,一直保持民兵團練能戰的傳統。此外山東等地也多次募民兵,多者一次萬人,少者也有數百人。第二是所謂客軍,多是從山東、河北等地的官兵,向東南沿海地區調集御寇。第三是一些有地方特色的軍隊,隨其風土所長,募集調佐軍旅。如善習短兵器的河南嵩山“毛葫蘆”、以英勇善戰聞名的川軍、泉州以技擊出名的永春習武兵等,最出名的是西南土司所領兵,廣西東蘭那地歸順的“狼兵”等。
《明史·兵志三》曾經說:“嘉靖中,倭患漸起。”③《明史·兵志三》,《二十五史》第8冊,第238、239、238頁。于是明政府加強防范,始設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都御史。而這時,蘇州與現屬于上海的松江一帶即明代蘇松兩府逐漸成為倭寇進犯的重點之一。我們不妨分析一下當時的戰爭語境。其一,唐代白江大戰中,唐軍大敗日軍。統一朝鮮半島于新羅,滅亡原日本支持的百濟。日本政府看到大唐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農業文明與尚處于漁獵社會向農業文明過渡中的日本國力懸殊,立即轉向大量派遣唐使,學習大唐文明。這一時期原來通過朝鮮半島的北路交通線改為南路,即以江蘇、浙江為主要交通口岸線,蘇州、寧波是兩大主要口岸。蘇州是長江入海口(通過太倉瀏河港入海)地區的商貿交通中心,這里是日本各方最熟悉的地區。
其二在于蘇松的經濟樞紐地位。蘇松是明代蘇州府與松江府的合稱。蘇州府是元代平江路屬江浙省,設常熟、太倉縣。松江府則是元直隸江浙行省,設華亭、青浦(曾置青浦上海二縣),松江府因起源于蘇州的一條河吳淞江得名,這條河從上海進入黃浦江。④《明史·地理志》,《二十五史》第8冊,第98頁。蘇州與松江兩府合稱蘇松地區,通常因為有吳淞江從蘇州起流向上海,也稱為蘇淞,也就是現在“滬蘇”的中心地區。從上海到蘇州沿吳淞江一帶為中心的廣袤水鄉平疇,這里良田相接,水網密布,江南古鎮星羅棋布,地處長江入海口,又有3萬頃太湖為依托,還與大運河相鄰,農業商業手工業發達,經濟繁榮,是當時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是長江三角洲的核心。明代倭患興起之后,蘇松成為倭寇進犯最頻繁的地區,他們在這里肆意掠奪,燒殺搶劫,終于導致了大規模的抗倭斗爭的發生。
其三是日本國內原因,明朝前期正值日本南北朝后期與戰國時代,國內動亂不休。其實早自13世紀起,日本北九州的武士浪人已經結成海盜集團,在朝鮮與中國海岸線搶劫商船與居民。南北朝時失敗的武士更是大批加入海盜,與明朝流亡海島的張士誠、方國珍余黨相勾結,初步形成了倭寇勢力。明朝政府則采取剿倭與禁海的政策,打擊了倭寇,但也中止了中日貿易。日本國小資源缺乏,從隋唐起就依賴中國外貿發展經濟,海禁對日本經濟影響極大。日本進入戰國時代(1367-1568年)后,此時的明朝吏治腐敗,嘉靖年間倭寇活動最為猖獗。海盜徐海、王直等“巨魁”囂張,部分海盜甚至與明朝浙、閩官僚勾結,迫害抗倭將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兵部尚書張經雖然取得嘉興王江浜(《明史》記為王家浜)大捷,殺敵近千,卻被嚴嵩奸黨害死。直到嘉靖末年在戚繼光與俞大酋、劉顯等名將協同作戰中,才最終解除倭患。
三、任環率軍楓橋抗倭
由于嘉靖年間“倭寇益肆”,朝廷不得不調整軍事力量以應對。尤其是蘇松抗倭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官府先是增設金山參將分守“蘇松海防”,而且“尋改為副總兵”。并且開始調撥各地精兵強將來回固海防,包括與蘇松地區緊連的杭嘉湖地區。此時任環遷蘇州府同知,可見正是為抗倭而來。嘉靖二十三年,又因戰事緊迫,再急調山東民兵與青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揚地區。與蘇松相鄰的江蘇北部的重鎮淮安從唐代中日南路開通以后,也是日船進行貿易的主要港口之一,所以也為重點防范地區。山東兵能征慣戰,聽從總督南道軍務都御史張經指揮,嚴防沿海。從戰略上看說,倭寇的特點是以海戰力量為主,海船機動性強,尤其是小規模轉移靈活。但是明軍民以陸地城防為主,火力強大。初期雙方各有勝負,甚至倭寇窮兇極惡,還在部分地區建立基地,“時倭縱掠杭嘉蘇淞,踞柘林城為窟,大江南北皆被擾”。①《明史·兵志三》,《二十五史》第8冊,第238、238頁。但在蘇松戰場上,任環長期訓練的軍隊終于在正確的指揮下取得決定性勝利,隨后張經的大軍再次獲勝,成功扭轉戰局。《明史·兵志三》記載:“監司任環敗之,經亦有王家浜之捷。”②《明史·兵志三》,《二十五史》第8冊,第238、238頁。這是正史記載的任環與張經最重要的戰功。有的史冊中記載了抗倭名將兵部尚書張經在杭嘉湖地區的“王涇(家)浜大捷”,柘林城(鎮)位于松江府,而王江浜則在嘉興的運河之浜,兩地雖然分屬蘇松與杭嘉湖不同區域,但實際距離并不遠。明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初張經、俞大猷帶領明軍各路人馬在王江浜大戰從柘林城來的倭寇,明軍大勝,取得殲敵2000余人的戰績。從時間上來看,是抗倭戰史上明軍從戰略防御向戰略上主動出擊的轉向。
從歷史記載可見,當時任環官職為“監司”,監司一職不同朝代各有所轄,宋代監司職務范圍相當廣,其監察范圍包括轉運司、提點刑事與提舉常平等相關法律事項。元明兩代監司職務更為重要,明清兩代吏治的布政使、按察使都具有監察權,所以在碑文中,嘉靖皇帝諭祭任環職務為蘇松兵備、山東布政司。按《明史·職官志》,蘇州總兵官1人,守備8人,其中任環為蘇松兵備,處于抗倭前線。光祿寺卿從三品,是較高的職務,光祿寺主管祭享宴勞酒禮膳羞之事,就是管天子祭祀的部門。這應當是任環立功之后所擢升的官職。
蘇松地方史料記載了任環指揮蘇州楓橋戰役的經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進犯蘇松海防,倭寇中有部分中國海盜,對中國沿海地理環境熟悉,而且這些海盜多年征戰海上,熟悉海戰與沿海強攻。當時是從海上先進入長江口,從太倉瀏家河港口上岸。這里到蘇州城的直線距離大約只有不足50公里,倭寇一直將戰火燒到蘇州門戶閶門與楓橋。蘇州學者引《江南經略》卷二中“楓橋險要說”描述當時戰事的形勢:“自閶門至楓橋將十里,南北二岸居民櫛比,而南岸尤勝……天下貨財莫盛于蘇州,蘇州財貨莫盛于閶門。倭寇垂涎,往事可鑒。楓橋北近射瀆、長蕩,南通虞塘、太湖。寇所熱中者,城內十一,而此地十九。”①參見陳瑩:《從蘇州碑博三方碑刻管窺中日關系史》,蘇州博物館編:《蘇州碑刻博物館三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第46頁。楓橋地區當時無險可守,軍事要塞楓橋鐵鈴關尚沒有建立,鐵鈴關建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即戰事之后3年,所以倭寇驟至,燒殺搶劫,楓橋城外的數十萬百姓被迫逃難,涌向閶門、楓橋。守城官兵居然關閉城門,拒絕百姓入城,后邊倭寇追兵將至,情勢極度危急。
此時任環在蘇松練兵已經3年,軍隊經過他的訓練與整頓,已大大加強。任環立即決定在此阻擊倭寇,他一方面命令立即開城門放百姓入城,另一方面布署新訓練的軍隊與倭寇拼死戰斗,最終成功擊潰倭寇。倭寇主力戰敗后,從蘇松地區逃離,狼狽竄向杭嘉湖地區。楓橋阻擊其實是蘇松地區首次大敗日寇,大挫日寇銳氣,捷報傳來,大大鼓舞了明軍與民兵。長期與倭寇對壘的杭嘉湖地區與蘇松土地相連,河流湖泊相通,都是大運河流經之地,也同位于太湖之濱,楓橋之役是王江浜大捷之前明軍的首次勝利,也是長期以來抗倭斗爭的轉折點,對王江浜大捷中明軍士氣的提升有決定性作用。
正因為楓橋之役有如此價值,所以嘉靖皇帝才要諭祭蘇松兵備任環,在抗倭名將中,他的官職與名聲都不算高,卻能有如此戰績也是實至名歸。
四、文本釋詞:“倭變”與倭寇
碑文中措詞“爾執掌兵司,適逢倭變。領眾破敵,保民奠境”,表明了朝廷關于抗倭斗爭的基本態度。特別是從“倭變”一詞中,可以看出從隋唐到明代中日關系的一個重要轉折。
中國對日本的稱呼在不同歷史階段各有不同:
第一階段是倭國、倭奴、東夷倭奴等,漢代之前的記載見于《山海經》等,稱其為“倭國”:“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郭璞注:“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為主,其俗露 ,衣服無針功,以丹朱涂身,不妒忌,一男子數十婦也。”②《山海經·海內北經》,郭璞注,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第143頁。
東漢時也有稱為“倭奴”,有一字之改。《后漢書·光武帝紀下》:“中元二年春正月……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③《后漢書·光武帝紀下》,《二十五史》第1冊,第633頁。
第二階段是唐代。初唐仍然以“倭奴”為國名,武周時期改為“日本”。《新唐書·東夷列傳》:“日本,古倭奴也……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①《新唐書·東夷列傳》,《二十五史》第4冊,第753頁。關于日本名稱的來由,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日本本國自稱所改,因為日本人惡“倭”名而又自謂位于“近日”的東方,所以自稱日本。另一種說法是由武則天所改定,稱倭奴為日本。日本名稱自唐代開始普遍使用,這是一個新稱呼,也標志著中日關系的一個新時期。由于對“日本”國名改動這一重要事件沒有真跡刻符的證據,僅有文獻中的變化,一直令人感到遺憾。直到2004年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收藏的《井真成》墓志發現,在非文獻之外的石刻墓志中,首次直接出現“日本”國名,而且是在日本僧人墓志的銘刻上。志文記載:“公姓井,字真成,國號日本。”②參見拜根興:《石刻墓志與唐代東亞交流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6頁。

圖2 《井真成墓志》(現藏中國西北大學)
井真成于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去世,至少在此前“日本”國名已經為唐代朝野俱識,否則不會有墓志公開記載。唐代開始“日本”國名取代漢以來的“倭國”,并且后世也至此有了真跡刻符的證據,這是比較文明史的一個大發現。
第三階段是明代。日本海上來犯的武士與浪人及所有海盜被稱為“日寇”,并且普遍使用。這里要說明兩點:其一“倭寇”一詞主要被用來指海盜,與日本政府并不能相等。由于倭寇罪行嚴重,引起中國軍民憤怒,經常被用來泛指包括所有與華敵對的日本人,包括一些官吏與商人。但是中國官方文件仍然是將海盜與日本政府有所區分的。而《皇帝諭祭》碑中雖然是指稱倭寇,但是沒有出現這個稱呼,而是用了“倭變”,將倭寇進犯改為邊患襲擾的事件,從中可以看出嘉靖皇帝本人對倭患觀念及處理的基本態度。一方面對倭寇進犯已經深感焦慮,所以諭祭任環等抗倭將領,并且使用“倭變”來指倭寇進犯。另一方面,則仍將倭寇與日本政府相區別開來,沒有采用“倭寇”的稱名。
“倭寇”一詞最早是何時首次出現?卻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
答案同樣是由刻符真跡所提供,日本學者田中健夫說:
最早出現“倭寇”這一名詞的史料,據管見所及,是高句麗廣開土王(好太王)碑,“倭寇潰敗,斬殺無數”,不言而喻,這里的“倭寇”與中世的“倭寇”并不一樣,它的意思可以說是“日本侵略軍潰敗”。③田中健夫:《倭寇——海上歷史》,第8頁。
《好太王碑》(亦稱《好大王碑》)樹碑年代為公元414年(東晉義熙十年),是高句麗第20代王長壽王即位后第二年為其父談德即好太王(374-413年)所立。碑石現存吉林省集安市,漢字隸書。①藝美聯主編:《好大王碑》,北京:中國書店,2018年,第56頁。高句麗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逸周書·王會》晉孔晁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雖然號稱從周代存在,但其古代部族的正史記錄卻是公元前37年(漢元帝建昭二年)朱蒙(即《漢書王莽傳》的“騶”,也就是《好太王碑》中的鄒蒙)建國,其實就是從夫馀部族分離的。所以漢武帝滅朝鮮時高句麗仍然是一個未興盛的民族,《后漢書·東沃沮傳》說:“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為玄菟郡……徙郡于高句麗西北。”無論如何,“倭寇”一詞最早出現于公元5世紀的中國東夷高句麗《好太王碑》是無疑的。這又是真跡刻符對中日比較文明史的一個重要發現。而日本學者田中健夫的判斷也是正確的,當時“倭寇”一詞是指入侵朝鮮半島的“日本侵略軍”。他所說的“中世”就是指明代的“倭寇”,中世倭寇指海盜集團,也是明確無誤的。必須說明的是,“倭寇”一詞雖然起源相當早,但由于時代的不同,所指完全不同,古代指入侵日軍,中世指海盜。到了20世紀的抗日戰爭,日寇之名再次出現,此次是指侵華日軍。能指所指、語境都有真跡刻符的思想史觀念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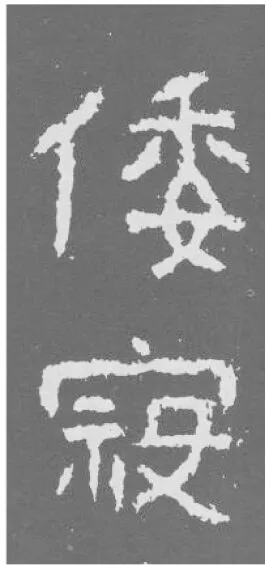
圖3 《好太王碑》局部(現藏吉林集安)
《尚書·呂刑》:“群行攻劫曰寇。疏曰不寇賊(引者注:不為寇賊的意思)。”
《易解》:“坎為寇盜。虞注致寇至。”
從經典釋文來看,寇是有貶義的詞,就是強盜,主要指群體性的結伙搶劫攻剽行為,性質是暴力性的團體。倭寇當然指明代的日本海盜,他們群體性地對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暴力侵犯搶掠。元末明初“倭寇”一詞即開始出現于民間與史冊。《明史》中的抗倭將領包括胡宗憲、譚綸、戚繼光等人的傳記中普遍使用“倭寇”一詞是完全正常的。
而嘉靖皇帝在碑文中所用的“倭變”一詞,則是指明代日本海盜所造成的世事變故。自唐后政治話語中用“日本”以來,用“倭”來稱呼日本人明顯減少,而此時恢復用“倭”,當然是含有貶抑意思。但是沿海倭寇主要是海盜而不是日本軍隊,戰爭也不是兩國正式交戰,所以用了“倭變”。畢竟明代倭寇入侵并不是兩國宣戰,皇帝諭祭也不是宣戰文書,所以碑文中沒有用“倭寇”而代之以“倭變”,這也是嘉靖的一種策略,代表中國官方是將倭寇與日本政府區分開來的,而且也表達倭寇只是中日關系中的一股逆流,并不可能逆轉歷史上中日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鑒。
事實上,明洪武二年(1369年)與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曾經兩派使臣與日本懷良親王協商,要日本政府出面來禁止倭寇,懷良親王和足利義滿與明朝關系不睦,雖然也曾將倭寇首領多次嘉靖《皇帝諭祭》碑用“倭變”,而明代的文獻中特別是民間抗倭斗爭中則常用“倭寇”,兩詞的交明處理,但并未全力禁倭。明成祖朱棣與足利義滿達成“勘合貿易”的朝貢形式,這一形式達百年,倭寇雖未絕但尚不足以危害邦國。嘉靖二十七年(1572年)勘合貿易停止,日本國內進入戰國時代,倭寇得到國內大名的支持,大興進犯,《明史·日本傳》指出由于中國海盜王直、徐海、陳東、葉麻素等勾結倭寇,為虎作倀,倭患日益嚴重。日本政府受到大名控制,大名公開豢養海盜,強掠中日商船與沿海財富,從中獲得各種利益。
中日文明互鑒仍然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明朝300年間入明僧多達114人,不但與中國僧人交流、學習佛法,而且居留中國學習中國文化,樂在其中。名僧大德甚至代表幕府,向中國皇帝明成宗面呈國書。永享四年(1436年)擔任遣明正使的天龍寺僧龍室道淵本是中國寧波人,30歲渡海傳法,歷住安國寺、圣福寺等名寺。永正八年(1511年)任遣明正使的東福寺僧了庵桂吾來時已是年逾80的名僧,率3條大船共292人,載著名的倭刀8000把,其他貨物滿倉。明武宗聞訊大喜過往,立即敕住持育王山廣利寺,并賜金袈裟。其返回日本時已經89歲,明大儒王陽明親自送行并作《送了庵和尚序》。日本僧人不僅精通佛法,而且深入鉆研漢學,很多人在中國學習多年,詩文書畫俱佳,與中國名士互訪交流,帶大批中國經典回國,傳播中國文化。而商業經濟發展是明代中日交往的基礎,勘合貿易(1401-1551年)150年間日本竟派19次遣明使,次數與遣唐使相同。人數就遠遠超越唐代,景泰四年(1453年)第11次遣明使人數為1200人。遣明使從中國所得銅錢多達數十萬貫,對于當時的日本經濟來說,這是極大的一筆海外收入。除了政府貿易之外,民間貿易發展更是令人驚嘆,有關資料統計:日本慶長十七年(1612年)7月25日,僅一天進入長崎港的明商船就有26艘。中國與日本的商業航線是當時最繁忙的,商貿交易量之大不僅是東亞,就是在世界商業中也是罕見的。可以說,中日人民之間的交往與文明互鑒是最終消除沿海倭患的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