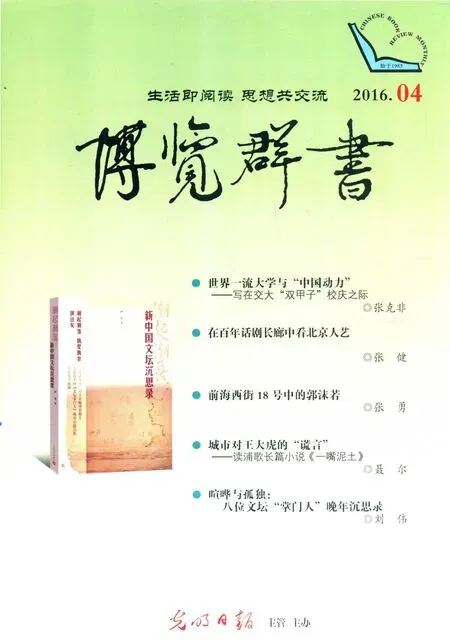不要把《鼠疫》看成“英雄贊歌”
2020-05-14 13:48:40李曉林
博覽群書
2020年4期
關鍵詞:小說
李曉林
作為最早向法國文壇介紹卡夫卡的哲學家,阿爾貝·加繆對于卡夫卡的作品可謂了然于心。正如加繆《弗蘭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誕》一文所言,卡夫卡小說既有深入骨髓的荒誕意識,又暗含著希望,二者如影隨形不可分割。加繆的小說同樣如此。加繆始終有清醒而深刻的荒誕意識,這種荒誕意識貫穿了他所有的作品。學界傾向于認為,作為加繆最出色的兩部小說,《局外人》體現出個人主義的冷漠疏離,《鼠疫》則是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的頌歌。這種看法未免割裂了加繆的反與正、陽光與苦難、荒誕與希望的辯證法,也割裂了兩部小說的內在聯系。
·鼠疫何來·
希臘神話中,瘟疫與人的罪惡有關,瘟疫是罪惡招來的神之懲罰。取材于希臘神話的著名悲劇《俄狄浦斯王》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可怕的瘟疫突然降臨到忒拜城,國王俄狄浦斯求得的神諭是,必須找到殺害先王的兇手,才能解除災禍。
那么《鼠疫》中的“鼠疫”,也是由于人的“罪惡”招致的“懲罰”嗎?加繆作為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者,不會從“罪”與“罰”的角度理解瘟疫。小說中的里厄醫生與朋友塔魯的一番嚴肅交談,可以看出加繆對于瘟疫的立場。里厄反對將鼠疫理解為“集體懲罰”,反對把療救的希望寄托于禱告,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治療患者、解除他們身體的痛苦。
既然不是從“罪”與“罰”角度理解鼠疫,那么《鼠疫》是記載了現實中一場可怕的公共衛生事件嗎?加繆這部小說寫于20世紀40年代,社會背景是納粹勢力興起,并不是對于歷史或現實中瘟疫的記錄。……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