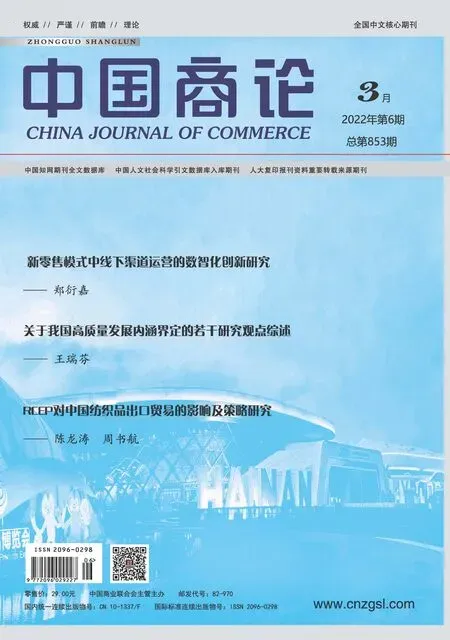雙重環境規制對不同進入動機FDI的影響效應研究
趙君麗 劉江薇



摘 要:本文構建環境規制綜合指數,考察了環境規制對于FDI的影響效應。全國樣本數據檢驗顯示:正式和非正式的環境規制對垂直型FDI呈現負效應,對于水平型FDI影響不顯著。門檻效應方面,只有正式環境規制對于垂直型FDI存在顯著的單門檻效應,說明正式環境規制與垂直型FDI存在非線性關系,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強,對于垂直型FDI的抑制作用上升。
關鍵詞:正式環境規制? 非正式環境規制? FDI類型? 門檻效應
中圖分類號:F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298(2020)03(b)--05
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近三年連續下滑的背景下,中國的FDI流入持續增長,2018年增長4%,達1390億美元,規模位居世界第二(錢志清,2019)。但相關環境問題凸顯,《2018年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中國62.4%以上的城市大氣環境質量不達標。《2018年環境績效指數報告》顯示,中國EPI(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得分為50.74分,在180個經濟體中僅排名第120位。在綠色發展理念下,通過環境規制協調FDI與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各級政府的重要舉措,正確認識環境規制影響FDI的效應,可以在新一輪深化改革中,利用環境規制優化FDI結構,促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
本文在現有的學術研究基礎上,從環境規制的類型和FDI的類型兩個方面,綜合考查了環境規制對FDI的影響。一是從全球價值鏈的新視角考察了雙重環境規制(正式環境規制和非正式環境規制)對于不同環節FDI的影響效應的差異。二是方法上構建了環境規制綜合指數。單一環境規制指標難以全面反映環境規制的綜合影響,因此本文建立了環境規制綜合指數,采用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人口密度三項指標的加權平均值測度非正式環境規制;通過污染治理投入和污染治理結果等六項指標測度正式環境規制。三是對于雙重環境規制的影響進行了門檻效應檢驗,發現了影響的非線性特征。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1 雙重環境規制對不同類型FDI的影響效應
本文參照Markusen(1984)將全球價值鏈下不同環節FDI分為兩類:從事市場開拓環節的水平型FDI和從事低成本制造環節的垂直型FDI。水平型FDI指在東道國投資以規避高額關稅和貿易壁壘,其最終產品主要在東道國本地銷售。垂直型FDI是基于要素稟賦差異將低成本制造環節布局在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其產品主要用于出口其他國家。
研究正式環境規制對于垂直型和水平型FDI影響的文獻很少。以開拓市場為目的的水平型FDI,由于與其他外資企業和本地企業同樣受到東道國環境規制的影響,正式環境規制對于水平型FDI的影響不大。垂直型FDI由于正式環境規制增加了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本,進而會影響其進入決策(魏瑋等,2017)。非正式環境規制主要產生于社會公眾與輿論壓力,隨著一國居民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人口密度的提升,人們的環保意識逐漸增強,衍生出對高質量環境的需求,提高了非正式環境規制的影響力。對于水平型FDI而言,其與東道國的競爭企業面臨同樣的非正式環境規制壓力,非正式環境規制不會對其產生顯著負面影響。而垂直型FDI面對沒有非正式環境規制壓力的國外競爭對手,會處于明顯劣勢,非正式環境規制的加強可能迫使垂直型FDI進行遷移。基于上述研究與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H1:雙重環境規制對于水平型FDI作用并不顯著,而對于垂直型FDI具有顯著負向效應。
1.2 雙重環境規制對FDI影響的門檻效應
針對環境規制的門檻效應,學者們的研究差異較大。一些學者認為FDI能為發展中國家引入先進的技術,改善其產業結構,提升當地能源使用效率與生產能力,因此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環境質量的改善(原毅軍和謝榮輝,2014)。還有學者認為環境規制對FDI的影響效應呈“U”型,拐點之前環境規制對FDI具有負向效應,拐點之后則具有正向效應(傅京燕和李麗莎,2010)。但是對于不同動機FDI的影響的門檻效應的研究幾乎沒有。水平型FDI企業與東道國企業面臨相同環境規制,隨著環境規制的加強其對水平型FDI的影響程度可能不會發生明顯變化;垂直型FDI環境規制使FDI企業相對生產成本增加,基于波特假說,可能存在若干個關鍵值,當環境規制強度跨越該關鍵值時,其對FDI的影響方向或影響程度發生明顯變化。由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H2:雙重環境規制對于垂直型FDI存在門檻效應,對于水平型FDI不存在門檻效應。
2 環境規制水平與不同類型FDI的測度
2.1 環境規制水平的測度
2.1.1 正式環境規制強度的測度
本文參照傅京燕(2010)構建綜合指數來對環境規制強度進行測算,綜合指數法能全面準確地衡量環境規制嚴格程度,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構建正式環境規制綜合指數(ERS)評價體系。包括一個目標層(ERS綜合指數)和兩個評價對象(污染治理投入、污染治理結果)構成。
第二步,對各項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對相關指標按[0,1]的范圍加以轉換,以避免指標間的量綱影響。對于與所衡量的程度呈正相關的指標,即污染治理投入的各項指標標準化計算方法為:
對于與所衡量的程度呈負相關的指標,即污染治理結果的衡量指標,標準化計算方法為:
第三步,采用等權重加權線性綜合法構建ERS綜合評價指數。計算公式為:
(1)
其中, N代表所有基礎指標的總數, N1代表污染治理投入的基礎指標個數, N2代表污染治理結果的基礎指標個數,且。
近年來中國正式環境規制ERS綜合評價指數呈增長趨勢,其中在2009年出現下降后又繼續上升,這可能與中國2008年的經濟危機有關,嚴峻的經濟形勢使得環境污染被動降低,從而環境規制水平也相應出現下降。
2.1.2 非正式環境規制強度的測度
非正式環境規制的強度通過居民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人口密度加以衡量(Wheeler & Pargal,1999),三者均與環境保護行為之間具有正向關系,分別采用地區大專以上勞動力數量占該地區總人數比重、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及每平方公里人數衡量以上三項指標,并對各項指標進行標準化求得加權值。三大經濟區的非正式環境規制強度呈上升趨勢,與正式環境規制情況相似,東部地區非正式環境規制強度最高并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水平最低。
2.2 不同類型FDI的測度
由于缺乏足夠的微觀層面外商投資企業數據,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的度量一直是個難題。本文借鑒Beugelsdijk等(2008)的研究,采用外商投資企業在不同市場的銷售收入來度量不同進入動機的FDI。水平型FDI進入動機是打開中國市場,因此用FDI企業在中國市場的銷售收入來度量水平型FDI的發展水平。垂直型FDI的主要動機是利用中國的各種資源來提升垂直分工生產效率,屬于出口導向型,因此用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銷售收入來度量垂直型FDI。文中,分別用HF和PF代表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用PHF、PVF分別代表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與GDP的比值。
2005—2017年全國范圍內的FDI占比先上升后波動下降。水平型FDI自2005—2017年快速上漲后整體波動范圍不大,而垂直型FDI在金融危機前后呈現大幅下降趨勢。從區域差異來看,東部地區的垂直型FDI與全國范圍內FDI呈相同變化趨勢,在2007—2009年呈較快下降趨勢,后呈緩慢下降趨勢,且與中西部相比占比較大,西部地區次之,中部地區最小。
3 實證模型與數據來源
3.1 模型構建
3.1.1 面板模型
為了檢驗雙重環境規制強度對不同環節FDI的影響效應,本文將前文測算的水平型和垂直型FDI作為被解釋變量,以正式和非正式環境規制為核心解釋變量,引入市場規模等控制變量,并將各變量進行對數處理。設定模型如下:
(2)
(3)
其中,PHF和PVF分別表示i省份第t年的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FOR和INFOR分別表示i省份第t年的正式環境規制和非正式環境規制; Xit為控制變量。
3.1.2 門檻模型
在環境規制分析中要明確“合理的環境規制”這一前提,不合理的環境規制會提升企業成本產生擠出效應。本文基于Hansen(2002)研究發展的面板門檻模型來對前述分析加以驗證設定模型如下:
(4)
其中,d為示性函數,q為門檻變量,為待估計門檻值,,分別表示當和時環境規制對FDI發展水平的彈性系數。以上為單門檻模型,多門檻模型與之類似,在此不予列示。
3.2 數據來源與指標設定
被解釋變量選取前文測算的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分別記作PHF和PVF。
核心解釋變量為雙重環境規制強度,具體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環境規制。正式環境規制強度通過構建ERS綜合指數體系衡量,記為FOR;非正式環境規制強度通過居民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人口密度加權值加以衡量,記為INFOR,具體指標在前文已經進行測定。
控制變量包括(1)市場規模(GDP):市場規模是吸引外資企業到東道國投資建廠的主要因素。選取各省份的人均GDP度量其相應的市場規模。(2)貿易開放度(OPEN):一國或地區的對外開放水平反映了其融入全球經濟的程度,選用地區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各省份的貿易開放水平。(3)非國有企業發展狀況(MKT):部分跨國企業為了打開中國市場會選擇合資的方式進入,而中國合資方更多的是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可能會影響水平型FDI。本文選用非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值度量非國有企業的發展狀況。(4)交通設施(INFR):交通設施越完善,企業的運輸成本也就越低,使之更具競爭力。本文以各省市鐵路和公路里程占土地面積的比重表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
本文指標選取中國 2005—2017年共13年的30個省、市和自治區面板數據,樣本量共計390個。各相關變量數據選自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勞動經濟年鑒》。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全國數據估計結果
在進行面板模型實證分析前,為保證估計結果的有效性需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 LLC針對同質面板假設,IPS、Fisher-ADF和Fisher-PP則針對異質面板假設,本文同時通過上述四種方法進行檢驗。經過1階差分后各變量均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原始序列為一階單整序列,可直接進行后續計量分析。接下來采用Kao檢驗對原始序列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因此認為面板數據間存在均衡關系。
進行實證分析首先需要確定選取的模型,對模型進行F檢驗以確定選擇混合模型,還是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P值為0.000,表明應選取固定效應模型;其次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也顯示P值為0.000,因此拒絕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選取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適。綜上分析通過固定效應模型來研究雙重環境規制對FDI的影響效應。通過采用Driscoll & Kraay(1998)提出的“異方差—序列相關—截面相關”模型有效解決組間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問題,并引入時間虛擬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實證結果如表4所示。
水平型FDI回歸模型中,解釋變量雙重環境規制對水平型FDI的影響并不顯著,這與前文的分析預期一致。由于水平型FDI企業競爭對手是國內的企業,其與國內廠商面臨相同的環境規制強度,環境管制強度的增加對其造成的生產成本上升與國內企業相差無幾,因此其對于環境規制強度變化的反應并不顯著。垂直型FDI回歸模型中,正式和非正式環境規制均會對垂直型FDI產生顯著負面影響,這也驗證了“污染避難所”假說的存在。垂直型FDI企業的競爭對手是國外的同行業企業,如果其競爭對手所處國家的環境規制強度不變,而中國的環境規制強度提升會增加垂直型FDI企業的相對生產成本,最終可能會促使其向環境規制較為寬松的國家轉移。
在控制變量中,市場規模對垂直型FDI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中國實際GDP的提升會促進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從而為垂直型FDI企業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貿易開放度對于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一結論與前文分析一致,說明一國的開放程度確實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重要影響,是外商企業進入時區位選擇的重要考慮因素。非國有企業發展狀況提升對垂直型FDI具有負面效應,這是由于FDI企業大多以國有企業合資方式進入中國市場,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會對其產生阻礙作用;交通設施對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均產生正向影響,但效果并不顯著。
4.2 門檻效應檢驗
環境規制對于垂直型FDI確實起到顯著抑制作用,但這種抑制作用的強弱是否會隨著環境規制的加強而愈發顯著,特別是正式環境規制這種強制性的手段是否需要有一個合理的范圍,還是力度越大效果越好,則需要進行進一步的驗證。經過實證分析,非正式環境規制門檻效應并不顯著,故在此不做特殊分析。選取正式環境規制綜合評價指標對數LFOR作為門檻變量,結果均顯示單一門檻效應顯著,而雙門檻效應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正式環境規制對FDI的影響被劃分為兩個區間,環境規制對水平型FDI的作用方向在門檻值左右兩側均為負向,且門檻值左右兩側系數估計值絕對值增大,然而其效應并不顯著。而正式環境規制對垂直型FDI影響效應的門檻值為-0.9169,環境規制的參數估計值在門檻值左右兩側有顯著差異,表明正式環境規制與垂直型FDI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當正式環境規制強度低于-0.9169時,環境規制系數為-0.362,但影響效應并不顯著。當正式環境規制強度高于-0.9169時,環境規制系數為-0.866,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與較低程度的環境規制相比,環境規制依然對垂直型FDI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而絕對值的增加說明這種抑制作用顯著增強。即隨著正式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強,對于垂直型FDI呈現“絕對值擴大”的特征。
5 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從全球價值鏈這一新的視角,對雙重環境規制和FDI環節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再檢驗,豐富和拓展了吸引外資與環境治理關系的研究。研究發現(1)從全國樣本數據看,正式環境規制和非正式環境規制強度呈上升趨勢,兩種環境規制未對水平型FDI產生顯著影響,但是對垂直型FDI產生明顯抑制作用。(2)門檻效應反面,正式環境規制對于FDI的影響效應分為兩個區間,對于垂直型FDI影響呈現顯著的單門檻效應,這也從環境規制加強的角度解釋了追求低成本的加工制造型外資轉移的現象。針對以上發現有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制定針對性監管措施。地方政府長期致力于通過吸引外資促進經濟增長,而各地區的環境規制力度可能對FDI產生顯著差異化影響,垂直型FDI可能更傾向于進入環境規制較為寬松的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在引進垂直型FDI的過程中,應注意加大環境監管督查力度;而水平型FDI傾向于進入市場規模大的東部地區,東部地區應進一步提升市場開放水平,如加強自貿區等建設,吸引更多優質的水平型FDI進入,更好地發揮FDI的溢出效應。
第二,重視非正式環境規制的作用。作為正式環境規制的關鍵補充,非正式環境規制在環境保護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民眾的環保意識是非正式環境規制的基礎之一,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等因素都會對民眾的環保意識產生影響。例如,上海作為收入水平較高、教育程度較高、人口密度較大的城市,非正式環境規制影響較大,目前實施的垃圾分類處理進展較為順利。政府應采取相應措施增強居民環保意識,大力推行環境信息公開制度,為公眾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提供有力保障,提高非正式環境規制對FDI企業的約束力。
參考文獻
[1]Porter M E and Van der Linde C, 1995,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4).
[2]Tang J,2015, “Testing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Does The Type of FDI Matter?”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60(4).
[3]傅京燕,李麗莎.環境規制、要素稟賦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實證研究——基于中國制造業的面板數據[J].管理世界,2010(10).
[4]魏瑋,周曉博,薛智恒.環境規制對不同進入動機FDI的影響——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國際商務,2017(1).
[5]原毅軍,謝榮輝.環境規制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研究——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中國工業經濟,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