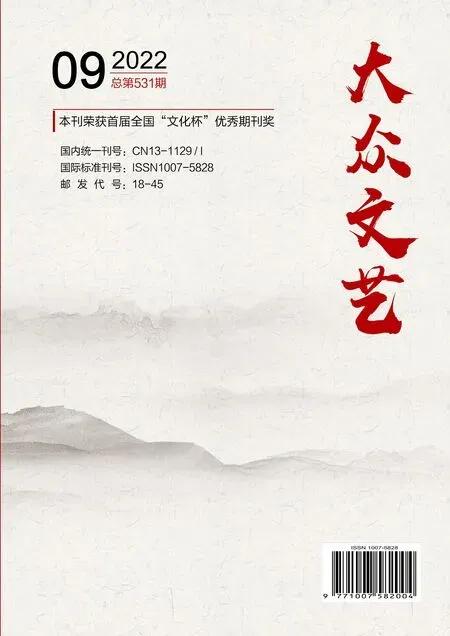和聲的色彩
——解讀拉威爾《丑角的晨歌》和聲特征
黃 珩 (四川音樂學院 610021)
《丑角的晨歌》是法國作曲家拉威爾·莫里斯于1905年創作的鋼琴組曲《鏡子》中的第四首,該組曲代表了典型的印象主義音樂特征,而這首作品也是整個組曲中最出色、最具有異國情調的一首。19世紀后半葉新興的音畫體裁是《鏡子》這部組曲主要的創作手法,在這部作品中,拉威爾強調了印象派的旋律化作曲特征,并且還在體現旋律化特征的同時,在和聲的使用上也做出了創新—即繼承了古典功能和聲的精華,同時又沖破了古典功能和聲的功能屬性的制約,加入了作曲家自己的全新色彩和聲的使用及碰撞,也以此成為了拉威爾和聲風格的重要轉變。正如他自己所言:“《鏡子》標志著我在和聲演變中一次相當大的變革,從個人消除了過去按照慣常方式進行創作的窘迫感。”本文以對作品和聲風格特點的全面研究,分析作曲家使用的印象主義時期的典型和聲手法,例如高疊和弦、模糊調性、民族調式、不協和音碰撞等等,通過以點蓋面的研究方式,從而達到研究拉威爾這一重要和聲語匯發展時期的目的。
本首作品結構相對短小,符合印象主義音樂的基本特征,從樂曲結構來看是一個典型的三部曲式,準確地說是一個縮減的復三部曲式,作曲家在再現時省略了首部的第一部分,作品保持了傳統曲式結構的框架,但內部結構處理的更具特色,通過適當的變化形成了不規則的曲式結構,以此來體現曲式上的傳統與更新。其中,首部為1-70小節,是一個綜合型中段的三段曲式結構;中部為71-165小節,是一個由三段組成的多段并列曲式結構,并且變化重復了后兩個樂段;再現部為166-229小節,縮減了首部的第一段,使原本首部的三段式結構變為了一個無再現的二段式結構。
本文主要對該首作品的調式使用特點及和弦使用特點進行分析,以期在專題研究上對本作品的和聲運用有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
一、調式使用特點
拉威爾在本首作品中,除了傳統大小調式的運用之外,還使用了嶄新的印象主義音樂中最具有特色的全音調式,并且他還從五聲調式、古老的教會調式、以及西班牙調式等各類調式中汲取養分,使得調式在傳統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擴展。當然,在本首作品中最重要的調式使用特點是作曲家將古老的教會調式以及富有濃郁西班牙民族風格的西班牙民族調式相結合,形成了特殊的西班牙調式音階,并且將該音階的使用貫穿整個音樂,從而達到奠定整首作品基調以及渲染調式色彩性和聲效果的目的。
首先,在樂曲的一開始就使用了帶有小丑歌舞主題的舞蹈節奏來描寫小丑的步態,以及模仿了西班牙吉他的快速撥弦。在這段音樂里,d弗里幾亞調式就作為了主要調式出現,但是在作曲家使用的d弗里幾亞調式中,又多次出現了bE、#F、#C這三個音,這三個音的使用就使這個音階中出現了兩處增二度音程結構,這兩個增二度音程也就成為了這個調式中最富于西班牙特色的特征音程,從而d弗里幾亞調式就演變為了西班牙民族音樂中一種特有的調式音階,
例1:d弗里幾亞音階

西班牙特殊調式音階

作曲家對該調式的調性明確做出了充分的鞏固和發展,我們可以總結認為作曲家這種有意識的調式變體 ,形成了較為典型的d弗里幾亞西班牙調式特殊音階,這種調式音階所產生的作用除了能給音樂帶來濃郁的西班牙民族音樂特色以外,也模糊了調式音階原有的固定性,產生了印象主義特有的朦朧感和游離感。
那么作曲家就完全摒棄了大小調式的運用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作曲家在這種調式創新的同時,也很好地繼承了傳統的調式和聲思維,并沒有完全摒棄調性和主音的使用方法,通過對作品地分析,我們仍然能夠很清晰地找到全曲的主音——D,作品一開始就出現了主音的持續,并且該主音一直保持到音樂的結束,而且作品最后終止在一個以D為根音的大三和弦上,從調式的角度觀察,可以感受到此處會有明顯地結束在D大調上的調式終止感,并且在第228小節,出現的bsi音剛好可以看作是D大調的bⅥ級,典型的和聲大調特征,調式感的強調愈加明顯。但是這么突出的調式特征很明顯不是作曲家所期待的,因此拉威爾將最后一個小節D三和弦用以三音作低音,即D音上的六和弦,這種轉位和弦地使用相對減弱了和弦的穩定性、削弱了調式和聲的感覺,但又讓傳統的調式特點成為一條似有若無、隱形的主線貫穿全曲的始終。
例2:1-2小節D音持續

228-229小節終止D六和弦

D大調:bⅥ7I6
二、和聲結構特點分析
拉威爾在這首作品中,根據他自己的和聲使用特點,進行了和聲使用上地傳承與創新。筆者通過分析,將這些和弦運用方式歸結為了三類:第一,傳統三度高疊和弦地使用;第二,同和弦不同性質地碰撞;第三,根音增四度和弦地使用。下面筆者就將遵從這三個方面的特征,對和聲使用進行詳細全面地分析。
1.傳統三度疊置和弦地使用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三度疊置和弦仍被廣泛使用,只是這種使用演變為高疊三度和弦的使用,比如九和弦、十一和弦、十三和弦等的使用,并且可獨立使用,無須再同古典時期一樣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則進行解決。這些高疊和弦有時保留了和聲的功能意義,但有時卻是僅僅作為一種色彩性地表達而使用。而拉威爾在本首作品中選擇了功能與色彩地融合,賦予了高疊三度和弦功能及色彩的雙重意義。
在本首作品的第一部分的再現樂段,旋律部分基本保持和前面相同,但和聲配置發生了較大變化,采用了D大調的II9—V11—I的古典的和聲進行,這里的高疊和弦就承擔著除了色彩性作用以外的功能意義,形成了古典和聲中強調的完全進行,鞏固了D大調的和聲功能特征。
例3:191-193小節的完全功能進行

2.同和弦不同性質地碰撞
在本曲中,作曲家大量地運用了和弦地構成音級相同但性質結構不同的兩個和弦的縱向結構形態同時使用使其產生碰撞的和聲手法,形成了極具有代表性的個性化和弦材料,并通過這種和弦形態的運用來營造其獨特而具有個性的和聲音響,使和聲的色彩性得到更進一步地渲染、增強,同時,這樣的使用方式,還起到了模糊調式的作用。
比如,本曲從一開始,就使用了D音上構成的大小三和弦同時結合所產生的復合和弦,以及在A音上構成的大小七和小大七和弦的同時結合產生的復合和弦。這兩個音作為d弗里幾亞調式的主音和屬音,很明顯起到了鞏固調式的作用,但是由于不同結構的和弦帶來的印象碰撞,又讓調式感變得不那么明顯和穩定,從而得到了調式不確定性的音響效果。同時,在主屬和弦中使用的#F和#C音作為西班牙調式音階中升高的二級音和七級音,將它們運用在主屬和弦的呈示中所得到的獨特的音響效果也更好地體現出了音樂所具有的濃郁西班牙民族風情特征。
例4:3-4小節(相同音高不同結構對置)

在作品97-103小節中,也使用了相同的手法。這段音樂的主音是#F音,但是,由于作者在使用的時候,使用了以#F音為主音的變化三音的大小九和小小九和弦的復合和弦、大小七和小小七和弦的復合和弦,以及大小三和弦的復合和弦,這些相同主音不同性質的復合和弦,就從本質上造成了調性模糊感,因此這段音樂可以理解為#F大調,也可理解為#f小調。
例5:97小節 100小節


大小九和小小九復合和弦 大小七和小小七復合和弦
104小節

大三和小三復合和弦
拉威爾運用以上不同結構的和弦,以不協和音響地碰撞來加強突出和聲的不穩定性,以此削弱和聲的功能屬性,使這些被復雜化使用的和弦體現出了典型的印象派追求“色彩”性和聲的重要作用。這些和弦地使用也是我們能夠在拉威爾這部作品中體會到新穎的音響與強烈的色彩感的根本原因。
3.根音增四度和弦地使用
兩個和弦的根音形成增四度音程關系,特別是當這兩個和弦為屬主關系時,這樣的一種使用方法,其實可以理解為使用的古老的教會調式—洛克里亞調式的屬主和弦的根音關系,這種屬主和弦的增四度關系,應該是整個調式功能運用中最具有特色的屬主關系。由于兩個具有增四度根音關系的和弦進行能起到遠離原有調性中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調性和聲功能地作用,因此拉威爾就常采用根音升高半音的下屬和弦或者是根音降低半音的屬和弦進行到主和弦的進行,這種進行在保持調性突出增四度關系和弦特有的和聲色彩的同時又大大降低了調性中心音的穩定性。
這種增四度的屬主關系的使用方法,較常見的使用者可以追溯到肖邦,在肖邦的作品中,特別是夜曲中,很多這種增四度的屬主關系和弦的使用,但是肖邦作品中,這種增四度的使用,多半是短暫的(以拍為單位的使用),并沒有長時間的延續,但在拉威爾本首作品的使用中,這種增四度的和弦關系的時值就明顯增長了(以小節為單位的持續),那么由此所造成的不穩定性和色彩性的突出也就大大的增強了。
本曲中,最突出的使用位置是在第174-181小節,通過和聲分析,這里的和聲結構應該是#C大調:I—bVII7—I—bVI7—I—bV7—I 。
例6:180-181小節

同時,bVII7、bVI7、bV這三個和弦,還可理解為下方半音的同名C大調的VII7、VI7、V和弦,也就是說,這8個小節的片段,我們除了可以理解為#C大調以外,還能理解為C大調,那么它的和聲進行就是C大調#I—VII7—#I—VI7—#I—V7—#I,這是典型的交替和弦的使用手法。
例7:174-181小節和聲標記

其實,有關交替和弦的使用手法,古典和浪漫時期的音樂中也已經大量存在了。但是,拉威爾在古典和浪漫的手法上進行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古典時期常采用相差三個調號的大小調式交替,也就是同主音大小調交替和弦;浪漫時期則用相差四個調號的大小調交替和弦會比較常見一些,也就是同中音大小調交替和弦;而拉威爾則運用了相差七個調號的距離最遠的同名半音大小調交替和弦,和弦之間如此巨大的差異、激烈的碰撞,都讓我們感受到作曲家希望帶給聽眾的強烈的聽覺刺激,并以此來強調調式和聲的不協和性,增強色彩性和聲的強烈對比,當然,肯定還有調式間的不明確性和游移性。
通過對《丑角的晨歌》的調式使用特點和三個主要的和聲使用特點的分析,可以看出拉威爾在繼承發展作曲理念和運用手法上的創新及其所占有的重要地位。這些具有典型“色彩”性的和聲處理方式使其作品產生了更為立體多變的音響效果,這樣的和聲使用方式也對以后的西方音樂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并且也對民族調式在音樂創作中通過其它調式和聲的融合使用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和運用手法。通過研究并發展以拉威爾為代表的印象派和聲技法對我們了解印象派音樂以至整個20世紀音樂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