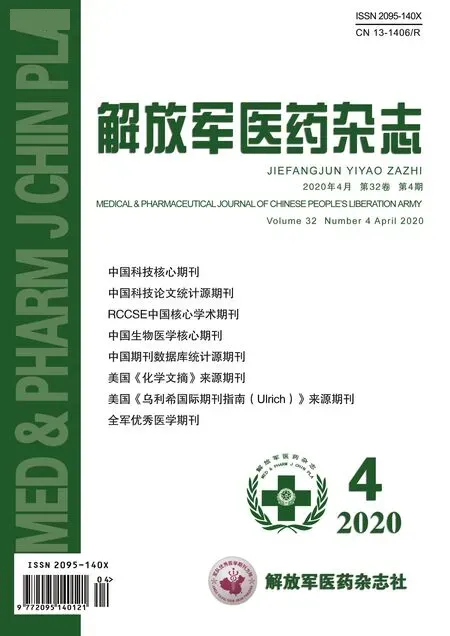胰腺癌患者外周血sPD-L1的表達水平及其與免疫功能的相關性分析
韓 瑞,張建業,祁生福,韓玉成
胰腺癌作為惡性程度較高的癌癥,其腫瘤細胞有較強組織浸潤和遠處轉移傾向,且由于早期缺乏典型的臨床癥狀,其診斷率多年來持續偏低,80%~85%的胰腺癌患者確診時已喪失手術切除治療的機會[1],由于癌癥病灶缺乏血供,且纖維組織包裹,靜脈注射藥物難以深入病灶,故治療效果及預后生存狀態極差。目前,有關胰腺癌早期生物學行為惡化機制的研究尚未完全明確,但已有較多研究借助惡性腫瘤共有的免疫抑制或逃逸理論對其做出初步解釋,認為胰腺癌細胞可通過多個信號通路導致自身免疫殺傷功能減弱,對內源性因素及外源性的化療、靶向治療等抗腫瘤作用均造成較大負面影響[2]。由于淋巴微轉移灶及脫落的循環腫瘤細胞更易于存活逃逸,為胰腺癌的遠處轉移提供助益[3]。程序性死亡分子-1(PD-1)/程序死亡分子-受體1(PD-L1)通路是腫瘤分子學領域近年來的研究熱點,其負性免疫調節作用已較明確,尤其明確在乳腺癌組織及間質浸潤淋巴細胞中表達活躍[4],部分西方國家也以此為據研制出單抗類生物制劑,在晚期癌癥治療中獲得廣泛認同[5]。可溶性程序性死亡分子-配體1(sPD-L1)是PD-L1游離在內環境的形式,與細胞膜表面mPD-L1在功能上甚為相似,然而由于外周血標本更便于臨床檢測,其在食管鱗狀細胞癌患者腫瘤免疫微環境評估方面的臨床價值獲得證實[6],但對于惡性程度更甚的胰腺癌研究仍較少。本研究旨在探析胰腺癌患者外周血sPD-L1水平與機體免疫功能的關系,取得一定成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4年1月—2016年12月青海省交通醫院收治的64例胰腺癌患者的臨床資料。①納入標準:所有患者的臨床表現、影像學檢查及細針穿刺活檢結果均符合胰腺癌相關診斷標準[7];年齡在18~80歲;臨床資料及隨訪信息完整。②排除標準:診斷為急慢性胰腺炎、良性胰腺囊性病變或其他部位原發惡性腫瘤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炎癥、結核病或活動性感染者;指標檢測前已接受手術、放化療、免疫治療等任何抗腫瘤干預措施者;有器官移植手術史,激素或免疫抑制劑應用史。以入院時血漿sPD-L1水平中位數為界將64例胰腺癌患者分為高表達組(sPD-L1≥3.61 ng/ml)和低表達組(sPD-L1<3.61 ng/ml),每組32例。
1.2方法 患者入院后,在空腹狀態下常規抽取肘前靜脈血樣2個抗凝管各3 ml,其一在30 min內以4000 r/min離心15 min,提取上層血漿凍存于-80℃冰箱,統一檢測時提前1 d將血漿置于4℃冰箱平衡融化,分別采用sPD-L1、干擾素-γ(IFN-γ)對應的酶聯免疫吸附法試劑盒,嚴格按照其說明書執行加樣、加抗體、溫育、洗板、顯色等操作,30 min內通過酶標儀讀取吸光度,標準樣數據繪制標準曲線,計算血漿樣品中sPD-L1、IFN-γ的濃度。另一靜脈血樣加入CD8+、CD4+對應的熒光標記抗體混勻,經由避光冰浴、加紅細胞裂解液、避光溫育等步驟,以2000 r/min轉速離心5 min,棄去上清后洗滌并重懸細胞,注入流式細胞儀進行檢測,獲取上述抗體T淋巴細胞占比。另外,通過病歷資料,回顧包括年齡、性別、臨床分期、病理類型、腫瘤直徑在內的臨床特征,并將患者的2年隨訪結局納入統計分析。

2 結果
2.1臨床特征比較 2組的年齡、性別、病理類型及腫瘤直徑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表達組的臨床分期明顯晚于低表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
2.2免疫功能比較 高表達組外周血CD8+、CD4+ T淋巴細胞水平均明顯低于低表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組外周血IFN-γ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OS比較 高表達組的中位OS為9個月(95%CI為7.466,10.534),低表達組的中位OS為14個月(95%CI為11.032,16.968)。高表達組的中位OS明顯短于低表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圖1。
2.4相關性分析 外周血sPD-L1與CD8+、CD4+ T淋巴細胞以及OS水平均呈負相關性(P<0.05,P<0.01),而與IFN-γ水平無相關性(P>0.05)。見表3。
3 討論
人體免疫系統清除壞死細胞與腫瘤細胞有賴于T淋巴細胞的活化作用,腫瘤細胞表面可表達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8],被T淋巴細胞特異性識別后可將其活化,協同共刺激分子與共抑制分子調控活化程度,維持整體免疫穩態,以防范正常情況下出現免疫活化不充分或活化過度,減少不必要的炎癥損傷或引發自身免疫性疾病。

表1 2組胰腺癌患者的臨床特征比較

表2 2組胰腺癌患者外周血CD8+、CD4+ T淋巴細胞以及IFN-γ水平比較
注:IFN-γ為干擾素-γ;與低表達組比較,aP<0.05

圖1 2組胰腺癌患者的總生存期生存曲線

表3 外周血sPD-L1水平與免疫功能指標以及OS的相關性分析
注:sPD-L1為可溶性程序性死亡分子-配體1,IFN-γ為干擾素-γ,OS為總生存期
據相關文獻報道,PD-1作為典型的共抑制分子,可固有表達于T淋巴細胞、B淋巴細胞及自然殺傷細胞表面,而惡性腫瘤細胞及影響其浸潤的免疫細胞則大量分泌PD-L1,二者結合后產生負性刺激信號,抑制免疫細胞活化,使其逃避免疫系統監視作用,腫瘤生長、侵襲與轉移活性獲得增強[9]。本研究結果顯示,高表達組外周血CD8+、CD4+ T淋巴細胞水平均明顯低于低表達組,且外周血sPD-L1水平與其呈明顯負相關性。提示sPD-L1可通過與PD-1結合,促進T淋巴細胞凋亡、延緩細胞周期進展并減少其髓系來源,從而整體上大幅抑制T淋巴細胞增殖作用而使其衰竭。有研究報道,PD-1/PD-L1信號通路能有效減低T淋巴細胞運動性,增加其與中心/濾泡樹突細胞間的作用時間[10],共刺激分子控制失衡,增強調節性T淋巴細胞功能,效應T淋巴細胞活性隨之下降。
IFN-γ為常見的炎性反應及腫瘤殺傷因子,其水平隨細胞免疫功能提高而增高[11],但在PD-1/PD-L1通路系統中,該物質也是PD-L1重要的誘導因子。有研究報道,PD-L1表達水平與IFN-γ存在顯著劑量依賴性[12]。本研究結果發現,2組外周血IFN-γ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與外周血sPD-L1水平無明顯相關性,提示sPD-L1與IFN-γ之間具有相互但又相反的作用,IFN-γ可增強sPD-L1表達,但sPD-L1抑制免疫功能則減少IFN-γ合成,加之IFN-γ同樣受到體內其他更多因素影響,因此不能單純通過IFN-γ反映胰腺癌免疫應答能力。部分研究提出,通過藥物阻斷PD-1/PD-L1通路后,IFN-γ水平明顯升高,猜測IFN-γ可能是腫瘤免疫激活與免疫抑制啟動的關聯物質,但該過程也可能被Janus激酶/信號轉導與轉錄激活子信號通路所抑制,可成為腫瘤免疫治療的新靶點[13]。
通常情況下年齡較大人群的免疫功能更差,因此可證實sPD-L1表達增高[14],而針對胰腺癌而言,腺鱗癌與合并十二指腸腺癌的交搭跨越腫瘤惡性程度相對較高,理論上可通過PD-1/PD-L1途徑更強效抑制免疫,但由于其發病率遠不及導管腺癌,臨床研究仍較少。本研究中,2組在年齡、性別、病理類型及腫瘤直徑方面未見顯著性差異,而高表達組臨床分期明顯較低表達組晚。提示胰腺癌進展程度更快的患者sPD-L1表達水平更高并向外周血釋放,但其水平并未明顯受患者年齡及腫瘤病理類型影響,究其原因可能與本研究納入樣本量較少有關,需在以后的研究中擴大樣本量進一步探索其規律。
臨床上針對不同分期的胰腺癌患者提出完全不同的治療策略,隨著PD-1/PD-L1單抗的研發與臨床試驗成功,能夠一定程度上優化胰腺癌患者的預后,但由于尚未建立治療適應證人群的篩選依據與評估標準,其次癌癥病灶環境對單抗的敏感程度并非均勻,且規律又尚不十分明確,加之受到設備與技術限制,PD-1與PD-L1動態變化令其檢測準確性與可重復性欠佳[15],因而該療法目前在國內推廣應用仍有一定困難。本研究還發現,高表達組的中位OS明顯短于低表達組,其與外周血sPD-L1水平呈明顯負相關性,這提示不僅能在早期通過檢測外周血sPD-L1評估預后,還證實可通過該指標結合臨床分期情況,建立簡單易行的PD-1/PD-L1單抗免疫治療篩選機制,臨床應用潛力較大。Kruger等[16]研究認為,sPD-L1可參與血液循環,與遠處免疫細胞表面PD-1相結合發揮生理作用,因此其引起免疫抑制或逃逸作用并不局限于腫瘤的微環境內,而是全身廣泛免疫功能障礙的表現,對其臨床檢測可初步了解腫瘤影響免疫范圍。
綜上所述,外周血sPD-L1水平可充分反映胰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抑制情況,可通過早期檢測為相關的臨床診治決策及預后評估工作提供可靠證據,有明確的臨床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