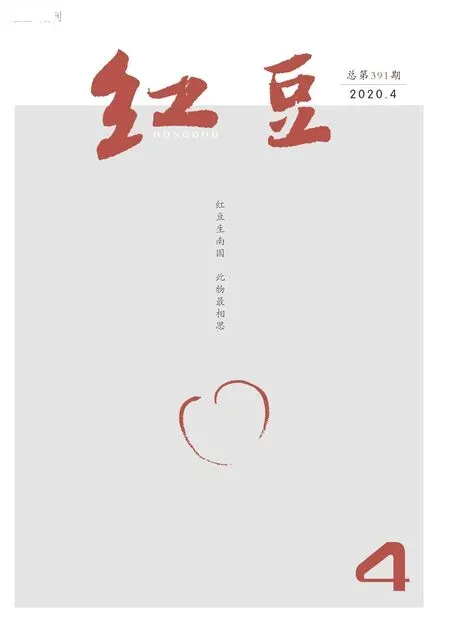索南才讓微篇小說二題(微篇小說)
索南才讓
我過去的位置
可可諾爾,一座湖。一片海。一個圍繞著青色的風旋轉的巨大冰塊。那里有我過去的位置,而今我跳出來,但仍然在那里,唯獨沒有位置。我看見一只孤獨的黑頸鶴。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用它來做比喻,但我覺得我錯了,我遙遙向它道歉。那里是一片沼澤,這片湖北岸唯一的巨型沼澤,目測有五千畝的樣子,相當于我的五個草場。沼澤地也是我的羊群愿意光顧的地方,那里有鹽土,可能還有別的它們喜歡的東西。有一次我趴到地上舔了舔,是一股腐蝕的味道。也許這才是它們的最愛。時至今日,我遵循著傳統,每年趕著它們來此地住上一段時日。這里有一大片稀疏的草地,看著好像沒有多少草但羊吃了反而更好,這些一根一根獨立硬而有刺的冰草可以把羊缺的東西補充起來。我說不上來它們的身體到底缺些什么東西,但它們自己知道怎么做。十四天前我出門時,父親要我描述一下進入沙漠后的步驟,我的答卷父親不可否認地頷首。他正在編制一條牛毛線的韁繩,現在估計快要完工了,我很期待。我就差一條好韁繩,馬的其他裝飾我都有了。我有一套馬嚼子,是純牛皮的。從軍馬場弄出來的,父親的手段。我還有一副前后橋都用銅銀包裹的馬鞍,肚帶有一個巴掌寬,用兩個扣子才能扣得住。一旦扣好了,你和馬跑多快多遠鞍子也不會往前竄,下山也不會。父親說肚帶要用能抓馬肚皮的東西,要糙要軟。我想到了流水,但這太不靠譜,而且也顯得我愚蠢。所以我說,阿爸,這是什么東西做的?父親說,一個好馬鞍最好的地方恰恰是最不起眼的地方,誰會想到——我是說那些不知底細的人——馬的肚帶是鹿皮呢。而且還是鹿皮中最柔軟的地方。鹿皮?我看著黑乎乎的這條肚帶,感受著上面濃烈的時間的味道。我問阿爸,這是什么時候的東西?阿爸說三十年前的一頭鹿……越老越高級了。我再次無奈地想到,阿爸是否在說他自己?不然他干嗎說越老越高級這樣的話?我覺得他的感慨源自我幾日前的放肆言行,他預感到我將變得像他年輕時一樣不近人情不知好歹,所以借用這種微弱而婉轉的方式告誡我……但我不接受!其實,我見證了父親和祖父之間既像兄弟又似仇敵的關系,打心底里感到享受,并且做好了切身之時的所有準備。因此,當我和父親的關系開始微妙起來的時候,我的心情跳脫而愉悅,我仿佛回到了正常的環境當中,被保護起來了。我并不怎么理解他的這種處理方式,我是他兒子,他完全可以對我吼。但他和那些父親不一樣,他不吼,他甚至從來沒有兇過我。他大部分時候對誰都顯得和和氣氣過了頭,于是有人就欺負到他頭上來了,我太看不慣。當久美為一片公草的承包權開玩笑地嘲笑父親說你那幾只羊能吃多少草時,父親很生氣,可卻沒有說出狠話,只是說你還不讓窮人的煙筒里冒煙了。他說出這樣丟人的話后我生氣了。我說久美你個老混蛋,然后給了他兩拳一腳。送久美去醫院途中我還在想,父親的言行如此軟弱,是否他正處于道德困境中而無法自拔?他或許真是這樣,我開始原諒他,但我沒有原諒久美。他的性質太惡劣,我以前就討厭他,我的舉動絕不突兀。父親擔憂我的處境,打發我例行每年一度的沙漠之行。自進入沙漠,手機信號全無,不知外面如何。但我想久美鬧也鬧不出花樣,他很可能會要錢,那才是真麻煩。萬一他要一萬塊錢,就是我家的災難,三萬塊錢什么也不會剩下,與其如此,還不如我去蹲一蹲牢房。但坐牢對我的名聲不好,我還沒結婚,正在節骨眼上,父親一定不會同意的。但賠錢更難,沒錢了誰會和我結婚呢?久美膽敢過分我就殺了他,賠他一命。這么說似乎有點難為情,有點愚蠢,然而這就是我。
進入沙漠第十四天,我盒子里的卡片用完了。我把盒子放在沙地上,退后瞭它。一個很不正經的東西,串聯著那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后的保存。我寫的東西也很不好,但不好歸不好,我舍不得扔掉一片。現在把卡片裝回去,我想不起來寫了什么,但很重要的感覺還在。我仿佛寄出去了很多重要的信件,一些救命的東西。我之前就已經數過,卡片有六十六張,我一張不落全部寫滿。現在盒子就在幾步之外,我撩著它,正午的大太陽戳著腦袋,我的帽子被風刮走五天了,臉上的皮子曬裂了,卷了起來,早晨起來時有灼痛感。沙漠里的水咸味大,喝著可以,洗臉遭罪。我似乎記得寫過這個事情,我說狗日的帽子像嫖客一樣匆匆離去……世事如斯,心中的苦楚也得笑臉展示。我倒是不后悔打了久美,我逃離出來后有一大半時間根本不在乎這件事。第十二天才重新開始琢磨。第十三天我覺得形勢依舊不容樂觀。到了最后一天,我則認為大可不必這樣,這年頭誰沒有過不去的坎兒?盒子里的更多的內容有了,我有一些計劃,寫過之后再也不管。我撩著它,然后踩住它,揉了揉,盒子沉入沙中。我的羊群早就翻過三座大沙山,踏上堅實的鹽堿地了。回家的路,畜牲絕不迷茫。
它們來了
我們從早晨坐在這里喝酒,一直沒離開。朗坐在沙發上抽煙,漩渦狀的藍煙和亮堂堂的光線交織著貼到彩鋼的屋頂上飄游。
“你說什么來著?”朗再次問。
“扎巴。”我說。
“他出來了?這進去才幾年呀就出來了?”朗高著嗓門,“他偷我三十頭牛,才坐幾年牢啊,這就算完啦?”
朗的心情變得很糟糕。他的那么多牛是被扎巴偷走賣掉的,事發后朗一分錢也沒有要回來,損失了十幾萬。扎巴才吃了三年監獄飯,就沒事了。
“他得病了。”我補充道。
“所有的人都在得病,我也有病,你也有病。得病不是事兒。”
“但他是精神病。”
“管他什么病。”他憤懣地說,“總有一天我要讓他還錢。”
“你還是不要去找他。”
“我會去找他的,不能就這么算了,哪有那么好的事?那樣豈不是人人都愿意當賊?”
“我才不愿意,給我多少都不會那么做,你愿意?”
“我也不。但我氣不過。”他說。
“說氣話沒有意義。”我說。
“他們怎么還不回來?”朗把右腿抬到茶幾上面,伸了伸說。
“我們該走了,他們倆忙著呢。”
“大概是不想陪我們了。”
“這兩口子人不錯。”我說,“她叫什么來著?”
“我們都叫他小龍。”
“我說的是他老婆。”
“哦,你叫她黛青措吧。”
“他們兩口子趕羊去了。”我說,“一個人趕生羊羔的母羊,一個人趕沒生羊羔的母羊。”
“他讓我們等著,我看他還想接著喝。”朗說。
“我看他喝不動了,咱們走吧。”我說著站起來。
朗也站了起來說:“還是等他們回來吧。”
我看了手機上的時間,看了微信朋友圈,看了郵箱。我看QQ郵箱是因為和她的交流都是通過QQ郵箱進行的。前天傍晚我給她寫了信,到現在她還沒回復。我有點難過,我對自己沒有信心。更讓我難過的是,她遠比我想象的鎮定。她一直沒有表現出異樣的情緒,我難以判斷她是不是生氣了。
他們回來了。小龍說:“今天這么冷,羊羔生了五個。你們怎么樣了?”
朗問:“你的羊羔是歐拉羊嗎?”
“全是歐拉羊羔,一個比一個好。”小龍滿臉笑容。
“我今年錯過了好時機,羊價漲得太快。”朗抹抹臉,痛惜地說,“春天的時候我也差點就買一百多只歐拉大母羊。”
“我一心寫作,等回過神來,已經痛失良機了。”我說。
“你寫字賺了多少錢?”小龍好奇地問。
“一兩萬吧。”
“這么少?”小龍驚奇地看著我,“我以為有七八萬呢。”
朗倒滿三個酒杯說:“咱們干一個。”
我說:“好的。咱們干一個,就走吧。”
小龍說:“干嗎呀?吃完飯咱們接著喝呀。”
朗說:“不行,我還要去見一個人。”
小龍說:“好啊,那我也去。”
“你還有事呢,你忘了?”黛青措說。
小龍偏頭望了她一眼:“對,我還有事,那我就不能去了,你們去吧。”
朗說:“我的車呢?”
“在房后面停著呢。”小龍說。
“再見黛青措。”朗說。
“再見。”她終于正正規規地看著我說。
之前的一天,我去山里。我之所以去山里是因為那天我無事可干,我一旦無事可干就心焦,于是我就想,干嗎不去山里看看今年草長得怎么樣呢?要是長得不好,我還需早做打算。于是我爬上對面的山頭,回望遠處的公路,我看見315國道上十幾輛白色的汽車串連著駛向海西方向。我想那些都是豐田霸道。我最喜歡霸道了,我多想擁有一輛啊。長久以來,我都在為這樣一個夢想努力奮斗著,現在也是。可我不愿意自己這樣,于是我喝酒的時候越來越多了,我已經喝上癮了。這件事誰也不知道。
我在我的草場里看見一輛藍色的摩托車,摩托車旁邊有一頭死牛。這不是我的牛,我的牛要到十二月份才會到這兒來。過一陣子,大概有一個小時吧,桑日杰來了。
“桑日杰你來了。”我說,“這是你的車嗎?”
桑日杰笑道:“就是我的。我的車沒油了。”他把手里的塑料桶提高了給我看。
“這牛是你的嗎?”
“牛也是我的。”他把油桶放到地上說。
“牛怎么在我的草場里?”
桑日杰瞅了瞅我:“我也不明白。它是一頭母牛。”
“我知道是母牛。”我說,“它從哪來?”
“它從夏窩子來,我的牛全在那兒。”
“你在偷吃夏窩子的草?這可不好,我們都沒吃,你卻先吃上了。”我說。
“我沒有偷吃,是它們自己跑掉的,我今天就要去把它們趕出來。”他說。
“我會在群眾大會上提出來的。”我說,“你太過分了,你的行為很過分。”
“我再說一遍,我不是故意的,我又不是傻子。”他圍繞著死牛走了一圈,語氣硬邦邦地說。
“我不明白,它怎么在我的草場里。”
“老天知道。”他說。
“你這是什么意思?”
“那你想怎么著?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一直在說你不是故意的。”
“我當然要說,因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說。
“可你的牛在我的草場。我的草場正在長草,我都舍不得讓我的牛吃,但你的牛卻光明正大地吃,你的牛群還在光明正大地吃夏窩子的草。”
“得了,才讓。”他不耐煩地說,“不就一頭牛嗎?你干嗎發火?”
“你這是什么意思?難道你沒錯?”
“好了好了。你說怎么辦吧?”他這會兒已經騎到摩托車上了。
“你要把這牛怎么著?”我看著那牛,這是一頭有土黃色皮毛的成年牛。
“我沒時間管它,再說它已經死了。”
“你不能把它留在我的草場里,你把它弄走。”
“我怎么弄走?這是一頭牛。”
“我不管。總之你不要留下它。或許你可以卸開了弄走。”
“再見,才讓。” 桑日杰啟動摩托車說,“你今天讓我感到吃驚。”
“你讓我感到震驚。” 我朝他的后背喊。
他走了很久,我還坐在那里盯著死去的母牛,我認為它是一頭懷有小牛犢的母牛。這么說就是死了兩頭牛。如果牛犢是一頭母牛,那么再過幾年,就會變成好幾頭牛,這么算桑日杰損失不小。我以前不這么算賬,我覺得沒有的東西不能算在財富里,但有一個老頭一直在我耳邊嘮叨,他永遠這么算賬,漸漸地我也認可了這種算法,因為當你和別人有財產糾紛的時候,這是一個很有用的法子。它可以保證你不吃虧。
當我回到家時,朗在等著我。他說:“才讓,咱們走吧。”
在沙礫路上,我意外地聞到了尸臭。我說:“這是怎么回事?”
朗說:“哦,我車后備箱里裝了死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嗎?”
我說:“我當然不知道。”
“是我打死的。我在羊棚里把它扔了五天,現在丟到大坑里去。”
“都已經發臭了。”我說,“臭死了。”
朗說:“我是故意的。我要讓它們知道我的厲害,我得讓它們害怕我。我告訴你,所有招惹我的羊都已經死了,真的。”
“那它們害怕你嗎?”
“它們快害怕死我了。但它們不怕我老婆。”他說,“你看,它們來了。”
這會兒快到他家了。他的羊群出現在山梁上。我們給他的那匹安靜的黃馬打了針。它是一匹比賽的馬,卻被一場流感擊垮了,瘦得翹起了三叉骨。
后來我們到了黛青措家里。這是第二天的事了。
責任編輯 ? 侯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