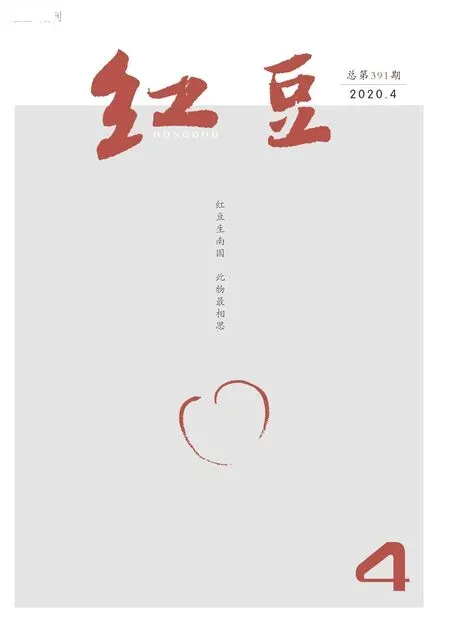是什么讓我們成為親人?(創(chuàng)作談)
周李立
近來(lái)越來(lái)越覺(jué)得寫(xiě)作的無(wú)力。這是一個(gè)一言難盡的冬天,因?yàn)橐谎噪y盡的疫情。小說(shuō)這種鏡花水月般的存在,這種虛構(gòu)之物,在此時(shí)便尤其顯不出什么力量來(lái)。遲遲未動(dòng)筆也與這種心境相關(guān)。我們待在家里,看似時(shí)間更充裕、狀態(tài)更松弛,然而這段日子又顯然不是正常的日子。且但凡日子是反常的,便根本談不上什么狀態(tài)松弛或時(shí)間充裕——何況當(dāng)下,我們都是緊張的。緊張的我們就這樣難得地與家人長(zhǎng)久相處、共同生活,體驗(yàn)著久已疏離的日常生活的細(xì)微末節(jié),也承受著長(zhǎng)期相處有可能發(fā)生的摩擦或矛盾,于是難免,會(huì)想起有關(guān)家庭生活的種種話題。
我以為所謂家庭生活、親屬關(guān)系,吵吵鬧鬧作為題中應(yīng)有之義總是免不了的,有多少親密團(tuán)結(jié)的家庭,就有多少臉紅脖子粗的親人。因?yàn)槭怯H人,我們彼此關(guān)切,恨不能進(jìn)一步再進(jìn)一步地參與對(duì)方的日常生活。我們的關(guān)心與熱情體現(xiàn)在想了解對(duì)方生活中最細(xì)枝末節(jié)的事情,知曉對(duì)方最微不足道的習(xí)慣。因?yàn)槭怯H人,我們沒(méi)有界限感,我們也不需要界限感,我們只要密切交融——這一切,想必都是因?yàn)閻?ài)吧。然而我們又都是獨(dú)立的,我們走出家門(mén),離開(kāi)故土,只是成千上萬(wàn)形單影只的個(gè)體之一,都是落落寡歡煢煢孑立的現(xiàn)代人。除了年節(jié)假日的相聚,還有多少時(shí)刻能夠證明我們是親人?而年節(jié)假日相聚的時(shí)刻,你會(huì)不會(huì)突然想這么問(wèn)自己,是什么讓我們成為親人?
如果你生在一個(gè)大家庭,你會(huì)體驗(yàn)到,大家庭的運(yùn)轉(zhuǎn)一定依存于某種約定俗成的法則。人類就像無(wú)數(shù)渺小的齒輪,總是在磨合,也總是在撕咬,撕咬讓我們圓潤(rùn),也讓我們有了團(tuán)結(jié)的可能。我們?cè)诩彝ド钅撤N不成文甚至根本捉摸不定的法則之下,吵吵鬧鬧又相親相愛(ài),彼此疏離又相互依存,就這樣矛盾地咬合、共存。《每周要聞》只不過(guò)讓這種狀況極端化了,濃縮在謝家人祭祀這天的一小段時(shí)間里。他們和我們一樣,在一套既定法則的籠罩之下,表面看謝家的法則是每周需匯報(bào)個(gè)人日常生活近況,我想實(shí)質(zhì)上遠(yuǎn)比這要復(fù)雜。這套法則中也許還有真誠(chéng)的關(guān)切,也許還有攀比,也許是需通過(guò)對(duì)方的存在確認(rèn)自己的位置,更有可能是在對(duì)方身上看見(jiàn)自己真正缺失的東西。至于到底是什么,謝家人不會(huì)知道,我也不會(huì)知道。復(fù)雜而無(wú)從知曉,這本就是生活的本質(zhì),正如我剛才用過(guò)兩次的那個(gè)詞,一言難盡。
一言難盡,但還是要“言”。也許一言難盡的東西,萬(wàn)語(yǔ)千言就可以說(shuō)盡呢?哪怕謝家的人,在“爺爺”去世后,也依然讓這種每周匯報(bào)各人日常生活近況的傳統(tǒng)延續(xù)下去。雖然他們也深知,這不過(guò)和我們熟稔的諸多傳統(tǒng)與規(guī)則一樣,最終流于形式,甚至帶有表演色彩,它不再與各人真實(shí)而隱秘的哀愁喜怒有絲毫相關(guān),它的效果也早已與它的初衷背道而馳。然而它依然有效,就像我們生活中許多殘酷而華麗的時(shí)刻——比如祭祀——一樣有效,且將長(zhǎng)期存在。這是小說(shuō)完成后我意外獲得的體悟——形式感,無(wú)論多么華而不實(shí),它也終究是生活的必需。
責(zé)任編輯 ? 丘曉蘭
特邀編輯 ?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