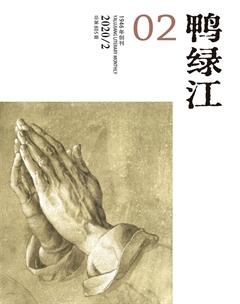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的狄奧尼索斯特性女性意向的缺失
林夢含
摘要:本文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男性身上女性意向的缺失,以及其筆下的女性呈現的映像。陀氏創作的人物身上多數帶有酒神及酒神信徒的形象特點,是俄羅斯民族性格特點的真實寫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與其所處的十九世紀后半期社會環境緊密相連。本文結合榮格夫婦的原型理論,分析論述作家筆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心理特征,探究俄羅斯心靈之謎
關鍵詞:陀思妥耶夫斯基;狄奧尼索斯;阿尼瑪;阿尼瑪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性”映像模糊不清,“愛”意象忽隱忽現。這并不意味著,陀氏作品中缺乏愛的元素。恰恰相反,其作品充滿了強烈,熾熱又極端的愛。斯塔夫羅金永遠給讀者帶來一種充滿神秘感,這種氣質往往能旋即轉變為激情的氛圍。激情與暴力纏繞交錯,緊密環抱,使文字流淌出怪異卻合理的音樂性,有著灰暗而充滿吸引力的畫面感。究其原因,正如別爾嘉耶夫所言,除了陀氏一人,再沒人能發現俄羅斯心靈中本能的情欲、肉欲。這不應與作家本人的經歷分割開來,在俄羅斯的文學史上,再也無法找到第二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的心靈,有著與其一模一樣的經歷。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愛情一如其男性人物,并不贊揚日神阿波羅式的體型美;恰恰相反,他所創作的多數“迷人”的人物都是狄奧尼索斯的信徒。無論是斯塔夫羅金,還是拉斯柯爾尼科夫,亦或者是維爾西洛夫,都追求破除外在的幻覺,與本體溝通融合。這一點恰恰與陀氏作品中的宗教內涵相矛盾,因而這些“圣徒”人物無一例外走的是一條艱難至極的受難之路。如果說陀氏筆下以斯塔夫羅金為代表的狄奧尼索斯信徒追求與本體的溝通融合,演繹的是形而上學的悲劇;那么其筆下的女性形象就是唯心觀的忠實支持者,宗教神靈者,乃至是既成的圣女。仿佛天生受到圣母指引,這些女性形象帶著天然的使命,觸發男性命運,使后者成為宗教救贖精神的化身。而男性角色對待母親和對于所愛女性的態度是完全割裂開來的,這種現象并不符合艾瑪·榮格對于男人心理的阿尼瑪原型的描述。陀氏的作品中,男性與女性間,愛情關系是遭到割裂的;而對個體來說,其心中的女性意向是殘缺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處的19世紀末的俄羅斯文學殿堂內已經出現許多豐滿的女性形象。無論是普希金筆下代表傳統美好品格,近乎完美的塔季揚娜,還是托爾斯泰塑造的倔強而追求愛情自由的安娜·卡列尼娜,更不用提及“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上述女性角色均為“雌雄同體”的完滿人格:塔季揚娜一方面善良含蓄,一方面敢于主動給奧涅金寫信訴說情感;一方面忠于自己的愛情,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家庭;安娜·卡列尼娜一方面為愛情背叛家庭,一方面在遭到愛情不公待遇時,選擇放棄了自己的生命;《貴族之家》中的麗莎一方面深深愛著拉弗列茨基,一方面善良地選擇退出不正常的戀愛關系;《前夜》中的葉蓮娜一方面為英沙羅夫的死傷心欲絕,一方面獨自踏上完成二人革命理想的道路;縱觀上述作品中的愛情主題,“愛”與“情”的意向完整,“愛情”的結局往往并非男女主人公終生相伴,但在感情上,二者是互相滿足、互相填補空白的。而男女主人公之間相識、相互理解、達成共識的過程,是一個“夏娃”找到“亞當”的過程,尋找與本體相對立的性別,在這個過程中對立性別的精神氣質也會在本體身上補充完整。愛情中,性別互補的不只是生理,更是心理。男性心中本有的“阿尼瑪”得以突顯;女性心中的“阿尼姆斯”顯現。原本預存在情緒、反應、沖動中的自然原型,在與異性交往的過程中被激發,于是男性出現女性心理,女性則相反。陀氏筆下人物的“愛情”心理狀況是變態形態,而非自然發展的過程。原因何在?
典型而特殊的一個例子是《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在俄羅斯,乃至在整個世界,尼古拉·斯塔夫羅金都是一個永恒、耀眼的迷。在這樣一個角色身上,讀者可以觀察到在其他角色身上鮮少能看到的作家對自己角色的愛與迷戀。這種迷戀超過了作者與創作角色之間的界限,而是一種浪漫、誠摯、強硬的愛。斯塔夫羅金不屬于任何人,任何流派,任何文學形象,他身上有著最強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印記,但不屬于陀氏小說中任何一個類型的人物。展示了人性最深處的弱點、不得不受到的種種誘惑,以及黑暗、未知的罪孽。《群魔》的故事開始于斯塔夫羅金死去之后,又以斯塔夫羅金的死亡告終,而通篇故事里的主人公,正是尼古拉·斯塔夫羅金一個人,他曾“做到了自己的母親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也曾經“瘋狂地吃喝玩樂起來,野蠻地放蕩不羈”,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斯塔夫羅金的描述把后者身上狄奧尼索斯的特征以最直白的方式展現了出來。而在《群魔》中現身的斯塔夫羅金,不同于眾人口中傳說的那個歡樂的狄奧尼索斯,而是一個詭異的、沉靜的形象——什么事情曾經發生在這個年輕人的身上,而斯塔夫羅金所隱藏的秘密在書中始終沒有得到明確的描寫。斯塔夫羅金的父親早年便去世,母親對他寵愛有加、甚至是嬌生慣養,那么斯塔夫羅金心靈當中的“阿尼瑪”究竟是什么樣的呢?根據艾瑪·榮格的理論,如果母親的作用力多數是正面的,那么“阿尼瑪”將會被內化成為夢中情人的形象,而男性將在愛情中獲得完整的人格。反觀斯塔夫羅金,書中出現的形象,是一個精神已經衰敗、性格消解了的人物。他并沒能與麗薩、列比亞德金娜,或是其他不知名的任何一個女人在一起。在斯塔夫羅金與二者的對話中,他的性格并未能與任何一個人的性格融為一體,而是不斷外擴,沒有彈性,無法收回。斯塔夫羅金的特殊之處在于,他的童年缺少父親角色的參與,而是在瓦爾瓦拉“一個人的呵護下長大的”這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其認知的發展、社會行為、個性品質,性別形成。斯塔夫羅金的男性外部形象存在著缺陷,而內部的女性傾向從其對待愛情的態度可以得知呈現為消極、負面的。斯塔夫羅金的人格中缺少了阿尼瑪的存在,而他的外部“面具人格”又是殘缺的。心理上的不完整導致了他的與眾不同、旁人無法感受的痛苦,以及悲劇的人生。盡管斯塔夫羅金背負著罪孽,內心是“壞透了”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迷戀這一角色,哪怕斯塔夫羅金首先是一個“貴族的公子哥”。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陀氏對于“人”這個概念的接受,并沒有受到宗教、宗法、禮儀甚至是社會道德的影響。誠然,如同別爾嘉耶夫所說,陀氏對待“惡”的態度是矛盾的,但他并沒有否定惡存在的合理性,也并沒有悲觀、絕望。小說的開頭,斯塔夫羅金已經死亡,但個人的意識,自由的精神,在《群魔》之后,將會讓斯塔夫羅金獲得新生。一如還未足月便遭遇雷電之劫的宙斯之子,狄奧尼索斯:災難屬于酒神命運的一部分,卻不是終結。而酒神瘋狂、熱列的形象特點,也正是在母親孕育的過程中、隨著母親受難的過程中獲得的天性。
首先需要指出,情愛并不是構成作品的主要內容。這也是作家生命的真實寫照。比起與女性纏綿悱惻的愛情,對其觸動最大的是一生坎坷艱苦的經歷。彼時的俄國在世界海洋的漩渦中沉浮,陀氏作為漩渦中的俄國人,體會到了19世紀沙俄社會苦難的種種。在陀氏的筆下,這一時期俄國女性的心靈未閃現太多色彩,他沒有多余精力去揭示俄羅斯女性心靈奧秘。女性從未是作家筆下的中心人物,甚至很少得到關注。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沒揭示人類本性中雌雄兩性的特點。其作品通常圍繞著一個男性展開,有諸多男性參與,一兩個女性在其命運中“推波助瀾”。男性心靈缺失“阿尼瑪”原型,即男性的無意識之間的紐帶是斷裂的,心靈上僅是男性因素在起著作用。從這個角度,愛情總呈現為欲望對男性因素能量無窮無盡的消耗。納斯塔西亞、阿格拉婭的愛情帶給讀者緊張的氛圍;斯塔夫羅金與麗莎的愛情將所有人卷入不安之中。男性與女性的靈魂永遠無法真正融合,男人與女人肉欲的結合總是帶來麻煩。男人負著命運的原罪,腳上拷著鐵鏈,背上是沉重的枷鎖,行走著悲劇的道路。女人并非命運的最終意義,女人是男性命運的羈絆,甚至僅僅是產生一些作用。男性因素不僅有作家個人的印記,也屬于整個俄羅斯民族。而所有的女性因素卻只屬于作家本人,是作家設置于創作中的一種個人私密的體驗:男性靈魂在女性靈魂面前弱小而又無力。
與個性特征鮮明,內心活動活躍的男性形象不同,陀氏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始終處在一個被觀察的角度,居于疏遠的位置。男性人物無法了解女性的想法,而是永恒地處于自己的心理活動中,永遠活躍在自己的頭腦中。這也給讀者在閱讀時帶來了相同的體驗。陀氏并沒有屠格涅夫那樣精巧的手法來描繪俄羅斯女性心靈的美好,也沒有像托爾斯泰那樣,將女性渴望解放,渴望自由的意志力表現出來。讀者可以稱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男性人物有血有肉,卻無法像描述“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一般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中的女性人物,因為往往呈現靜態性,帶著一種符號象征意義,沒有男性人物那么活躍,似乎永遠被一層紗幔所圍繞,處于某種異己的世界,而不是陀氏筆下那瘋狂而光怪陸離的世界。與其說是作家的表達障礙,或者說是陀氏與女性角色之間的隔閡,不如說,作品高度還原了創作者的視角,心理活動。讀者是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睛,去看他眼中的世界。而“影印”在書中的女性,似乎總是帶著阿波利納里亞和其第二任妻子安娜的影子,有時候體現在截然不同的兩個角色身上,有時兩個人的形象似乎糅合在一起,形成一個人,這個人在不同的階段顯現不同的性格。在陀氏作品中,女性或是拯救男性命運的光,或是男性不得不經歷的考驗。換言之,很多情況下愛情只是男性悲劇的命運中的一個符號,探索自由時的一個因素。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曾對人性中的自私進行遮掩,這種自私似乎是人性解放的一部分。作家曾近十年癡迷于賭博。散盡錢財后,依然向自己的妻子索取。往往在承諾戒賭后,依舊輸掉最后一個塔勒。痛苦的輪回似乎永無休止。值得引發思索的是,作家對于自己給妻子帶來的痛苦,是否只是理解與同情?十年的賭博經歷讓陀氏感受到不受自己控制的、某種精神力量的主宰。在精神世界中,滿足個人的欲望是首要的。這是作家本人的悲劇性所在,而這種悲劇性,在其作品中,就變成了一個個虛無而痛苦,具有二重性格特征的男性形象。反觀陀氏的妻子安娜,正如《群魔》中的麗莎,也像《罪與罰》索尼婭·馬爾梅拉達,心甘情愿接受了一切苦難,作出讓步,無償奉獻。作為妻子生活苦難不幸的目擊者,作為其筆下女性人物的創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僅有愛情的憐惜,這其中也激蕩著陀氏那典型的俄羅斯式心靈中平靜不下來,人性的漣漪。
從這一視角看,縮小了身體層面內涵以及行為方式內涵的女性,展示了超越了性別、自我的形象,是具有普度精神的形象;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社會訴求,通過改變、影響男人,改變、影響了整個世界。圣潔之美的外表下,這些女性由內而外地散發著神性的魅力。
參考文獻:
[1]陀思妥耶夫斯基. 臧仲倫, 譯. 群魔[M], 漓江出版社, 2013.PP.
[2]陀思妥耶夫斯基. 張雨, 張有福, 譯. 作家日記[M],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PP.
[3]尼古拉·別爾嘉耶夫. 于培才, 譯. 文化的哲學[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PP.
[4]Emma Jung, Animus and Anima[M],Continuum Intl Pub Group, 1998.PP.
[5]Редактор А.А. Радугин.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и ответств. [M] — М.: Центр, 2001. — 304 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