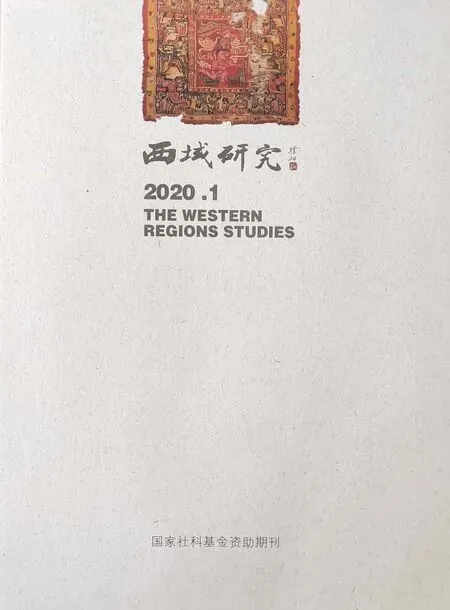《大谷文書集成》未命名典籍殘片整理札記
李紅揚
內容提要:《大谷文書集成》未命名文書碎片中有不少屬于唐代各種典籍抄本的殘片。經過比定和初步整理,新近發現《唐中(龍)興三藏圣教序》殘片2件,《文選·西征賦》殘片1件,《論語·子路篇》殘片1件,此外還有2件與《本草經集注》和《大乘法苑義林章》有關的醫書和佛教文書殘片。這些殘片是當時典籍的原始物質形態,具有重要的古文書學研究價值。
1903~1914年間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在中國新疆、甘肅等地古代遺址、寺窟和墓葬盜攫大量古代文書,其中以在吐魯番所獲的數量最多,這批文書被稱為大谷文書。大谷文書現主要收藏在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中國旅順博物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也有為數不少的收藏。1984年至2010年,小田義久先生將龍谷大學所藏八千余號大谷文書殘片整理為《大谷文書集成》(一至四卷)(以下簡稱《集成》),公布于眾,嘉惠學林。由于大谷探險隊的掠奪性挖掘,這些文書破碎嚴重,且缺乏必要的出土信息,整理工作難度極大。經過小田義久先生長期不懈地整理、綴合,《集成》中仍有大量文書殘片性質不明。圍繞這些未定名殘片,中外學者相繼從中識讀、綴合出不少典籍文獻,(1)關于《大谷文書集成》中未定名的典籍文書殘片,主要研究成果見陳國燦、劉安志主編的《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近年,《集成》中又有不少殘片被識讀出來,張新朋從中認定出13片《千字文》和5片《詩經》(參張新朋:《大谷文書中十三則〈千字文〉殘片之定名與綴合》,《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第67~72頁;《敦煌吐魯番出土〈詩經〉殘片考辯四則》,《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第177頁);劉子凡發現2件《醫疾令》和《喪葬令》殘片(參劉子凡:《大谷文書唐〈醫疾令〉、〈喪葬令〉殘片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3期,第215頁);李昀比定出3件《文選·七命》(參李昀:《吐魯番本〈文選〉李善注〈七命〉的再發現》,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9輯,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35頁;《旅順博物館藏〈金剛經〉注疏小考——附李善注〈文選·七命〉補遺》,《旅順博物館學苑2016》,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88頁)等,限于篇幅,此不一一贅注。這些殘片雖然內容有限,卻是唐代典籍的原始物質形態,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近日筆者在研讀《大谷文書集成》時,經過仔細比對,又發現了數件屬于《大唐中(龍)興三藏圣教序》《文選》《論語》《本草經集注》等典籍的殘片。茲將相關殘片整理如下。
一 《大唐中(龍)興三藏圣教序》殘片

三藏法師義凈者,范陽人也。俗姓張氏,五代相韓之后,三臺仕晉之前,朱紫分輝,貂蟬合彩。高祖為東齊郡守。仁風遠扇,甘雨隨車。化闡六條,政行十部。(4)〔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一七唐中宗《三藏圣教序》,中華書局,1983年,第210頁。
據IDP數據庫(國際敦煌項目)所載圖片(以下圖片若未加說明皆來源于此)“蟬”字存下半部,“為”僅存上部,殘片的左端殘存有筆畫和朱點。
大谷10056A號文書(圖1),上下前后皆殘,殘存4行,有界欄,背面為胡語。《大谷文書集成四》(簡稱《集成四》)將其定名為“性質不明文獻斷片”(5)〔日〕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四),法藏館,2010年,第123頁。,錄文如下:

圖1 大谷10056A號文書

據圖版,第1行和第4行分別殘存左半部和右半部,但因為墨色較淺且有泥土覆蓋,難以辨識。“成”下字破損或未書。而據第2、3行可知,所抄內容應同樣源自《大唐中(龍)興三藏圣教序》,對應語句為:
開常樂之門,普該于有識。縱使浮天欲浪境風息而俄澄,漲日情塵法雨沾而便廓。歸依者銷殃而致福,回向者去危而獲安,可謂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而無能名者矣。
由此可見,對第2行殘缺的兩字釋讀為“殃”和“福”是準確的,“成”下字應為“功”“蕩”,第4行殘存的兩字應該是“悟”和“無”。以上兩片,皆可定名為“《大唐中(龍)興三藏圣教序》殘片”。
《大唐中興三藏圣教序》又名《大唐龍興三藏圣教序》(以下簡稱《圣教序》),作于神龍元年(705)。是年中宗即位不久,義凈于東都內道場譯《孔雀王經》,又于大福先寺譯《勝光天子香王菩薩呪》《一切功德莊嚴王》等經,正合中宗尊崇釋典之心,遂作此序以示褒揚。(6)〔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一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5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869頁。神龍三年(707)二月庚寅,朝廷下敕改中興寺、觀為龍興,內外不得言“中興”。(7)《舊唐書》卷七《中宗紀》,中華書局,1975年,第143~144頁。所以《中興三藏圣教序》同年五月立碑時,依敕更名為龍興。(8)〔宋〕佚名:《寶刻類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分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8417頁。
《圣教序》多見于敦煌文書中,楊富學和王書慶先生較早指出,從長安傳入敦煌的佛教文獻中有P.2780、P.2899、P.3127、S.343、S.462、北圖翔50、北圖玉92諸號《圣教序》。(9)楊富學,王書慶:《唐代長安與敦煌佛教文化之關系》,韓金科主編:《19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181頁。實際上,P.2780、P.3127、S.343、北圖玉92均為唐太宗為玄奘撰寫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而非中宗撰《圣教序》。(10)吳超:《俄藏敦煌00293號〈三藏圣教序〉文書考》,《陰山學刊》2015年第3期,第60頁;王衛平:《關于〈大唐中興三藏圣教序〉——兼及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殘片考略》,王振芬,榮新江主編:《絲綢之路與新疆出土文獻:旅順博物館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19年,第255~270頁。馬德和于芹先生在《敦煌研究》上同時發表的兩文中介紹了山東博物館藏《圣教序》,但前者編號作LB.004,后者作LB.002,未知孰是。(11)馬德:《國內散藏敦煌遺書的調查隨筆》《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第46頁;于芹:《山東博物館藏敦煌遺書敘錄》,《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第59頁。王衛平先生又在上述學者基礎上,搜括出P.2632、P.2803、P.2883、P.3154、S.1177、Дx.00293、Дx.02223、Дx.06265、Дx.06599、北1439、北2004、北8410、北812445諸號敦煌本以及旅順博物館藏LM20-1505-0680、LM20-1511-0079、LM20-1511-0086、LM20-1486-29-10四號吐魯番本《圣教序》殘片。(12)王衛平:《關于〈大唐中興三藏圣教序〉——兼及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殘片考略》,第255~270頁。所以,若將山東博物館存疑的編號視為一號,則現存敦煌發現的《圣教序》有17號,而吐魯番文書由于比較破碎,《圣教序》的發現遠遠少于敦煌文書。
就筆者目力所及,吐魯番所出《圣教序》除旅順博物館藏四號外,還有大谷4005、大谷10056A(兩號見上考)、大谷7233、大谷7325四號。(13)〔日〕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四),第44頁、第57頁。因此,共有8號。由于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與大谷文書同屬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所以這8號殘片間關系應是比較密切的,茲略述于下。
LM20-1505-0680上下前后皆殘,存3行;LM20-1511-0079存4行字,有界欄,殘片上部保留有較寬的天頭,所以這部分內容應是整件文書的上部;LM20-1511-0086存4行字,有朱點,殘片下部有較寬空白,應為地腳,這部分應位于整件文書的下部;LM20-1486-29-10是件印本殘片,存2行;大谷7233和大谷7325兩號,前者存3行,后者4行,皆有界欄,皆存地腳,兩號也可綴合。根據上述8號殘片的內容,其中幾片十分接近,僅字體略有差異。姑且復原出其在整件文書中的相對關系,以觀上述諸號殘片間的密切關系。(旅順藏兩件圖版掃描自王衛平文)

圖2 LM20-1511-0079、LM20-1511-0086、大谷7233、大谷7325等綴合比對圖
將這5件殘片綴合后(圖2),能清晰地看到其在整件文書中的位置,也能大致了解殘片完整的形態。這些殘片前身和敦煌所存的大多數《圣教序》寫本一樣,每行有16至17字,有界欄,應是較為標準的《圣教序》寫本。字跡整齊且有章法,應出自水平較高的書手。《圣教序》是為褒揚義凈譯經而作,內容上也反映出尊崇釋教的色彩,敦煌本《圣教序》多寫于義凈翻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卷首,可見兩者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僧人將由中宗撰寫的《圣教序》抄寫于《金光明最勝王經》之前,賦予了該經某種權威性或合法性,使其更加便于傳教。吐魯番所見《圣教序》可能也是伴隨著釋典由敦煌傳入西州,抑或出自西州當地僧人之手。
二 《文選·西征賦》殘片
大谷4435號文書(圖3),前后上下殘,存4行,殘存數字。《集成二》定名為“性質不明文書小片”(14)〔日〕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二),第254頁。,《總目》題為“文書殘小片”(15)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第263頁。,據《集成二》錄文如下:

圖3 大谷4435號文書

查檢殘片所書,應是西晉潘安所撰《西征賦》,對應內容據《文選》摘錄于下:
華蓮爛于綠沼,青蕃蔚乎翠瀲。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于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邀于后福。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今復。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楫棹。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圖4 大谷4435號文書比對圖
據圖版,“尉”當為“蔚”之下部,“瀲”和“繳”僅存右半部,“基”當為“舉”之誤識。按《文選》李善注本,第2行“福”下應有小字夾注“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于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于已后之福也……”等字,(16)〔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十《西征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73頁。而該殘片“福”后無夾注,直接跟正文。所以據此可以推斷,該殘片應該是《文選·西征賦》白文無注本。由此,可定名為“《文選·西征賦》殘片”。(圖4)應科舉考試需要,唐人對《文選》非常重視乃至成為一門顯學,這是敦煌吐魯番地區頻繁出現《文選》殘片的主要背景。而具體從書法風格來看,上述殘片似為唐前期的寫本。
吐魯番本《西征賦》殘片見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藏,榮新江先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一書最早對其進行著錄,其寫于佛教故事畫的背面,白文無注本,有朱筆句讀及訂正處,上下均殘,中有斷裂,存《羽獵賦》至《西征賦》部分文字,共239行。(17)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4頁。后饒宗頤先生《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一書對當時所見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寫本有所擴充,其中就收錄有德國藏《西征賦》,并依據1991年朝日新聞社印之《吐魯番古寫本展》的影本附圖于書中。(18)饒宗頤編:《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中華書局,2000年,第52~53頁。此后,相關學者相繼圍繞德藏《西征賦》,對其進行校注,并探討該文書的書寫年代、版本價值等,使該文書得到了充分研究。(19)束錫紅,府憲展:《德藏吐魯番本〈文選〉校議》,《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第56頁;秦丙坤:《〈德藏吐魯番本〈文選〉校議〉商兌補校》,《圖書館雜志》2009年第9期,第71頁;秦丙坤:《〈德藏吐魯番本〈文選〉校議〉摭遺校補》,《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9頁;金少華:《敦煌吐魯番本〈文選〉輯校》,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30頁。
吐魯番本《文選·西征賦》似僅見德藏,大谷4435號《西征賦》殘片與德藏《西征賦》都是白文無注本,但德藏字跡行書較濃,與大谷4435號《西征賦》略有差異。德藏《西征賦》所抄起于首句,訖于“由此觀之”一句,幾乎包含了《西征賦》全部的內容。將德藏《西征賦》復原,每行大約33~35字,與大谷4435號復原的每行25~27字不同。所以兩件應不是同一件文書。
三 《論語·子路》殘片

圖5 大谷3546號文書
大谷3546號文書(圖5),前后上下皆殘,存4行字。《集成二》定名為“性質不明文書”(20)〔日〕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二),第121~122頁。,《總錄》題為“文書殘片”(21)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第186頁。。《集成二》錄文如下:

據圖版,“政”字上字存有一左半部首,“一”字中部有一筆穿過,只是下部墨色較淺。經核查,文書所書內容應是《論語·子路篇》,對應內容為:“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通過比對,“政”上殘存部首應為“以”的殘存筆畫,“一”當為“子”的中間一筆,“日”為“曰”的誤書。第1、4行字略小于第2、3行正文,應為小字夾注,但字跡比較模糊,無法辨識。因此不能確知該殘片為鄭玄的《論語注》還是何晏的《論語集解》。但從書法來看,認定其屬于唐代寫本應大致不誤。
此前吐魯番已發現的《論語·子路》有大谷8110v、大谷8088v、旅順LM20-1461-06-02v、LM20-1461-12-18v和大谷5788諸號,其中前四號皆為鄭注,后一號為何晏集解。(22)參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42~144頁;王啟濤:《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巴蜀書社,2017年,第458頁;何亦凡:《新見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唐寫本鄭玄〈論語〉注》,王振芬,榮新江主編:《絲綢之路與新疆出土文獻:旅順博物館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12~137頁。總的來說,唐代西州地區鄭注《論語》要比何晏《集解》更為流行,(23)姚崇新:《唐代西州的私學與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西域研究》2005年第1期,第1頁。上揭大谷3546號文書不無為鄭注《論語》的可能。
四 《本草經集注》殘片
大谷3608號文書(圖6),前后缺,上部殘,存4行。《集成二》定名為“文學關系文書”,懷疑是書信,(24)〔日〕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二),第131~132頁。《總目》題為“古籍寫本殘片”。(25)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第191頁。《集成二》錄文如下:

圖6 大谷3608號文書

據該殘片圖版,第1行“山”上字有涂抹,第4行三字皆僅存右部。經核查,該殘片第2~4行能夠與《本草經集注》(簡稱《集注》)、《新修本草》和《千金翼方》中的“梅實”條對應。陶弘景《集注》是在《神農本草經》(《本草經》)的基礎上撰成的,其中新增了三百五十六種藥物,并增加《本草經》藥物新功用和陶氏注釋。無論體例還是內容,都較之《本草經》更加完備。唐《新修本草》又是在《集注》的基礎上,增補注文與新藥而修成的。《千金翼方》的前四卷大部分內容又是引錄自《新修本草》,而“梅實”正位于卷四。在不知殘片具體抄自何書的情況下,結合其僅有的信息,只能將其追溯到記載“梅實”信息的源頭,即《集注》。(26)實際上,在《本草經集注》所繼承的《神農本草經》中已有“梅實”的記載,但《集注》較《本草經》內容更加完備,如殘片中所出現“采,火干”的采造時月不見于《本草經》。所以殘片中所載內容應追至《集注》,不能是《本草經》。茲摘錄如下:

圖7 大谷3608號文書比對圖
梅實 味酸平,無毒。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肢體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惡疾,止下痢,好唾,口干。生漢中川谷,五月采,火干。(27)〔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輯校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第467頁。
與圖版比對,大致可以看出第4行前兩字分別為“采”“火”的右部,而“于”應為“干”。此外第3行“止”似可以與“痣”通用,或為誤書?而第1行四字與第2行中間相隔較遠,“南山川谷”與“漢中川谷”對應,應該也是某種藥物的生長地,那么第1行所缺之內容記載的應該是區別于“梅實”的另一種藥物。恰好《集注》中記載的“橘柚”生長地就位于“南山川谷”:
橘柚 味辛,溫,無毒。主胸中瘕逆氣,利水谷,下氣,止嘔咳,除膀胱留熱,下停水,五淋,利小便,主脾不能消谷,氣沖胸中吐逆,霍亂,止泄,去寸白,久服之去臭,下氣,通神明,輕身長年。一名橘皮,生南山川谷,生江南,十月采。(28)〔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輯校本)》,第230頁。
因此,文書第1行前所缺內容很可能為“橘柚”的其他功效。“南”上字僅存筆畫為“一”,應為“生”。結合殘片對應《集注》的內容,能大致復原該殘片的原貌(圖7)。
但這里又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無論《集注》還是《新修本草》都是有注文的,而殘片中僅有正文而無雙行小注。(29)敦煌吐魯番出土有《本草經集注》和《新修本草》,皆有注文。參見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第336~384頁。《千金翼方》雖無注文,但依靠殘片僅有的信息,并不能判斷其抄自《千金翼方》。所以考慮到“橘柚”和“梅實”的史源,將殘片認定為抄自《集注》應是較為穩妥的。并且,在敦煌吐魯番地區,主要的本草教材是《集注》,即使《新修本草》頒布后,仍沒有立刻取代《集注》,兩者并存大致延續到公元700年左右。(30)姚崇新:《唐代西州的醫學教育與醫療實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三》,氏著:《中古藝術宗教與西域歷史論稿》,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71~473頁。這說明《集注》在敦煌吐魯番地區十分流行。那么上述殘片很可能是抄手在抄寫《集注》時將注文省去。
另一個問題是,在《集注》中“橘柚”“梅實”分屬草木上品和果部藥物中品,《新修本草》《千金翼方》沿用之,但殘片中兩者是緊挨著的。按尚志鈞先生輯校的《神農本草經》中,“橘柚”和“梅實”同屬中品藥物,排列序號也相鄰,分別為236、237。(31)尚志鈞校注:《神農本草經校注》,學苑出版社,2008年,第175~176頁。那么殘片是否為《本草經》呢?或抄手依《本草經》的目錄,抄錄《集注》的內容呢?不然。《本草經》內容上,缺少“采,火干”這樣的采造時月,無法與殘片對應。又,“橘柚”在《新修本草》《證類本草》中為上品藥,但因其有“久服去臭下氣通神”的功效,不符合《本草經》上品藥“久服輕身益氣,延年不老”的原則,所以尚志鈞先生輯校的《本草經》將其列入中品藥,與“梅實”相鄰。但其又補充言:“其黑字有‘久服輕身長年。’如確認本條為上品,則此等黑字應改為白字。”(32)尚志鈞校注:《神農本草經校注》,第26頁。可見尚志鈞并不十分確定“橘柚”應當劃歸入中品藥,其所輯校的“橘柚”和“梅實”相鄰的排序也就不十分可靠。總之,無論如何,上述殘片其內容來自于《本草經集注》當是無疑的。
沈澍農先生主編的《敦煌吐魯番醫藥文獻新輯校》對敦煌吐魯番出土的120余號價值較高的醫藥文書進行了校注,該書代前言《敦煌吐魯番醫藥文獻研究總論》一文,對目前所能見到的敦煌吐魯番醫藥文書做了較為全面的編號收錄,并將其分為四級,(33)沈澍農主編:《敦煌吐魯番醫藥文獻新輯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3~67頁。但其中未見上述大谷3608號,由此可作一添補。
五 《大乘法苑義林章》(?)殘片
大谷3555號文書(圖8),由數紙粘貼,附有泥土,前后上下殘,存3行,帶行書風格。《集成二》定名“性質不明文書”,并懷疑可能與書信有關。(34)〔日〕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二),第123頁。《總目》題為“文書殘片”。(35)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第187頁。《集成二》錄文如下:

圖8 大谷3555號文書

據圖版,上引錄文略有疏誤。“以”上字的右部較為清楚,為“攵”,而非“復”的右部。“去”上字為“音”,《集成二》漏,“音”上字殘存筆畫“土”,字形很像“在”。查檢文書內容,似部分對應唐代僧人窺基撰寫的《大乘法苑義林章》:“四明敬意者。瞿波論師二十唯識釋云。欲顯大師有天眼,故以身業禮。有天耳,故以語業禮。有他心,故以意業禮。如律中說。若在明處,以身業禮,以可見故。在闇去近,以語業禮,以可聞故。在闇復遠,以意業禮……”(36)〔唐〕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5冊,第316頁。比對圖版可知,“復”為“故”,“恙”似為“業”,“音”上字為“在”。而第3行“在音去□”似乎能對應“在闇去近”,但仔細辨識殘片“去”下字的字形似不像“近”。按一般情況來說,殘片所存三行之間所缺字數應是均衡的,但如果將第3行對應《大乘法苑義林章》中“在闇去近”一語,則第1行與第2行間缺22字,第2行與第3行間缺8字,兩者相差較大。若將第3行內容對應“在闇復遠”一語,則第2行與第3行間差20字,與殘片前兩行間所差字數接近。而“去”下字的字形也比較像“遠”,所以我們初步比定殘片第3行“在音去□”對應《大乘法苑義林章》中“在闇復遠”一語,那么“去”可能就是“復”的異文。因殘片所存字數不多,不能確知是否就是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的殘片,但其與《大乘法苑義林章》應當存在某種聯系。
窺基撰寫的《大乘法苑義林章》,以章的形式闡明唯識教理并融攝他宗理論,是理解唯識宗學說、教義的指南和重要論著。其在唐末逐漸亡佚,幸日本有所保存,但已非唐時原貌。(37)詳參劉奉禎:《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研究》,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4月,第13~16頁。吐魯番文書中保存有一些窺基的論著,但上考殘片與《大乘法苑義林章》略有異文,尚不能由此確認《大乘法苑義林章》切實地在唐代西州流傳,姑且聊備一說,以期新發現文書。
小結
通過對大谷4005、大谷10056A、大谷4435、大谷3608等諸號殘片的比定和初步整理,我們在《集成》未命名文書殘片中新發現了吐魯番出土的《圣教序》《文選》《論語》等數件漢文典籍。雖然這些殘片殘破嚴重,所含字數非常有限,僅有十余字,卻是唐代典籍的原始物質形態,具有非常重要的古文書寫本學價值。同時,這些唐代典籍抄本內容包羅萬象,展示了唐代西域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進一步證明中原文化在西域邊陲之地也得到極為廣泛的傳播,在文化上西域與內地已是密不可分的統一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