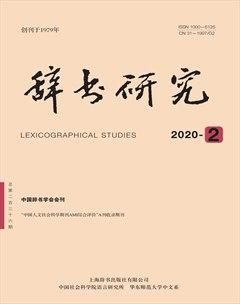從工具書到知識服務
于殿利
摘?要?文章從“應對網絡詞典叢生的需要”“傳統詞典價值創新的需要”“專業知識服務與技術創新的需要”三個方面論述了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提倡從傳統工具書編纂轉向知識服務的原因。面對知識服務時,必須要從理念到實踐徹底改變傳統工具書的編纂和出版。
關鍵詞?工具書?知識服務?傳統詞典?網絡詞典?技術創新
處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時代,傳統的工具書就必須提升到新的知識服務層面。在辭書領域,一談到知識服務,人們就會想到電子詞典、網絡詞典和工具書數字化,但網絡詞典和工具書數字化不等于知識服務,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傳統的工具書編纂理念、編纂方法及所呈現出來的成果,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同知識服務的需求和要求相差太遠。
知識服務跟傳統工具書的編纂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不是把傳統的工具書搬到網上就實現了知識服務。兩者有諸多不同: 首先是理念上的不同。我們編工具書通常也做市場調研,但主要還是自己設置體系,確立收詞原則、釋詞方法等一系列符合規范性的東西,主動權還在我們編者手里。而知識服務是完全不同的,雖然也做市場調查,但不知道對方需要什么,主動權不在我們手里。所以我們必須要根據每一個讀者和用戶的需求去組織我們的知識,提供服務。其次是編纂方法的不同。對于傳統工具書而言,我們是主動創作,讀者則是被動接受。在知識服務環境下,雖然強調了我們的服務意識,但讀者已經不是被動地接受了,讀者也參與其中,他們也是創作者,共創共享,從理念到實踐,這是最大的不同。最后是呈現的成果不同。傳統工具書(不含專業辭書)都是從語文的角度來解詞釋義,而知識服務則不限于此,因為詞語不只是簡單地具有語詞意義,用古羅馬著名思想家和演說家西塞羅的話來說,詞語是事物的符號,而事物是立體性的多方存在,僅從語詞角度是無法對事物進行全面描繪的,甚至僅從語詞角度都無法抓住事物的本質。
為什么說知識服務既是理念也是實踐?因為我們用現有編工具書的方法或者是現有的工具書的存量來提供知識服務是不夠的,我們只能把眾多的工具書拼在一起供讀者查詢,比如一個詞,《新華字典》怎么解釋,《現代漢語詞典》怎么解釋,《辭海》怎么解釋,最終把這些所有的解釋歸結到一起而已。然后才發現,它們大同而小異,能夠查到的意思都有,查不到的,這本沒有其他的也多半沒有。所以從實踐上來說,這促使我們面對知識服務時,必須要從理念到實踐徹底改變傳統工具書的編纂和出版。
為什么要提倡從工具書到知識服務?下面從三個方面談一些粗淺的認識。
一、 應對網絡詞典叢生的需要
(一) 網絡詞典的優勢
首先說說網絡詞典的優勢是什么?我覺得有兩個大優勢。
第一,海量詞匯。我們紙質的工具書,如正在編纂的《現代漢語大詞典》,目標是收詞15.5萬條,也可能有突破,但不會突破太多。我國國內最大的英語詞典之一,陸谷孫先生主編的《英漢大詞典》,收詞約20萬條。與線上提供的各種所謂的“詞霸”相比,傳統工具書中這些大部頭詞典的收詞和規模,還是無法望其項背的。
第二,免費獲取。網絡詞典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免費獲取。為此我們還總遭受道德的考量,包括有一次我在央視做節目,讀者直接就問,你們的詞典為什么不免費?我說知識也是一種勞動創造,而且可能是更復雜、更高級、更耗成本的勞動創造,如果大家不支持知識付費,知識就不能創造出來!沒有人創造知識,對整個人類就是一種災難。現代人應該樹立現代的觀念,用自己的勞動價值去換取他人的勞動價值,而不是總企圖不勞而獲,免費獲取。《新華字典》第11版App上線時,人們對它的強大學習功能贊不絕口,但其40元的零售價,卻引發了熱點式的討論。
(二) 網絡詞典的劣勢
對任何事物而言,所謂的優勢和劣勢,幾乎都是相伴而生的。網絡詞典的所謂優勢,也伴隨著它的三大劣勢。
第一,內容缺乏科學性、準確性,雜亂無章。這就是所謂“海量”的結果之一,各種東西拼湊在一起,不像我們傳統的辭書專家們編的那么成體系。不成系統、雜亂的信息,缺乏準確性,更不具有科學性,這不能叫知識,只有成系統的、科學的、有用的信息才能叫知識,而且才能心安理得地傳授給一代又一代人。我們說現在網上的很多信息不具備這樣的特點,為什么?他們不是在做知識生產、知識創造和知識傳播,他們是以“知識”做釣餌,進行賺錢活動,這也是他們走不遠,而我們還能存活的原因。
第二,功能單一,僅供查詢。這離我們需要的知識服務就差得非常遠了。我們傳統的工具書也一樣,只能夠查詢。但是要面向知識服務,僅供查詢是不夠的。傳統上通常是把字詞典分為查考型和規范型。無論是查考型還是規范型,雖然它們很重要,滿足了讀者對工具書的需求,但是不能滿足知識服務的要求。所以我們要做知識服務的話,就會有多種多樣的內容,要有知識鏈和知識樹,這是我們的優勢,這是網絡詞典所不具備的。因為它們不生產知識,只是拼湊,甚至是搶奪和抄襲。
第三,拼湊的辭書是沒有思想性的。而思想性是辭書編纂的要義,是辭書文化性的核心,也是傳統辭書出版的命脈。近年來,辭書界開始強調用辭書來凝固“集體記憶”,這體現了辭書編纂的一個新思想。一個同樣的事情,不同的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記憶,這就是說,辭書在面對同樣事物的時候是會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闡釋的,這就是我們說的思想性。胡編、堆起來的辭書是沒有這個意識的。
所以這里有一個概念,希望我們做編輯的人能夠記住,叫“信息守門人”或“知識守門人”。這是現代新文化著名史學家彼得·伯克(2017)在他的《知識社會史》一書中所提出的。我認為編輯就是最大的、最重要的“知識守門人”。還有我們的專家和學者,他們不僅僅是守門人,還是把第一道關的創作者,編輯是又一道守門人。沒有這道關卡的守門人,就沒有這些辭書。同樣一個事物,無論是自然的事物,還是社會歷史的事物,都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釋。所以現在大家講,我們的學術建構、我們面臨文化競爭的時候,最大的問題來自什么?話語權缺失。話語權缺失就是我們知識體系的建構出了問題。我們的知識體系建構要反映我們自身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以及我們自身的社會發展。所以,工具書編纂在這些方面要重新樹立起這樣的意識,要樹立起思想性這個意識,而這是網絡詞典所不具備的。
(三) 應對策略
面對來自外部、汗牛充棟的網絡詞典,無論是就其所謂優勢給我們造成的沖擊,還是就其劣勢所造成的不良社會影響而言,我們傳統的辭書出版界都有必要,也有責任采取相應的策略進行應對。
第一,以專業海量來搏泛海量。我們可以在專業領域科學性、嚴謹性、準確性、系統性的基礎上,擴大我們的收詞,這是首個必經之路。網絡上的所謂海量,無法做到傳統辭書專家慣常所做的,全用專業的態度、專業的知識、專業的技能去解釋。而專家和專業,恰恰就是我們的強項。關鍵在于我們要加大專業的范圍、收詞的范圍、解詞的范圍,要用專業的海量去搏這個泛海量。一個個領域的專業海量集合在一起之后,那就是巨大的海量。而那些完全不足信的泛海量,就變得僅僅是應一時手頭之急查一下而已,不足征信,不足引用,因為它們不能作為科學知識傳播。這就是我們應有的策略。
第二,用知識服務去搏簡單查詢。知識服務要提供知識窗、知識樹和知識鏈,這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創造,耗時、耗力、耗人、耗財,這是急功近利的網絡詞典無法做到的。就算基于傳統工具書去做簡單的知識服務,也是網絡詞典難以企及的。以《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App為例,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突出了學習性和學習功能。比如,在傳統據詞查義的基礎上,這款App提供了更為強大的同義詞、近義詞和反義詞的比較、辨析功能;在查閱過程中,只要在任何地方遇到不認識、不理解的字詞,只要點擊它,就可以直接進入到其查詢頁面,非常便捷;此外,還設置了成語接龍和自定義學習文件夾等。
第三,以持續增值服務搏一次性查詢。當龐大的專業數據庫建起來后,不是只提供一次性的查詢、一次性的服務,而是要提供持續的增值服務。即使不斷有新版,原來在紙質圖書里被刪除的舊詞,作為歷史資料,仍舊可以保留在數據庫里。因為我們看的書不只是反映現代社會的,還反映過往歷史、社會發展階段的,甚至還有反映人類其他文明的。傳統的紙質辭書,受篇幅所限,注定要與時俱進,不斷修訂,不斷增刪,這是符合辭書編纂規律和社會發展需要的,但歷史數據庫建設和在此基礎上提供的知識服務,是符合新時期辭書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需要的。這是新時代給我們提出的新任務,我們傳統辭書出版人責無旁貸,也是別人無法“旁貸”的。
二、 傳統詞典價值創新的需要
傳統詞典最重要的出發點是從語詞解釋語詞,盡管我們很努力地去闡釋它的社會價值,闡釋它在其他專業里的意義和內容,但這畢竟不是我們的專業所長,我們編來編去還是善于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現代辭書編纂學的角度給它進行語詞式的定義。這就使知識服務面臨一個難題。盡管語言學家們經常強調,所有知識都是用語文作為工具在閱讀的,但我要強調的是另一個方面,即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詞匯都不只是語詞的存在。西塞羅說,詞語是事物的符號,任何一個詞語反映的都是一個事物,所以我們解詞,從詞語解釋詞語的時候,就不一定能夠揭示出這個事物的本質性存在。這是一個問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著名詩人斯蒂芬·格奧爾格在其詩篇《詞語》的最后一句說:“詞語破碎處,無物可存在。”[1]海德格爾的名著《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幾乎就是在研究這一句話。所以我接下來想說的是,我們傳統詞典價值創新要向知識服務努力,就是要突破語詞這樣的一個界限,從而進入到事物之中,進入到事物的本質之中。
(一) 把語詞釋義引向深入
傳統詞典在語詞的釋義方面也有不夠的地方,僅從語詞解釋詞的角度來說,還可以有再深化的地方。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在本文中所舉的例子都出自《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辭海》《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等權威辭書,我沒有任何對這些字詞典的不敬或者認為不好的意思。大家知道這些辭書都是一座座的高峰,甚至可以說是無法超越的。我只是想說,從知識服務的角度來說,傳統辭書的這些解釋還需要進一步再擴展、再深入。
比如說“褥子”這個詞的解釋:
《新華字典》第11版: 裝著棉絮鋪在床上的東西。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 睡覺時墊在身體下面的東西,用棉花做成,也有用獸皮等制成的。
《辭海》第6版: 坐臥時墊身的用具。
限于篇幅,《新華字典》的解釋相對簡單,沒有“床上用品”這樣的定性語,但也指出了功能“鋪在床上”和材料“裝著棉絮”等關鍵要素;《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又增加了“睡覺時墊在身體下面”等詳細功用,但仍然用“東西”這樣泛的概念,而缺乏具體、確切的定性表達;釋義最簡單的是《辭海》,本來作為具有百科特征的辭書,其釋義應該更全面,但卻只有簡單的八個字,而且拋開“褥子”這個詞,人們根本無法從釋義中聯想到這個東西是褥子,它只描述了一個簡單的功能“坐臥時墊身”,而用于“坐臥時墊身”的東西還有許多,且“坐時墊身”的解釋明顯不合適,坐在身下的不叫“褥子”。無論“褥”這個字在古代是否用于坐,但現代的“褥子”只用于“臥”,且與床或具有床的功用的東西相關。《辭海》的釋義還缺少了制作材料之類的內容。僅就“褥子”這個例詞而言,我們在解釋這個事物的時候,至少要考慮到它的材料、工序,甚至制作流程、功能、效用等,這在很多方面是不能缺的。而《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和《辭海》等的解釋,可以說都難令人滿意。就功能而言,三部權威的工具書都指出了“墊身”的功能,卻無一進一步指出墊身是為了“保暖”或“柔軟舒適”的效用,而這恰恰是“褥子”的主要功能,“墊身”只是表象,如果只用來墊身,還可以用其他東西,比如為了涼爽的功效,墊身就不能用褥子,而要用“涼席”;就工藝而言,只有《新華字典》給出了“裝著棉絮”的解釋,而對于最為關鍵的信息,即外面要用棉布或其他可縫制材料做成里面可以裝填充物的東西,然后里面才可以均勻地排布上棉絮之類的材料,最后用針線把外面的布料和里面的填充材料縫制在一起;就產品品相而言,“褥子”還與床以及用作床功用的東西的形狀和大小尺寸等相關,例如圓形的就不能叫“褥子”,而叫椅墊或蒲團,太小的可能用作“枕墊”等。
再比如說“走、跑、跳”。什么是“走”?這些詞典從語詞的角度、行動的角度解釋都是對的: 一個人有兩條腿,兩條腿不能同時離地,要交叉前行叫“走”;四條腿的動物也是一樣的,至少是兩條腿和兩條腿交叉,不能四條腿同時騰空離地的,這叫“走”。“跑”是什么?就是兩條腿可以同時離地快速前行。所以我們看到世界競走錦標賽,裁判員給這個運動員出示紅牌和黃牌的依據是兩個腳有沒有同時離地,有同時離地的就不叫“競走”,他判定你是“跑”。關于“跳”,《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的解釋最準確,無論是“走”“跑”,還是“跳”,各權威詞典都只是側重于“行動”,而無暇顧及其他豐富的含義。
我再說說“顛兒”。從走路的姿勢和語詞的角度來說,幾乎沒有辦法描繪它。我們通常用到這個詞的時候,表示的是什么?這個人的精神狀態、精神面貌,重點是這個。比如我們在說“跑”的時候,《現代漢語詞典》和《辭海》都說,“跑”有的時候不一定意味著跑,有的時候它也是走,比如“會還沒開完他就跑了”,也經常說“會還沒有開完他就顛兒了”。這個時候的“跑”和“顛兒”表達的都是一種情感,描述的是人的神態、狀態和意愿,他不愿意開這個會了,沒等開完他就先走了。這里的“顛兒”還有“偷偷地走”的意思,不告知,不請假。所以僅僅是從兩條腿還是四條腿離不離地的角度來說,或是向上還是向前的方向,是沒有辦法解釋的。另外,跑跑顛顛和蹦蹦跳跳描繪的就更是情境、情感和狀態了。所以,詞典中的“顛兒、走、跑、跳”都是從語言學角度對動作本身的闡釋,沒有辦法表達神態和情感狀態。這些提醒我們在做知識服務的時候,注意這些詞之間的差異和辨析,能夠把它真正的意義,尤其是在語詞之外的意義解釋出來,但我們傳統的工具書由于篇幅有限,可能容納不了。
再舉一個例子。閱讀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但關于什么是閱讀,閱讀的本質是什么,在學術上也存在著模糊的認識。這也引發了我的好奇。什么是“閱讀”?《現代漢語詞典》說看書報等并領會其內容。《漢語大詞典》意思跟這一樣。《辭海》沒有收“閱讀”條,卻收了“閱讀框”和“閱讀衛生”。我們只好向古人求助。許慎的《說文解字》[2],“讀,誦書也” ;“誦,諷也”;“諷,誦也” 。鄭玄及后代名家的注解釋了,“倍文曰諷”,那個“倍”通“背誦”的“背”。“以聲節之曰誦。”所以,朗誦是要有韻律、有節奏地發聲的。接下來在《說文·竹部》里邊又看到了“籀,讀書也”。“籀”是什么?段玉裁的注里解釋,“蓋籀、抽古通用”。“籀”和“抽”兩個字互訓,古代是通的。所以就知道了“籀”是“抽”的意思。那“抽”又是什么?是“抽繹其意蘊至于無窮,是之謂讀”。由此我可以抽繹出閱讀本來有三層含義。第一,誦也,就是有節奏地朗讀、朗誦。第二,背文也,就是要把文字背下來。第三,要不斷地思考領會其意蘊,不是看完一遍就完了。所以一次領會還不夠,不是說你懂了它就行了,還要不斷地去發現它的意義、去思考,沒有止境。現在我們還有人批評讀書不過腦、不走心的現象,說的就是光念不行,不背、不記、不領會記憶、不思考不行。真正的閱讀是什么?接觸能夠促發思考的文字才能叫閱讀。閱讀的真諦在于促進思維和思想,積累知識是促進思維和思考的前提。
(二) 突破語詞釋義的藩籬
這里我舉三個例子。
一個是“興趣”,interest。權威工具書的解釋如下: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 喜好的情緒。
《辭海》第6版: 注意與探究某種事物或從事某種活動的積極態度與傾向。表現為個體對某種事物或某項活動的選擇性態度和積極的情緒反應。是個體需要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9版: the feeling that you have when you want to know or learn more about sb/sth.
這三部中外權威工具書對“興趣”的解釋,都集中在了人對于事物的情緒、情感和態度方面,這體現了語言學家和辭書編纂家典型的視角。
從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的角度來說,“興趣”是什么呢?美國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喬治·桑塔亞那(2016)3、5講了這么一段話:“某些東西之所以有趣,那是因為我們關心它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需要它們。如果我們對所感覺的那個世界毫無興趣,我們就會對它閉上眼睛;如果我們的理智并不幫助我們的情感,而是偷懶地讓幻想自由奔馳,那么,我們甚至會懷疑二加二是否還會等于四。……當理智是活生生的和強有力的時候,它會給那些有可能成功的興趣愛好以勇氣和特權,而削弱或泯滅其他那些看起來注定要失敗的興趣愛好。”
接下來我們看interest。海德格爾(2017)在《什么叫思想》里,特別強調了interest,他做了拉丁語詞根的追溯,是inter+esse。inter是“進入到……當中去”,轉化成介詞之后就變成了“在……之中”。esse是一個拉丁詞,就是具體事物本身,哲學上翻譯成“存在”(海德格爾2017),就是具體事物的存在。所以真正的興趣,在海德格爾看來是什么?是進入到事物當中去,是行動。他說:“興趣的意思是: 處于事物當中,在事物之間,置身于某個事物的中心并且高于這個事物。”光說對什么有興趣,浮光掠影的,走馬觀花的不叫興趣;進入到里面去,進入到實踐當中去,才叫興趣。海德格爾針對的是當時人人都說自己喜歡哲學卻沒有人去思想的現象,他說這就不是有興趣,真正對哲學有興趣就是要思想,思想了,才叫有興趣。所以“興趣”是什么?第一,它是一種情感,但不能僅僅停留在娛樂層面,必須附著意義和價值。人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性的存在,如果沒有價值,人沒有必要更沒有理由活在這個地球上。所以人所有的興趣,包括娛樂也是一樣的,都不僅僅是為了娛樂。娛樂只是一種手段。第二,興趣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培養的,它需要理智來幫助培養,如果失去理智,興趣就會信馬由韁,會讓我們毀掉本來可以很美好的東西,甚至毀掉原本已建立的認知和秩序。第三,真正的興趣意味著行動和實踐,進入事物之中,對事物的喜好,如果只停留在口頭上或情緒上,而不付諸行動,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興趣。比如說,真正的足球迷是要喜歡踢足球,并且經常到場上去踢,而不喜歡踢只喜歡看的球迷,不能說對足球有興趣,只能說對看足球比賽感興趣,甚至有的人還只喜歡看電視轉播,從來不走進球場看現場比賽。
第二個是“品牌”。《現代漢語詞典》認為“品牌”是產品的牌子。《辭海》采用了舊式管理學家對品牌的解釋,除了牌子之外,它還指企業能夠辨識的標識。但是就現在近二三十年來的企業管理實踐來說,品牌不能僅停留在牌子上,而必須與價值連在一起。當你說到麥當勞的時候,你就一定要知道它的價值是什么,這是它的品牌核心。所以真正的“品牌”的最新概念是,“產品或生產企業在消費者心里的記憶,或者在消費者心中留下來的印象”,它是隱藏在牌子背后的價值。所以品牌不屬于企業,品牌屬于消費者,屬于顧客,他認你你就有,他不認你你就沒有。從管理學角度看,“品牌=品質+招牌”。所謂的“品質”就是產品內在和外在的質量,“質量”是指產品達到合格標準前提下的自然等級,“品”還含有道德評價;所謂的“招牌”,就是自己用以區別于別人的獨特之處。從品牌戰略角度來說,就是“差異化”。品牌有高低之分,無貴賤之別。
最后一個是“家”。先看權威語文辭書如何解釋: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 掌握某種專門學識或從事某種專門活動的人。舉例有科學家、藝術家、野心家和陰謀家等。
《辭海》: 經營某種行業,掌握某種專門學識、技能或從事某種專門活動的人。如: 商家;行家;專家;科學家。
應該說,《現代漢語詞典》和《辭海》都沒有把“家”在這個義項上的核心或本質特征揭示出來,其他辭書雖然我未曾查考,相信情況應該相似。這里面最大的問題在于,專門從事某種活動的人不一定能成為“家”。農民工每天都在建筑隊里搬磚、建造房屋,但他永遠不能成為建筑家。能夠成為“家”的關鍵因素是什么?不在于是否“專門”,否則就無法理解有的人為什么可以身兼多種“家”的稱號了。第一,無論干好事還是干壞事,只有從事某種活動并達到一定的水準和成就,才能稱為“家”。干好事的如科學家、歌唱家,干壞事的如野心家、陰謀家,但是必須得達到一定的水準或者取得一定的成就。第二,這水準和成就必須被社會公認才行。達到一定的水準沒有具體規定,也不一定能量化。比如,歌唱家不是以唱多少首歌為標準,而是以所唱的歌的影響多大為標準。酒吧里的歌手即使一晚上可以演唱近百首歌,也不一定能成為歌唱家,但是郭蘭英的一曲“一條大河波浪寬……”影響了那么多年,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她就是歌唱家。第三,“家”是別人對自己的稱呼,本人不能自己稱呼,尤其是用在尊稱或表示敬意的時候。我曾兩次在電視里看到,錢學森先生接受采訪的時候,都說“我作為科技工作者”,從來都不說“我作為一個科學家”如何如何,因為不管成就多大,“科學家”也得由別人稱呼。我們在媒體上經常看到在采訪時有人說“我作為××家”之類的,這些都是錯誤的。另外,《辭海》還把商家和科學家等一并拿來舉例,也是不恰當的。諸如“商家”“廠家”之類的“家”,與“科學家”和“歌唱家”等稱呼的“家”,根本就不是一個意思,“商家”指的不是自然人,“商家”等不一定具有專門性,或專門從事某種行業,有的綜合性大商場或大型超市,也叫“商家”,所銷售的商品五花八門;在零售行業里,它們也不一定非要達到一定水平或具有一定影響,只要是從事銷售或生產的企業,就都可以稱為“商家”或“廠家”。
(三) 用法錯誤與詞義辨析
我們傳統的詞典里很少有詞義辨析和用法提示等內容,而諸如“聆聽”這樣的詞經常會被錯用。在很多高級的會議上,甚至是很高層面的學術會議上,經常能夠聽到演講者以“謝謝聆聽”作為結束語,或者在其最后一頁PPT上寫著醒目的四個大字:“謝謝聆聽!”這樣的用詞錯誤,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應該引起我們辭書工作者和出版機構注意和重視。
“聆”和“聽”是互訓的,“聆”就是“聽”,“聽”就是“聆”,這個詞本身是沒有情感的。但是語言學中有一個“語義偏移”的現象,給了我一個啟示。這個詞在實踐過程中語義開始偏移了,偏移到什么地方了?漢代王充《論衡·自紀》提道:“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這句話的意思是指當我的耳朵獲悉到一個信息之后,我就好像盲人突然開目可視,又像聾人突然開耳可以聽到一樣。在這里,本來中性、沒有情感只作“聽”的“聆”,具有了情感,具有了“自謙”的意蘊。因此,“聆聽”有仔細傾聽并清楚知道、細致了解而得到教益的意思,其中通過認真聽而受教,既表達了一種恭敬的態度,也表達了自己肯定能夠聽并有所獲從而對講者的稱贊甚至崇拜之情。所以這個話就只能自己說,你不能跟別人說:“你聆聽我的話,你是不是像盲人一樣突然能看見了?”“聆聽”的語義偏移,從而變成了一個聽者自謙的詞,屬于“表敬”語。“聆教”也好,“聆取”也好,“聆聽”也好,都是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去聽別人在說什么。無論你多么牛,你也不能對人家說“謝謝聆聽”,只能說“我非常有幸聆聽您的教誨”。
接下來再說有點兒爭議的“會師”。《現代漢語詞典》《辭海》《漢語大詞典》對它的解釋都沒有問題,但是隱含的一個事情沒有說出來,這就造成了用法的錯誤。這個詞隱含的意思是在一個團隊和一個組織內的分支從不同的方向或地方聚到一起,不屬于一個組織的不能叫“會師”。我們經常會看到錯誤的用法,比如“林丹和李宗偉又一次會師決賽”,他倆是對手,不能會師。那么“自己人”和“自己人”就可以會師嗎?我們看到了丁寧和王曼昱在中國公開賽會師,這個可以。中國公開賽也是有外國選手參加的,它是國際賽事,她們同為中國選手參賽,所以是可以會師的。會師就是勝利會師了,她倆進入決賽之后還要再打,能叫會師嗎?這事我就不知道了,交給語言學家去討論吧。但是當她倆參加全國錦標賽,就不能叫會師了,因為她們代表了不同的省市參賽。
報紙、廣播等媒體和日常生活中人們讀錯“粗獷”的頻率很高,隨處可以聽到cūkuànɡ,其實應該是cūɡuǎnɡ。這么高頻率出錯的詞,在詞典中應該標注出來。但如果所有的錯都標注,詞典的篇幅無法滿足,因此就又得借助數字技術所提供的知識服務,知識服務能夠滿足這個需求。
最后再舉一個“愉快”和“高興”的例子。我們通常解釋“愉快”的時候是高興,解釋“高興”的時候又說愉快。然后人家問到底啥是“愉快”,啥是“高興”?“愉快”包含兩個豎心旁,重在內心體驗,不一定能夠感染別人;“高興”是一種外在的表現,是外露的情緒,是可以感染別人的。二者是可以區分開的。但我們的解釋有不少是互訓的,所以這就造成了缺陷。因此在辨析這一塊,我們的知識服務大有可為。
三、 專業知識服務與技術創新的需要
辭書不僅僅包括語詞詞典,還要包括各學科的專業辭書。那么,各個專科的知識辭書就是我國辭書事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多年來我們也一直在呼吁,也盡可能身體力行地做,但是收效不大,其中有很復雜的原因。比如,語文辭書專家不熟悉各學科的專業知識,他們只懂得辭書編纂的方法和辭書編纂規律性的東西,這還遠遠不夠;專業學者在專業領域有很深的研究,但是不會編詞典,不懂得辭書編纂的方法和規律;這兩者之間相互學習、取長補短需要長效機制,而學界尚沒有建立起這種長效機制;學界和相關主管部門對辭書編纂抱有偏見,致使辭書編纂不被納入學術成果考量范圍,很少有學者尤其是專業學者愿意投入到辭書編纂事業中來。就連語文辭書的專家隊伍建設,都令人擔憂。早在一百余年前,《辭源》的編纂者就發出了“一國之文化常與其辭書相比例,國無辭書,無文化可言”的吶喊,我國的辭書工作者也以此為自己的座右銘,希望它能在新時代激發起我國辭書事業新的發展,尤其是盡快彌補專業辭書編纂、出版的短板。希望媒體融合時代的知識服務,能夠為新時代的辭書創新,提供新的、更加強大的動力。
另外,在媒體融合的新時代,我們寄望于技術創新,也寄望于內容創新與技術創新相互激勵,共同成長。技術創造大數據,提供歷史資料數據服務。新技術使知識綜合化,提供釋義的文化延伸服務。新技術創造新知識,提供定制知識服務。新技術創造新形式,新形式創造新價值。
總的說來,知識服務是時代的呼喚,傳統的辭書編纂距離知識服務的要求和需求,還差得很遠,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很艱苦甚至長期的努力。《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和《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等中外品牌辭書的App,已經具有了標志性的意義,中國辭書的知識服務已經拉開了序幕,只要辭書人努力,未來就值得期待。
附?注
[1]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0: 150。
[2]以下引文均引自許慎.說文解字.湯可敬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2018: 473-921。
參考文獻
1. 彼得·伯克.知識社會史(下卷).汪一帆,趙博囡譯.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 99.
2. 海德格爾.什么叫思想?.孫周興譯∥孫周興,王慶節主編.海德格爾文集.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7: 7.
3. 喬治·桑塔亞那.人性與價值.陳海明,仲霞,樂愛國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6.
(商務印書館?北京?100710)
(責任編輯?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