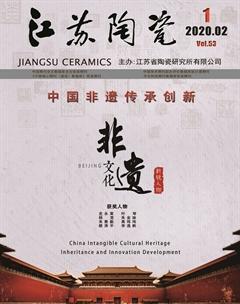在藝術的獨特性上尋找自己的創作語言
龔潔
《陽羨名壺系》有一段關于陳仲美的文字能引起我們對于設計創作的思考,“陳仲美,婺源人,初造瓷于景德鎮。以業之者多,不足成其名棄之而來。好配壺土,意造諸玩,如香盒、花杯、狻猊(傳說中似獅子的猛獸)爐、辟邪鎮紙,重餿疊刻,細極鬼工,壺像花果,綴以草蟲,或龍戲海濤,伸爪出目;至塑大士像,莊嚴慈憫、神采欲生、瓔珞花蔓,不可思議。”這一段記載給我的啟示有三:一是陳仲美不愿在江西景德鎮“萬人造瓷”的環境中碌碌無為,顯示不出自己的個性,因而來到宜興,在紫砂這一領域尋找能夠顯示他獨特才能的作品。二是他來到宜興后,他所創作的主要作品是不與人同的“雜件”,如香盒、花杯、狻猊爐、鸚鵡杯等。三是他把自己擅長的重餿疊刻的技藝用于紫砂壺創作,他創作的“束竹柴圓壺”,化廢為寶,在被人廢棄的放置年久的竹柴中,尋找到一種陳舊的、殘缺的美感。宜興多山又多竹,廢棄的竹柴家家都有,他能從人們眼中所常見之物中發現不尋常的美,說明他對生活的仔細觀察和尋覓,把這種竹柴環束成壺,同時他對紫砂的泥色也有獨特的研究,選用的泥色在燒成后接近于這種竹柴的原色,所以,“束竹柴圓壺”無論在“形”,還是在“色”上都有自然天成、生動逼真的欣賞功能,他的作品被《陽羨茗壺系》列入“神品”。這種在藝術上有獨特性的作品,人們是不會忘記它的。
“南瓜壺”(見圖1)的設計創作,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加進自己的藝術思考、美學見解,對自然界的形有所取舍、有所變化而設計創作的。傳統的“南瓜壺”,明代有陳子畦的“南瓜壺”,清代有陳鳴遠的“東陵瓜壺”,皆以南瓜之形為壺身,以南瓜的藤、葉、柄為把、嘴、鈕,妙造自然、形態逼真,發揮了他們的塑器專長。“南瓜壺”在創作設計的過程中對南瓜的形態作了大膽的取舍,甚至變筋紋壺為圓壺,保留的僅是具有南瓜特征的藤、葉的形態。楊永善在《陶瓷造型藝術》一書中關于“模擬變形與簡化”的一節中論述到:“依據客觀存在的形態,其中包括自然界的形態和人為創造的形態,研究其基本結構特征和視覺印象,根據陶瓷造型的需要加以選擇,進行概括、刪除、轉換和變形,突出器物所需要的部分,減弱不必要的部分和細部,通過各種方法形成新的形態,并引發出更多的樣式,使之符合陶瓷器物造型的條件,我們把這種形態形成的方法稱為模擬概括。”變化了原有形態的“南瓜壺”產生了另一種自然情趣,把南瓜的藤莖、瓜葉之美展現在人們眼前,成為了“南瓜壺”的另一種樣式。
“南瓜壺”的鈕、嘴、把皆以南瓜的藤莖形狀塑成,嘴為直嘴,鈕為向一側彎曲的形態,把為環把。南瓜的藤莖為多棱形,要塑造這一形態,必須制作專用的工具,把這一條條的“棱”精細地刻畫出來,達到線型流暢、生動自然的要求。一張南瓜葉履蓋在壺蓋上,包裹到壺體的中部與嘴、把的部分。對葉的形態作了夸張變形的處理,使之狀若荷葉不規則地伸展,由于蓋為嵌蓋,蓋口相合又基本無縫,保證了葉的形態的完整性。葉的筋脈細密、縱橫分布,對之要作精細的刻畫。其主葉脈從壺鈕底部直貫而下,直至葉的邊緣處,流暢的線型向四面伸展,與下部光潤的壺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動一靜,相互映襯。“南瓜壺”把造型與裝飾融為一體,在光貨壺的基礎上作簡約的裝飾,從上而下,瓜葉覆蓋的面積接近于壺體的二分之一,這種有控制的裝飾使下部光潤的壺體顯示出紫砂特有的肌理之美,從而襯托出裝飾部位精到細膩的裝飾效果。
在礦泥的選材上,“南瓜壺”也有它的獨到之處。在燒成后,它顯示出黃中透白的米黃色。在段泥中,泥色偏黃的多,燒成火候偏高的則偏青,但黃中偏白的少。在黃龍山礦泥中有一種被稱之為“定窯白”的礦泥,它在《陽羨茗壺系》中有記載:“泥色有海棠紅、朱砂紫、定窯白、冷金黃、淡墨……”這種“定窯白”的礦泥,與丁蜀鎮白泥場所產的白泥有所不同,白泥場所產的白泥泥質粗,與泥漿混合制成的坯體在燒成后產生不了如紫砂泥在燒成后能顯現的如玉色一樣的“包漿”,所以這種白泥只能制作日用陶的砂鍋等。而黃龍山的“定窯白”礦泥在燒成后能生成紫砂泥獨有的“包漿”,這是這種礦泥的顯著優點。“南瓜壺”所選用的段泥,含有大量的“定窯白”礦泥,燒成后黃中透白,顯示了它的珍稀的特征。
現在的生活多姿多彩,給我們營造了良好的創作環境。構思和技藝是創作必不可少的條件,獨特的構思需要精湛的技藝來完成。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需要多方面的藝術修養,只有在創新的道路上不斷探索、勇往直前,我們才能創作出眾多的新作,這樣才無愧于我們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