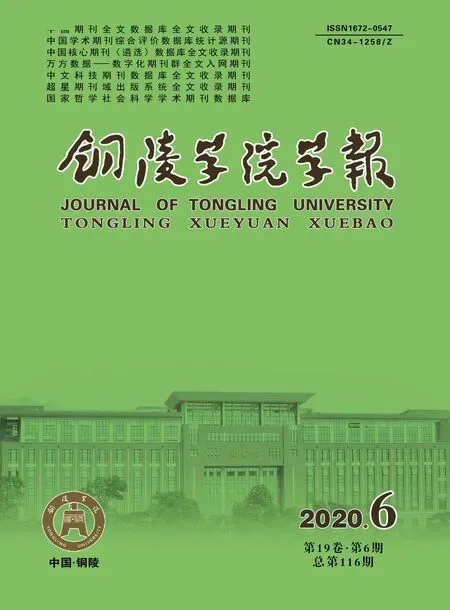金融集聚、政府干預與出口競爭力
張 盟 阮素梅
(安徽財經大學,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出口貿易作為經濟支柱之一,在我國的快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的出口貿易總額從2000 年的20,634.44 億元增長到2019 年的172,342.00 億元,同比增長了7.35 倍;此外,貿易差額從2000 年的1,995.63 的億元增長到2019 年的29,180.00 的億元,同比增長了13.62 倍,貿易順差增長率遠大于出口增長率。同時,高新技術商品出口比重不斷擴大,出口結構不斷優化,我國出口的綜合競爭能力不斷加強。金融業作為服務業的核心產業,金融資源也開始在空間上呈現出一種集聚現象,對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著推動作用。此外,各地政府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率不斷引導資源流動和干預資本配置。在此背景下,金融集聚能否有效促進出口規模擴張和優化出口結構?在此過程中政府干預有具有怎樣的調節效應?研究這些問題,對于提高我國出口競爭力,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在金融集聚的概念方面,Kindle Berger(1974)最早提出金融集聚其實就是金融機構在位置上的一種集聚現象[1]。目前我國對金融集聚的概念未達成一致,主要有劉軍等(2007)和梁穎(2006)分別從地域性和產業集聚的角度進行定義[2-3]。對于金融集聚產生的動因和效應,Krugman(1990)和David B(1996)等認為金融集聚具有外部性、規模經濟、技術創新和信息服務等效應,同時這些也是金融集聚出現的內在動因[4-8]。在國內的目前研究中,黃解宇(2011)從微觀角度進行分析,發現空間地理的外在性、信息的不對稱性和內外部的規模經濟是金融集聚的三點因素[9]。
但是,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能夠有效促進出口貿易。曾璐璐(2015)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對于地方出口增長具有促進作用[10]。吉陽(2015)以北京市為例進行實證分析,得出金融業規模的擴大對進口貿易規模的擴張存在顯著的正效應的結論[11]。劉鉆石(2016)對金融發展水平和國際貿易結構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證明了金融發展水平會影響出口貿易的結構和比較優勢[12]。杜運蘇(2016)運用面板分數位模型證實了金融發展從金融結構、金融效率和金融規模三個維度均能有效促進中國出口二元邊際增長[13]。黎日榮(2019)將企業出口具體分解為出口規模和出口競爭力兩個層面,發現金融發展在促進出口規模擴張的同時,并沒有提高企業的出口競爭力[14]。
梳理文獻發現,金融集聚能夠促進信息流動、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同時金融發展對于出口貿易具有明顯的促進效應,但是目前國內缺乏金融集聚與出口貿易的關系研究。因此,本文從金融集聚的角度出發,將出口競爭力細分為出口規模和出口結構兩個維度,全面、深入地考察金融集聚對我國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實證檢驗政府干預的調節作用。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參考現有文獻,本文對出口規模和出口結構設定了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模型如下所示:

為了驗證政府干預在作用過程中的影響,加上交互項之后,上述模型調整為

在(1)至(4)式中,變量下標中的i 和t 分別表示年份和省份;lnexport1it和export2it是本文的兩個被解釋變量,分別代表出口規模和出口結構;LQit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代表金融聚集水平;goverit是本文的調節變量,代表政府干預程度;LQit*goverit表示兩者的交互項。其余變量均為控制變量,按照順序分別代表投資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技術水平、交通運輸能力和產業結構,εit代表系統隨機誤差項,θt為年份效應。
(二)指標說明
1.被解釋變量:出口規模(lnexport1)和出口結構(export2)
出口規模采用經營單位所在地出口總額,為了保證統計單位的統一,根據當年美元兌人民幣的平均匯率,出口總額以人民幣為單位進行計量,用符號export1表示,為消除數據的波動性,避免異方差對其進行對數化處理;用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與出口總額的比率表示出口結構,符號為export2,這一比率越高,表示出口結構越好,優化程度越高。
2.核心解釋變量:金融資源的聚集程度(LQ)
為了便于金融資源的量化統計,本文參照秦放鳴(2020)使用GDP 中的金融增加值來代表金融資源,采用衡量產業集聚的區位熵(LQ)的方式衡量金融資源的聚集程度,同時該指標能夠反映某一產業部門的專業化程度以及某一區域在高層次區域的地位和作用[15],公式為:

(5)式中,fGDPit是i 地區在t 年份的金融業增加值,Yit是i 地區在t 年份的第三產業產值,∑fGDPit是全國各地區在t 年份金融業增加值之和,∑Yit是全國各地區在t 年份第三產業增加值之和。LQit>1,表示金融集聚程度大于全國平均水平,LQit=1,表示金融集聚程度等于全國平均水平,LQit<1,表示金融集聚程度小于全國水平。
3.調節變量:政府干預(gover)
地方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收支來干預金融經濟,本文根據劉海飛(2017)選取財政支出和收入的比值來代表政府干預指標,LQ*gover 表示金融集聚和政府干預的交互項[16]。
4.控制變量。資本水平(capital):資本存量與投資量直接關系到商品的生產能力,進而影響出口的規模和結構。本文采取各省份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衡量資本水平;技術水平(tech):先進的技術創新能力能夠有效促進出口擴張和結構優化。本文選取各省份的專利受理數量衡量技術水平;經濟發展水平(gdp):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一個地區的出口競爭能力。本文選取各省份的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經濟發展水平;交通運輸能力(transport):便利的交通運輸能夠有效促進出口增長。本文選取各省份年貨運量衡量交通運輸能力。產業結構(ts):合理的產業結構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產出能力,增強出口競爭力。本文選取第二產業增加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衡量產業結構。為了消除數據的波動,避免異方差,對上述產業結構之外的控制變量進行對數處理。各變量經過匯總后,可以得到如下描述性統計表格,見表1。
(三)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取的為30 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平衡面板數據(由于西藏地區部分數據缺失,未納入統計)。所有原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時間跨度為2002-2017 年。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需要對數據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以避免出現偽回歸的現象。本文同時使用LLC 和Fisher-ADF 兩種方式進行檢驗,并根據結果綜合判斷數據是否平穩。根據表2 可以判斷各數據均為平穩時間序列,不存在偽回歸的現像。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2 平穩性檢驗結果
(二)全樣本估計結果
首先,為了驗證金融集聚對于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對模型(1)和模型(2)進行檢驗。同時,為了考察模型中是否存在年份效應,設立不控制年份效應和控制年份效應的兩組回歸進行對照分析。根據表3 結果顯示,無論是否控制年份效應,金融集聚都會同時對出口結構和出口規模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加入年份效應后回歸結果發生變化,且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更加符合實際情況,可靠性更高,因此本文均采用控制年份效應的模型進行分析。
金融集聚在全國范圍內對出口規模影響結果如模型(1)所示,金融集聚的影響系數為0.740,1,且在1%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金融集聚對出口規模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金融集聚程度每增加1 單位,可以帶來74.01%出口增長率。這是由于金融集聚所產生的效應促進了金融資源快速流動和配置優化,提高了金融資源的整體效率,進一步促進出口規模的擴張。對于其他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交通運輸能力、技術水平的產業結構系數大于0,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對出口規模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資本水平的影響系數為-1.132,4 并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明顯地阻礙了出口規模的擴張。參照陳虹(2018)的研究,是因為我國很多地區投資效率低下,資本配置錯位,出現邊際效率遞減的現象,資本水平的提高不僅不會拉動出口,反而會對出口規模產生負效應[17]。

表3 全國范圍內的金融集聚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
金融集聚在全國范圍內對出口結構影響結果如模型(2)所示,金融集聚的影響系數為0.041,0,并且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金融集聚能夠有效推動出口結構優化,金融集聚每增加一單位,能夠帶來4.1%的出口結構優化。這是由于金融集聚所帶來效應尤其是技術創新效應能夠明顯提高高新技術產品的產值,進一步優化出口結構。對于其他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技術水平和產業結構系數大于0,并通過顯著性檢驗,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出口結構的優化,其中產業結構影響系數為0.157,6,優化作用最明顯;此外,交通運輸能力和資本水平影響系數為負數,并且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抑制了出口結構的優化。這是由于資本的錯誤配置所帶來低效投資會對出口結構產生負效應,而交通運輸能力的增強對低技術產品的出口促進效應大于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促進效應,進一步抑制出口結構的優化。
(三)分樣本估計結果
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地理位置劃分,本文將所選擇的30 個地區細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進行分樣本回歸,一方面可以具體分析金融集聚在不同地區對出口競爭能力的影響差異,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全樣本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4。

表4 我國各地區金融集聚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
金融集聚在各地區對出口規模的影響結果如模型(1)所示。金融集聚在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083,9 和-0.271,4,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對出口規模無明顯影響;西部地區金融集聚系數為1.065,0 且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對出口規模的促進效應顯著。根據黎杰生(2017)的分析,在金融集聚程度比較高的情況下,金融資源會產生效率損失和資源浪費,金融集聚所具有的積極效應受到削弱,金融集聚對出口規模促進作用變得不明顯甚至有負效應[18]。與西部地區相比,東、中部地區的金融集聚水平較高,金融集聚產生的正效應受到削弱,對出口規模的影響不明顯,而西部地區因為金融集聚程度較低會明顯促進出口規模增長,且影響系數絕對值最大,影響水平最高。
金融集聚在各地區對出口結構的影響結果如模型(2)所示。金融集聚在東區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影響系數為-0.014,1 和-0.043,0,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對出口結構無明顯影響;金融集聚在中部地區的影響系數為0.220,6,在1%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對出口結構具有明顯的優化作用。這是由于東部地區的金融集聚程度最高,過度的金融集聚會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損失,對技術創新產生排擠作用,進而削弱甚至對出口結構具有負效應;而西部地區金融資源稀缺,金融業發展緩慢,還未形成良好的金融集聚效應,對出口結構無明顯影響。同時,根據表4 可以發現,即使在同一地區,相同的金融集聚水平也會對出口規模和出口結構產生不同影響,出口結構和出口規模對金融集聚的反應程度具有差異性。
(四)交互項檢驗結果
為了檢驗政府干預是否影響金融集聚對出口競爭力的促進作用,在模型中加入金融集聚和政府干預的交互項后,分別對出口規模和出口結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 和表6 所示。
根據表5,交互項的影響系數在全國范圍內和東部地區為-0.202,3 和-1.146,1,均在1%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全國和東部地區的政府干預會抑制金融集聚對出口規模的效應;交互項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影響系數為0.051,2 和-0.092,4,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政府干預不會明顯影響金融集聚對出口規模的效應。這是因為政府干預會引導金融資源的流動和資本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扭曲金融集聚所帶來的效應,降低金融資源整體效率,抑制金融集聚對出口規模的促進作用。同時,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東部交互項系數顯著且絕對值較大,這是由于東部地區的金融集聚水平最高,加入政府干預之后所帶來的扭曲效應也最強烈,抑制金融集聚對出口規模的促進作用也最顯著;而中、西部地區金融集聚水平的明顯低于東部地區,這個時候政府干預產生的影響也不明顯。

表5 政府干預與金融集聚對出口規模的影響

表6 政府干預與金融集聚對出口結構的影響
根據表6,交互項的影響系數在全國范圍內和東部地區為-0.022,2 和-0.164,8,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全國和東部地區的政府干預會抑制金融集聚對出口結構效應;交互項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影響系數為-0.082,0 和-0.007,3,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政府干預不會明顯影響金融集聚對出口結構的效應。與上文情況相似,金融集聚的水平越高,政府干預的扭曲效應也就越大,因此東部地區政府干預的扭曲效應最顯著,而中、西部地區無明顯影響。
四、穩健性檢驗
由于從分樣本回歸中判斷全樣本回歸結果是否穩健并不明顯,因此本文對全樣本回歸和交互項結果再次進行穩健性檢驗。參照已有的文獻,用各地方GDP 替代第三產業產值,再次使用區位熵的方法重新構建金融資源集聚的指標,如下所示用符號LQ1表示:

(6)式中,fGDPit表示i 地區在t 年份的金融業增加值,GDPit代表i 地區在t 年份的國內生產總值,∑fGDPit代表全國各地區在t 年份的金融業增加值之和,∑GDPit代表全國各地在t 年份的國內生產總值之和,結果如表7 所示。金融集聚和交互項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并未發生改變,表明全樣本回歸和交互項檢驗結果很穩健。

表7 穩健性檢驗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2002-2017 年30 個省級地區面板數據對金融集聚是否影響出口貿易進行了實證檢驗,并且在此基礎上加入了金融集聚和政府干預的交互項,進一步考察政府干預的調節作用,得到以下幾點研究結論:
第一,在整體水平上,金融集聚會對出口競爭力產生顯著的促進效應。金融資源集聚所帶來的規模經濟、信息流動和技術創新等效應會提高金融資源的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同時促進出口規模增長和出口結構優化。
第二,在地區水平上,金融集聚在中、西部地區的促進效應要明顯優于東部地區。過高的金融集聚水平會造成效率損失和排擠作用,低程度的金融集聚促進出口競爭力作用更為明顯。
第三,政府干預會抑制金融集聚對出口競爭力的正效應。各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既定政策目標會干預資本的配置,引導金融資源流向,削弱金融集聚帶來的高效率,扭曲金融集聚對出口競爭力的促進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進一步發展金融產業,引導金融資源適度集聚。尤其是我國西部地區,金融業發展緩慢,金融資源稀缺,金融集聚水平很低。在這種情況下,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會明顯提高出口競爭力,因此西部地區需要大力發展金融業,引導金融資源流入和資本投入,產生集聚效應,發揮金融資源的積極作用。
第二,在保證經濟正常發展的前提下,盡量減少政府干預。政府干預雖然可以保證經濟的穩定,但是過度的干預和引導資源流動,會扭曲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削弱金融集聚的正效應,不利于我國出口競爭力的提高。
第三,從控制變量上看,我國需要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優化資本配置。落后的經濟發展模式和不合理的資本配置在我國尤其是西部地區普遍存在,這些現象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和出口貿易,應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合理配置資本,提高資本的邊際效率,促進我國經濟健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