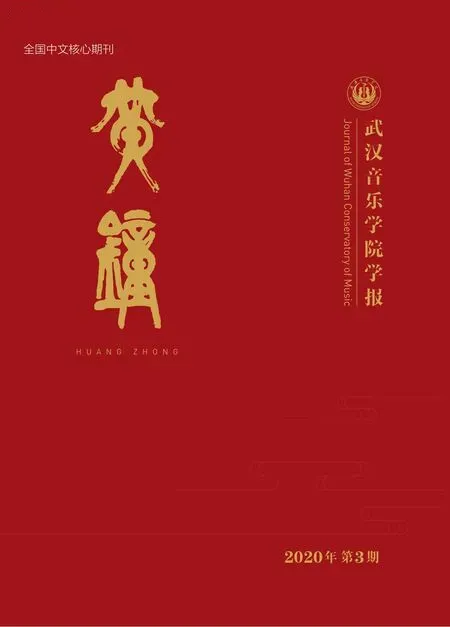承佛界天神風骨 融漢土道儒仙韻
——云岡石窟的飛天樂舞
吳巧云 姬 樂
在佛教八大護法神中,包含了天樂神乾闥婆和天歌神緊那羅,在古印度神話傳說中他們是恩愛夫妻,形影不離,后被佛教吸收,化為天龍八部眾神中的兩位天神,又合稱為“香音神”。在佛教藝術中,乾闥婆和緊那羅常以千姿百態的飛行形象出現在佛教石窟或壁畫中,以歌舞散花供養禮贊,成為飛行于天宮的“諸天”中一種特定的形象,在變文或佛經中被稱為“天人”“飛仙”等,“飛天”則是世俗的稱謂。
在公元5 世紀中葉由北魏皇家主持開鑿的大型佛教石窟寺云岡石窟中,飛天形象多達2300多身,在這些飛天造像中,有的為不持樂器而呈舞蹈狀態的舞伎形象,有的是手持樂器的樂伎形象①王恒:《云岡石窟佛教造像》,太原:書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頁。,他們自由飛翔的曼妙身姿,把莊嚴肅穆的佛國世界營造成了輕松快樂、令人神往的天堂。本文將著眼于云岡飛天中不持樂器的飛天舞伎,通過云岡早中晚三期飛天的舞蹈姿態造型和面貌服飾變化,探尋北魏平城時期東西、南北、胡漢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在飛天藝術中的體現,對云岡不同時期飛天舞伎的造型與風格演變進行分析梳理,并就南北朝時期釋、儒、道三教合流,以及各民族文化大交融的歷史背景下,北魏平城時期融匯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云岡飛天,在佛教飛天中國化的進程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予以剖析。
一、飛天在佛教藝術中的職能與作用
印度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早在佛教產生之前,古印度神話中就有許多天人、天女的傳說。印度神話故事《百道梵書》中就記載了美貌而善于誘惑的天女緊那羅被神派遣,與天神乾闥婆結為夫妻的的愛情傳說。乾闥婆,梵語“Gandharva”,原是婆羅門教的群神之一,后演變為佛教中的樂神,能自由飛翔于天宮,因其周身散發香氣,又叫香音神。《大智度論》曰:“佛在舍衛國祗樹給孤獨園……城中有五百乾闥婆,善巧彈琴,作樂歌舞,供養如來,晝夜不離,名聞遠徹,達于四方。”②《撰集百緣經》卷二,[吳]支謙譯,《大正藏》第四冊,第211頁。還有佛經中記載,乾闥婆頭戴八角冠,身呈赤肉色,左手執簫笛,右手持寶劍,體態魁偉,具大威力相,由此可見呈男性特征。緊那羅,梵語“Kimnara”,亦典出印度神話,因其能歌善舞,是佛教中的為歌舞神,其任務是在天宮為佛陀、菩薩、眾神奏樂歌舞。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載:“真陀羅,古作緊那羅,音樂天神也。有微妙音聲,能作歌舞。男則馬首人身能歌,女則端正能舞。次比天女,多與乾闥婆天為妻室也。”③[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四冊,第374頁。
在印度約建于公元前2 世紀巴爾胡特佛塔的佛傳故事畫中就已雕刻了飛天,這些飛天有的長著翅膀,有的沒有翅膀,身后揚起飄帶來表現飛動之感。建于公元前3 世紀的印度桑奇大塔的佛經故事畫中,出現了很多人首鳥身的飛天形象,上半身為人形,手持花環作散花狀,下半身為鳥形,作飛翔狀。此后的飛天顯然是在此基礎上的繼承與演變。隨著佛教藝術的發展需要,乾闥婆和緊那羅由人軀馬首或人首鳥軀的猙獰面目,逐漸演化為體貌端正的天人形象,同時由于夫妻倆皆善于歌舞音樂,在后來的佛教造像藝術中常常不分男女,合體為一,兼具男性陽剛和女性陰柔之美,成為不長翅膀,憑借飄逸的衣裙、飛舞的彩帶凌空翱翔的飛天形象,且常常成雙成對出現,不僅是帝釋天的執法歌神、樂神、舞神,還成為佛國世界歡樂祥瑞的使者。
佛教在印度產生后,對音樂舞蹈藝術給予了高度重視,誦經贊佛等音聲活動成為重要的佛事活動,音樂舞蹈也列為娛佛頌佛做功德的重要內容。印度佛教在公元前后經由西域傳入我國內地的漫長傳播過程中,沿線的佛教石窟寺如莫高窟(甘肅敦煌)、麥積山石窟(甘肅天水)、云岡石窟(山西大同)、龍門石窟(河南洛陽)等,都留下了各個朝代雕刻的飛天藝術形象,這些樂舞圖像不僅成為最打動人心和最喜聞樂見的佛教傳播手段,還融合了歷朝歷代現實中的音樂舞蹈形象,成為我們后世研究各民族、各朝代音樂舞蹈發展狀況的寶貴史料。
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學術界對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留存的飛天藝術進行了各有側重的研究。敦煌研究院現任院長趙聲良先生,于2008年在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飛天藝術——從印度到中國》,對飛天的起源和發展脈絡進行了詳細研究。對云岡飛天進行較系統論述的相關學術研究主要有:王克芬前輩在2005 年云岡國際學術研討會參會,并發表《云岡石窟舞蹈雕像多元風格溯源》④王克芬:《云岡石窟舞蹈雕像多元風格溯源》,《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第3-5頁。,概述了云岡舞蹈雕像集中體現了南北朝時期中、西、北、東樂舞薈萃北魏平城時期的繁盛景象,簡述了一些云岡代表性飛天形象的世俗舞蹈原型與造型風格特點等。此外,2013年東北師范大學何丹虹同學的碩士論文《云岡石窟“飛天”伎樂舞的審美范式研究》,2017年陜西師范大學李婧雯同學的碩士論文《云岡石窟“飛天”樂伎風格溯源及價值探究》,也探討了云岡飛天舞姿特點與審美價值。
2020 年5 月,習近平總書記專程來到大同云岡石窟考察調研,提出:云岡石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要堅持保護第一,在保護的基礎上研究利用好。總書記的指示極大地推動了“云岡學”的建設與發展,北魏云岡石窟在歷史文化長河中的獨特價值將獲得充分挖掘,云岡飛天樂舞作為“云岡藝術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也必將隆重的搬上舞臺,期待云岡樂舞也能創編出如《絲路花雨》一樣經典的劇目。
二、云岡飛天不同時期的造型特點
建造于北魏平城時期的云岡石窟(460—524年)現存45 個主要洞窟,多數洞窟都雕刻有飛天形象。云岡不持樂器的飛天舞伎,一般雕刻在窟頂、龕楣、門拱等區域,或繞團蓮,或護佛龕,或飾門拱,體現了他們在佛教中的護法職責和身份。本文將對云岡飛天舞伎從藝術造型、舞蹈姿態、服飾頭飾等加以剖析,以概述云岡飛天不同時期的造型特點及演變,探尋云岡樂舞藝術的文化內涵。
(一)云岡早期飛天
云岡早期(460—465年)開鑿的第16至20“曇曜五窟”中,樂伎和舞伎的雕刻數量都不多,云岡早期飛天具有豪健、粗放、質樸之美,代表性飛天見圖1至3。

圖1 第16窟明窗西側交腳菩薩龕內的飛天⑤文本選用的云岡飛天圖片,均為大同云岡石窟研究院數字中心提供。

圖2 第18窟東壁左脅佛上部天蓋中的飛天

圖3 第20窟露天大佛背光右側的飛天
云岡早期大部分洞窟中的飛天造型粗笨,動作呆板,身體造型基本呈“V”型或“U”型,缺乏美感,男女體貌特征不清,身披的飄帶也很短,只起到象征作用,局限在龕楣格內的飛天缺乏動感,有些飛天感覺只是在地面上作跳躍狀,無論雕刻技術還是審美品味云岡早期飛天還較粗糙。
第20 窟露天大佛背光兩側各有一身飛天,大佛左側的一身已殘,右側飛天是云岡現存最大的飛天,也是云岡早期飛天的代表。這身飛天造型古樸,頭后有圓光,頭戴印度式花蔓寶冠,面相豐腴,圓臉大眼,面露微笑,頸飾項圈,上身半裸,斜披絡腋,著印度貼體濕衣,佩戴臂釧腕鐲,裸露雙腳,其衣冠服飾與印度貴霜時代印度婦女的服飾相似,左手虔誠地托著花蕾收于胸前,右手在身后舒展開來,正向佛飛來。這身飛天接近水平的飛翔姿態及造型,與公元3 世紀開鑿的新疆吐魯番吐峪溝石窟寺西區第4 窟中的一身飛天很接近,與公元2—3 世紀犍陀羅地區出土的“佛陀涅槃”浮雕中的童子飛天的服飾造型也有相似之處。云岡早期飛天無疑借鑒了印度、龜茲等早期佛教造像藝術中飛天的造型樣式,而從云岡早期飛天的造型、數量及所處位置來看,相較云岡早期“曇曜五窟”中雕工精致、氣魄宏偉的五身主佛,明顯處于陪襯和裝飾地位,但從第20 窟這身背光飛天的笑容里,可以看到拓跋氏君王們對坐擁中原的憧憬與自信,為來自西方的飛天已注入了一縷鮮卑精神。
(二)云岡中期飛天
云岡中期(470—494 年)12 個洞窟中,東部的第1、2窟,中部的第5、6、7、8窟,以及西部的第9 到13 窟都雕有飛天,且造型風格多樣,舞蹈姿態生動,服飾異彩紛呈,體現出拓跋民族兼容并蓄、昂揚豪放的精神。代表性飛天見圖4至7。

圖4 第7窟后室窟頂的飛天

圖5 第8窟后室窟頂的飛天

圖6 第6窟中心塔柱東面的飛天

圖7 第6窟的飛天
云岡中期飛天成群結隊出現于佛龕、門楣、窟頂,身披臂繞的飄帶明顯加長,飄帶的中部從頭頂高高揚起,飄帶的兩頭飄飛于身后或手臂兩側,以此加強飛天的動態感。從造型姿態來看,大部分飛天動作比較舒展自然,面帶微笑,昂首舉臂,健壯中蘊含著自信與力量,頂風而上、直沖云霄的姿態,表現出一種雄健、奔放的拼搏精神,彰顯出拓跋鮮卑好武善斗的民族特性。中期飛天的服飾和發型非常多樣,真實記錄了北魏平城時期印度、西域、鮮卑、中原等各民族服飾大薈萃的多元文化形態,堪稱為北魏各民族時裝秀的大舞臺。從發式面相衣著來看,主要有三類:一類是仍沿襲印度、西域式飛天造型:梳天人高髻或平頭逆發,頭后有圓光,高鼻突眼,鼓腹露臍,身體健壯,有的斜披絡腋、下著低腰貼體露足長裙,有的上身赤裸、下著牛鼻短裙;有些飛天的頭后仍帶圓光,頭頂圓髻、五官舒朗,上著窄袖圓領口或V 領口短上衣,下著露膝短裙或露足緊身褲,已經具有游牧騎射的鮮卑服飾特點;第三類飛天已經沒有頭光的束縛,身形清瘦,梳細長高髻,穿對襟廣袖交領短上衣與束腰遮足長裙,已初顯中原漢族女性形態。
云岡中期飛天出現了用鳥翅膀形狀的裙裾包住雙腳的造型,這不僅符合了中國古老文化中女子的腳屬于個人隱私、不能輕易示人的禮教約束,也吸收了古印度藝術中人首鳥身的緊那羅形象,以裙裾代羽翼,更有利于表現飛天的動感。云岡飛天下肢飛翔的造型體態多見兩種,一種以膝蓋為界,采取一腿向前屈膝成銳角,一腿向后伸展為鈍角小腿向上翹起,表現出向上騰飛或向下俯沖的強勁動感;一種為兩腿都向后揚起,形成一腳略高一腳略低的平行狀,呈御風而飛的輕盈姿態。云岡飛天的這些飛翔造型在古代印度文藝理論家婆羅多(約100—200 年)編寫的《舞蹈經》中都有過總結與描述。
云岡中期飛天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設計布局上常成雙成對的出現,明顯受到古印度雕刻藝術的影響。在古印度傳統的雕刻與繪畫中,經常出現男女愛戀歡娛的“艷情”描繪,且女性多為裸體,生理特征突出,毫無掩飾地表現女性之美。在古印度馬圖拉(貴霜王朝的兩大佛教藝術中心之一)的早期佛教雕刻中,男女飛天成對出現、相擁相伴的情況已非常常見,在后來的印度教藝術中“雙飛天”的表現更為豐富。在云岡中期多數洞窟的龕楣格或洞頂中,都可以看到成雙成對的飛天。“雙飛天”雖然承襲了印度雙飛天模式,但裸露上身的飛天也斜披絡腋或飄帶,沒有刻畫性別特征,消除了印度慣有的那種渲染男女性愛的因素,云岡中后期飛天多數著各式衣裙,秉承了儒家文化傳統。
第6 窟是一個中心塔柱窟,規模宏偉,雕飾富麗,塔柱上雕有四方佛,窟四壁滿雕佛、菩薩、羅漢、飛天等造像,窟頂有三十三諸天及各種騎乘,令人目不暇接,是云岡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也是云岡飛天造像藝術的集大成者。第6窟中心塔柱四面佛龕的龕楣格、龕拱、龕緣層層疊疊都布滿了樂伎和飛天,神態各異,蔚為壯觀,營造了歌舞升平的極樂世界,讓人嘆服北魏工匠豐富的藝術創造力和北魏社會樂舞藝術的繁榮景象。僅以圖6為例,第6窟塔柱東面龕楣中的5身飛天處在同一位置,但服飾、造型都不一樣,有的為西域式飛天,有的為鮮卑裝束,中間的拋蓮飛天身形清瘦、挽高髻、著漢裝,舞姿溫婉,體現出漢文化對飛天造型的影響。從舞蹈動作來看,圖6 左上角的逆發飛天左手托于左側斜上方,右手按于右下胯部旁,其形象與印度舞蹈中“濕婆神”舞非常相似;中間拋蓮女性飛天雙臂的姿態,維吾爾族舞蹈中稱為“一位手”形象,又名“提裙式”;右上角的逆發飛天,其手臂動作與當今蒙族舞蹈中的“勒馬位”很相似,這是所有游牧民族策馬騰飛最熟悉的姿態了;而下層兩身對稱的飛天,一只手斜托于頭頂斜上方,另一手立掌推于身旁,這是維吾爾族舞蹈中在身體各部分旋轉、扭動時最典型、最常用的“五位手”(見圖7)。佛教自西域、西涼一路東傳中原進入平城,云岡中期飛天的舞蹈姿態,自然帶有濃郁的印度與龜茲樂舞的特征,成為當時北魏社會盛行胡樂胡舞的見證。總體來看,云岡中期的漢裝飛天雖常與游牧民族和西域風相融的飛天形象出現在同一組飛天中,但漢化飛天還沒有成為主流。
(三)云岡晚期飛天
云岡晚期(494—524 年)洞窟主要包括東部的第4 窟和西部的14、15 窟以及20 窟以西的第21 至45 窟,大多為太和十八年(494 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開鑿,云岡晚期飛天以漢化飛天為主流,較有代表性的飛天見圖8至10。

圖8 第34窟西壁佛龕拱額上的飛天

圖9 第30窟窟頂西部的飛天

圖10 第34窟西壁的飛天
云岡晚期北魏的漢化政策已經獲得大力推廣,這一政策直接影響了云岡石窟的造像風格。晚期洞窟中的主佛穿上了褒衣博帶式的漢風服裝,面相削瘦,呈現出“秀骨清像”的新風格。云岡晚期飛天多以群體形式出現,大多雕刻在窟頂和龕楣上,從本文圖8 至10 的飛天圖像中可以看出,這些飛天多為漢族妝扮,去掉了圓形頭光,由于受到南朝“魏晉風度”的影響,頭束高髻,面容清秀,體態輕盈,身著中袖廣口對襟短襦,束腰長裙,裙裾裹足,飄帶的長度比中期加長,從肩臂兩側向后揚起,飄揚的弧度自然流暢,比較寫實。
云岡第34 窟西壁佛龕拱額上的飛天,被認為是云岡最美的飛天之一,尤其是拱額左側雕刻完整的這身飛天,其形象已經接近漢代石刻畫像中魚尾托云的神話人物。⑥梁思成:《佛像的歷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頁。這身飛天造型優美,面貌清瘦、腰身纖細、身材比例適中,身體曲線柔和細膩,表情神韻溫婉安詳,飛動的飄帶線條流暢,收斂的雙腿與裙裾顯示出一種大家閨秀的風范,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對拓跋鮮卑統治者的深刻影響,既具有漢族端莊的淑女風范,又蘊含乘風羽化的飛仙韻致,眉目神情中仍不失鮮卑人爽朗的胡氣,在北魏太和改制政策的推動下,云岡晚期飛天不僅基本完成了佛教飛天的中原化、世俗化,也是胡漢文化融合的最好見證。
三、有待重構創編的幾種云岡飛天樂舞
云岡樂舞是一種有待舞蹈家們挖掘復建的新興舞蹈藝術品種,云岡石窟兩千多身飛天舞伎圖像是創編云岡樂舞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多姿多彩的舞姿神韻,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服飾妝扮,以及直觀豐富的舞蹈道具,都是創編云岡佛教樂舞的真憑實據。
(一)飄帶舞
飛天身披臂繞的飄帶,在我國又可稱為“巾”,巾舞在我國中原地區有著悠久的歷史,西周時期用于祭祀的《六小舞》中,舞者就已手執五彩繒,漢代女樂中已流行《巾舞》。漢代的《巾舞》由《公莫舞》發展而來,因歌辭首句有“公莫”二字而得名,它流行的地區很廣,是漢代著名的雜舞。長巾不僅是舞者身上的裝飾品,更是重要的舞具,舞者所用巾帛最長可達兩丈多,漢畫像石(磚)中多有反映巾舞的生動場面。據《宋書·樂志》記載,南朝宋宴饗的舞蹈中也盛行《巾舞》,到盛唐時期,婦女的服飾中普遍使用披帛,宮廷宴樂中的巾舞更是盛行不衰。巾舞的流行與中國的絲綢應有密切關系,光滑、輕盈、艷麗的絲綢,在舞者手里才能做到上揚翻飛、下垂卷曲、舒卷自如的動態效果。
飄帶不僅在漢族舞蹈中使用,“昭武九姓”中康國的胡旋舞、石國的胡騰舞也廣泛運用飄帶。漢文史籍記載,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今甘肅臨澤),漢初,匈奴破月氏,迫其西遷至中亞粟特地域。昭武九姓擅經商、善歌舞,他們通過絲綢之路在東西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龜茲壁畫、敦煌壁畫中有大量的胡旋轉形象,舞者兩腳交叉、左手叉腰、右手擎起,全身彩帶繽紛,飄逸飛卷,元稹《胡旋女》中描述“柔軟依身著飄帶,徘徊繞指同環釧”。
云岡早期個別飛天沒有雕刻巾帛,有披巾帛的也很短,只在兩臂繞了一圈,巾尾或飄于身后,或垂于兩旁,上揚高度不過頭,下垂長度沒過胯,巾帛還只起到飛舞的象征、點綴作用。中后期至晚期的飛天,幾乎都有飄帶,且越來越長,有從左肩斜披至右腋下向后飄揚的,也有從繞頸經雙臂向下或向后飄垂的,再晚一些,環繞在兩臂間的飄帶向后和向上高高飛揚,迎風舞動,空中飛翔的姿態越來越明顯。如圖12 中第6 窟中心塔柱上的6 身飛天姿態兩兩對稱,手臂和巾帛飛揚的方向、角度、造型各不相同,極具觀賞價值。晚期第34 窟西壁的飛天,已經掙脫了天宮圍欄,自由飛翔于天空,身姿清秀,造型脫俗,動作舒展,披肩繞臂的的巾帛動感十足,流暢飄逸,在氣韻格調上已經體現出漢民族的審美情趣(見圖8)。

圖11 第17窟西壁西立佛背光頂部的飛天(早期)

圖12 第6窟中心塔柱北面龕楣格內的飛天(中期)
(二)瓔珞舞
瓔珞,梵文是“keyūra”,原為古代南亞次大陸的貴族們用來裝飾身體的一類環狀飾物,用珍珠、寶石和貴金屬串聯制成,戴于頭、頸、胸、臂、腿等部位,以顯示其高貴的身份。古印度佛教興起后,成為佛像頸間的一種裝飾,《妙法蓮華經》記載用“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真珠(即珍珠)、玫瑰七寶合成瓔珞”,寓意為“無量光明”。據《佛所行贊》所載,釋迦牟尼當太子時,就貴為“瓔珞莊嚴身”,由此瓔珞成為佛教的十種供養之一。在佛教藝術中,飛天手中所挽的花繩,源于希臘,只是希臘的瓔珞花圈由花與葉編成,而云岡的瓔珞花繩則用寶珠貴石穿成。⑦梁思成:《佛像的歷史》,第19頁。云岡飛天手持的瓔珞花繩一般由橄欖形和圓形寶石間隔串聯而成,體現佛法供養的宗教意義,而雕刻于造像龕和洞窟口的瓔珞紋則作為一種特定的紋樣和圖案起到美術裝飾作用。
云岡手持瓔珞的飛天都在中期洞窟,尤其在五華洞中雕刻了大量的瓔珞飛天。如第9 窟前室北壁中國傳統瓦頂門樓下雕刻了一字排列的8 身飛天,左右各4 身呈對稱分布,均為單手持瓔珞繩,色彩華麗,象征寶石的紋路清晰,兩個相鄰的飛天之間下垂的花繩呈“V”字形狀,瓔珞繩上端雕刻較細,隨著下垂明顯加粗,在瓔珞繩下垂的最低點還雕刻了一朵蓮花。第12窟東、西、南三壁與窟頂連接處都布滿了雙手持瓔珞繩、朝同一方向飛行的飛天,這些瓔珞繩都呈現出雙層復式交叉下垂結構,設計嚴謹、色彩富麗、充滿動感。第12 窟壁面最上層三面合圍的飛天,左手的瓔珞繩高舉,右手低垂,形成高低不同的兩個層次,在視覺效果上形成更豐富的立體感與排列形態。第13 窟龕楣上的飛天為了適應拱形門洞的造型,采取從中間到兩邊依次從高到低排列,雙手所持瓔珞繩也采取一手高、一手低的精巧造型,從而使瓔珞雙層弧線過度圓滑自然,飛天的姿態也變化多樣。云岡晚期洞窟出現的瓔珞繩無人牽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裝飾紋樣。總之,云岡姿態多變的瓔珞花繩飛天,是一種極具造型的舞蹈素材,也是云岡石窟留存的彌足珍貴的民俗舞形象,至今在新疆民間歌舞集會——“熱西來甫”中還有花繩舞的傳承。

圖13 第12窟后室南壁瓔珞飛天
(三)團蓮舞與拋蓮舞
荷在植物學中也稱蓮。荷花的花語是堅貞、純潔、信仰和愛情等,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蘊含著超凡脫俗、清凈無礙的氣度。在古希臘、古羅馬,睡蓮與中國的荷花一樣,被視為圣潔、美麗的化身。蓮花在佛教與印度教中象征神圣與不滅,印度的國花是荷花,印度荷花有七種,故有“七寶蓮花”之稱。根據《佛陀本生傳》記載,釋迦佛出生時向四方各行七步,步步生蓮花,故早期佛教雕塑中蓮花成為佛祖的象征,后引申為整個佛教的象征。云岡石窟作為公元五世紀北魏皇家營造的大型佛教石窟寺,蓮花成為頻繁呈現的佛教藝術形式。
云岡石窟的蓮花除了作為裝飾圖案出現外,還作為舞蹈形象出現。尤其是云岡中期洞窟出現了大量的托蓮舞和拋蓮舞的飛天舞蹈形式。如第7窟后室窟頂的平棊藻井中雕刻6朵團蓮,每朵蓮花四周兩兩一組雕刻8 身飛天,平棊枋交叉處還有2 朵團蓮,蓮花之間的枋拱上也雕刻了成雙成對的飛天,整個窟頂共有8 朵蓮花、48 身飛天,形成花團錦簇、歌舞升平的佛國天宮景象。第12窟窟頂長方形平棊格內雕刻了8 朵大團蓮,每個團蓮四周都有倆倆相隨、盤旋飛舞的8身飛天,藻井拱梁上還雕刻了3朵大團蓮(見圖14),共64身飛天,窟頂外緣還雕刻有8 身夜叉飛天。這些飛天以西式妝扮為主,上身半裸,著三角牛鼻裙,裸露腿腳,彩帶多為綠色,舞姿調皮,神情活潑,每身飛天的姿態都各有不同,既顯佛界祥瑞又具人間情趣,華美絢麗的氛圍讓人嘆為觀止。
第9、10 窟的明窗頂部都刻有一朵具立體感的兩層大蓮花,蓮花周圍都環繞著8 身斜披絡腋的飛天。第9 窟的8 身飛天中4 身逆發飛天身軀高大,似男子體魄,雙腿彎曲,有的單臂托蓮,有的雙手高擎,似在托蓮奮力前行或推動其旋轉,流露出拓跋男子的神勇英武;在逆發飛天之間還穿插了4 身體型較小的束發飛天,身形窈窕,似有女性神韻,或仰頭托舉或回頭顧盼,展現了北魏女子的活潑俏麗(見圖15)。而第10 窟的8 身飛天造型則有變,4身體型較大、頭束天人高髻的飛天在單手托蓮,身著露足長裙;4身體型較小的飛天頭頂無髻,發式接近鮮卑人特有的“索發”⑧王恒編纂:《云岡石窟詞典》,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頁。(見圖16),姿態嫵媚,身著牛鼻短裙,游弋在蓮花周圍,這兩類飛天形成此起彼伏、遠近變換的動感。北魏藝術家在飛天的發式、服飾、性別刻畫與設計上可謂構思精巧奇特,充分反映了北魏社會中原與西域、宗教與世俗多元文化并存的現象。

圖14 第12窟窟頂蓮花飛天舞

圖15 第9窟后室南壁明窗頂部托蓮飛天

圖16 第10窟明窗頂部托蓮飛天
云岡飛天樂舞中還出現了如圖17 中的拋蓮飛天,這身高浮雕形式的飛天,身姿優美,比例適中,飄帶翻飛,裙尾上揚,穿漢族服飾,有女性神韻。雙手正將團蓮拋于空中,為了體現蓮花剛從手中拋出的飛舞形象,團蓮與雙手之間還雕刻了充滿動感的弧線,極富視覺效果,透發著勃勃生機,反映了北魏藝術家豐富的想象力與創作才能,也為今天創作飛天拋蓮樂舞提供了絕好的素材。圖18 中的兩身漢裝托蓮飛天,舞姿曼妙、衣帶飄飄,也給人無盡遐想。
(四)摩尼寶珠舞
佛經有記載說摩尼寶珠是佛之舍利變化而成,也有說是出自海底龍宮的如意寶珠,相傳摩尼寶珠是由火焰和五色寶珠組成,能放射萬丈光芒,普照眾生,能解除他們的貧困和疾苦,是人們用以祈求幸福平安、招財進寶的象征。云岡石窟的摩尼寶珠有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多見桃形或橢圓形寶珠,雕刻富有立體感,圖19至22中的寶珠形態最具代表性。云岡早期第17 窟中有單身飛天,單手持寶珠飛行于空中;云岡中期有四身飛天上下排列、共同護持寶珠飛翔;也有兩身飛天各出一手共擎寶珠(見圖21)。摩尼寶珠作為消災、吉祥的象征,在云岡摩尼寶珠飛天群舞中,體現出一種崇高、圣潔、莊嚴的氣氛,透出一種強烈的儀式感(見圖22)。
總之,南北朝的統治者都信奉佛教,在每年舉辦的佛事活動中,被用于娛佛的樂舞場面都極其盛大,通常由寺院常設的音聲伎樂人表演,既有縱情開放的西域特色,也有柔美迷幻的中原傳統,云岡飛天樂舞應是南北朝時期佛教樂舞情況的真實寫照。在當今創編云岡飛天樂舞時,瓔珞飛天舞、摩尼寶珠舞佛教思想濃郁,飛天應有頭光,上身半裸,斜披絡腋,下著貼體露足長裙,造型服飾應以印度西域風格為主,在美學情趣上理應“健而不猛、凝而不滯”,體現“正、和、雅、肅”的佛教境界;團蓮舞本身就有團結之意,飛天造型匯聚了印度、西域、鮮卑、漢族等多種文化,應具有活潑輕快、和美喜樂的吉祥氣氛;而飛天飄帶舞與拋蓮舞則應巾卷流云、變幻莫測,既可以著印度、西域服飾,體現曼妙清麗的異域情調,也可以著端莊典雅的漢裝服飾,體現李白《古風》詩中“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的道家仙境,再運用電、光、聲、色、氣等現代化科技手段,一定會極具欣賞效果。

圖17 第6 窟中心塔柱東面拋蓮飛天

圖18 第13—18 窟窟頂托蓮飛天

圖19 第9 窟窟門頂部寶珠飛天

圖20 第10 窟后室明窗下面寶珠飛天

圖21 第13 窟窟頂飛天

圖22 第9窟南面門拱上的兩層寶珠飛天
四、云岡飛天樂舞承載的文化內涵
魏晉南北朝(420—589 年)是中國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亂的時期,也是各民族文化大聚合、社會思潮大解放的時期,還是儒、佛、道三教既斗爭又合流的時期。北魏王朝以武建國,在定都平城(今大同)的近一個世紀(398—494年)中,一方面憑借征戰掠奪、外交進貢,促進東西、南北的文化交融;另一方面,北魏統治者既信奉佛教,還喜好莊老,也極力推行中華儒家文化,云岡飛天舞伎的造型及舞姿演變,就是這多種文化思潮作用下的直接顯現。
(一)佛、儒、道三教交融在云岡飛天樂舞中的體現
印度佛教產生于公元前六五世紀古印度恒河流域一帶,到公元前3 世紀的阿育王時代達到興盛。古印度貴霜帝國時期(55—425年)形成了兩大佛教藝術中心,一是在古印度北部的犍陀羅地區,并形成了融合古希臘羅馬藝術、古伊朗藝術和古印度藝術的犍陀羅佛教藝術,其中希臘因素對犍陀羅藝術影響更深,在犍陀羅時代雕刻的佛說法圖上方已有兩身長著翅膀的童子天使形象;另一個是貴霜帝國的東都馬圖拉,位于犍陀羅東部,處于印度中部與西北部的交通要塞,在馬圖拉的早期佛教雕刻中,佛說法圖的上方兩側也雕刻了兩身披繞飄帶的飛天形象。而飛天裸體的原因則在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譬喻品》中有云:眾天人在佛前心生歡喜,各個脫身上所著上衣,以供養佛。由此以奉獻為由,形成飛天坦胸露腹的造型。飛天這一藝術形象在佛教藝術的發展中,不斷融合各種文化,在不同區域和時空中都成為一種喜聞樂見的宗教載體。
漢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與西域地區建立行政關系的王朝,漢代以來絲綢之路的開辟與長期繁榮為中西文化的傳播交流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也為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東漢時期,漢傳佛教由西域通過河西走廊傳入我國中原地區,承載印度古代佛教藝術的石窟營造也沿著絲綢之路自西向東在我國西北地區延展開來,再由涼州傳入北魏平城,這條佛教傳播路徑對云岡石窟的造像風格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印度飛天在中原大地上獲得了新的生命。
公元1 世紀佛教傳入絲綢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塞——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公元3 世紀龜茲發展成為西域的佛教中心,并因佛教興盛和名僧輩出而盛極一時。這一時期開鑿的克孜爾石窟是龜茲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也是中國開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窟中雕刻的飛天形象有裸體、長雙翼的童子形象,也有裸體、男女生理特征鮮明的雙飛天形象,一脈傳承了印度早期佛教藝術的飛天刻畫形式。東漢初年,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地區是我國最早一批接觸佛教的地區。據史料記載,我國漢民族地區最早的佛教石窟大約是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開鑿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早期洞窟中的飛天裸上身、露雙腳、高鼻深目、體魄健壯,既傳承了印度飛天的造型,也融入了西域人的神態。內地最早建造的石窟則是西秦建弘元年(420 年)開鑿的炳靈寺169窟,炳靈寺早期洞窟中的飛天上身雖半裸、但長裙與飄帶遮體,相貌已有漢人形態。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滅北涼,從涼州強制遷入平城的三萬戶吏民中,至少有三千涼州僧匠被整體東遷,成為云岡石窟設計與建造的主力軍,他們把西域龜茲、河西敦煌的石窟建造經驗與模式帶到了云岡石窟。南北朝是中國佛教的興盛發展階段。北魏平城時代雖經歷了殘酷的“太武滅佛”,但“文成復法”(452 年)后,北魏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巡民教化,舉國上下信奉佛教,賦予佛教強烈的政治色彩,使其獲得了驚人迅速的發展。云岡石窟作為北魏皇家建造的大型佛教石窟寺,足以說明佛教在北魏社會的地位。云岡早期飛天的造型基本屬于舶來品,更多受到希臘藝術和印度佛教造型藝術的影響,并以西域石窟藝術為藍本。云岡中晚期飛天形象的嬗變,則受到北魏漢化政策催動與華夏道、儒兩教的影響。
東漢末年張道陵創立天師道,亦稱正一道,成為我國民間宗教發展史上最早的教派。北魏太武帝時期,寇謙之成為封建史上第一位被皇帝承認的道教天師,北魏開始“崇奉天師,宣揚道教,傳布天下,道業大行”⑨[北魏]魏收:《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上海: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8頁。。此后北朝歷代皇帝都臨壇受道家法箓,老莊玄學盛行于北朝,由此也引發了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在北魏的激烈交鋒與滅佛運動。道教龐雜的文化內涵中有一個核心就是道教的神仙信仰,認為人通過努力可以成為長生不死的神仙。因此,在佛教傳入我國前,中國本土就有仙人信仰。在我國戰國時期甚至更早的墓葬中就有升仙場景,東漢以后道教的神仙思想就更為流行了。隨著道教在北朝的深入發展,以及魏晉神仙理論體系的建立,北魏皇家寺廟云岡石窟中的飛天從頭戴寶冠、背有頭光、上身半裸、身材粗短的印度佛教飛天,逐漸轉變為梁思成先生所說身形清瘦、發髻高束、具仙風道骨的道家“飛仙”⑩梁思成:《佛像的歷史》,第29頁。形象。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中國自漢代以來大多數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識,起到了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際關系、維護專制統治的作用。另一方面,儒家提倡的三綱五常和名教觀念,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原則和觀念,起著規范禁錮人們思想行為的作用。尤其是鼓吹“男尊女卑”,要求女人必須遵守“三從四德”的“禮教”與“婦道”,將貞節、服從、柔順與卑弱定為古代中國女子的終生追求。西漢著名思想家劉向編撰的《列女傳》中提出女子應該“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婦德觀念屬于儒家的傳統倫理思想,根深蒂固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由此才產生了女子“行不露足,笑不露齒”的行為規范。北魏統治者入主中原后,為了贏得漢族民眾的認同與支持,也為了擺脫拓跋鮮卑少數民族粗俗落后的風俗習慣,大力推崇儒學,從政治、文化、服飾、語言等多方面積極吸收南朝漢族的先進制度與禮儀文化,尤其是馮太后與孝文帝積極推行漢化政策,推動了北魏從塞外游牧部落聯盟到中原封建王朝的華麗轉變。云岡石窟的晚期飛天,弱化了灑脫豪放的少數民族氣質,擺脫了坦胸露腹露腳的印度習俗,轉變為端莊內斂、裙裾包腳的漢裝形象。
(二)東西、南北文化交融在云岡飛天樂舞中的體現
兩晉南北朝時期中華大地四分五裂,人民飽受戰亂流離之苦,但在文化領域卻呈現出春秋戰國以來少有的繁榮,各民族文化激烈碰撞,社會思想異常活躍,東西、南北各地文化匯聚于北魏平城,并在云岡飛天樂舞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東西文化交融對云岡飛天的影響:北魏從道武帝建國到太武帝結束北方十六國群雄割據的混戰局面,一直推行武力掠奪與強行移民的政策,才使平城這個邊陲小縣迅速發展為中國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魏對西域的經營,最初自道武帝拓跋珪(371—409 年)太延元年與西域諸國開始互通使節。太武帝拓跋燾(408—452年)即位后,逐次消滅了夏國(431 年)、北燕(436年)、北涼(439年),至此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區,打通了通西域的道路。公元445—452 年間,太武帝兩度出兵征伐西域,先后征服了鄯善、焉耆和龜茲,并設立鄯善和焉耆兩個軍鎮,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柔然開啟了對西域諸國軍政管理的極盛時期。至孝文帝(471—499 年)、宣武帝(500—515年)在位期間,龜茲、高昌、高車、于闐、疏勒等西域諸國都曾多次遣使朝貢,同時還有大量的西域民間商胡往來于絲路之上,所謂“商胡販客,日奔塞下”,由此迎來了我國歷史上第二次東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尤其是古龜茲國(現新疆庫車一帶)作為西域古絲綢之路的交通要塞,是印度佛教東傳的主要中轉站,公元3 世紀中葉,龜茲佛教已經非常興盛,龜茲歷來以能歌善舞聞名,在佛教浸染下龜茲樂幾乎成為佛樂的代名詞,龜茲樂舞既有濃郁的西域少數民族舞蹈特點,又帶有印度佛教色彩。北魏拓跋作為游牧民族本就喜愛歌舞,通過戰爭、朝貢、貿易、人口遷移、佛教傳播等多種渠道,把以龜茲樂為首的西域、西涼樂舞都匯聚于平城,宮廷貴族蓄養歌舞伎成風,一方面供自己享樂,同時也以樂舞炫耀武功與國威。云岡石窟早中期飛天面如滿月、直鼻大眼、四肢裸露、項飾瓔珞、臂帶環鐲,其面相服飾無不體現出印度、西域西來文化的影響。
南北文化交融對云岡飛天的影響:永嘉之亂后,晉王室為避戰亂南遷至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魏晉名士群體不滿社會時局,對封建政權采取逃避態度,崇尚玄學,常從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尋找精神寄托,這種思潮對南北朝的文學藝術形態都產生了極大影響。魏末晉初的竹林七賢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常聚于竹林喝酒、縱歌、撫琴,肆意酣暢,他們的詩作、文論不僅流露出魏晉名士超凡脫俗的玄遠氣度,還影響了東晉南朝人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的審美情趣。這一時期還形成了以瘦為美的風潮,人們為了清瘦苗條,寧肯吃糠咽菜,竟然出了“看死衛玠”的典故。曹魏文學家曹植創作的辭賦名篇《洛神賦》描述了作者與洛水女神人神邂逅的凄美傳奇,描寫了美麗的洛神“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肩若削成,腰如約素”的仙女神韻。東晉大畫家顧愷之(346—407年)用流水般的線描繪就《洛神賦圖》,傳神地把曹植的意蘊展示了出來,成為后世表現清瘦綽約、云髻巍峨的仙人形象的典范。
北魏建國后,一方面通過啟用中原士大夫參與北魏國家制度的建設,同時也效仿漢朝和親政策,通過拓跋氏與中原士族閨秀的聯姻把漢族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乃至倫理觀念、意識形態帶進拓跋社會,促進北魏社會從草原文化到農業文化的轉變;另一方面北魏與江南的宋、齊、梁三個朝代對峙期間,既有戰爭對抗,也有戰爭間隙斷續維持的外交貿易關系,史料記載南北雙方統治者互派有姓名的使者就達161 人次,?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北京:中華書局2006版,第258頁。而且這種外交貿易北魏君王比南朝更為迫切。由此,北魏不僅盛行胡樂胡舞,還在征戰中獲得了中原舊樂,盛行江南的“清商樂(吳歌與西曲)”等柔曼輕靈的漢族樂舞。在北魏馮太后主持的“太和改制”以及孝文帝太和十年(486 年)推行的服制改革和漢化政策推動下,在南朝文化的種種影響與滲透下,云岡石窟晚期造像融入漢文化的審美觀念與藝術技法,形成了中國北方石窟藝術“秀骨清像、褒衣博帶”的風格,晚期飛天成為面容清瘦、削肩細腰、高髻闊袖、裙裾裹腳的漢族舞伎模樣。總之,云岡中晚期飛天則由于受到東西、南北各地世俗樂舞的影響,佛教飛天的莊重神秘感趨于淡化,呈現漢化、世俗化傾向,成為北魏社會宮廷、世俗、佛教樂舞的真實反映。
結 語
北魏平城作為絲綢之路東端的大都會,匯聚了印度、中亞、西域、涼州各地的佛教文化,從云岡飛天的服飾、造型及舞姿演變,可以看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包容力之強,改造力之大,無論飛天藝術來自希臘、波斯、印度異域,還是西域、鮮卑異族,經過漢文化的濡染,都被偉大的中華文化漢化為華夏的模樣。北魏平城時期的云岡飛天,雖起源于印度,承繼于西域,但在北魏的漢化進程中,逐漸從男女不分、體格健壯、裸露較多的西式飛天演變為身形清秀、衣袂飄飄的中原女性形象,完成了佛教飛天的中國化與世俗化;與此同時,北魏作為拓拔鮮卑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文化形態無不打上其民族的烙印,云岡飛天在早中期造型神態中流露出的粗狂有力、純樸自信,顯現了北方少數民族的陽剛之氣,這不僅體現在男性飛天的舞蹈姿態,同樣體現在云岡中晚期女性飛天的神韻之間,這和魏晉南北朝時期女樂的高度發展和廣泛普及相關,也和女性人格覺醒與婦女地位的提高有關,無論是北魏文明太后執掌朝政的威嚴,還是花木蘭替父從軍的英姿,都彰顯了北魏女性的風采。因此,云岡飛天有著樂觀的微笑,強健的體魄,身著豐富多樣的各民族服飾和發飾,弱化了宗教的莊嚴肅穆,褪去了印度的男女艷情,也不同于敦煌飛天的寫意與夸張,是北魏社會現實樂舞形態的真實寫照與當時封建貴族仕女的時世裝扮。云岡飛天樂舞記載了古代絲綢之路音樂舞蹈文化的傳播路徑與交融盛況,就如中國音樂舞蹈藝術發展長河中的一個橫切面,記錄了北魏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樂舞形態,雖然胡、漢、鮮幾種文化還處在碰撞、交匯時期,此時的融合還顯得生硬,甚至有隔閡,但卻生動、鮮活。
總之,北魏平城時代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其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不可低估。?張焯:《云岡典藏》,青島:青島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頁。云岡石窟作為中國石窟藝術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時期的典范,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云岡飛天藝術作為佛教藝術中國化、民族化、世俗化的結晶以及絲綢之路東西樂舞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希望有志于復現創編云岡飛天樂舞的同仁們,不僅要從理論上研究飛天文化,還應挖掘獨特的北魏文化,通過構建融合中西南北多元文化的云岡飛天樂舞,來傳承與發揚我中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