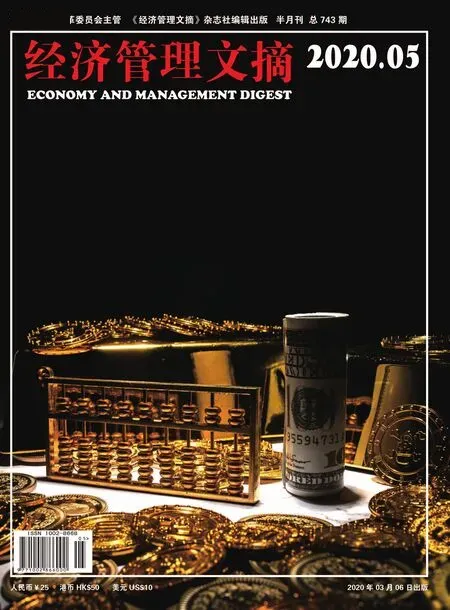藏醫藥商品化開發中存在的知識產權問題
■羅 澍
(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
知識產權制度在推動發達國家的西醫藥資源取得全球性成功的同時,并不必然導致中國的醫藥(包括藏醫藥在內的民族醫藥)取得相應的成功。相反,藏醫藥的商業化開發存在的知識產權及相關問題比較突出,值得關注。
1 “重義輕利”與商事“功利主義”的沖突
受苯教和藏傳佛教的影響,在藏醫藥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道德約束,“重義輕利”就是其中重點強調的內容之一。雖然不排斥對醫療行為收取費用,但是也不提倡“重利輕義”的行為。而現代商業活動以“營利”為目的,與“功利主義”下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很多方面保持一致,具體表現在:一是知識產權的經濟激勵制度需要在商業活動中得以實現;二是知識產權的專有性及其市場價值能夠刺激商業投資;三是商業活動也是對知識財產研發具有引導功能。可見,藏醫藥的“重義輕利”傳統與商事“功利主義”之間的沖突不容忽視。
筆者認為,這種沖突不能成為否定和反對知識產權的理由。一是“重利輕義”等觀念無法否定和制約其他競爭對手的營利行為。如西醫藥已經在藏區廣泛存在,不僅與藏醫藥展開直接競爭,也客觀改變著年輕藏族人的醫藥消費行為與習慣;二是藏醫藥實踐中形成的體驗性消費及評價、道地藏藥材等對藏醫、藏藥的傳統識別做法與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商標、商譽等有本質的一致性;三是圍繞著名的藏藥材發生的利益爭奪、不正當競爭等行為客觀存在,除道德、習慣等約束外,也需要進行規范和調整。四是許多藏區制定了藏醫藥發展規劃綱要,明確將藏醫藥產業發展界定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這體現了對藏醫藥進行商業開發和參與商業競爭的迫切需要,因此知識產權制度就更顯重要。五是強調藏醫藥的權利就是強化利益,而利益爭奪本身及相關規則的適用就必然違背“重義輕利”的道德底線,這與功利性應有內容是一致的。一方面,以滿足病人和社會大多數人的健康功利需要為首任,強調醫療行為實際效果價值的普遍性和最大現實,因此功利論是醫學理論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另一方面,功利論在理論上割裂了醫德行為中的動機與效果的辯證統一關系,容易導致道德對負面評價。因此,在多少人的觀念中,是排斥在藏醫藥中強調權利的。實際上,這種矛盾是可以通過對權利的限制而實現平衡和調節的。
導致這種沖突的原因在于:一是延續上千年的藏醫藥自成體系,對藏醫藥的法律認識缺乏獨立性思考;二是對知識產權規則的不了解;三是未嘗到甜頭,也未付出代價,對知識產權制度有“距離感”。
2 藏醫藥創新產品的開發與供應不足
藏醫藥創新產品的開發不僅包括具有代表性的藏醫藥文化表現形式的產品開發,也包括藏醫藥技術產品的開發。以藏醫藥技術產品開發為例,受專業人才少、企業發展規模小、藏醫藥技術轉化率、藥品等因素影響,藏藥新藥研發面臨的實際困難不小。具體表現在:一是除幾家上市公司外,更多藏藥企業普遍處于創業初期,規模小、產值低,藥材種植公司僅僅停留在小規模的種植基地建設階段,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直接影響藏醫藥科技產品的研發與供應;二是重藏藥材交易,輕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轉型,新的主體發展不充分,難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參與藏醫藥創新產品的研發;三是科技支撐不足。由于藏區制藥企業內部缺乏完整的產、學、研、營銷結合機制,自主創新與研發力量薄弱,外部又與其他藏醫藥研究機構未建立緊密合作、利益共享的機制,具有本地特色的藏藥優勢品種也難以有效推向市場。
究其原因,一方面,作為鼓勵創新的專利制度對專利藥品和醫療設備進行了強有力的保護,實現了西醫藥成本投入與成本回收的良性循環,極大的推動了西醫藥的科技和經濟發展;一方面在創新過程中產生的醫療風險也可以很好的通過制度性屏蔽而不影響其創新的努力。因此,創新是今天現代醫學成功的重要驅動力,這點對藏醫藥有啟發意義。
3 藏醫藥的交易方式及權利運作模式單一
一般而言,藏醫藥商品化所形成的交易對象包括貨物貿易(如藏藥材、藏成藥銷售、藏醫藥文化產品交易等)、服務貿易(如藏醫院的藏醫服務、技術交易于服務等)和知識產權貿易(如許可證貿易等)。但是在藏醫藥實踐中,交易主要圍繞藏藥材展開,更多是為世界醫藥產業的發展提供原材料,交易方式及權利運作方式單一、簡單,不能有效應對生物醫藥的發展沖擊。生物醫藥是當今世界經濟中最富活力的先導性、戰略性產業,隨著人們對藏醫藥的了解和認識,在美國、日本、印度、尼泊爾等地設立藏醫藥診療機構或藏醫藥研究中心,雖然使藏醫藥的影響不斷擴大,甚至已走向歐洲和東南亞市場,但是并不代表我們的優勢在擴大,相反,比較優勢在不斷縮小。
特定環境所造成的模式有其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一是藏醫藥的固有發展模式更多處于自然經濟狀態,缺少應對市場經濟的經驗。二是非制度化的激勵機制未很好調動研發積極性,即便是對于少數人的創新活動也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三是從業門檻缺乏認證,產生的風險由特定人承擔,而沒有實現制度性的吸收。
未來,醫療業整個商業模式應該是倒置的:基于每一位用戶的個性化數據,實現健康管理服務為主、醫療為輔;實現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藥品、健康器材乃至食品的生產。因此,在實現商品化過程中,要善于將其他優勢資源與藏醫藥資源進行整合,實現聯盟式“捆綁”發展。這就需要改變當前單一的交易方式和權利運作模式,通過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學習、借鑒與運用,突出其他交易方式的可行性研究,以提升參與市場競爭的實力和應變能力。
4 產品與服務的商業識別以商譽和道地藥材為主
與今天商業活動中成熟的商標識別體系不一樣的是,在藏醫藥實踐中更關注的是藏醫體驗性消費基礎上的商譽和藏藥材的道地藥材規則。即便在其他領域中形成了“重招幌輕商標”,在藏醫院中也有很大差異,表現在寺廟本身及其高僧的名氣與保有量直接關系到人們對藏醫院的選擇。雖然從藏傳佛教的角度,很難將這種實際的影響力界定為一種商譽,但是從其內容看所形成的消費信念與商業社會中對某產品和服務形成的信賴關系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究其原因,一是在維持社會秩序中,形成了道德約束下人格利益激勵與藏醫服務、藏藥質量等捆綁,以促成商譽或信譽。一方面,對疾病的治療效果的追逐與藏傳佛教中的修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高原獨特的地理環境不利于一般的商業社會和商業市場的形成與發展,人們對藏醫藥資源的尋求旺盛而且也特別關注其他人對藏醫藥技術和產品持有者的評價,也容易通過自己的體驗而不斷擴大和強化其社會評價,在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中就形成了道德約束下的人格利益(主要是名譽、榮譽類人格利益)與藏醫服務和藏藥質量相連,并促成商譽形成。二是青藏高原藏藥材資源豐富,而受地理環境和醫藥技術水平等因素影響,所呈現的藥性差異較大,另外,藏醫藥還取材于其他地區,藥材交易也是重要的傳統的商貿活動,因此,為滿足不同層次的消費者的需求,就延續了來自內地的道地藥材規則,并對藏藥材進行區分。
不過,無論是商譽還是道德藥材在今天也開始發生改變。表現在:一是其他醫藥產品強勢進入,增加了消費者的選擇項的同時,也因為獲得的信息量不斷增加、信息渠道多元之后,對以往商譽形成產生較大影響。二是在利益驅動下道德約束的約束力降低,導致商譽評價所依賴的信息可能受到不同利益主體的不同態度而表現出差異性,也直接影響到商譽的公信力。三是人工培育技術的推廣應用,導致很多藏藥材的藥性難以與傳統野生藏藥材的質量相比,不過量的增加與產出的可預期性也抵消了其消極影響。四是參與評價的群體也發生變化,尤其是基于對文化的好奇還是偶然的其他原因,對藏醫藥的評價與識別的參與群體發生較大改變,也導致傳統評價方式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