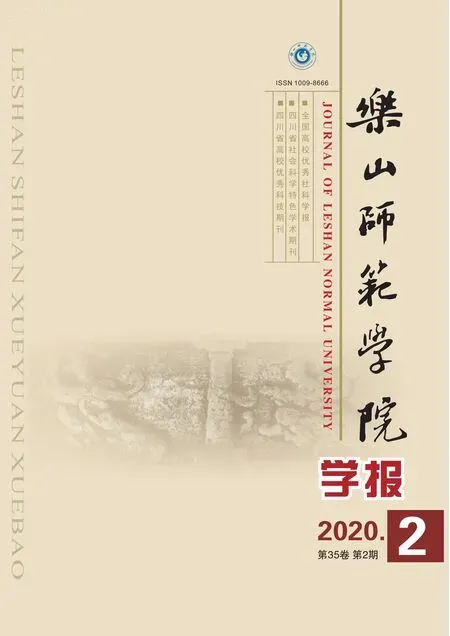以詩為詞與詞之本色新辨
梁翠琴
(暨南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以詩為詞”的明確提出以及它與本色論的爭端都始于宋人陳師道一句“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追也。”[1]286隨后李清照也在《詞論》中以“別是一家”的觀念直接駁斥了蘇軾的“自是一家”的理論,進而對其“以詩為詞”的創作傾向作出了質疑和批評。不可否認,蘇軾“以詩為詞”的創作傾向確實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詞文本的獨特性,影響詞體獨特表現力的發揮。然而它是否真的如“本色論派”所強調的“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宋人長短句雖盛,而其下者,有曲詩、曲論之弊,終非詞之本色”[2]7-8;“曲如詞,詞如詩,亦非當行,要皆有清冽無欲之品,肅括弘深之才,瀟灑出塵之韻,始可以擅絕技而后名世”[3]175……與“詞之本色”形成了對立甚至是水火不容的關系呢?筆者以為不然,因為“以詩為詞”的本質在于:在詞創作中吸取詩的元素,對詩的題材、內容、手法、風格、形式等進行吸收與拓展,以此開拓新詞境,提高詞的格調。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詞擺脫浮艷頹靡的羸弱氣質,逐漸成為與詩同等地位的文學樣式”[4]。它是蘇軾有意將詞雅化、拓展其功能的嘗試。并且在將詞“詩化”的同時蘇軾并沒有泯滅詩詞之間的界限,相反他是在堅持詞的“本色”的基礎上,將詩的表現手法有機地融入到詞作中,由此達到將詞雅化,提高詞的文學地位的目的。
從詞的源起及發展歷程中發掘、考量“詞之本色”的合理內涵,在此基礎上對具體作品再作細致的賞析,將有助于厘清對兩家學派的內在一致性和分歧的認知。以對蘇詞的細致賞讀為基礎,從何為“詞之本色”、蘇詞中“詞之本色”的顯現以及黜俗尚雅的詞學發展觀三方面探索“以詩為詞”和“本色論派”的分歧及內在美學觀念的一致性。
一、何為“詞之本色”?
陳師道在《后山詩話》中首次引入“本色”二字來論詞,為“本色論派”的先聲。但他僅以“教坊雷大使之舞”為例說明蘇詞是“非本色”的詞,并沒有明確給出“本色”的定義與內涵。隨后李清照在《詞論》中提出了“別是一家”的觀點,把前人有關詩詞之別的朦朧感受以及零星見解,發展成為了較為系統的本色理論。而之后“本色論派”的觀點大體是在繼承李清照“別是一家”的基礎上完成承衍的。“本色論派”對于詞之本色的定義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詞必須合乎音律,既要分五聲也要辨六律;二是詞應有自己的審美特點,講究情致,風格婉約,情思細密;三是詞在題材和內容上自有其所適宜表現的對象,內容應以男女情思、閨情別怨為主等。由此可知,“本色論派”對于“本色”定義不僅僅局限在音律方面,它還包括了風格、功能、題材等方面的內容。但事實上風格的差異、詞的功能是否可以歸屬于詞之本色的范圍內還是有待斟酌的。那究竟“詞之本色”應該包括什么呢?
先來看看《說文解字》中對“本”一字的解釋,“木下為‘本’,為木之始”[5]114, 故引申為初始之義。而在劉勰《文心雕龍·通變篇》里“夫青生于藍,絳生于茜,雖逾本色,不能復化”[6]533一句中的“本色”則是指事物本來的顏色,可引申為事物本來的面貌。所以我們要討論何為“詞之本色”就不得不回歸到詞的源頭以及詞的誕生歷程去梳理、厘定。
首先,從詞的源頭——敦煌曲子詞來看,“詞之本色”并不包括題材以男女情思為主、風格須婉約典麗、詞的功能當以言情為重等“詞本色派”所強調的內容。關于敦煌曲子詞所承載的廣闊題材,如著名學者王重民教授所言,“有邊客游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子之熱情與失望,以及佛子之贊頌,醫生之歌訣,莫不入調,其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7]17。可見詞在發展之初內容的豐富性以及題材的廣闊性,以及作為一種文體,它是兼有言情和述志兩種功能的。而且由于承載題材的廣闊,它也并未拘泥于某一種風格,相反它所呈現風格是多種多樣的。所以,“本色論派”對于詞在題材、風格、功能等方面應具有的“本色”的論述其實并不能歸劃到“詞之本色”的范圍內。而且“本色論派”以花間詞作為“詞之本色”的規范,并以相關作品作為基礎來推導“詞之本色”的內涵本來就是有失偏頗的。因為“花間詞派”不過是詞體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規范,只能稱為一家之“宗”,而不能將之看作詞源。“本色”必須回歸到事物發展的源頭和它發展之初的面貌進行發掘、梳理才能得到,否則是不能讓人信服的。
在詞體發展之初,雖然已有張志和的漁父詞,戴叔倫、韋應物的邊塞詞,王建的宮怨詞,白居易的相思詞等題材不同、風格各異的詞作,但總體上來說作品數量不多,質量也是良莠不齊的,能夠讓文人所信服的風格、規范還沒有形成。一直到晚唐五代時期,花間派的崛起,溫詞的廣泛傳播,詞這一種文體才正式有了創作的規范,要求題材上以男女情思為主,標榜了“詞為艷科”的取向;風格上以香濃軟艷為宗,初步確立“詩莊詞媚”的區別,建立起綺羅香澤,柔媚淺艷的審美追求;初步形成“男子而作閨音”,抒情主人公與作者相分離的虛構表達方式;詞體功能上突出了詞應歌、娛樂、娛情的功能。但需注意的是:以溫庭筠為代表花間詞派所確立的“詞之為體”的屬性,它僅能作為詞的某一種宗派的創作模范,并不是詞作唯一的形式規范,更不是詞之源頭。若錯誤地把“花間詞”當作詞之源頭,把它奉為唯一的模式規范,然后對那些與它在題材選擇上不盡相同、風格展現上也各有差異的詞作就大肆加以“要非本色”“亦非當行”的批判、指責顯然是不盡合理,有失公平的。畢竟雙方都是由敦煌曲子詞等民間詞這一源頭發展過來的不同分流,只是有可能一方發展得早、追隨者眾多而獲得更多的關注與認可。但平心而論,雖然文學成就上各有千秋,可兩者的地位應是平等的。
其次,從詞誕生之初的形態來看,它是“隋唐時期隨著燕樂興盛而產生的一種合樂可歌的新詩體。原名‘曲子’、‘曲子詞’、后有‘詩余’、‘長短句’等別稱”[8]1844-1845。由此可知,詞體誕生之初與其他文體相區別的特征主要在于“協律而歌的音樂性”以及“長短不一的句式”兩方面。而這兩方面才是“詞之本色”應有之義。至于風格須婉約媚麗、題材以艷情為主、功能以娛樂言情為重等內容只是后人深受某一詞派作品的影響,并以之藝術特征作為正確的規范附加到“本色”上的要求,實際上它們并不能作為“詞之本色”的原始內涵。
然而還應注意到,“協律而歌的音樂性”和“長短句式”都僅是從詞體的外在表現形式進行劃定的,從詞內在的美感特質而言,詞之本色還體現在了“要眇宜修”——一種精微幽深的曲折美。如王國維所言,“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9]46早期詞大多是寫男女情思、離愁別緒并交給歌妓傳唱的,因而詞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柔婉細膩的美感特質,許多無法在詩里表達的感情,通過詞便能輕而易舉地傳達出來,所謂“曲盡人情也”。而且詞較詩更能引發人的聯想,感發人之情思,賦予人以韻味悠長的美感體驗,故而“言長”。同樣地,礙于篇幅所限,詞也不能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或《長恨歌》等長篇詩一般,具有反映整個社會歷史的宏壯觀,賦予所詠之情以歷史的厚重感。所謂“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也。而詩兼具抒情述志、紀事議論等多重功能,使之幾乎無所不能言,內容題材上的廣泛帶來了境界的壯拓開闊,故而“境闊”。所以,詞之本色還包含了“一種深遠曲折耐人尋繹之意蘊”[10]185,也即一種深微幽遠,耐人尋味的美感特質。
在精神分析治療模式中,治療師與患者并非處于平等地位,患者只是整個治療過程中的服從者,而治療師作為指導者,可掌控整個治療過程,患者一直處于被動地位。在行為主義治療模式中,治療師和患者則扮演科學家與受實驗者的角色,其在關系地位上也具有不平等性。而在人本主義治療模式中,治療師與患者的關系有了改變,其具有平等性,兩者均作為治療過程的參與者,無地位上下之分。后現代心理治療模式將一切都認為是社會的構建,治療師與患者之間存在合作關系,兩者具有互動性。治療師只作為治療的參與者,其不具有判斷的權利,這種治療模式將患者原本的被動性變為了主動性,提高了患者的地位。
因此,對“詞之本色”內涵的理解應結合馬興榮先生在《中國詞學大辭典》中給出的定義和葉嘉瑩教授有關詞之美感特質的論述。“本色,此指本行,從詞體特征來說,又指協律而歌的音樂性。”[11]22可以看出,馬先生顯然是站在詩詞形式之別的角度上定義詞之本色,他從文體最具有區別意義的形式特征出發,突出了相較于詩,詞更注重于音樂性的特點。這一種定義主要從詞體在誕生之初的形態以及其發展源頭兩方面進行了考量,但卻忽略了對詞內在美學追求的關注。葉嘉瑩教授則對詞體形成、演進的整個歷史進程進行了考察,發現詞在發展過程中早已形成了一種幽微要眇的富于言外意蘊的美感特質,從詞之內在審美追求補充了“本色”的應有之義。
二、蘇詞中“詞之本色”的顯現
“本色論派”向來不喜甚至是貶斥蘇軾“以詩為詞”創作傾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蘇詞音律不諧的問題。最典型的莫過于李清照在《詞論》中所說的“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12]79。就這個問題,后世甚至還流傳過“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13]469“世言東坡不能歌”[14]354的看法。而從上文的討論可得知,從表現形式來看,“詞之本色”包含了“協律而歌的音樂性”和“長短不一的句式”兩方面。所以詞作是否合音律自然可以作為考量作品是否符合詞之本色的必要標準。然而蘇詞真的如“本色論派”所強調的“多不協音律”甚至是“東坡不能歌”嗎?
首先來回答“東坡不能歌”的問題,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蘇軾是知曉音律并且知道作詞應該諧律的。且看他在詞作《水調歌頭》(昵昵兒女魚)的序云:“歐陽文忠公嘗問余:‘琴詩何者最善’答以退之《聽穎師彈琴》詩最善。公曰:‘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為歌詞。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詞稍加檃栝,使就聲律,以遺之云。”[15]130從此序中我們可以看出,該詞是蘇軾把唐朝詩人韓愈所做的《聽穎師彈琴》一詩按照詞牌的格式以及聲律改寫而成的。若蘇軾真如世人所言“不能歌”,那么其他諸如《哨遍》(為米折腰)、《定風波》(與客相攜)、《定風波》(好睡慵開)等將本不入樂的詩、文改成合于聲律的檃栝詞的出現又該作何解釋呢?可知那些因東坡不能歌而攻擊蘇詞不諧律的言論是沒有事實依據作為支撐的。
其次是針對“本色論派”對蘇詞“多不協律”的指責,其實縱觀蘇軾傳世的360余首詞作,不難發現他的大部分詞作仍是合乎聲律的,只是偶有少數不合音律之處,并非“往往不協音律”。并且后世認為蘇詞中“不協音律”的地方有可能是后人對蘇詞之標點不同造成的“錯覺”而非真的是蘇詞不合格律。就如歷來被人們爭議的,在《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中最后十三字“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應如何點讀的問題。一般選本多采用“七、六”停頓而非合乎格律的“五、四、四”停頓,事實上蘇軾結尾處的十三字的平仄與格律完全相合,沒有不諧平仄之處,若以后人斷句之不同就加以“不協音律”的判斷實在欠妥。因為按照著名學者葉嘉瑩教授的說法,標點的不同主要在于“古人詩詞之讀法,原有以聲律為準之讀法與依文法為準之讀法二種”[16]128。一般蘇詞選注本的標點是依文法的斷句,因此難免與依聲律標點的斷句存在差異,有不合律之嫌。然而出現這種情況并不是因為蘇詞不合音律而是后人標讀的不同所致罷了。遍讀蘇詞,可知蘇詞只是偶有少數不協音律之處,但從整體上來說,蘇軾仍是在遵守詞之格律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的。
至于為何會出現偶不諧律的原因,筆者以為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的“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14]354一言頗有道理。正因蘇軾為人性情豪放,行文寫詞來往往“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13]469,很少或不會因為遷就音律而裁剪已成之作。并且這里其實暗含了蘇軾對于詞之文學性與音樂性的考量。眾所周知,詞在流行之初與音樂是不可分割的,它開始是為配樂演唱所用的。作為一種文體,它是兼顧文學性與音樂性的,比起詩,它更講究對音調格律的遵從。因此有些時候音樂性比文學性顯得更為重要。“本色論派”對蘇詞的質疑、指責很多時候就是站在維護詞的音樂性的立場上闡發的。因為在詞的音樂性與文學性的關系問題上,蘇軾兼顧文學性與音樂性并重,甚至有時是把文學性置于音樂性之前的。蘇軾看重詞體、文本的表意結果,于是便有意地將詩之題材、內容、手法、風格、形式等融入到詞的創作中,以此凸顯詞的文學性,增強詞的述志表意功能。但這并不代表他就完全忽略了詞的音樂性,使詞脫離了音樂。蘇軾本人曾在《與鮮于子駿書》中說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是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17]1754俞文豹《吹劍續錄》中記載:東坡在玉堂(翰林院),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18]139可見,雖然蘇軾通過“以詩為詞”提高了詞的文學性,增強了詞的言志表意功能,但他從未忽略過詞的音樂性,所作之詞都是可唱的。只不過別于花間、柳詞的“香秾軟語”、“鶯歌燕舞”的婉轉聲情,他的詞是要由關西大漢抵掌頓足而歌的豪放詞調。從另一種角度看,蘇詞非但沒有脫離了音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以耳目一新的作品豐富了詞樂。故從“諧律的音樂性”和“長短句式”這兩方面來看,蘇詞仍是符合本色的作品。
除此之外,就詞之特有的深微要眇,意于言外的美感特質而言,蘇詞也沒有因為“以詩為詞”而拋離了詞的藝術特征,失卻了詞之美感。相反它更多地體現了詩之美感與詞之美感的雜糅結合,呈現出了“在天風海濤之曲里雜有幽咽怨斷的聲音”[19]195,兼具詩詞雙重意蘊及美感特質的風貌。下面我們不妨通過比較蘇詩與蘇詞在題材選擇、風格塑造及表達效果上的差異來論述這個觀點。
雖然“以詩為詞”是要把詩之題材納入到詞的創作中,讓人對蘇詞形成了“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20]497的認識。但這并不意味著蘇詞與蘇詩在題材上完全對等,它只是把“詩中習見的某些題材移植到詞苑中去,并用在詩中已發育得十分充分的手法、意境來改造詞中原有的題材”[21],因此兩者在展現題材的范圍上還是存有明顯差異的。一如同樣抒發了自身壯志難酬的苦悶而與弟弟蘇轍同勉的《戲子由》一詩與《沁園春》(孤館燈青)一詞。在《戲子由》一詩中以“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一句直抒胸臆,暢快淋漓地抒發了自身滿腹經綸又不受國家重用的憤懣,蘇軾的苦悶與不滿溢于言表。而《沁園春》(孤館燈青)一詞中雖然同樣表現了作者壯志難酬的抑郁憂憤,但末尾卻以“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的口吻抒發了一種看破官場浮沉、超脫的人生觀,使全詞徒增了一種無奈感慨又灑脫出世的深遠意味。原本詩中滿腹的苦悶牢騷,一經詞的轉述,就變成了含蓄的無奈和超脫的感傷。雖少了一番直抒胸臆的酣暢淋漓卻多了一層曲折深幽的感慨。兩者相比不難發現蘇詩在抒懷言志方面比蘇詞更具力度,更顯得痛快淋漓,而蘇詞則較之多了一層婉轉流離的情致。
事實上,即使是同題而作,蘇詞與蘇詩在風格塑造上也會呈現出明顯的差異。而這也可作為蘇詞并沒有剝離“詞之本色”的映證。關于兩者在風格上具體有哪些差異,著名學者莫礪鋒教授曾總結出三個表現:一是蘇詩有時表現出粗豪的缺點,而蘇詞卻主要表現出細密、精麗的特征;二是蘇詩常有傷于直露、淺顯的特點,然而在詞中少有這種情形;三是蘇詞在藝術上就呈現出一種蘇詩頗為缺乏的委婉蘊藉,意在言外的風格傾向。[21]個人以為莫教授的觀點還是比較可取的,試取同為友人李公恕贈別的詩作《送李公恕赴闕》與詞《臨江仙》(自古相從)相比較,同樣是贊揚友人有才氣、能干,前者開篇就是一句“君才有如切玉刀,見之凜凜寒生毛”直接表明了作者對友人才能的贊頌與肯定。而后者通過“聞道分司狂御史,紫云無路追尋”一句運用杜牧的典故,來比擬李公恕,暗地稱美他的才氣,避免了過于直露、淺顯的表達而顯示出一種細密、婉轉的情致。同時后者還通過“問囚”“見鶴”等表明自己為官務所累,不免損傷身體以此委婉地暗示友人為官時要注意身體,充滿關切之情。比起前者只是熱情地贊頌友人的才氣豪情更添了一絲委婉蘊藉的柔情。由此看來同題而作的蘇詞與蘇詩在風格上其實是有明顯的差異的,而這正說明了蘇詞在風格塑造上對“詞之本色”的堅守與發揚。
自“古今一大轉移”(陳廷焯語)的張先將贈別酬唱的功能賦予小詞后,后世文人也不再只把詞看作僅是“聊佐清歡”的“薄技”,在一些重要的送別、酬唱應答環節也紛紛填起詞來,蘇軾亦不例外。然而即使是贈別同一個人蘇詞與蘇詩在表達效果上也是各有千秋。尤其是當詩之豪情逸志與詞之曲折幽微的美感特質雜糅在同一篇詞作中時,就會呈現出了“天風海濤之曲,中有幽咽怨斷之聲”的兼具詩詞美感的表達。試取《八聲甘州·寄參廖子》一詞來分析。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愿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15]148
詞作上闕以錢塘江潮寫起,潮來“有情”,潮去“無情”,氣象開拓,豪氣超拔。在無情還似有情之間,轉入對人世悲歡離合和古今變幻滄桑的無限感慨。“悲歡離合總無情”呵,可“人間自是有情癡”,縱它江潮、落日無情去,詞人自把眼前人思念,不必去思量以往那些古今迭代、人是人非。他將忘掉機心,無意功名,超脫于這些俗世煩惱之外。
下闕將筆鋒一轉,回憶起了與參廖同游西湖春景的賞心樂事,前闕“萬里卷潮來”的豪氣一下子被美好回憶的柔軟所覆蓋,將對滄桑變遷、人事代謝的慨嘆轉化為知交間的親密叮嚀。今日雖別離,但我們相約他年一起踐行謝公未竟的雅志,攜手歸隱山水。詞寫到這里仿佛已把別離之情訴盡了,然而蘇軾在豪宕超脫之外也有其敏感怫郁所在。此番回京,禍福未知,蘇軾已隱約預感到了再次被貶的未來,不禁悲從中來,于是只好祈愿參廖不會像羊曇哭謝公一樣,為己淚濕沾衣。可如佛家所說:“才說無便是有”,蘇軾此刻寬慰好友的“無”更反映了其內心對“有”的擔憂、悲哀。整首詞以錢塘江潮喻人間的悲歡離合寫起,開篇氣勢不凡,如詩一般奔騰澎湃。后又轉而抒發了對世事變幻的無限感慨,知交別離的傷感,雖然有超然物外,歸隱山水之志但也有事與愿違,恐難相隨的隱憂。將離情和己憂寫得如此低回婉轉,富具詞之曲折深幽的美感。正如鄭文焯在品讀《東坡樂府》時的手批,此詞“云錦成章,天衣無縫”,“從至情流出,不假熨貼之工”。[22]498相比之下,同樣是贈別參廖的《和參廖》一詩就略顯單薄了。詩篇以自己受官務所困無法與參廖一道云游說起,以舉案齊眉的梁鴻、孟光戲喻自己和參廖互相敬重、互相期許的友情,最后則表達了自己對參廖離去而感到茫然若失的心情。全詩在整體表達上不功不過,既展現了自己與參廖之間友誼又體現了自己對別離的傷心、惘然。但一與《八聲甘州·寄參廖子》一詞相比,在意蘊內涵之豐富、情感表達之深微等方面高下立見。可知,即使是贈別同一個人,蘇詞也能在堅持詞之美感的基礎上有機吸收了詩之美感的表達,呈現出兼具詩詞雙重意蘊及美感特質的奇特風貌。
綜上所述,可以得知蘇詞除了在“諧律而歌的音樂性”和“長短句式”這兩方面都是符合“詞之本色”外,在諸如題材選擇、風格塑造等藝術特征及詞的美感特質方面均沒有因“以詩為詞”而剝離了詞之本色。相反它有機融合了詩之美感,中和了“花間派”帶來的浮艷頹靡的羸弱氣質,塑造了一種“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的審美風格,“纏綿芳悱,樹秦、柳之前旃;空靈動蕩,導姜、張之大輅”[3]31,為后世詞的審美取向的轉變及詞學理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黜俗尚雅的詞學發展觀
從上文的討論可見,縱然“本色論派”對蘇詞多有“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指責,但其實兩家學派在具體創作時都堅守和發揚了詞的文體特征,都體現了對窈微要眇、意在言外的詞之美感特質的追求。同時,兩者在推動詞的雅化,提高詞的文學地位的目的上亦是殊途同歸的,兩者都體現了黜俗尚雅的詞學發展觀。“詞”作為一種隨燕樂興盛而產生的合樂可歌的新詩體,它發源于民間,流行于花間樽前,原本是民間“俗文學”的代表。可當它一進入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領域中,深受儒家雅正詩教觀浸染的文人們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改造其審美趣味,為其注入黜俗尚雅的審美取向,使之向“雅”文學過渡,從而獲得獨立的文學地位。正所謂“雅者,正也”,詞一旦成為了“雅”文學的一部分,那么自然就可以擺脫“小道”“末技”等“非正統”身份,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喜愛。
除此之外,黜俗尚雅的詞學觀的形成還與蘇軾、李清照等人所處的歷史背景有關。“詞”這一種起源于民間,帶有明顯的俚俗、粗鄙色彩的文學樣式能進入文人的審美領域還有賴于唐及唐以前帶有貴族色彩的“雅”文化觀念已被宋代以平民取向為底色的“雅”文化所嬗代。“門第觀念,由中唐后,經五代的喪亂流離,已掃除殆盡,所以宋代士人多出身平民,也以平民身份自甘。平民的氣質,自然是素樸平淡的氣質。”[23]487正是因為士人們大多出身平民,他們對待“雅”的態度已不如唐人那般封閉、傳統,反而能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去接納詞、戲曲等民間“俗”文學,逐漸養成了“以俗為雅”,雅俗兼融的趣味指向。
可雖說宋代士人們能接受“詞”進入他們的審美領域,但一開始他們仍免不了將“詞”視為“薄技”、“小道”、“謔浪游戲”、“詩余”,是難登大雅之堂的佐歡唱辭。彭國忠先生從道德觀、文學發展史和創作主體三方面對“詩余”的命名分析道:“從道德觀看,詞同其他各種文藝形式一樣,是‘德’之余,是作者的道德、事功的一部分,最微末的部分。……從文學發展角度看,在中國文學中,每一種新興的文體都被認為是前一主流文體的余緒……從創作主體看,作者在創作了詩歌之后,才力有余,遂溢而作詞,詞便稱為詩之余。”[24]58-59然而也正是因為文人們對“詞”的普遍輕視,才讓他們能夠在作詞時脫除“言志”與“載道”的束縛,以作筆墨游戲的態度,不自覺地將潛藏和久蘊于內心的某種精微深幽的情感表露于詞中。或者于此“謔浪游戲”之中流露了自己的真實性情、想法,而不必擔憂有心之人會以此為據來攻擊自己。可以說,詞的“非正統”文學地位給予了他們更多的創作自由、創作空間,讓他們可以藉“男子而作閨音”的方式隱晦地表達己思己想,己歡己悲。所以即使要“自掃其跡”,“文章豪放之士”也“鮮不寄意于此者”。[3]117而已如上文所言,文人士大夫的接受和創作必然會帶來詞的“雅”化,這是由他們固有的審美習性帶來的,亦是詞提高自身地位的必經之徑。
另外,蘇李兩派共同尊雅的一大原因還在于要擺脫或者升華以柳永詞為代表的“俗詞”。作為第一個專力寫詞的文人,柳永以其深厚的文學素養大力豐富了詞的曲調、題材、語言,然而他并不能跳脫出民間詞的俗調、俗情、俗語,使之往“雅”文學方向邁出關鍵性的一步。再加上柳詞又擁有了“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25]29的廣泛影響,導致詞壇上一直流蕩著一股淫艷浮靡、骨弱格卑的“俗”詞風。于是為了提高詞之格調、品格,兩家學派都不約而同地反對、貶斥了柳詞內容的俗艷、格調的卑下以及語言的粗俗。蘇軾雖然曾盛贊過柳詞中“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一句“不減唐人高處”,但也對風格與柳永相似的弟子秦觀提出了多次批評。“不意別后,公卻學柳七作詞”“‘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言語間,可知蘇軾并非針對全體柳詞,他反對的是那些格調卑俗,語言粗鄙的“俗詞”。而李清照則在《詞論》中亦道:“(柳詞)雖協音律,而語出塵下”,陳師道則直言:“(柳詞)骫骳從俗,天下詠之。”兩家學派都表示了對柳永將詞變成充滿世俗趣味、浮艷頹靡的羸弱氣質,而缺乏高雅情致的不滿。因此出于文人的審美習性和反對柳詞之俚俗趣味的需要,“以詩為詞”和“本色論派”都致力于尋找到維護和提高詞的高雅格調,提高其文學地位的方法或途徑。而正是“雅化”途徑的不同再次帶來了兩家的分歧。
以蘇軾為首的“以詩為詞派”從提高詞的整體格局出發,引入詩的寫法、題材等,拓寬詞的表現功能,使之能無所不言。同時將抒發個人情性納入詞,改變了“男子而作閨音”的代言體模式,將詞提升為自述其志、表現自我意趣的文學載體。誠如葉嘉瑩所言,“一直到了蘇氏的出現,才開始用這種合樂而歌的形式,來正式抒寫自己的懷抱志意,使詞之詩化達到了一種高峰的成就。”[16]103正是因為蘇軾注重情性的抒發,才把詞的創作模式由為曲造文、為文造情轉變為緣事而發、為情造文,以此開拓了詞之境界,升華了“詞為艷科”的品格,“指出向上一路”。還有一點就是,蘇軾在作情性文字時也將自身曠達高雅、超塵脫俗、逸懷浩氣等精神、品格注入詞中,使之從整體氣韻上脫除浮艷頹靡、柔媚卑俗之弊。正如胡寅所云:“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豪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3]117
而以李清照為代表的“本色論派”則從詞體的藝術特征出發,在語言上,要尚文雅,不能用“語出塵下”的俗辭鄙語;在布局上,要渾然一體,即追求全篇意象氣韻的整體美,不能如拆碎七寶樓臺一般“不成片段”;在形式上,要協音律,可倚聲而歌;在藝術手法上,需鋪敘展衍、尚典重、主情致而有故實。可見,“本色論派”更多的是站在堅守和發揚詞之形式美的立場上來維護詞的格調,它更注重發揮詞的“個性”、獨特表現力,使之能發獨家之言。由此可知,黜俗尚雅的詞學觀是兩家學派的共識,它反映了詞的“雅”化是詞體發展的客觀趨勢,只是在使詞“雅”化的方式或途徑上,兩者各有所側重,才會給人以彼此水火不容的表層認知。究其根本,則會發現兩者其實具有內在一致性,在實現詞的雅化,提高詞的文學地位的目標上是殊涂同致的。至于為什么兩家會各有所側重,里面還關涉了他們對“雅”的內涵的不同理解或關注。
“雅”作為一個復合型的美學范疇,它具有多層涵義,具體來說大致可以分為雅意、雅格和雅韻三重層面。“雅意是作品內在形式諸如情、理、意等方面的要求;雅格是作品外在形式諸如字、詞、句、律等方面的要求;雅韻則是作品藝術感染力的要求。其中,雅意是基礎,雅韻是目的,雅格是載體。”[26]“以詩為詞派”注重從雅意和雅韻兩方面對詞進行改造,因此以情性為文字,將哲理也一并納入詞中,同時亦追求超逸絕塵、曠達自然的審美風格。而“本色論派”則著重塑造和維護詞之雅格,從音律、語言文辭、藝術手法等形式、法度方面要加以規范、約束,突顯了形式美在文藝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所以雖然兩家學派都致力于推動詞的“雅”化進程,但蘇派的雅化努力在于提高詞的整體格局和境界,使之成為獨立文體,往“純文學”的方向發展。而李派的雅化努力在于堅守、發揚詞之形式美,充分保持和發揮詞的個性、獨特表現力。
“以詩為詞”與“本色論派”看似是對立、火不容的關系,但由于共同的時代歷史背景和文人階層的審美習性,兩家都體現了黜俗尚雅的詞學發展觀,都致力于“詞之雅化”。只不過“以詩為詞派”通過“借詩入詞”來改造詞柔媚淺艷、骨弱格卑的氣質,使其能夠跳脫出“詞為艷科”的藩籬,成為正統的“雅文學”。而“本色論派”則從聲律、語言、藝術手法等方面要求去俗崇雅,使詞在外在形式上先符合了“雅文學”的風貌。其實無論是形式上的尚雅,還是格局、境界上的拔高,它們都是詞建構和加強自身“文學性”的內在轉向的反映。也正是因為“文學性”的不斷增強,詞逐漸從一種民間文學變成文人士大夫的案頭文學。而案頭化往往帶來規范化、統一化的創作,由此詞又重蹈詩的覆轍,陷入了“二京無詩法,兩漢無詩人”的發展困局中。
綜上所述,“以詩為詞”借詩材、詩法拓寬了詞之題材,提高了它的境界、格局,推動了其“雅”化進程,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就如“本色論派”所批判的“要非本色”。相反,從“諧律的音樂性”“長短句式”以及詞之美感特質這三個“詞之本色”的應有之義來看,蘇詞并沒有泯滅詩詞之間的界限,除了偶有少數不諧律之處,總體上蘇詞都是在遵循詞之格律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的。且蘇詞非但沒有剝離詞之要眇深幽,耐人尋味的美感特質,還讓它兼具詩詞的雙重美感和意蘊,塑造了一種“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的審美風格。所以“以詩為詞”和“本色論派”其實體現了不同程度上對詞之本色的堅守和發揚。除此之外,兩者均體現了黜俗尚雅的詞學發展觀,可選擇了不同的“雅”化方式或途徑。但它們在推動詞的“雅”化,提高詞之文學地位的目的上是殊途同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