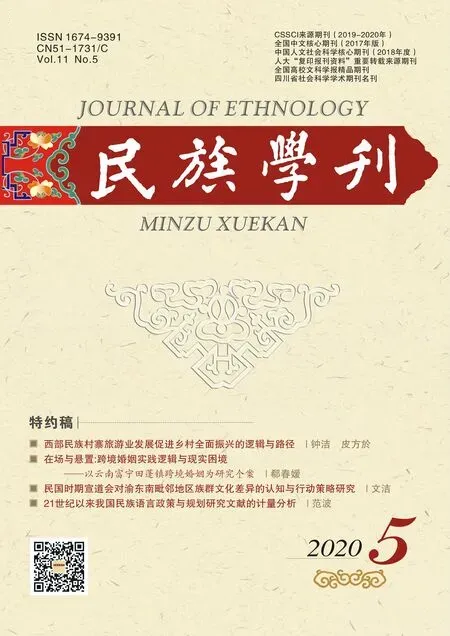從古歌到民族史詩:《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綜述
覃 琮 吳絮穎
《密洛陀》是以口承為主的瑤族史詩,主要流傳在布努瑤支系,流傳區域覆蓋滇、黔、桂、湘交界地帶,以桂西北的都安、巴馬和大化三個瑤族自治縣(以下簡稱都安縣、巴馬縣、大化縣)及其周邊區域為主要流傳地,涉及十幾個鄉鎮,近五十萬人口。 布努瑤民間把密洛陀稱為“雜密”,把世代傳下來的關于密洛陀神話、傳說和故事統稱為“密洛陀古歌”。 古歌主要講述人類創世祖母密洛陀和她的兩代兒女工神、武神創造天地萬物和人類,以及瑤族先祖及其南遷的故事,是一部集創世、英雄和遷徙為一體、擁有很多分支歌的完整群系統的復合型史詩,敘事宏大,內容龐雜,被譽為布努瑤的“百科全書”。
從20 世紀60 年代開始的零星調查到80 年代以來的全面搜集整理和出版,《密洛陀》吸引著眾多學者的關注。 人們希望通過《密洛陀》來了解這個偏安于桂西北石山地區、最晚近被外界所知道的瑤族支系。 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密洛陀》搜集整理的歷程以及相關研究,不僅有助于今后對這部史詩進行更深入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挖掘它的獨特價值和普遍意義,滋養包括瑤族在內的現代人的心靈,更好地為現代社會服務。
一、《密洛陀》的搜集整理
(一)《密洛陀》搜集整理的進程
《密洛陀》的最早記錄,發現于民國時期桂嶺師范學校校長劉錫蕃所著《嶺表紀蠻》一書,其云:“桂省西北之苗瑤于盤古大帝外,兼祀伏羲兄妹及迷霞(女性)、迷物(女性)、含溜(性別不詳)諸神”。[1]這里所說的“迷霞”“迷物”,從名稱和性別上看,應是“密洛陀”的音譯。
不過,《密洛陀》真正意義上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從20 世紀60 年代才開始的。 先是廣西民間文學調查組的農冠品、黃承輝到都安縣采風,在七百弄鄉(今屬大化縣)收集到了三千多行的《密洛陀》,油印成資料在社會上傳閱。 受此影響,中央民族學院的劉保元、盤承乾等人也前去七百弄等地采錄。 莎紅和黃書光(廣西民族學院教師)等人則順藤摸瓜到巴馬縣東山鄉采訪,獲得七份有關《密洛陀》的原始材料,莎紅整理了其中的“創世”部分,發表在1965 年《民間文學》的第1 期,引起世人關注。
這一時段的《密洛陀》搜集整理比較零散,參與者中大多數不是土生土長的布努瑤人,存在著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礙,特別是不懂《密洛陀》宗教語,①造成工作艱難、進度緩慢,還引起了許多誤訛。[2]“文革”期間,《密洛陀》被斥為封建余毒,不少巫公、歌手慘遭游斗、毒打,相關搜集人員也因此遭殃,有的還被關進了牛欄,《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工作被迫中斷。[3]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極“左”思想開始得到全面糾正。 進入80 年代,我國各民族民間文學事業慢慢復蘇。 1983 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民研會向原河池地區文化局下達相關通知,《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和翻譯工作重新啟動。 此后,以藍懷昌、蒙通順、蒙冠雄、藍永紅、藍正錄、蒙有義為代表的一批布努瑤學者逐漸成為搜集整理甚至研究的中堅力量。 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至2002 年,包括1981 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莎紅版《密洛陀》單行本,一共出版了五個版本的《密洛陀》。這些不同版本的《密洛陀》,分為以下兩大類:一類是文學版本,即漢語意譯的版本,共有四個版本;另一類是科學版本,即在整理和翻譯《密洛陀》時,要有瑤文(布努語)、國際音標、直譯、意譯四道工序,或最少要有三道工序,即國際音標、直譯和意譯。 目前,科學版本只有2002 年張聲震主編的《密洛陀古歌》一版,有三道工序。
(二)不同版本的《密洛陀》的比較
莎紅版《密洛陀》是第一個漢譯本,由巫公、歌手吟唱,自己先逐句用漢語譯出,莎紅再做整理,材料原始可靠。 為更好地表達“創世始祖”之意,莎紅在瑤、壯和漢語的對譯過程中,把布努瑤民間的稱謂“雜密”譯成“密洛陀”。 “雜密”本意是“話密洛陀”,又隱含“母道理”之意。“密洛陀”一詞中,“密”即“母親”,“洛陀”意為“古老”,兩部分合起來即為“古老的母親”。 這個譯名,既蘊含“至尊的創世之母、偉大的母親神”之意,又符合“密洛陀”是“一切道理之母”的豐富內涵,后一直沿用至今。 這是莎紅的一大貢獻。 但是,因為顧慮到當時的民族政策,有關原始材料中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斗爭章節全部刪去,同時,不會講漢語的巫公、歌手的傳唱材料無法收集,所以這個版本內容不全,只分為“造天地、造森林、造房子、射太陽、殺老虎、找地方、造人”七個部分,九百多行。 此外,莎紅是壯族詩人,因而這個版本被認為“滲入后來的成份太多、在運用俗語方面有不準確的地方。”[4]
1986 年的潘泉脈、蒙冠雄、藍克寬搜集整理的《密洛陀》(以下簡稱潘版),后被編入第七冊的《廣西瑤族社會歷史調查》(1986 年)。 這個版本的《密洛陀》,古歌源于當時保存相對完整的七百弄鄉。 除“開頭歌”外,共分為二部十八章。 第一部創世歌十章,記錄從密洛陀出世到為密洛陀做“補糧做壽”,分為密洛陀出世、造天地、賣種子、造動物、懲罰動物、找地方、造人、判是非、射太陽、補糧做壽,古歌展示更加具體形象,出現了一些新的材料。 第二部也叫創世歌,計有分家、西天學法、報仇、逃難、智斗財主、抗暴、為了后代、酒歌共八章,反映的是布努瑤來到廣西,特別是來到都安以后的傳說和故事,既表現瑤民反抗封建統治階級(壯族土司土官和朝廷皇帝)的斗爭,也表現了瑤民與壯、漢各族人民的友好往來。 這些內容是莎紅版本所沒有的。
第三個版本是1988 年由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密洛陀》。 這個版本由藍懷昌、藍京書、蒙通順搜集整理(以下簡稱藍版),歌源主要來自巴馬縣的東山鄉、都安下坳鄉的隆石、加文、崇山等地,計有序歌和三十四章,主要內容為造神、造天地萬物、懲殺日月妖獸、造人類、分族分家與逃難遷徙、祭祀六個方面,內容基本完整,南方民族史詩復合型特點已清晰可見。 由于藍懷昌、藍京書、蒙通順三人都是文學出身,文學造詣較高,而蒙通順的祖輩、父輩們又都是當地有名望的巫公、歌手,這些便利的條件使全書在瑤、漢的對譯過程中遵循史詩講究對偶、對仗的語言特點,大量運用比擬、夸張、復疊的表現手法,文學性強,藝術想象豐富,極富感染力,是文學版本中的珍品。
第四個版本是1999 年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密洛陀》,這個版本由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整理,實際上是2002 年《密洛陀古歌》科學版本出版之前的文學版本,因為蒙冠雄是《密洛陀古歌》項目的重要負責人和參與者。 這個版本共有三十四章,一萬兩千多行,從內容版塊上與藍版《密洛陀》大體相同,但章節安排與故事情節有較大差異。 比如,藍版《密洛陀》用了五章(第二十九章至三十三章)來敘述布努瑤來到都安后分家逃難以及各姓氏世系的歷史,而這個版本只編排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各奔一方”。 這個版本有幾大貢獻:一是首次區別了《密洛陀》和《祖宗歌》《族譜歌》三部古歌,澄清了以前的許多不解、誤解;二是為古地名作了注解,特別是宗教語喃唱古歌時提到的古地名;三是附錄了演唱者的名單,介紹他們的生平簡歷和藝術特長;四是對《密洛陀》史詩中提到的44個神祗按冥界(五位)、神界(十四位)和陽界(二十五位)進行了分類和附錄,初步厘清了神譜關系;五是配有《造神界》《造神童》《造天地》等35 幅插圖,圖文并茂,生動形象。 因此,這個版本,原始材料更加翔實可靠,被瑤族學者認為是“達到較高的藝術境界”“融文學、史學、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語言學、哲學、美學、宗教學等各學科的豐富史料于一體,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和文化積累價值。”[5]
科學版本,是1987 年“密洛陀古歌”成為國家民族古籍出版“七五規劃”重點項目后在編譯整理方面的體例要求。 這個項目是目前廣西民族古籍辦跨時間最長、資助最多的項目。 2002年,在歷經14 年的漫長煎熬后,由藍永紅和藍正錄搜集、整理和譯注的《密洛陀古歌》終于問世。 《密洛陀古歌》的歌源主要來自大化縣的七百弄鄉、板升鄉,以及都安縣、巴馬縣和東蘭縣個別鄉鎮,采錄的歌師上百名,最后取當時宗教語保留比較完整的七百弄鄉的唱本作為參照進行辨別和編譯。 從編排來看,《密洛陀古歌》設篇、章、節,分有上篇和下篇,各章又分為若干節,共計八十八節。 上篇主題為“造神”,共九章:密洛陀誕生,造天地萬物,封山封嶺,造動物,遷羅立,射日月,抗災,看地方,羅立還愿;下篇主題為“造人”,共五章:造人類,分家,密洛陀壽終,逃難,各自一方。 每一章(包括序歌)都采取“題解” +“古歌” +“附記” +“注解”的基本框架。 書后附有藍永紅編制的“神譜表”“曲調”和“采訪歌師情表及主要歌師簡介”三個附錄。其中,“神譜表”按原始神(一位)、始祖神(四位,其中密洛陀是人類神)、密洛陀首批造的“工神”(十二位)、密洛陀第二批造的“武神”及女神(十位)、其他小神(五位)、人類誕生后的主要人物(八位)進行分類,徹底弄清密洛陀傳說中紛繁復雜的各個神話人物關系,使史詩的神譜結構更加嚴密。 全書分上、中、下三冊,九萬多行,共計340 多萬字,篇幅恢宏,是目前已經出版的各個《密洛陀》漢譯本中搜集規模最大、歷時最長、體例最規范、內容最齊全、故事情節最生動、資料最全面的版本,被稱為“一部集布努瑤古文化的鴻篇巨作”,[6]為研究《密洛陀》及布努瑤提供了極大方便。
《密洛陀》是布努瑤一代傳一代的思想和智慧的結晶。 它的整理成書,飽含著布努瑤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熱愛和崇敬。 為此,半個多世紀以來,不少布努瑤的地方學者、文化人、民間文化工作者不計名利,嘔心瀝血,前仆后繼,走遍千山萬弄,歷盡千辛萬苦,將蘊藏于民間的、散亂的古歌一點一點挖掘出來,成為今天的鴻篇巨著。 不同版本的《密洛陀》先后問世,終使布努瑤的這座“民族精神標本的展覽館(黑格爾語)”走出瑤山,匯入中國民族史詩的星空長廊,成為南方民族史詩的典范文本。
二、《密洛陀》的研究
1981 年,韋其麟為莎紅《密洛陀》單行本出版所撰寫的序言,首開《密洛陀》研究之先河。此后,伴隨每一次《密洛陀》漢譯本的問世,都掀起學界不大不小的研究熱潮和評介。 截止2020年6 月,史詩《密洛陀》的研究,出版專著1 本;碩士論文11 篇,其中題名為“密洛陀”的共有5篇;期刊論文93 篇,其中篇名為“密洛陀”的共計49 篇。 這些研究,主要討論了以下議題:
(一)《密洛陀》的定位
《密洛陀》被譽為瑤族的民族史詩,但它無法回避一個事實:為什么只有在桂西北的布努瑤支系中有密洛陀傳說,其他支系,包括瑤族的第一大支系盤瑤,以及與布努瑤同屬苗瑤語支的其他分支、小支也無此傳說? 由此,怎樣認識《密洛陀》所描繪的遠古社會,它對理解整個瑤族的歷史文化有何作用? 進而,與另一部瑤族古籍經典《盤王歌》相比,《密洛陀》在瑤族文化中的地位如何?這些都是《密洛陀》研究必須予以回應的問題。但遺憾的是,多年來卻沒有學者專門探討,只是有所觸及。 藍芳敏從史詩、譜牒、服飾、銅鼓、語言等方面論述布努瑤的文化特征,推斷桂西北的布努瑤不是“盤瓠種”,而與黔中苗族有親緣關系,只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將其標之為瑤。”[7]毛珠凡也談到,布努瑤只信奉密洛陀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作為瑤族歷史文化核心的盤王神話傳說,可以斷定布努瑤來源以苗族為主,兼有漢族、壯族甚至侗族,而來源于信奉盤瓠(王)瑤族的不是主流。[8]譚振華指出,《密洛陀》和《盤王歌》是瑤族文學的兩座高峰,分別被瑤族的兩大支系所繼承。《密洛陀》是“母親之歌”,代表女神,象征母親的慈愛。 《盤王歌》是“父親之歌”,代表父神,象征父親的威嚴。 瑤族的“民族根”恰恰是附在這兩部史詩中,更體現在《密洛陀》之中,因為《密洛陀》的篇幅和體量是《盤王歌》的十倍之巨,它才是瑤族文學的巔峰。[9]
(二)《密洛陀》的創世特點
《密洛陀》是創世史詩,對它的創世特點很早就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 陸桂生認為《密洛陀》突出地反映了布努瑤先民創造世界的英雄業績,具有“人類創造了自身創造萬物、人是萬物之靈、反映了母氏社會痕跡、運用半人半神的表現手法”的創世特點。[10]張利群認為在《密洛陀》的“創世”史詩中,體現了“人與自然互生關系、在創世精神指導下確立人類改造自然的主體性”的自然文化觀。[11]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密洛陀神話揭示人類從神到人、從自然到人、從個體的人到社會的人的特征,顯示出人類起源過程中人的巨大的“創世”力量及其在創造人類、創造民族、創造文明中的巨大作用,由此體現出“密洛陀”神話傳說的文化人類學意蘊及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大意義。[12]
(三)《密洛陀》的哲學思想
對《密洛陀》進行哲學思想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多,共有10 多篇論文。 這些文章主要討論了《密洛陀》的唯物論、辯證思想、天人觀、生態觀等內容,側重點各有不同。 陳路芳認為《密洛陀》體現了瑤族先輩以神話的形式表達了“氣生萬物的宇宙起源說、動物變人的人類起源說、萬物異動的樸素辯證法思想”的哲學思想。[13]朱國佳從生存智慧的角度分析了《密洛陀》天人合一、群體責任意識、堅定生存信念三方面的特征,認為這是布努瑤作為一個弱勢群體的生存之道,其意義在于反思各民族最佳的相處之道是什么?[14]謝少萬、劉小春先是從語言學的角度詮釋《密洛陀》所蘊涵的人類精神和民族精神,[15]再從西方哲學的本體論觀念出發,指出《密洛陀》包含有本體論思想萌芽、普遍聯系的樸素辯證觀思想、“人定勝天”以及“天人合一”的人天觀,由此要看到瑤族的哲學思想源遠流長,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應當有適當的地位。[16]盧明宇以生態審美為視角,認為《密洛陀》存在萬物同源、人類同根、內在價值的生態平等思想,對當今構建平等和諧的生態社會有著啟發和借鑒意義。[17]
(四)《密洛陀》的文化認同
史詩是文化表達的源頭,也是民族文化認同的根譜,是最為擅長表述這種認同的文類。[18]鄭威認為《密洛陀》實際上是一個記憶文本,包含有一個族群自我認同的多個要素,它對布努瑤族群歷史、族群認同和族群邊界進行了建構和解釋,并將它們聚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不斷強化布努瑤的族群認同和歸屬意識。[19]伍君則運用神話—原型批評分析方法,結合《密洛陀》對瑤族作家藍懷昌的長篇小說《波努河》里人物形象的原始意象進行探討,認為當代文化藝術與遠古人類民族文明之間存在脈脈相承的相應的象征意義。[20]藍芝同探討了《密洛陀》對研究人類起源、瑤族先民逃難原因和遷徙路線、瑤族生產生活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習俗方面的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其實也隱含著民族記憶和文化認同。[21]王憲昭對《密洛陀》的功能性母題進行了分解與梳理,發現這部創世神話史詩具有古老性、完整性、持續性和實踐性,并由此發揮著民族歷史的記憶功能、生產生活經驗的傳承功能以及日常教化與行為規范等功能。[22]
(五)《密洛陀》的傳承規律
近年來,在口頭詩學的理論影響下,開始有學者探討《密洛陀》的傳承規律問題。 何湘桂通過對不同《密洛陀》文本的梳理與比較,指出《密洛陀》能夠活形態世代相傳,不僅源于其特定的生態環境、傳承形態以及思想內涵,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創編規律和生成機制。 其一,《密洛陀》是典型的南方創世史詩敘事范型(原形和母題),即它的母題包括始祖誕生、開天辟地、造人造物、洪水泛濫、族群遷徙、農耕生產等幾大部分,始終以“創世”主線為中軸,依照歷史演變、人類進步的發展程序展開,通過天地神祇、先祖人物、文化英雄及能工巧匠的塑造,把各個詩章連接起來,關注更多的是人與神、人與自然的關系。 其二,《密洛陀》依靠程式這一內部法則,使史詩具有程式化特點,然后不斷進行積累、加工和完善,使史詩便于記憶、儲存、回憶、現場創編。 具體而言,《密洛陀》的敘事程式,包括語詞程式(人稱地名程式、疊音詞程式、數字程式)、句式程式(對稱式平行、層遞式、排比式)、結構程式(襯詞的使用、復合大型程式)。[23]林安寧則結合歌手蒙鳳立的現場演唱,分析“聲音”對密洛陀史詩研究的意義,強調對史詩演述背景的敘述與記錄,都是密洛陀史詩研究者要面對的共同話題。[24]
(六)《密洛陀》和其它史詩的比較
對《密洛陀》與其它史詩的比較研究,學界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探討。 第一,《密洛陀》與瑤族的另一部經典《盤瓠》的神話比較,代表作是何潁的《對瑤族神話〈密洛陀〉與〈盤瓠〉的深層思考》。 該文認為按照社會發展過程排序,《密洛陀》排于先,《盤瓠》出現于后,兩則神話串連起來構成了瑤族神格觀念的順序,是瑤族長久以來“先有瑤,后有朝”觀念產生的直接誘導。[25]第二,《密洛陀》與壯侗語族的神話比較,重點是與壯族史詩《布洛陀》進行比較,代表作是李斯潁的《壯族布洛陀與瑤族密洛陀神話比較》。 該文從神祇、神話母題兩方面詳細比較布洛陀和密洛陀神話,發現兩者在世界的最初結構方式、創世的始祖內容上保持了較高的相似性,從而論證了壯、瑤是文化上互通有無的兩個民族。[26]第三,《密洛陀》與漢族遠古神話的比較。 蒙有義從創世神話定義、相同創世神話的比較、不同創世神話的比較三個方面揭示了瑤漢創世神話的異同及其動因和規律。[27]張利群則以女媧作為參照系來比較密洛陀,指出各民族文化表現出某種共同性和某種趨向性,從而成為一種潛在的人類意識,因此,密洛陀越是走出瑤山,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就越能表現出它的永久魅力和巨大價值。[28]第四,密洛陀神話的“世界比較”,代表作是林安寧《〈密洛陀古歌〉和〈古事記〉神話比較》。 該文不僅比較了《密洛陀》與日本《古事記》在神譜敘事、女神兩方面的異同,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提出了以下思考:神話研究如何從傳統的中外比較走向世界比較? 其中,又如何凸顯中國少數民族神話的地位?[29]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三十多年來《密洛陀》的研究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至少現在,《密洛陀》不再象改革開放之前的那樣,是學界無人問津的“研究盲點”。 自2011 年《密洛陀》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后,這部史詩在整個瑤族歷史和文化中的地位、非遺價值、學術價值、傳承狀況、創新性發展等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學界對《密洛陀》研究日漸深入,正進入活躍期。
三、今后《密洛陀》搜集整理和研究展望
盡管《密洛陀》在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較為明顯的缺陷。 比如,搜集整理方面,成果形式比較單一、搜集區域過于集中;在研究方面,重文本、輕田野的研究傾向非常明顯,以致于目前《密洛陀》的研究,尚無法深挖它的文化內涵,更無力邁向精審深細的詩學分析。 因此,今后《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提高。
(一)全方面、立體式地進行搜集與整理
《密洛陀》是活形態的史詩,布努瑤把《密洛陀》及其分支歌與日常生產生活聯系起來,形成包括宗教活動、節日活動、婚嫁、生育、立房上梁、交易、狩獵、神判與詛咒等多個使用場合,每個場合都會演唱一部分《密洛陀》或其分支歌的相關內容。 從傳承形態來看,《密洛陀》是由語言敘事、儀式化行為敘事、圖像敘事和景觀敘事共同構成的完整譜系。 因此,僅僅是文字文本的《密洛陀》,缺乏其它材料的共同形構,勢必會割裂掉史詩活形態傳承的完整性和聯系性。
所謂全方面、立體式地搜集和整理《密洛陀》,有兩個層面涵義:其一,運用文字、聲音、圖像、視頻等多種記錄手段,整理出包括語言、聲音、民俗場景、歌手創編、現場演述、觀眾互動等在內的豐富素材。 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國家層面推進的節日影像志和史詩影像志兩大研究工程的逐步發現和理解,影視人類學的學術理念、研究方法和技術方法在國內已經日臻成熟,影像志或影視作品的獨特優勢和價值越來越受到學界和公眾的認可。[30]《密洛陀》已入選中國史詩影像志的子課題,要利用這一契機,豐富《密洛陀》的資料素材和形式,成為研究者的一手田野資料。 其二,同樣運用現代新媒體手段,搜集、記錄老巫公和老歌手們的各個唱敘版本,建立數據資料庫。 特別是過去較少進入的鄉鎮,如都安縣的東廟、大興、隆福、龍灣、青盛等地,大化縣的板升、雅龍、江南等地,以及布努瑤的韋氏、羅氏等其它姓氏的版本。 根據筆者近幾年的調查,散落民間的各種古歌唱本依然數量龐雜,即使鄰近村落也有不同的版本。 這是一項非常迫切的任務,因為那些參加過大還愿的老巫公,大多年過90 歲,搶救、記錄和整理這些老巫公的演述版本迫在眉睫。
(二)加大對《密洛陀》的田野調查研究
由于布努瑤主要聚居在廣西的“石山王國”,交通極為不便,加上巫公群體所喃唱的是一種古老的宗教語言,必須有懂宗教語的布努瑤學者協助才能整理和翻譯,田野工作難度極大,導致過去《密洛陀》研究最大的缺憾就是田野調查太少,史詩的傳布狀況、傳承群體、傳承形態、創編規律、傳承現狀等基本資料沒有被充分調查、掌握和研究。 今天,桂西北幾個瑤族自治縣的交通狀況已大有改觀,基本實現硬化公路村村通。 與此同時,國家近年來不斷加大扶貧攻堅力度,許多偏僻的瑤族村寨被整體搬遷到縣城或鄉鎮中心居住,而這些村寨往往又是布努瑤文化保存最為完整的地方。 一旦脫離原來的生態環境,《密洛陀》是否還能保持活態傳承是一個問號。 因此,加大對《密洛陀》的田野調查,恰逢其時,也正當其時。
1.《密洛陀》傳承形態的綜合調查
語言敘事的調查,一是要調查各傳承群體在不同場合唱敘《密洛陀》的各種語言,包括宗教語言、史歌語言和情歌語言等;二是要調查布努瑤在不同的場合對密洛陀的不同稱呼(有10種不同的稱呼)及其含義;三是要調查圍繞《密洛陀》主體詩下的其它史詩、神話和傳說,當務之急是盡快整理出英雄史詩《阿申·耕杲傳》(阿申和耕杲是密洛陀創造的第二代兒女中的大兒子和二兒子),因為這是《密洛陀》史詩集群中最重要的子史詩。 儀式化行為敘事的調查,重點是《密洛陀》的各種使用場合,包括喪葬和各種祭祀場合的喃唱、世俗場合的盤唱、日常生活的“講古”等。 圖像敘事的調查,包括各種祭祀儀式中的竹卦、麻衣麻帽、紙衣紙褲、紗紙、插神枝、倒神水、火盆等構成圖像。 景觀敘事的調查,包括大型祭祀場合搭建的祭棚、各家各戶的密洛陀神臺、村寨里的雷神林、史詩提到的古地名,以及近年來與史詩內容的主題景觀公園、雕像、廣場、酒店、閣樓、村落、傳習基地等公共文化建設和文創、物語營銷等。
2.《密洛陀》傳承現狀的全面調查
首先,調查《密洛陀》在布努瑤聚居地各鄉鎮村寨的流布情況,借以劃分當前《密洛陀》的主要流傳區、次要流傳區和外圍流傳區三大區域。 這既是研究要掌握的必備資料,也是為地方政府提供保護史詩對策建議的重要憑據。 其次,調《密洛陀》的“布西”、“分”歌手、“布商”和“耶把”和愛戀歌歌手四大傳承群體的傳承譜系,包括師承系統、傳授方法、記憶悟性、熟練程度、表達技巧、吸收借鑒、相互合作等材料,借此了解和掌握《密洛陀》的傳承規律。 再次,調查《密洛陀》傳承群體的生活狀況。 重點是巫公的生活史,因為巫公不是簡單的史詩演述人,而是“什么都懂、什么都會”全能型人才,了解巫公的生活和地位變遷,有助于把握當下《密洛陀》活態傳承遭遇的困境。 最后,調查《密洛陀》的演述場域,包括民俗背景,巫公(歌手)的素質、聲音、使用的句式程序、與現場觀眾的互動、現場的創編、修正,儀式結束后主家和觀眾的評價等內容,借以掌握《密洛陀》的演述規律。
(三)拓寬《密洛陀》的研究領域
《密洛陀》是布努瑤的“標志性文化”,但它不是獨立存在的。 布努瑤的民間說法是“什么都是密洛陀創造的”“什么都要用到密洛陀”,由此可見《密洛陀》是與布努瑤的其它文化互滲共生的。 今后對《密洛陀》的研究應借勢延宕開來,與其它相關表意文化研究互相印證呼應。
《密洛陀》的表意文化形式很多,其中祝著節和銅鼓應是《密洛陀》研究重點要拓展的領域。 祝著節原本就是為了紀念密洛陀的仙逝而過的節日,加強對它們的關聯性研究是應有之義。 對布努瑤銅鼓的研究過去偏重于音樂、藝術和技藝制作,實際上這樣研究還遠遠不夠,甚至有點“本末倒置”。 因為在史詩《密洛陀》中,銅鼓是密洛陀創造的,武神們曾利用銅鼓射殺日月、抗災,布努瑤的銅鼓是密洛陀送的,并在楠妮婚宴中跟危娘(一只母猴)學會了敲打銅鼓、銅鼓舞……因而,對布努瑤銅鼓的研究,今后應著力挖掘附著在它身上的傳說、故事等文化意涵上。 此外,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挖掘《密洛陀》相關的其它布努瑤口傳文化、服飾文化和美食文化等方面的內涵,促進布努瑤聚居地各縣創建優質的全域旅游示范區,形成《密洛陀》的非遺旅游、非遺扶貧、非遺傳承保護和非遺研究的良好互動局面。[31]
不同形式的表意文化,充當著《密洛陀》活形態傳承的記事、敘事、說事、演事等不同功能。但是,目前對這些表意文化形式的研究,有的基本上還沒有,已有的個別研究,相互間則缺乏整體的有效呼應,這是今后《密洛陀》研究亟需整合的地方。
(四)實現與國內外史詩研究的接軌
實現與國內外史詩研究的接軌,目的是要讓《密洛陀》及其研究“走出去”,匯入詩學研究的大潮流,擴大《密洛陀》在中國乃至世界史詩學界的影響力。 要做到這一點,一是要在理論和方法上自覺運用口頭程式理論、民族志詩學、表演理論、敘事學理論等當代史詩學重要學說對《密洛陀》進行精審深細的詩學分析。 具體做法就是把嚴格的田野作業引入《密洛陀》的研究之中,從靜態的文本轉向了對史詩的唱敘群體、程式、創編、演述語境、交互指涉、流布與變異、史詩與民俗信仰的互滲等議題的綜合研究,形成多學科的延展觀察,探索《密洛陀》的表達系統,揭示其創編和傳承規律以及其作為活形態史詩的諸多體裁樣式的社會文化意義,豐富、檢驗甚至修正以印歐語系為研究對象而抽象出來的口頭詩學理論,為中國史詩學學科建設添磚加瓦。 二是通過對《密洛陀》的研究探尋瑤族文化的底色,從史詩文脈之根中尋找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和新時期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的根基,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文化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學理支持。
四、結語
瑤族在歷史上遷徙十分頻繁,因而形成現如今居住分散、語言差異極大、風俗習慣不同、支系繁多的“民族共同體”。 布努瑤是瑤族的第二大支系,由于封建統治者的迫害和民族歧視、民族紛爭等原因,長期在石山地區過著顛沛流離的游耕生活,被認為是歷史上遷徙時間最長、“受苦最深、受難最重”的瑤族支系,解放前還一度被視為“末開化的特種部族”。②但在每一個苦難、困境面前,布努瑤都高唱古歌,堅信密洛陀能幫助他們走出險境、絕境,通達新的人間樂土。 正是依靠世代傳唱《密洛陀》,布努瑤構筑了共同的族群記憶、精神寄托和抗爭支撐,頑強地保留了民族凝聚力和族性。
作為神話、傳說史詩化的成果,《密洛陀》的文本化過程,既是瑤族民間文學的發展史,也是20 世紀50-60 年代以來中國少數民族史詩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映射。[32]隨著民族史詩研究南北格局的確立,中國少數民族史詩搜集整理和研究正進入學理反思階段,中國史詩研究的學科化和制度化正在有序推進。[33]今后《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應當充分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盡快彌補短板與不足,在理論和方法上自覺與國內外史詩學接軌,彰顯出《密洛陀》的學術價值和獨特貢獻。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和重大的課題,需要《密洛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注釋:
①所謂宗教語,主要是指瑤族巫公在驅神趕鬼的宗教場合唱述《密洛陀》所使用的歌唱語言。 布努瑤除日常交際語言外,還創造出三種歌唱語言,分別是宗教語言、樂歌語言和愛戀歌語言。 宗教語,布努瑤民間稱之為“鬼語”,主要是用古漢語詞和古瑤族詞以及少量其他民族的語詞混合構成其詞匯的,特點是一詞多音。 比如,在宗教語中,“密洛陀”的稱謂是“密本洛西·密陽洛陀”。 樂歌語言只限于喜慶場合使用,主要涉及歷史題材的歌,包括密洛陀歌、族史歌、開親史歌等,語言的構成成分是古瑤語和古壯語。 愛戀歌語言是布努瑤年輕人用來唱愛戀歌的語言,民間叫“撒旺”,是樂歌語言語匯和布努瑤交際語言詞匯混合在一起的歌唱語言。 三種語言中,宗教語最古老,最難掌握,所以過去一名巫公的培養,從他幾歲就開始跟著長輩出門看、學、唱、做宗教法事活動,直到十七、八歲才能完全掌握這種語言和各種法事活動。 外來學者如要搜集整理《密洛陀》,必須有懂宗教語的布努瑤學者或會漢語的巫公協助才能順利完成。
②1930 年代中期以后,廣西省政府對尚未與漢族“同化”的瑤、苗、侗及少數壯族等所謂“特種部族”進行“開化”,以期實現少數民族“同化”于漢族。 在都安,“化瑤”成為“開化”政策實施的重點(彼時苗瑤不分)。 《都安縣志稿·民國》(由都安縣縣志辦整理,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出版)第183 頁“特種教育”記載:“本縣漢苗雜處,歷有年所。 惟苗(大部分實為瑤族)與漢言語隔閡,不相往來,故其生活習慣,均與漢人(大部分實為已“同化”的壯族)異。 政府迭令遣子弟入校讀書,以其同化,惟苗人視學校為畏途,結果很少識字興趣。 民廿九年調查有特種部族雜居十鄉,共三十二村。 令其無分畛域種族,悉施以國民教育。 惟師資缺乏,收效很少,幸得桂嶺師范學校招生,政府考送特種部族優秀之人計二十五名,自行前往投考,取得肄業學位者不下廿十人,先后畢業回籍,服務鄉校間及縣府統計室,引起苗人求學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