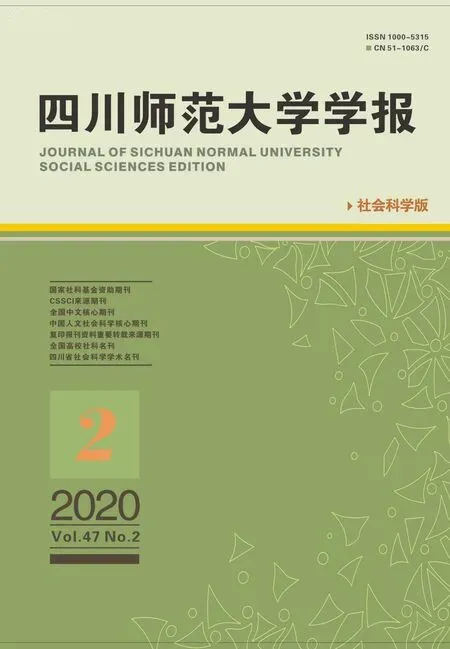清末民初的小說讀者及其對語體的選擇
莊 逸 云
(四川師范大學 文學院,成都610066)
在清末民初,隨著城市的發展、市民人口的增長及文化市場的擴大,加之特定社會思潮的推波助瀾,市場對于小說的需求量與日俱增,小說讀者也就成為影響小說創作與生產愈來愈重要的因素。目前學界在近代或晚清小說的研究中,對讀者問題越來越關注,已有較多論文談及讀者對小說的編輯、創作、翻譯和傳播的影響。但是,真正聚焦于小說讀者本身、探討當時小說讀者的具體構成和因時而發生的變化等,這方面的研究還較薄弱。①立足于晚清小說讀者,探討其構成或變化的文章,如:袁進《試論晚清小說讀者的變化》,《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1期;王姍萍《西學東漸與晚清小說讀者的變化》,《西安外事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但二文僅論晚清,不及民初,且對晚清小說讀者問題的討論仍不夠全面深入。此外,讀者的知識結構、文化層次、閱讀心理不僅影響到小說文本的內容與表現形式,還深刻影響到了作品的語體。②“語體”是語言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語體是運用全民語言選擇語言材料所形成的語言特點體系或語言特點綜合,也是民族標準語經由歷史演變而形成的幾種相對穩定的語言功能風格類型。(李熙宗《關于語體的定義問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當然,關于“語體”一詞的定義,語言學界因其側重不同,仍有所紛歧,茲不贅引。本文所討論的“語體”,具體指小說采用的是白話語體還是文言語體的問題。可以說,清末民初每一個階段對小說語體的整體選擇,都離不開對小說讀者的考量。關于清末民初讀者與小說語體這二者之間的關系,目前學界亦鮮少有專文探討。基于此,本文以1872年申報館的創立作為清末民初的起始點,擬將1872年至1919年間的小說讀者及其對語體的選擇分為三個階段,加以具體考察。
一 1872-1894年:城市人口的增長與士大夫作為小說讀者
近代城市的崛起,可以上海為代表,近代小說的產生,也主要集中于上海,因此若要剖析小說與讀者之關系,上海是足以作為研究典型的。從1843年開埠到20世紀初,上海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繁華的大都會。上海的繁華也屢屢見諸于時人的筆下,如晚清小說家李伯元在小說《海天鴻雪記》中描述:“上海一埠,自從通商以來,世界繁華,日新月盛,北自楊樹浦,南至十六鋪,沿著黃浦江,岸上的煤氣燈、電燈,夜間望去,竟是一條火龍一般。福州路一帶,曲院勾欄鱗次櫛比,一到夜來,酒肉熏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這個地方,覺得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情,無有過于爭逐者。正是說不盡的標新炫異,醉紙迷金。”①《李伯元全集》第3冊,薛正興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城市的發展必然使得城市人口即市民的數量增加。19世紀初,中國的城市人口約有1200萬,占當時中國3.5億總人口的3%-4%。20世紀初,城市人口增長至1680萬,占當時4.3億總人口的4%-5%,城市人口的年增長率約為1.4%,高于約0.8%的總人口年增長率。盡管從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這一百年間,城市人口的增幅不算大,但其穩定增長的趨勢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19世紀后半期,城市人口的增長率有顯著提升。而在1900年至1938年之間,城市人口的增長更是明顯加快,其增長率幾乎是總人口增長率的兩倍。②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6、37頁。就上海市而言,1865年,英、美公共租界有9萬多人,法租界有5萬多人,到189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是24萬多,法租界是5萬多,加上華界,共有80多萬人口。而到1900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增加至35萬多,法租界增加至9萬多,加上華界,上海的城市居民已經達到100多萬人。③袁進《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頁。城市人口的增長勢必導致消費市場的擴大,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也會進一步拓展消費市場。在類似上海這樣以商業和工業為主導的城市中,人們的作息不再受制于節氣或晝夜等自然條件,而是有了更明晰和固定的工作與休閑時間。街燈的設置、煤氣燈及后來電燈的普及,也在客觀上延長了人們的休閑時間。此外,在市場謀生方式下,人們的收入也不見得與投入的勞動時間和勞動量發生必然的關系,因此娛樂休閑活動很有可能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在以上海為龍頭的大城市中,出現了一個日漸增長的消費群體和日漸擴大的消費市場,他們的消費需求當然也包括了書籍、報刊特別是小說這一類的文化消費品。自1872年申報館的成立伊始,一些大型的近代出版機構的創立、報紙副刊及小說期刊的發行、小說單行本的出版等,皆是因應了這一文化市場的需求,讀者的閱讀需要成為影響這些出版物的重要因素。1872年至1894年,小說的發展尚未受到社會思潮和文學運動的強勢影響,在該階段,小說讀者的閱讀需求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休閑娛樂需求成為多數出版者考量的重要因素。1897年,李伯元創辦《游戲報》,特設“記注倡優起居欄”,且為妓界“開花榜”,在十里洋場引發熱議,大受追捧。《游戲報》的熱銷引起多家報紙效仿,上海每天均有十余種小報同時發行,以迎合讀者低層級的文化消費心理。1872年至1894年間,小說讀者的構成、報刊對小說讀者的定位,可以《申報》為例略窺一二:“至于稗官小說,代有傳書。若張華志博物,干寶記搜神,齊諧為志怪之書,虞初為文章之選,凡茲諸例,均可流觀。維其事則荒誕無稽,其文則典贍有則,是僅能助儒者之清談,未必為雅俗所共賞。求其記述當今時事,文則質而不俚,事則簡而能詳,上而學士大夫,下及農工商賈,皆能通曉者,則莫如新聞紙之善矣。”④《發刊詞》,《申報》1872年4月30日,創刊號。這段文字說明,《申報》預期的讀者是“上而學士大夫,下及農工商賈”,幾乎涵蓋社會的各個階層。《申報》在創辦之初,試圖通過“記述當今時事,文則質而不俚,事則簡而能詳”的辦報風格,吸引各階層人士訂閱該報,從而爭取利潤的最大化。生活于城市下層的流民、工人、小商販不是沒有訂閱報刊的可能性,如清末有人談及:“自有《申報》以來,市肆之傭夥,多于執業之暇,手執一紙讀之。中國就賈之童,大都識字無多,文義未達。得《申報》而讀之,日積月累,文義自然粗通,其高者兼可稍知世界各國之近事。鄉曲士人,未必能舉世界各國之名號,而上海商店傭夥,則類能言之,不詫為海外奇談。”⑤姚鵬圖《論白話小說》,《廣益叢報》第65號,1905年。但整體而言,“農工商賈”中的“農工”訂閱《申報》的數量應該不大,《申報·發刊詞》中的內容及文字表述本身便不是一般的“農工”所能理解的,所以《申報》事實上的讀者主要還是包括“學士大夫”及部分商賈在內的社會中上層人士。如:1877年11月21日,針對署名“寓滬遠客”者在《申報》上刊登的照圖編撰小說的啟事,《申報》特地配發了題為《書請撰小說后》的評論:“近來稗官小說幾于汗牛充棟,然文人同此心、同此筆而所撰之書各不相同,實足以開拓心胸,為消閑之一助。但所閱諸小說,其卷首或有圖,或無圖,從未專有圖而無說者。茲見本報后寓滬遠客所登之請撰小說告白,似即征詩征文之遺意,文人雅士于酒后睡余,大可藉此消遣工夫,行見奇情狀采奔赴腕下,而諸同人又得擊節欣賞矣。”①《書請撰小說后》,《申報》1877年11月21日,第1712號。這段文字透露出《申報》對當時的小說作者及讀者身份的更為清晰的認識,即小說的撰述者為“文人雅士”,其撰述目的乃“藉此消遣”、展露“奇情狀采”,而小說的讀者是同為文人雅士的“諸同人”。
身為學士大夫的讀者,他們自來的閱讀傳統是,既要讀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話小說,也要讀隸屬于子部的文言小說,因此申報館在出版小說時,亦并未流露出對特定語體的偏好或倚重,其所出版的文言小說的數量略多于白話小說,但大體上二者的數量是持平的。如1877年申報館所刊《申報館書目》,其中列入“新奇說部類”的文言小說共計14種,列入“章回小說類”的白話小說共計7種;1879年申報館所刊《申報館書目續集總目》,其中列入“說部類”的文言小說共計5種,列入“小說類”的白話小說共計5種;兩年的書目合計,申報館共出版文言小說19種,白話小說12種。②據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統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198頁。另據陳大康先生統計,咸豐元年(1851)至光緒二十年(1894)這四十年里,出版了文言小說共計71種,白話小說共計53種。③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前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兩組數據對比,可以看出,在1895年前,選擇白話或文言來寫小說的問題并未受到外力的沖擊,文人學士作為小說讀者的主體,基本上還是秉承了舊有的閱讀習慣,并未對小說的語體問題產生群體的關注自覺。文言小說的數量略高于白話小說,或基于文言小說多筆記性質,有增進學識之功效。另外,從1872年申報館成立到1879年《申報館書目續集總目》的刊印,申報館在這數年間的年均小說出版量約為4種,這個數字高于過去年均1至2種的小說刊印種數。這說明,隨著城市的發展,文化市場對小說的需求是在逐漸增加的。
二 1895-1911年:士大夫成為小說讀者的絕對主力
1894年后,因中日甲午戰爭及戊戌變法等系列大事件的發生,知識分子大力倡導白話文運動,并從改良社會的角度提倡小說,以引導文化消費市場,英人傅蘭雅在1895年的《申報》上刊登“求著時新小說啟”,嚴復、夏曾佑在1897年的《國聞報》上發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皆可視為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先聲。1902年的小說界革命更是極大地刺激了白話小說的興盛。1902年至1911年是小說的生產突飛猛進的時期,當時的小說作者和出版者們往往將“中人以下”、“愚氓”、“婦女與粗人”等視為期待讀者,如商務印書館主人在《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中稱“借思開化夫下愚,遑計貽譏于大雅”④商務印書館主人《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繡像小說》1903年第1期。。那么,這一時期事實上的小說讀者真的是所謂“愚民”嗎?當然不是。1908年徐念慈在《小說林》上撰文,十分明確地指出:“余約計今之購小說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說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學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歡迎新小說者,未知滿百分之一否也?”⑤徐念慈《余之小說觀》,《小說林》1908年總第10期。作為當時人及《小說林》的主編,徐念慈的這段話自然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因此也廣受征引。據其統計,當時的小說讀者百分之九十是所謂“出于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說者”,即以舊學為根基又接受了新知的士大夫,或曰士紳。這個看法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有學者認為,在上海這樣的近代城市中,市民群體的構成大致如下。1.資本家,主要來源于買辦、進出口貿易商以及本籍和外地移居的紳商。2.職員,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憑籍新式職業謀生的市民階層;舊式職業從業人員的轉型;20世紀20年代后,成批接受過近代教育的青年被納入各種社會職業。3.產業工人,主要來源于農民,市民和熟練的手工業工人只占極少數,是一個由鄉民匯集而成的市民群體。4.苦力,主要指蘇北逃荒來滬的農民,帶有明顯的地域色彩。⑥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政治社會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5-587頁。當然這個分析未見得全面,比如政府官員、家庭主婦、尚未進入職場的學生,也應隸屬于市民群體。在清末民初的市民群體中,士紳階層的分化又無疑是其重要的來源。“紳為一邑之望,士為四民之首”,原本在封建社會具有重要社會地位的士紳在進入近代社會后,出現分化,“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紳商,從而成為市民群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紳商,就是指紳與商兩者合流之后產生的一個新的社會群體”①陶鶴山《論中國近代市民群體的產生和發展》,《東方論壇》1998年第4期。。除了轉化為商人和資本家,傳統士紳階層中還有相當一部分轉化為近代新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編輯、記者、醫生、律師、學校教員等,也即成為憑借新式職業謀生的市民階層。不難看出,在近代市民群體的四大構成中,紳商和相當一部分的職員都是出自傳統的士紳,而其文化素養也正是如徐念慈所概括的“出于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說”。這部分人士關心時局、有變革社會的意愿,他們一改過去視小說為小道末技的觀念,開始熱衷于寫作和閱讀小說。時人曾談及小說受文人追捧的現象:“嗟乎!昔之以讀小說為廢時失事、誤人心術者,今則書肆之中,小說之銷場,百倍于群書。昔之墨客文人,范圍于經傳,拘守夫繩尺,而今之所謂小說家者,如天馬行空,隱然于文壇上獨翹一幟。觀閱者之所趨,而知著者之所萃。盛矣哉其小說乎!”②黃世仲《小說風尚之進步以翻譯說部為風氣之先》,《中外小說林》1908年第2卷第4期。在近代城市中,曾經的士紳們雖然已經轉化為市民群體中的紳商或編輯、記者等角色,其生存方式發生了較大變化,但其關注國是的傳統與過去一脈相承,他們視小說為改良社會的利器,從而成為清末民初小說讀者的一個重要構成,在小說讀者中所占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袁進先生提出:“小說市場的擴大主要不是由于市民人數的增加,而是在原有市民內部,擴大了小說市場。換句話說,也就是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說作者與讀者的隊伍,從而造成小說市場的急劇膨脹。”③袁進《試論晚清小說讀者的變化》,《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1期。市民人數客觀上在逐年增加,這一點前文已有分析;但認為大量士大夫的加入,成為小說市場急劇膨脹的重要原因,這一論斷是很精辟的。
除了士大夫們熱衷于閱讀小說外,當然也不乏“普通之人物”閱讀小說,只是在小說讀者中所占比例僅為百分之九,數量遠遠低于士大夫。徐念慈所謂的“普通之人物”大抵包括學徒、工人、商販或部分職員等。這部分人士盡管文化素養普遍不高,但對小說中之言語淺俗者還是有閱讀欲望的。1905年姚鵬圖談到,“自有《申報》以來,市肆之傭夥,多于執業之暇,手執一紙讀之”④姚鵬圖《論白話小說》,《廣益叢報》第65號,1905年。,這段話雖是針對《申報》而談,其實報刊所載小說在這部分人群中的接受情況,也大致可以依此類推。比如清末民初著名的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少年時曾為鐘表店學徒,“十二歲時,得《福爾摩斯探案集》讀之,浸淫其中,寢饋俱廢,一若別具慧心者”⑤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香港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469頁。。事實上,文化程度不太高的普通市民向來就是通俗小說的閱讀者,他們被稱為“里耳”,以與士大夫的“文心”相對應,馮夢龍編“三言”,就以普通人為訴求對象,“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為一刻”⑥馮夢龍《喻世明言·敘》,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2頁。。在清末,這個讀者群仍然是存在的,只是他們的人數有限,購買力遠不如士大夫,對新小說的格調也較難適應,所以算不上小說讀者的主力。
徐念慈所提到的第三類人群“其真受學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者”,即所謂新式學堂學生或以學生出身的人士,在他看來,這部分人群在小說讀者中所占的比例更小,可能不足百分之一。事實上,當時的學堂建設尚未全備、學生尚在成長中,這可能是學生在小說讀者中所占比例甚小的重要原因。近代學堂的興起可追溯至洋務運動時期,當時中國出現了最早的一批新式學校,近20所。百日維新時期,頒布了設立京師大學堂,籌辦高、中、小各級學堂,改各省會書院為高等學堂等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但因變法的失敗,措施未能得以真正落實。所以,直到19世紀末,新式學堂仍較稀少。據周作人回憶:“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國還沒有中學校。”“那時候還沒有中學校,但是類似的教育機關也已有了幾處,不過很是特別,名稱仍舊是‘書院’,有如杭州的求是書院,南京的格致書院,教的是一般自然科學……幸而在這些文書院之外,還有幾個武學堂,都是公費供給,而且還有每月津貼的‘贍銀’。”⑦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頁。魯迅出生于1881年,若以1891年至1898年算魯迅的“青年時代”,那么這個時期中國的新式學堂是很匱乏的。直到20世紀初期,近代學堂才開始大量興起。1901年9月,清廷諭令建各級學堂,“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①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776頁。,1905年清廷諭令自1906年起廢止科舉制度,更是為近代學堂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到1908年徐念慈撰文分析小說讀者的構成之時,學堂的發展已較為可觀。據王笛先生統計,近代學堂的數量1903年為769所,1904年為4476所,1905年為8277所,1906年為23862所,1907年為37888所,1908年為47995所;學生人數1902年為8912人,1903年為31428人,1904年為99475人,1905年為258873人,1906年為545338人,1907年為1024988人,1908年為1300739人,其增速不可謂不快。②王笛《清末近代學堂和學生數量》,《史學月刊》1986年第2期。但就整體而言,新式學堂的建設時間甚短,其發展不可能在短短數年間趨于全備,所培養的學生尚在成長中。譬如清廷在1902年3月頒布的上諭中稱:“前經通飭各省開辦學堂,并因經費難籌,復諭令仿照山東所擬章程,先行舉辦。迄今數月,各該省如何辦理,多未奏復。即間有奏到,亦未能詳細切實。該督撫等身膺重寄,目擊時艱,當知變法求才,實為當今急務。其各懍遵迭次諭旨,妥速籌畫,實力奉行。即將開辦情形,詳細具奏。如再觀望遷延,敷衍塞責,咎有攸歸,不能為該督撫等寬也。”③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第779頁。于此可以看出,在興辦學堂的過程中,存在諸多的阻力和困難。另外,在上述諸年份的學生人數中,尚有相當部分是小學生,如小學生人數1903年為22866人,1904年為85213人,1905年為173847人,1906年為481659人④王笛《清末近代學堂和學生數量》,《史學月刊》1986年第2期。。所以綜合來看,晚清時期“有思想、有才力、歡迎新小說的學生不足百分之一”的判斷大致是切合實際的。
三 1912-1919年:學生成為小說讀者的生力軍
1912年進入民國后,中國城市的近代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從1912年至1949年,中國人口幾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長,城市人口的增長率可能達到2%。1913年,中資工廠有698家,擁有工人270717名;1920年,中資工廠有1759家,擁有工人557622名。在民國的前十年間,外資和中外合資的企業也有增加,投資增長最快的時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后的幾年。⑤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第59、45頁。
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民群體進一步壯大,小說讀者的數量當然也隨之增加。關于1912年至1919年間小說讀者的構成,1919年刊載于《小說新報》的一封讀者來信有所提及:“購讀新小說者,以何如人占其大多數?林下士,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學校青年,其三也;農商界及下等社會所讀者,必非新小說。”⑥“讀者來信”,《小說新報》1919年第5卷第7期。這封信件中的分析頗為粗略,且未見得妥當,如“農商界及下等社會”未必不讀小說,事實上,商界中的部分商人、公司職員,下等社會中如部分商販、店鋪伙計、工人等,很可能是要讀小說的,而且隨著工商業的發展,這一群體在日益壯大,他們對文化消費品的需求也是與日俱增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隸屬于所謂“下等社會”的產業工人的人口基數雖然在快速增長,但對他們作為小說讀者的數量還是不宜過高估計。1928年,在對上海978位工人的受教育程度的調查中,不讀書的男子占男子總人數57.7%,不讀書的女子占女子總人數98%⑦劉明逵《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1卷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51頁。,民初時期,工人群體的文盲率應該更高。
該讀者來信將林下士、世家子女、學校青年視為小說讀者的主力軍,還是很有道理的。所謂林下士,即文人學士或曰士紳,近代城市中的官員、紳商、編輯、記者、教員、醫生等知識分子群體皆可隸屬于林下士,其知識結構也大體如徐念慈所說,是“出于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說者”。1915年梁啟超曾感嘆:“舉國士大夫不悅學之結果,《三傳》束閣,《論語》當薪,歐美新學,僅淺嘗焉為口耳之具,其偶有執卷,舍小說外殆無良伴。”⑧梁啟超《告小說家》,《中華小說界》1915年第2卷第1期。這雖是批判之語,但無疑說明了民初時期士大夫對小說的閱讀熱情。
上述讀者來信中提到的世家子女與學校青年皆可歸為學生這個群體。相較于清末,民初學堂和學生的數量增長更快,1908年學堂為47995所,學生人數為1300739人,到了1912年,學堂數已達87272所,學生人數則上升至2933387人①王笛《清末近代學堂和學生數量》,《史學月刊》1986年第2期。,增幅接近一倍。當時的學生加上赴海外留學者,人數應該更多。到1919年,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都已發展到十分可觀的程度。沈從文在《從文自傳》中回憶:“民三左右地方新式小學成立,民四我進了新式小學。”②沈從文《從文自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頁。偏遠如湖南湘西一帶,在民國三、四年亦有了新式學校,據此可管窺近代學堂在民初的蓬勃發展。經過十余年的建設,近代學堂的規模不僅增大、學制在探索中日趨成熟,如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在《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中就規定了教育改革的若干措施,包括“從前各項學堂,均改稱為學校”、“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等③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3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相應地,學生對新知及西學的渴求與相關素養也都有所提升。在民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十年間,學生成為小說讀者的一個重要構成,在小說讀者中所占比例較之清末肯定有大幅的上升。以晚清小說界之巨擘林琴南的翻譯小說為例,自1899年首部林譯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問世以來,清末民初的廣大學子就成了他的忠實讀者。如魯迅兄弟在日本留學時,林譯小說一出版,二人必定購買:“我們對于‘林譯小說’有那么的熱心,只要他印出一部,來到東京,便一定跑到神田中國書林,去把它買來,看過之后魯迅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硬紙板書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④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頁。郭沫若說,林譯小說是他少年時代“嗜好的一種讀物”,他讀的第一部外國小說正是林紓翻譯的《迦茵小傳》。⑤郭沫若《少年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頁。廬隱稱,林譯小說她“幾乎都看過了”。⑥閻純德《五四的產兒——廬隱》,《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冰心則是十一歲時就被林紓翻譯的《茶花女》所吸引,這成為她以后“竭力搜奇”林譯小說的開始,也是她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⑦冰心《憶讀書》,《冰心選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頁。郭沫若生于1892年,廬隱生于1898年,冰心生于1900年,林譯小說風行時,他們正處于少年求學階段。
四 清末民初讀者對小說語體的選擇
概言之,從1872年到1919年這近五十年間,小說讀者的變化主要呈現出如下特點:其一,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小說讀者的總人數也一直在相應地增長;其二,分布于多個職業領域的士大夫或曰士紳一直是閱讀小說的主力軍,尤其在1902年小說界革命之后,大量的文人學士加入到小說讀者的隊伍,造成了小說市場的急劇膨脹;其三,進入民國后,近代學校所培養的學生人數增加、文化素養提高,他們成為小說讀者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其四,所謂的“農商界及下等社會”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小說讀者群,雖難以精確估計他們的構成及人數,但其人數民初較清末肯定有所增長,他們對民初小說消遣性、娛樂性特點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
在清末民初,既然大量的文人學士或曰士大夫加入到了讀者隊伍,那么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必然會給小說帶來強勢影響,小說因此而發生的最明顯的變化,當屬語言。1895年前,并無驟然而起的文藝思潮波及小說,士大夫作為主要的小說讀者,對語言亦無特定的要求,不過是延續了過往的閱讀傳統,即在私底下既讀文言小說,也讀白話小說,在觀念上對帶有筆記性質的文言小說更看重一些。此時期的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在數量上相差不大。1895年后,白話文運動逐漸興起,1902年小說界革命發生,小說界大都視下層百姓為假想讀者,所以一時間白話小說大為繁興。以晚清四大小說期刊為例,在它們所刊載的創作類小說中,白話小說的比例都超過了70%;《繡像小說》尤甚,該刊一共72號,刊載創作類小說18種,其中白話小說17種,文言小說僅1種。⑧莊逸云《清末民初文言小說史·前言》,復旦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5頁。不過,小說界很快即認識到小說讀者的真正主力并不是下層百姓,而是士大夫,他們的閱讀需求和品位才是最應該也最值得考量的因素。當時的士大夫們雖以各種渠道接受了新知的一些熏陶,但舊學畢竟是其思想的根基,傳統學養已深入其骨髓,一旦小說的地位上升、成為“文學”之一種了,他們必然會思考小說的語言問題,長期以來形成的雅俗觀念和閱讀習慣都使得他們更青睞文言。1908年,徐念慈很清楚地指出:“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之二者,就今日實際上觀之,則文言小說之銷行,較之白話小說為優。”①徐念慈《余之小說觀》,《小說林》1908年總第10期。徐念慈主要是從士大夫的知識結構、鑒賞能力的角度分析了文言小說更為熱銷的原因,其實除了這方面的因素,作為主要讀者的士大夫也往往容易受社會思潮的影響,自1905年左右就漸興的復古思潮大力主張文言為國粹、倡導保存和捍衛文言文學,這無疑助長了士大夫們對于文言語體的選擇。
進入民國后,士大夫仍然是小說讀者的主要來源,他們的需求和品位繼續在強勢影響小說的語體選擇。除此,學生及學生出身者成了小說讀者的另一大來源,不過這一時期的學生依然頗具舊學的根基,他們也習慣于文言文學的閱讀和寫作。學生出身者如魯迅,他于1898年至1901年在南京的礦路學堂學習,但在進入新式學堂前,他已接受了頗為完整的舊學的熏陶與訓練。十四歲時,他前往私塾三味書屋求學,十六歲前已將四書五經讀完,又讀了《爾雅》《周禮》《儀禮》等。經書讀完,他在私塾先生的指導下,學寫八股文及試帖詩,以備科舉考試。至于因個人興趣所致而閱讀的舊籍,包括《古詩源》《古文苑》《六朝文絜》《周濂溪集》《二酉堂叢書》《酉陽雜俎》《閱微草堂筆記》《淞隱漫錄》等,則難以枚舉。②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第23、29、42頁。魯迅在私塾里所受到的一般性的訓練可以代表與他年紀相當或者年紀更大的一批人,在這樣的熏陶下,閱讀與喜愛文言文學幾乎是根深蒂固的習慣,五四前魯迅寫作與翻譯小說皆是使用文言就說明了這一點。至于出生較魯迅晚一些的清末民初學子,也有相當的舊學素養。清末存古學堂的學生需在長達七年的學制里窮研經書、博覽史傳、練習詩文詞章,就是一般性的學堂,清廷亦規定“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③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第776頁。。清末出生的一批人在這樣的教學內容的熏陶下,舊學的修養自然得到了相當的積累。進入民國后,因復古思潮的盛行,他們的舊學根基事實上獲得了進一步的涵容和滋養。民國政府雖在1912年宣布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但很快又在中小學校恢復了讀經科目。1915年1月袁世凱在《特定教育綱要》中規定:小學生需讀《孟子》《論語》;中學生需選讀《禮記》《左傳》;在大學校外獨立建設經學院,各省亦設立經學會,以為講求經學及養成經學教員之所。此外,在民國元年教育部所頒布的《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中,可以看到小學校的國文一科基本上占了每周一半的學時。④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3輯上冊,第48、52、53頁。這樣的文化氛圍為文言文學的盛行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學生及學生出身者歡迎包括文言小說在內的文言文學,勢在難免。有文人回憶民初小說界的情況:“那時候小說的作風,不是桐城古文,便是章回體的演義,《玉梨魂》以半駢半散的文體出現,以詞華勝,確能一新眼界。雖然我前面曾經說過,文格不高,但在學校課本正盛行《古文評注》、《秋水軒尺牘》的時代,《玉梨魂》恰好適合一般淺學青年的脾胃。時勢造英雄,徐枕亞的成名,是有他的時代背景的。”⑤杰克《狀元女婿徐枕亞》,香港《萬象》1975年第1期,轉引自:范伯群《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上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頁。這一段話在總結駢文小說《玉梨魂》的暢銷原因時,明確提到讀者為“一般淺學青年”即學生,而在他們的學校教材中,《古文評注》、《秋水軒尺牘》都是學習內容。學生作為主要讀者之一,其受教育背景使得他們對文言小說頗具好感。較之晚清,民初出版界的商業性更重、更重視市場導向,在讀者趣味的引導下,民初的小說期刊大都偏愛刊載文言小說。就《小說月報》《小說叢報》《禮拜六》《民權素》《小說新報》這幾種最具代表性的民初小說期刊而言,其所載文言小說的比例都在85%以上。⑥莊逸云《清末民初文言小說史·前言》,第6-8頁。
總之,最遲從1908年開始到1919年,文言小說熱銷、其數量和影響遠遠超過白話小說,究其原因,士大夫與學生成為主要的小說讀者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當然,這兩類人群也最易調整其審美取向,因時而變,這是五四白話文運動能成功推行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