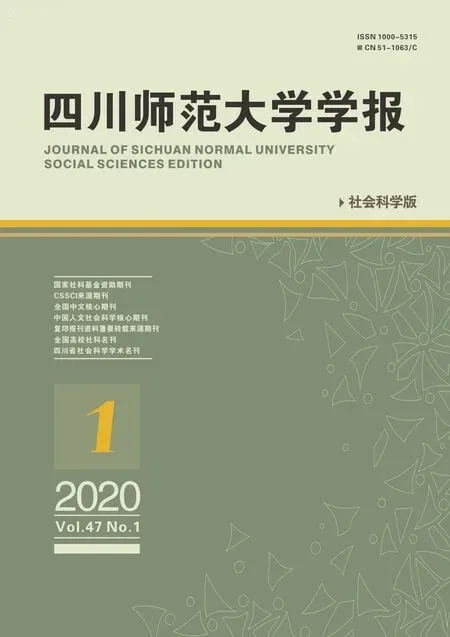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創作的影響
鄒 朝 斌
(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
陰陽五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骨架,它源遠流長且影響極廣。西漢董仲舒總結發展前人之說,將陰陽、四時、五行統攝于“天”之下而形成一個世界圖式,把自然現象、社會歷史、道德人倫都納入這個世界圖式之中加以闡釋,使陰陽五行思想變得更加完備而開始盛行。其后,東漢章帝為統一經義而召開白虎觀會議,班固奉命作《白虎通》,其中有《五行》一篇,從而使陰陽五行思想官方化。《漢書》與《后漢書》中亦列《五行志》,足見陰陽五行思想在漢代影響之盛。正如顧頡剛所言:“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陰陽五行。無論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學術上,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其結果,有陰陽之說以統轄天地、晝夜、男女等自然現象,以及尊卑、動靜、剛柔等抽象觀念;有五行之說,以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與其作用統轄時令、方向、神靈、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統和國家的制度。”(1)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作為漢代人的思想骨干,陰陽五行影響到社會人生的各個方面,也勢必影響到文學創作,特別是作為一代之文學的漢賦創作。學界對陰陽五行思想的研究已取得諸多成果,而對陰陽五行思想與漢賦之關系的研究甚少,且缺乏從漢賦文本內部出發探討陰陽五行思想影響的視角。目前,學界對陰陽五行思想與漢賦關系的研究僅有韓雪《論鄒衍對漢賦的影響——漢賦探源》《關于漢大賦與陰陽五行說關系的兩點補充》兩文,從鄒衍書與漢大賦在內容與形式上的雷同、漢代賦家的思想淵源、漢大賦產生的時間地點等方面對陰陽五行思想影響漢大賦作了初步探討(2)韓雪《論鄒衍對漢賦的影響——漢賦探源》,《社會科學輯刊》1987年第6期;韓雪《關于漢大賦與陰陽五行說關系的兩點補充》,《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但缺乏對漢賦文本的具體分析,論證過程亦有牽強之處。孫晶《陰陽五行學說與漢代騷體賦的空間建構》一文則探討了陰陽五行思想對漢代騷體賦空間建構的影響(3)孫晶《陰陽五行學說與漢代騷體賦的空間建構》,《齊魯學刊》2004年第3期。,頗有見地,但僅就騷體賦空間建構這一方面而言。可以說,目前還未有專文對陰陽五行思想如何影響漢賦作比較全面的探討。有鑒于此,本文即抉隱索微,試圖從共時性(4)所謂“共時性”,指的是本文的研究角度,與“歷時性”相對而言。本文研究從“共時性”角度出發,即將兩漢數百年視為相對靜態的時間維度,在此維度內研究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創作的整體影響。而非從歷時性角度出發,描述陰陽五行思想在兩漢不同時期的演變情狀及其對漢賦創作的影響。的角度論述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創作的影響,分別揭示陰陽、五行觀念在漢賦文本中的表現,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時間、空間、顏色表述的影響,以及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結構的潛在影響。
一 陰陽、五行觀念在漢賦文本中的表現
(一)陰陽觀及其在漢賦中的表現
陰陽觀念的出現早于五行,從文字上來看,殷商甲骨卜辭中就已經出現了“陰”“陽”二字,但是甲骨文中的“陰”“陽”二字均單獨出現,是對自然現象的描述,并無深意。陰的古字為“”,《說文》:“,云覆日也。從云,今聲。侌,古文省。”段玉裁注曰:“今人陰陽字小篆作昜。者,云覆日。昜者,旗開見日。”(5)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80頁。陽的古字為“昜”,《說文》:“昜,開也。”段注曰:“此陰陽正字也。陰陽行而侌昜廢矣。”(6)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458頁。又《說文》云:“陰,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陽,高明也。”(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738頁。故“陰陽”二字本義當是有無日光的兩種天氣,從有無日光衍生出明與暗、暖與冷的含義,進而與方位的背陰或向陽聯系,有了表示山水之南北的含義。在《詩經》《尚書》以及《周易》卦爻辭中的陰陽二字,多合上述表自然現象之本初義,“商周以前所謂陰陽者不過自然界中一種粗淺微末之現象,絕不含有何等深邃之意義”(8)梁啟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頁。。
春秋時期陰陽觀念有所發展,陰陽由自然現象演變為天所生六氣中的二氣。《左傳·昭公元年》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9)《春秋左傳正義》,杜預注,孔穎達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25頁。可見陰陽開始從具體所感之現象向抽象之概念發展,而且已經出現了將陰陽與四時相配的模糊意識。到了《易傳》,其中體現出來的陰陽觀念已經比較成熟了,將陰陽與《易經》中“”和“”兩個代表不同性質的符號相對應,以此為基礎生發出對宇宙人生的解釋。如《系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0)《周易正義》,王弼注,孔穎達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78頁。《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11)《周易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93-94頁。正如《莊子·天下》所云,“《易》以道陰陽”(12)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062頁。。至此,陰陽已經作為生發出宇宙萬物的二種基本元素而存在,陰陽觀念也逐漸被認作解釋宇宙社會人生的原則規范。
這種具有形而上意義的陰陽觀念對中國古代思想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自然也會在漢賦中表現出來。大體上看,漢賦在內容上主要通過對自然天道與社會人倫兩個方面的描述表現出陰陽觀念。
首先,我們來看漢賦內容中對天道與自然的描述所表現出來的陰陽觀念。如前所述,陰陽被視為形而上的兩種基本元素,用以解釋宇宙天地的形成與自然萬物的生長,這種以陰陽觀念為核心的宇宙天道觀在漢賦中多次出現。如崔骃《達旨》:“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13)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頁。張衡《骷髏賦》:“與陰陽同其流,與元氣合其樸。”(14)佚名《古文苑》,章樵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2頁。蔡邕《筆賦》:“畫乾坤之陰陽,贊宓皇之洪勛。”(15)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929頁。其中的“陰陽”均指宇宙中的陰陽二氣或兩種基本元素,亦可指代天地萬物。陰陽不僅構成宇宙天道,而且通過此消彼長的變化推動其運轉,這在漢賦中亦有描述。如賈誼《鵩鳥賦》:“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云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16)蕭統《文選》,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607頁。以爐喻天地,以工喻造化,以炭喻陰陽,以銅喻萬物,生動形象地描繪出在以陰陽為原動力的運轉推移作用之下,自然與社會中的萬物都在反復激蕩中消長離合,永不停歇。又如《論都賦》:“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17)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388頁。陰陽觀認為萬事萬物都處于不斷的消長變化中,正如《易傳·豐》中說:“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18)《周易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67頁。杜篤在此論述陰陽消長、相互轉化對天道運轉、萬物生長的影響,告誡光武帝要認識到物極必反,因此必須居安思危,仁義與城池兼備。
漢賦中亦有描寫陰陽運轉對自然萬物生長造成影響的內容。如《東京賦》中描寫陰陽平和、萬物順時生長的狀態:“于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19)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24頁。此處“陰陽交和”當指天地之間陰陽二氣此消彼長而達到和諧穩定的狀態,從而使自然界風調雨順、萬物依時生長。假使陰陽之氣不和諧時,自然社會就會失去平衡,災異就會出現。《東京賦》:“馮相觀祲,祈禠禳災。”李善注曰:“《周禮》曰:‘春官宗伯,馮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辨其災祥,以為時候。’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也。’”(20)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06頁。陰陽二氣不和而相侵,漸漸發展成自然與社會中之災,即“祲”,故進行祈福以求除去災害。
其次,我們再來看漢賦內容中對社會與人倫的描述所表現出來的陰陽觀念。漢賦中關于宮室營造的描述明顯體現出陰陽思想的影響。《西都賦》:“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方。”李善注:“《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21)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1頁。《魯靈光殿賦》:“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煙煴。”張銑注:“言此殿包含陰陽元氣以成之。煙煴,元氣之貌。”(22)《六臣注文選》,蕭統編,李善、呂延濟、劉良等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21頁。陰陽思想影響了漢代宮殿的營造觀念,這是賦中出現此類描述的思想基礎。不管是從細處描述未央宮的選址與布局體天象地,東西南北四方都符合陰陽運轉的原則;還是從大處概括靈光殿的形成,含陰陽元氣而成,兩者都能夠“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23)《周易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7頁。。賦中描寫宮殿的內容受陰陽思想影響,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
西漢時期,董仲舒“始推陰陽,為儒者宗”(24)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317頁。,儒家思想與陰陽思想相互交融,故漢賦中諸多涉及倫理綱常的敘述也可見陰陽觀念的影響。如蔡邕《協和婚賦》中論及幽微玄妙的人倫之始:“考邃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脢腓。”(25)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938頁。此處即是以陰陽觀念為統攝,將乾坤、剛柔與夫婦相對應,陰陽在此即指代男女。意謂考察遠古人類之本源,就要觀覽男女倫常之法度,蔡邕在此是以陰陽觀念追溯人倫之始。又如王褒《洞簫賦》先言蟲魚鳥獸聞簫聲尚且深受感染,又說:“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何況是天地陰陽之和,受到倫理道德之教化的人呢!故李善注:“《家語》曰:‘人也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26)蕭統《文選》,李善注,第789頁。在此用陰陽觀念意在闡明“人”有秉賦天地大德、受陰陽交合而生的倫理意義。
其實,陰陽觀念對漢賦內容中自然天道與社會人倫兩個方面的影響并非涇渭分明,漢賦中也會出現陰陽觀念同時影響兩者之處。如賈誼《旱云賦》:“或窈窕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邪而狼戾。”《古文苑》章樵題注云:“在《易》,坎為水,其蘊蒸而上升則為云,溶液而下施則為雨,故《乾》之‘云行雨施’,陰陽和暢也;《屯》之‘密云不雨’,陰陽不和也。在人,則君臣合德而澤加于民,亦猶陰陽和暢而澤被于物。”(27)佚名《古文苑》,章樵注,第69-70頁。很明顯,此處以“陰陽分而不相得”來說明自然界的陰陽不協調造成久旱無雨,其陰陽觀念首先是指向自然天道的。但是,縱觀全賦內容及其創作背景可知,當時政治環境黑暗,賈誼時運不濟,受周勃、灌嬰等人的排擠迫害,又遇大旱,故賦中亦用陰陽不相得來解釋人倫社會中君臣之道不合,從而造成貪邪狼戾之風,而這也成為久旱的原因之一。《旱云賦》以陰陽觀念為出發點,從自然天象、社會人事兩個方面指出不雨的原因。故費振剛說,“文中的陰陽不僅用來解釋云行雨施這個規律,還應用于君臣之道、天人感應方面”(28)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19頁。。
總之,陰陽觀念對漢賦內容的影響可以說是廣且深的,漢賦中涉及的天地之形成、自然之運轉、宮室之營造、人倫之秩序、成敗之法式等內容,都能找出陰陽觀念的痕跡。
(二)五行觀及其在漢賦中的表現
五行觀較之陰陽觀后起,較早對五行進行記載解釋的是《尚書·洪范》: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29)《尚書正義》,孔穎達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88頁。
孔穎達疏曰:“《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30)《尚書正義》,孔穎達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88頁。可知當時的五行指五材,是百姓生活中重要的五種物質資材,也即《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中“天生五材,民并用之”(31)《春秋左傳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997頁。之義,這代表了戰國以前五行的基本含義。
戰國時期五行觀逐漸發展,自戰國初期一直到孟莊時代,儒家系統與《墨子》、《莊子》中均無五行一詞出現,《墨子》中出現的“五行無常勝”一語當是雜采鄒衍之說(32)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附錄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頁。。但是從現存文獻來看,五行觀到戰國后期已經成熟,鄒衍將原來形而下的五種重要生活資材之五行看作是形而上的五行之氣,且將其與此時已經成熟的陰陽觀相結合而形成“五德終始說”。正如張毅先生所說:“只有像鄒衍一樣,將五行說成是五行之氣,才能與陰陽互為表里,形成以四時變遷相配合的五行相生相勝理論。”(33)張毅《陰陽五行與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審美理念》,《南開學報》2001年第4期,第15頁。關于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鄒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34)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848頁。其中“五德轉移”即《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劉歆《七略》所云:“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35)蕭統《文選》,李善注,第287頁。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氣所生發出的五種作用,每一個朝代對應某一五行之氣,等到這個朝代衰敗時,即由另一克制前者之德的五行之氣取而代之。
這種陰陽五行思想主導的歷史運行觀念,在秦漢時期頗為流行,自然也會反映到漢賦中。如《德陽殿賦》:“若炎唐,稽古作先。”(36)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576頁。此處“炎唐”即陶唐氏堯帝,因其在五德循環中被認為屬火德,故稱“炎”。《東京賦》:“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李善注引薛綜注:“赤氏,謂漢火德所統,赤帝熛怒也。”(37)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15頁。費振剛等《全漢賦校注》云:“赤氏:五帝中的南方赤帝。漢朝崇火德,所以尊赤氏。”(38)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705頁。《南都賦》:“曜朱光于白水,會九世而飛榮。”李善注:“朱光,火德也。”(39)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60頁。《魯靈光殿賦》:“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李善注:“言漢盛于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40)蕭統《文選》,李善注,第509頁。以上均是漢賦中涉及五德相應與轉移的內容,言堯帝或漢朝為火德。又如班固《幽通賦》:“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高頊”即傳說中的顓頊帝,《文選》呂延濟注:“玄,水色。高陽氏水德,故云。”(41)《六臣注文選》,蕭統編,李善、呂延濟、劉良等注,第269頁。班固在此敘述自己是顓頊的子孫后代,蘊含顓頊以水德王之義。五德終始說的內容不僅在于五行循環更迭,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循環的過程中,凡是某一五行之德興起,則會出現與之相應的征兆。《呂氏春秋·應同篇》中有被視為鄒衍佚文的以下文字記載: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42)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84頁。
帝王將興,上天必定會顯現出征兆、符命,且這些征兆與符命的五行屬性與將興帝王所屬之德相同,如黃帝以土德興,故有“大螾大螻”之征兆;禹以木德興,故有“草木秋冬不殺”之征兆等等。
漢賦中對這種與五行觀念密切相關的征兆與符命亦有諸多描述。杜篤《論都賦》:“天命有圣,托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勛,斬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43)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386頁。據《漢書·高帝紀》載,高帝初起,夜行澤中,醉斬大蛇,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顏師古注引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后,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44)班固《漢書》,第7-8頁。時人以為秦居西,祠白帝,屬金德,白蛇即象征秦。“斬白蛇”乃赤帝子斬白帝子,為火德勝金德之征兆,故賦中對此符命的描述是完全遵循五德終始說之內容的。漢高祖之后起兵遂以赤色為旗幟的顏色,這在漢賦中也有所描述。《東京賦》:“高祖膺箓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李善注曰:“《春秋命歷引》曰:‘五德之運征符合,膺箓次相代。’……《漢書》,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故曰朱也。”(45)蕭統《文選》,李善注,第96頁。“膺箓”即受符命之義,高祖斬白蛇即是受天命而為君的符命,漢賦中“杖朱旗”亦是其順天命行事的重要表現之一,這也是符合五德終始之說的,自然也是受五行觀念的影響。又如光武帝所受符命在漢賦中也有表現,如《論都賦》:“于時圣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獲助于靈祇。”(46)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388頁。此處圣帝即指光武帝劉秀,他所受的“天人之符”指強華自關中所持的《赤伏符》,《后漢書·光武帝紀上》載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47)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1頁。符命內容之“火為主”亦符合時人以漢為火德的五行觀念。
符命即是天命的代言,既然帝王受天命而建立新的王朝,就要對社會制度革故鼎新,以示對天命的遵循,“改正朔,易服色”就是一種這樣的措施。董仲舒所謂“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48)班固《漢書》,第2518頁。。《漢書·律歷志》亦載:“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49)班固《漢書》,第975頁。而這些改革的內容與五行的順逆也是息息相關的。如秦始皇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故以水德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50)司馬遷《史記》,第306頁。。這種五行觀念下的改革措施在漢賦中亦有表現。如司馬相如《上林賦》:“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李善注引郭璞曰:“變宮室車服,衣尚黑。更以十二月為正,平旦為朔。新其事。”(51)蕭統《文選》,李善注,第377頁。故此處描寫當是武帝太初改歷主土德之前,時人以為漢承秦尚水德的反映。
從以上所述五行觀及其在漢賦中的表現可知,五行觀念大多通過五德終始說在漢賦內容中表現出來,且與劉漢王朝的政治緊密聯系,其中敘述兩漢王朝之建立者——漢高祖與光武帝的事跡特別多(關于高祖的描寫尤甚)。這與陰陽五行思想對兩漢政治影響頗深的歷史現實密切相關,顧頡剛先生《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對此已有詳細論述,在此不贅。
二 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時間、空間、顏色表述的影響
陰陽與五行結合之后,進一步把季節、方位、顏色、音律、味道、帝王、神明等自然社會中的種種事物納入其中而組成一個完整系統的,是《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與《禮記·月令》。董仲舒則總結發展《呂氏春秋》與《禮記》之說,“把陰陽四時五行的氣,認定是天的具體內容,伸向學術、政治、人生的每一個角落,完成了天的哲學大系統,以形成漢代思想的特性”(52)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冊,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頁。,從而使陰陽五行思想變得更加完備而開始盛行。董仲舒認為:“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53)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355頁。他將陰陽、四時、五行統攝于天之下,認為陰陽未分時是合而為一的,再分為陰陽,陰陽分為四時。在此基礎上將時間、空間與陰陽五行相配:
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暖。……至于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于東方……至于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春秋繁露·陰陽終始》)(54)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331-332頁。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春秋繁露·五行對》)(55)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306-307頁。
董仲舒先言陽主春夏,陰主秋冬,再將陰陽分為太陰、少陰、太陽、少陽,在陰陽的消長中與四時、四方相配,又在四時中生出“季夏”,與五行中的“土”相配。這樣就成功地將陰陽、五行、時間、空間完整地對應匹配。這種匹配模式在《白虎通·五行》《漢書·五行志》《后漢書·五行志》中都得到了延續。
(一)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時間、空間表述的影響
將陰陽五行與四時五方相配的陰陽五行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漢賦中關于時間的表述。例如漢賦中對季節的表述,既用陰陽指代,又用顏色指代。如《七發》:“陶陽氣,蕩春心。”(56)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567頁。此處陽即春之義。傅毅《七激》:“陽春后榮,涉秋先彫。”(57)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427頁。張衡《溫泉賦》:“陽春之月,百草萋萋。”(58)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756頁。陰陽五行中陽主春夏,故春亦稱為陽春,以上賦中“陽春”即春季的意思。劉歆《遂初賦》:“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59)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318頁。“覽陰陽”在這里指觀察四季的交替變化。《西京賦》:“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李善注引薛綜注:“陽謂春夏,陰謂秋冬。”(60)蕭統《文選》,李善注,第48頁。以上均是漢賦中用陰陽指代季節的例證。漢賦中又有用顏色指代季節的,詳見下文。
在漢賦的時間表述中,也有用陰陽表示朝夕晝夜的。如《西都賦》:“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劉良注:“言宮殿千門萬戶皆夕閉朝開。夕為陰,朝為陽。”(61)蕭統《六臣注文選》,李善、呂延濟、劉良等注,第31頁。《西京賦》:“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李周翰注:“陽,日也,言光色可以曜日,深邃可以藏陰。”(62)蕭統《六臣注文選》,李善、呂延濟、劉良等注,第47頁。這都是以陰陽指代時間上的朝夕與晝夜。
另外,陰陽五行思想亦影響漢賦中對時間的動態描述,如王褒《洞簫賦》:“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63)蕭統《文選》,李善注,第783頁。此處陰陽變化即指四時變遷、寒暑易節。又如蔡邕《釋誨》:“日南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64)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948頁。這幾句話描繪了一個陰陽五行影響下自然界從冬季到秋季的動態變化過程。“南至”即冬至,《禮記·月令》中與仲冬時節相配的音樂為:“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黃鐘。”(65)《禮記正義》,鄭玄注,孔穎達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382頁。“融風”即東北風,《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66)《禮記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355頁。意謂暖風東來,冰雪融化,萬物復蘇,春季來臨。“蕤賓”之音律則是與仲夏時節相配,此時雖是陽氣盛,但陰氣已微微生成,正如《月令》所載:“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鄭玄注:“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67)《禮記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369-1370頁。故賦中曰“微陰萌”。秋季則是陰氣漸盛,故而蒹葭蒼蒼、露凝而白。
陰陽五行思想也極大地影響了漢賦中關于空間的表述。賦中用陰陽來表示四方的,如《大人賦》:“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68)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119頁。《魯靈光殿賦》:“承明堂于少陽,昭列顯于奎之分野。”(69)蕭統《文選》,李善注,第510頁。少陽、太陰即是董仲舒將陰陽二分為四中的兩者,少陽指東方,太陰指北方。《大人賦》以此指代仙境中的東方極遠之地與北方極遠之地。言其由東極斜渡北極,向真人求取成仙之道。在《魯靈光殿賦》中,靈光殿在魯,魯在東,故稱其為少陽。漢賦中也有以五行來表示方位的,《平樂觀賦》:“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70)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578頁。《西京賦》:“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李善注引薛綜注:“墉,謂城也。絕,度也。言閣道似此山之長遠,橫越西池而度金城也。西方稱之曰金。”(71)蕭統《文選》,李善注,第59頁。《東京賦》:“昭仁惠于崇賢,抗義聲于金商。飛云龍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李善注引薛綜注:“金商,西門名也。……西為金,主義,音為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故立金商門于西。……德陽殿西門稱神虎門。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72)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03頁。以上“金商”“金墉”之“金”皆指代方位之西。其中的“秋方”指代“西方”,出現了以季節指代方位、以時間表述空間的現象。不過,這些都符合陰陽五行思想中五行之金與方位之西、時序之秋對應的原則。
(二)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顏色表述的影響
陰陽五行思想將五行、五時、五方、五色等依次匹配為一個完整的系統,顏色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從而也極大地影響了漢賦中顏色的表述。在此先以《禮記·月令》為例,對陰陽五行思想系統中顏色這一環略加介紹。《月令》中先言時序為春之時,“其日甲乙”,以甲乙名東方,此時“盛德在木”,天子“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故其色尚青(蒼)。時序為夏之時,“其日丙丁”,以丙丁名南方,此時“盛德在火”,天子“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故其色尚朱(赤)。時序為季夏之末時,“中央土,其日戊己”,以戊己名中央,天子“乘大路,駕黃緌,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故其色尚黃。時序為秋之時,“其日庚辛”,以庚辛名西方,此時“盛德在金”,天子“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故其色尚白。時序為冬之時,“其日壬癸”,以壬癸名北方,此時“盛德在水”,天子“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故其色尚玄(黑)。(73)《禮記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352-1381頁。可見在陰陽五行思想中,五時、五方、五行、五色的對應關系為:
春季—東方—木—青(蒼)
夏季—南方—火—朱(赤)
季夏—中央—土—黃
秋季—西方—金—白
冬季—北方—水—玄(黑)
“時序—方位—五行—顏色”的對應體系在陰陽五行思想中得以確立,故在陰陽五行思想影響下,漢賦中存在著大量以顏色來表示方位、五行、時序的現象。例如以顏色詞來表示或暗含方位之義的如下。
青與東方:
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經。(李尤《德陽殿賦》)(74)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576頁。
《太平御覽》卷五三三引《周書·明堂》:“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75)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418頁。故“青陽”指明堂的五室之一,即位于左面東方的叫青陽,此處之“青”即暗含了東方之義。
朱(赤)與南方:
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枚乘《七發》)(76)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569頁。
西蕩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班固《東都賦》)(77)蕭統《文選》,李善注,第35頁。
南游赤野,北泏幽鄉。(張衡《骷髏賦》)(78)佚名《古文苑》,章樵注,第131頁。
《七發》中的“朱汜”指的是南方的水邊。《東都賦》中的“朱垠”,李善注曰:“朱垠,南方也。”《骷髏賦》中的“赤野”,《古文苑》章樵注曰:“極南之地。”以上朱、赤皆指代南方。
黃與中央:
伊黃虛之典度,存斗文之會宮。(黃香《九宮賦》)(79)龔克昌、蘇瑞隆等《兩漢賦評注》,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55頁。
龔克昌解釋“黃虛”曰:“言中央宮,五行在第五,屬土,在九宮居中央。……五方中央神名,也即地神名。土色黃,故云。”(80)龔克昌、蘇瑞隆等《兩漢賦評注》,第557頁。此處言黃虛所常居的中央之位,存在著文昌、斗魁眾星所在的宮闕,所以“黃虛”之“黃”亦暗含了中央方位之義。
白與西方: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臺行乎中野。(張衡《思玄賦》)(81)蕭統《文選》,李善注,第661頁。
《淮南子·地形訓》曰:“八纮之外,乃有八極。……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高誘注曰:“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82)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35-336頁。《淮南子》將西南方向與白相對應,高誘則釋“白門”為位于五行中“金”所生方位,所以此處的“白”在大方向上仍然是指向西方的。
玄與北方:
綜上所述,PPP項目的資本結構是融資內容的關鍵,股東構成和債本比例直接會影響到政府與企業雙方的經濟效益。對于公共設施的建設,不僅耗時長,資金的使用量也巨大,這就需要政府與社會企業通力合作,每一方都負責自己應盡的職責,做出各自的貢獻,能夠有效促進建設項目的順利完成,并且還能夠獲得一定的經濟效益,對促使政府與社會企業長久的合作有積極的作用。
遺屯騎于玄闕兮,軼先驅于寒門。(司馬相如《大人賦》)(83)司馬遷《史記》,第3710-3711頁。
遂作頌曰:麗哉神圣,處于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揚雄《羽獵賦》)(84)蕭統《文選》,李善注,第390頁。
《大人賦》中之“玄闕”,《史記》裴骃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羽獵賦》中之“玄宮”,李善注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個。’”很明顯,以上兩處均是用“玄”來指代方位之北。
漢賦中的顏色詞不僅可以表示方位,還可以表示季節時序。如以顏色詞表示春季,傅毅《扇賦》:“背和暖于青春,踐朱夏之赫戲。”(85)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425頁。“青春”一詞當與《楚辭·大招》中義同:“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洪興祖補注曰:“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86)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216頁。用顏色詞中的“青”與春季并列表示春季。又如以顏色詞表示夏季,王逸《機婦賦》:“于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87)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829頁。朱穆《郁金賦》:“歲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園以迥眺。”(88)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839頁。《爾雅·釋天》:“夏為朱明。”郭璞注:“氣赤而光明。”(89)《爾雅注疏》,郭璞注,邢昺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607頁。此處“朱明”即是指夏季。又如以顏色詞表示冬季,揚雄《羽獵賦》:“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李善注曰:“北方水色黑,故曰玄冬。隆烈,陰氣盛。”(90)蕭統《文選》,李善注,第390頁。以玄描述與指代冬季。
另外,漢賦中關于顏色詞的表述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既用顏色表述五行,亦用五行指代顏色。《東京賦》:“尊赤氏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李善注:“赤氏,謂漢火德所統,赤帝熛怒也。”(91)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15頁。赤即代表五行之德中的火,此為用顏色表示五行。禰衡《鸚鵡賦》:“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李善注:“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嘴有赤者,故曰火德。”(92)蕭統《文選》,李善注,第612頁。所以,這里的“金”與“火”分別指代鸚鵡羽毛的白色和嘴巴的紅色,此為漢賦用五行指代顏色的例證。
由以上論述可見,在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下,漢賦中時空、顏色的表述存在著一定的復雜性。就時空表述而言,時間可以用陰陽、顏色來指代,空間也可以用陰陽、五行來指代;就顏色表述而言,顏色詞既可以表示方位、五行、時序等多種含義,又存在顏色詞與五行互相指代的現象。而這些復雜現象的出現,正是因為陰陽五行思想體系內部的兼容并蓄,也只有將這種文本表述上的復雜性納入陰陽五行思想體系中加以考察,才能更為全面準確地認識與理解漢賦中時間、空間、顏色表述的真正內涵。
三 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結構的潛在影響
陰陽五行思想不僅直接地表現在漢賦文本中,影響其時空、顏色的表述,更為深層的是陰陽五行思想通過其方位意識潛在地影響漢賦的結構,使漢賦具有強烈的結構意識與秩序感。
漢賦在內容上“苞括宇宙,總覽人物”(93)葛洪《西京雜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頁。,但是在繁復的物象鋪排中卻表現出很強的結構意識與秩序感。胡應麟認為“騷復雜無倫,賦整蔚有序”(94)胡應麟《詩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頁。,這正是緣于漢賦大多以空間方位為敘述順序來構撰文本。雖然這種“空間方位描寫方式,與先秦以來人們重視空間關系的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95)郭建勛《辭賦文體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1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漢賦在局部結構上受到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陰陽五行思想對方位極其重視,司馬談說陰陽家“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96)司馬遷《史記》,第3995頁。。方位在陰陽五行思想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其思想系統中五方與陰陽、五行相配:木居東方,少陽起;火居南方,太陽盛;金居西方,少陰起;水居北方,太陰盛;土居中央。由此進一步論自然現象與社會人倫。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局部結構的影響自然也會表現在文本中。例如《子虛賦》中按照方位順序鋪排描寫云夢澤的具體環境: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薔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眾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鱉黿。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楠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鹓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97)蕭統《文選》,李善注,第350-351頁。
其中的方位順序為東南西北,大體上正好對應了董仲舒所云的“天次之序”:“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98)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313頁。《春秋繁露·五行對》:“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99)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306頁。五行相生的順序為木火土金水,此為“天次之序”,而五行與五方是一一對應的,故五方的“天次之序”當為東南中西北,這與《子虛賦》中東南西北的描述順序是大體契合的。另外,其中描述視角的“高燥”、“上”可歸于陰陽五行思想中之“陽”,“卑濕”、“下”可歸于“陰”。可以說,《子虛賦》這一局部結構中“地形從高到低,視角從上到下,方位從東至北,這最終都可以歸入董仲舒陰陽五行學說的系統觀”(100)劉昆庸《漢賦山林描寫的文化心理》,《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第142頁。。
又如《大人賦》在描述“大人”游歷仙境的四面八方時,所采用東南西北的順序也遵循了陰陽五行學說。“大人”結交真人,然后開始展開游仙的歷程,先“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從東方開始游歷,讓陵陽子明、玄冥、黔雷、長離等仙人陪同游歷完東方,接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在句芒的帶領下前往南方游覽。然后“西望昆侖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由南向西而去,西方的游歷以在昆侖之陰山與西王母相見為結束。接著“回車朅來兮”,經由北方返回人間:“近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101)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119-120頁。其中“大人”東南西北的游仙路線與上述“天次之序”是大體相符的,很明顯是受到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另外揚雄《蜀都賦》中開篇描寫即以“蜀都”為中心展開空間方位敘事:“東有巴賨……南則有犍牂潛夷……西有鹽泉鐵冶……北則有岷山……”(102)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第212頁。這一局部結構的安排順序也是符合陰陽五行思想中運轉模式的。
張衡《思玄賦》中亦是按照東南西北的順序來敘述神游過程的,尤為重要的是,賦中在描述主人公神游某一方時所經歷的情景也符合這一方位所對應的五行屬性。主人公的神游從東方出發:“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游覽東海蓬萊、方丈、瀛洲三山,據《月令》中陰陽五行系統,東方屬木,主生長,“句芒”乃主木之官,“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體現出的養生意識亦合木之屬性。然后進入南方:“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在南方“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郁悒其難聊”。《淮南子·天文訓》曰:“日出于旸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注曰:“昆吾邱在南方。”(103)何寧《淮南子集釋》,第233-234頁。賦中描述南方環境之炎熱:火光四射、沸水流涌、熱風聚合,這些都符合五行之火的屬性。然后前往西方:“顧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嬉。”西方屬金,主刑罰、殺戮,故賦中在此多描述肅殺兇險的情景,如“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牛哀病而為虎噬其兄;“王肆侈于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皇后恣意妄為而絕后;“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董賢死而無安寢之地。最后來到北方:“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游。”北方屬水,與冬季相配,陰氣盛,故賦中有“坐太陰之屏室兮”,“經重陰乎寂漠兮”。環境皆清冷蕭條,萬物潛藏,故賦中描述此地環境為冰雪皚皚、寒風凄凄,“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賦中按陰陽五行的運轉模式神游結束,末尾又云:“結典籍而為罟兮,驅儒墨以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104)蕭統《文選》,李善注,第657-676頁。此處的“陰陽”當指陰陽家、陰陽學說,在此將陰陽與儒墨相提并論,可見張衡對陰陽五行思想之重視。賦中或許是有意識地以陰陽五行思想去精心建構上述神游順序,使所描述之事物大多符合陰陽五行之屬性。與此同時使賦中結構井然有序,具有強烈的秩序感。
綜上而論,作為漢代人的思想骨干,陰陽五行思想在漢賦文本中既有直接的表現,漢賦中描述自然天道與社會人倫兩個方面的內容表現出陰陽觀念;五行觀念主導下的五德終始說也在漢賦中有諸多體現。陰陽五行思想又通過“時序—方位—五行—顏色”的對應體系極大地影響了漢賦中時間、空間、顏色的表述,這些表述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復雜性。陰陽五行思想還潛在地影響漢賦局部結構上的規劃與整合,使漢賦表現出強烈的秩序感與結構意識。當然,本文側重于論述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直接與潛在的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以上諸多漢賦的特征均出自陰陽五行思想之影響。事實上,盛世的時代環境、間歇的政局動蕩、文人的復雜心態、賦家的知識結構、漢賦的文體流變等因素與陰陽五行思想一起,共同構成了漢賦的體式與風貌、創作思想與藝術精神,進而成就了漢賦這“一代之文學”,這一點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另外,陰陽五行思想歷經漢代的盛行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骨架,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影響當然也不僅僅局限于漢賦的創作。實際上,陰陽五行思想對漢代詩文以及后代賦作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如陰陽五行思想中的“時序—方位—五行—顏色”對應體系也影響了漢代詩文及后代賦作中時間、空間、顏色的表述。但是,作為漢代人思想骨干的陰陽五行對作為“一代之文學”的漢賦的影響具有集中性與獨特性。即漢賦與漢代詩文、后代賦作相比,漢賦中有更多明顯地體現出陰陽五行思想影響的內容,除去《春秋繁露》《白虎通》《漢書》等散文中專論陰陽五行的篇章,其他漢代詩文、后代賦作較少受陰陽五行思想影響,且大都不像漢賦這樣明顯體現出來,此為集中性。相較于后代賦作,漢賦局部結構上受到陰陽五行思想影響,而漢代以后的賦作中很少有按照陰陽五行思想來安排局部結構的,此為獨特性。以漢代之后京都賦的典范之作左思《三都賦》為例,《蜀都賦》中描述蜀都地理位置時云:“于前則跨躡犍牂,枕輢交趾。……于后則卻背華容,北指昆侖。……于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于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105)蕭統《文選》,李善注,第176-180頁。其大致的方位順序為南北東西,與陰陽五行思想中的“天次之序”東南西北不相符,在整篇《三都賦》中也都找不出東南西北順序的方位描寫。陰陽五行思想對漢賦創作的影響具有集中性與獨特性,這也正是本文以漢賦為研究對象的重要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