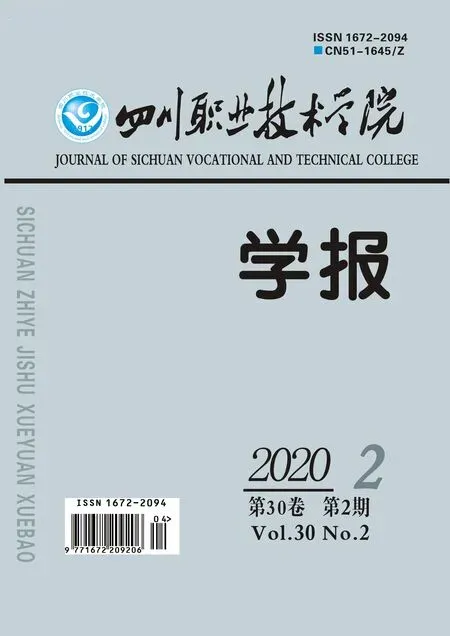另一種抗戰新詩
——論《哀夢影》的敘事空間
劉 平
(西南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
陳銓的新詩集《哀夢影》初版于1944 年,收錄新詩48 首。該詩集中的詩多發表在《民族文學》上,1943 年9 月 第1 卷第3 期 發表21 首,1944 年1月第1 卷第5 期發表20 首,其余7 首是陳銓早期所作。這部新詩集是陳銓為紀念戰死沙場的少年朋友劉夢影而作,屬于抗戰新詩。20 世紀80年代以降,學界對陳銓及其作品的研究逐漸增多,但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說和戲劇上,目前學界對這部新詩集有所忽略,許多抗戰新詩的選集也都沒有將它編選進去。李揚在《陳銓新詩簡論》中認為:“陳銓的文學創作雖然不以新詩為主,但是他有明確的詩歌理論和審美觀點,其價值是不應該被中國現代新詩史忽略的。”[1]因此,有必要給予《哀夢影》一些關注。陳銓曾言:“文學受時間空間的支配,空間是民族的特性,時間是時代的精神,時代精神有轉變,民族特性表現的方式也有轉變。”[2]4可見,陳銓認為空間是文學表現的重要內容。因此,筆者將運用空間敘事學來研究《哀夢影》的地理空間、心理空間、圖像空間,揭示另一種抗戰新詩是如何生成的。
一、充滿詩意的地理空間
不同地域的抗戰新詩研究,若是僅從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特征切入是不全面的。考察抗戰新詩在不同地域的特征,針對的仍是不同區域歷史的時間性解讀。要全面深入地掌握抗戰新詩,需要對其空間性進行考察,而考察抗戰新詩的空間性可以首先借助地理空間來實現。地理空間原本就是激起詩人情感的源泉,透過對地理空間的表現,可以寄托詩人的各種情感,當讀者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哀夢影》呈現的各種各樣的地理空間時,可以讓讀者循著地理空間的展現,看到由這樣的地理空間所衍生的不同意蘊和情感,并往往可以激起讀者感同身受的共鳴。例如在《催眠曲》[3]31中,“貓頭鷹”、窗前的“暴風雨”“溫暖的衾被”“蟋蟀”、林間的“杜鵑”“燭光”“熟寐的眼簾”等空間意象,將屋內的寂靜與屋外的喧鬧形成對比,襯托出身處室內的敘述者“我”對“你”的疼愛之情;在《那一天》[3]35中,“書房”“窗外土墻”“斜陽”等空間意象,為一對戀人的相見營造出凄涼感傷的氛圍,也可以見出這對戀人難舍難分;在《感情頌》[3]37中,開頭和結尾四句相同,形成了回環的結構,同時也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文本空間。詩中“莊嚴廟宇”的“花枝”“斜照”在“肅殺秋林”的“太陽”“孽子孤臣”等空間意象,營造出威嚴莊重而又陰森的氛圍,與封閉的文本空間結合,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傳達出詩人對“感情”的贊美之情。
不僅如此,要理解《哀夢影》敘事空間的產生背景和深層意義,需要考察生成詩歌的外圍空間。《哀夢影》的寫作不是孤立的,是與其產生的時代息息相關的,如果將《哀夢影》與它同時期產生的抗戰新詩放在一起,并進行總體觀照,《哀夢影》所蘊含的共有的“地志的空間——即作為靜態實體的空間”[4]便會彰顯出來。換言之,每個時代的詩歌在空間取向上都是相差無幾的,都會映射出生活于這個時代的人們所持有的各種觀念和意志以及一系列形而上的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詩歌的主題意旨。詩歌創作自身也擺脫不了對地方、景觀、方位等的敘寫。詩歌對這類空間的想象與關注是一種空間的再生產,或曰空間的再創造,而經由詩歌生產的空間反過來又會對現實中的地理環境產生重要影響,所以詩歌總是必然地和空間發生著互動關系。陳銓在《哀夢影》中經常將自己活動的地理空間作為主要的書寫對象,當然也可能不完全是這樣,將描寫的地理空間投射到遙遠的想象的空間亦是過去生命中曾出現的空間,例如在《中夜蟾蜍》[3]54-55中,蟾蜍“失伴的悲哀”暗指陳銓失去好友劉夢影。他還在這首詩里三次提到家鄉,即四川省富順縣,家鄉“有熊熊的愛火”“溫暖的聲音”,呈現出一個溫情脈脈的地理空間。但是,他在詩歌中主要關注的還是此在,關注當下活動的空域。詩人在《既然》[3]62-63中描寫了一個凄清破敗的山城,“岸邊”的“亂石殘痕”“天際殘云”等空間意象,讓地理空間的破碎性呈現出來。詩人雖未解釋山城為何滿目瘡痍,但讀者只要看一下此書的出版時間——1944 年,便可推知日軍對重慶的大轟炸下城市的遍地狼藉;在《期待》[3]5-6中,通過“山城”的“江水”“行船”等意象,敘述了“我”在山城的江邊等待從上游來的“你”一事,但“你”遲遲未到,“我”悵然若失。
此外,通過對不同地理空間動態的、立體的與綜合的分析與闡釋,不但能夠更真實地了解《哀夢影》生成的自然環境,還原經過陳銓重新建構的充滿詩意的地理空間,映射出隱藏在陳銓意識深處的心靈畫面,還能夠由此發現地理空間對于《哀夢影》的價值內化作用,那就是經過詩人主體的審美觀照,作為客體的地理空間形態逐漸積淀,最終升華為《哀夢影》的精神空間與詩性空間。
二、孤獨感傷的心理空間
心理空間的概念最早出自于語言學家法康尼爾。法康尼爾這一理論概念的構建是相對于真實條件下的可能世界而提出的。在法康尼爾看來,“心理空間與可能世界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心理空間并不包含現實或實體的一個如實再現,而是一個理想化的認知模式”[5]。詩歌通常都是濃烈情感的自然表達,無論什么樣的詩歌,讀者都能夠或多或少體會到其中詩人的情感流露與表達。但是,呈現出明顯心理空間的新詩,幾乎是詩人透過敘述主體將內心世界所作的一種最為形象的展現,這種映現在詩歌中的心理空間,往往可以最好地展現詩人的內心世界,例如在《寂寞》中,“檐前”“翻飛的蝙蝠”[3]36、無人的道路、斜月、荒塋、海棠等空間意象,襯托出詩人寂寞孤獨的心境。《事實與幻想》里的“事實”指的是劉夢影戰死沙場一事,“幻想”是指“我”幻想好友還活著。這首詩的開頭和結尾四句也相同,形成了回環的結構,同時也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文本空間。再結合“走進屠場”的“馴服綿羊”[3]47、“任風飛翔”的“顛狂柳絮”[3]48、在心里滾燙的“熱血”等空間意象,呈現出詩人滿腔熱血被壓抑和平定的心理空間。《梅花》里的“梅花”不再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傲雪寒梅形象,它代替了桃花、芍藥、合歡等作為情人之間送花定情的傳統意象,并且在這首詩中是女性送男性梅花,這就賦予了梅花新的內涵。詩歌里梅花的存放方式也很特別,不是插在花瓶里或擺放在肉眼可見的室內,而是藏在箱子里,暗示著“我”和“你”的感情不能公開,但“我”還以為這是一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秘密,后來直到一位朋友和“我”有同樣的經歷時,“我”才醒悟被你欺騙,“我”的心情瞬間由竊喜轉變為氣惱。《失眠之夜》結合“高懸天際”的“明月”[3]51“窗外柳枝”“陣陣吹來”的“寒風”“搖曳不定”的“枝影”等空間意象,呈現出敘述主體痛苦無奈的心理感受。《離愁》[3]66描寫了戰士在行軍過程中的離愁別緒,“疏林”“殘葉”“夕陽”“秋山”“孤雁”等意象和“桃花春水”形成對比,將戰士心中的愁苦渲染得淋漓盡致。此外,讀者也可以透過詩歌所呈現的心理空間,展開與敘述主體的廣泛交流。
鮮為人知的是,陳銓將作于早期的九首新詩收錄進《哀夢影》,分別是《失敗》《桃花》《既然》《催眠曲》《死后的安慰》《中夜蟾蜍》《失眠之夜》《恨不得》和《第一次的祈禱》。那時劉夢影并未戰死殺場,可見《哀夢影》并不只是為哀悼劉夢影所寫,也是陳銓自己思想情感與觀念意志的表達。這些詩歌的創作激活了陳銓關于這一特定對象的知識框架,并且留存在陳銓以前記憶中的心理空間具有某種特定的指向,陳銓以話語的形式,透過詩歌中的敘述主體將這一獨特的心理空間呈現在詩歌文本中。在讀者最終所讀到的詩歌中,在文本中所呈現的心理空間映射出了陳銓的心理空間。
詩人寫作詩歌是屬于精神領域的一項活動,建構的也是一種精神的空間。按照心理分析理論,詩歌和小說一樣創造了一種空間,詩人在這一空間中呈現出在現實中無法完全呈現的那部分自我,因此,詩人寫作詩歌是表達自我心理空間的一種方式。愛德華?索亞根據列斐伏爾提出的社會空間概念,再進一步提出三種空間形態,即第一空間主要是被感知的物質空間,第二空間主要是被構想的精神空間,第三空間則主要是一個容納所有的同在性的開放空間。在解釋第二空間時,索亞對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進行了擴充,在他看來,第二空間不只是列斐伏爾所言的那種再現“權力、意識形態、控制和監督”的精神空間,“也是烏托邦思維觀念的主要空間”,更是“藝術家和詩人純創造性想象的空間”[6]。換句話說,詩人寫作詩歌的過程也是在建構或生產精神空間。每一首詩以其獨具個性的方式生成一個特別的心理空間,以此來充盈和擴大由詩歌先前構筑起來的充滿詩意的地理空間。也就是說,《哀夢影》中的空間是以現實中的物理空間為基礎,與處于它所產生時代的人們的空間觀念相關聯,這屬于心理空間的范疇。陳銓新詩中表現出的敘事空間,正是依托詩人自身所處的時代環境下的心理空間觀念而進行的書寫。例如《不要信》中“戀愛和救國勢不兩立”[3]17,體現了愛情和事業的沖突;而“籬墻”“玫瑰”“陣云”等意象,加劇了沖突對給人造成的復雜心理。此外,這首詩用短短七十四字,就呈現出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流行的“革命加戀愛”小說類似的主題——“抗戰加戀愛”,拓展了文本的表現空間。
此外,時間與空間的關系“是一種帶著很大主觀色彩的感情心理關系。時間變成了心理時間,空間變成了心理空間。通常時空關系中那種不可逾越的界限變得富有奇異的彈性了”[7]。例如在《死后的安慰》[3]25中,抒情主人公是劉夢影,這是陳銓想象劉夢影戰死后為他代言的,代言劉夢影生前的夙愿。“關山”“舊日的庭園”“席上”等空間意象的轉換,過去與現在交織,暗示著抒情主人公心理的變化,由迫不及待到遺憾辛酸。
三、色調鮮明的圖像空間
詩人和空間之間有三種關系:一是詩人與深入其中的實體空間的關系,即物理空間;二是由詩人主體的審美觀照后所沉淀升華的精神性空間,即詩人的心理空間;三是以心理空間為構成其關系的框架,而具體呈現在作品中的第三空間表象,即圖像空間,這一空間才是最具有審美價值的空間。不能否認的是,意象是構成這一審美空間的主要支柱和實體元素,是詩人能通過圖像空間具體感受到的,詩人充盈的情感與具有深度的思想需要借助這些具體可感的意象來傳達。對生活深有體會并有著自己理解的陳銓,便把心中的想法與頭腦中的觀念、欲望、思考轉移到色彩鮮明的圖像空間上,例如《春雨》中的春雨、遠樹、煙霧、斜月、新柳等意象,白色和淡綠混合,而春雨朦朧襯托抒情主體的“心事浮沉”[3]8、猶豫不定而又迫不及待的矛盾心情;《別離》中的“明月”“窗欞”“江水”等意象,構成了一幅空明澄澈的江水月夜圖,同時,也與抒情主體剪不斷、理還亂的內心世界形成強烈的對照。既然意象以及通過意象表達的意義是圖像性的,那么由此推知,意象也必然是空間性的。由于色彩突顯意象的形態,喚起了讀者內心情感的波動,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融入詩歌主要呈現的空間上去,反過來鑄造出色彩鮮明的空間意象,使詩歌的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融為一體。法國著名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兼詩人巴什拉在其《空間詩學》中不僅將家、抽屜、鳥巢、貝殼、角落等詩歌意象看作是載物的容器,而且將其看作是人類意識的幸福居所,這就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印證了詩歌意象的空間特性。由此看來,由一系列意象以及意象之間的空白所組成的詩歌,實際上也是由一系列更小的空間所組成的一個整體空間。需要說明的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歌意象是指由語言描繪的具體可感而又充滿情感與理性的畫面,它不僅可被稱之一幅完整的畫,也可被冠之為整體意象,更可以是畫中的一片云、一朵花、一根草、一棵樹、一個人,可命名為局部意象。毫無疑問,對于自身而言,每一個局部意象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圖像空間,都是組成詩歌整體圖像空間中的某個部分,最終與其他局部意象一樣,構成詩歌的整體意象或整體空間。例如《我愛》[3]10中的“山間的白云”“溪畔的飛泉”“枝頭的小鳥”“水上的荷錢”“花”“月”“蔚藍色的青天”等空間意象,《我愿》[3]27中的“一只粉蝶”“一個鸚鵡”“一柄團扇”“一枝玉蘭”“一鉤斜月”“窗欞”“杜鵑”等意象,一個意象就是一幅圖畫,但這些意象組合起來又是一幅完整的圖畫,色調鮮明。詩歌意象成為了詩歌的建筑砌塊,是建構詩歌空間藝術的基石,因而也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進一步彰顯出詩歌的空間特性。
不僅如此,在《也許》[3]40中,陳銓通過“高陵”“深谷”“滄海”“桑田”“埋在黃土”的“英雄”“落紅”“青山”“戰場相見”的“友朋”“庭舍相殘”的“兄弟”“喋血宮前”的“君臣”這些特殊的意象勾織整首詩歌,每個意象都蘊涵著不止一層的意味,不同的讀者對意象的解讀也不盡相同,讀者可以從根據意象的色彩找尋與自我對應的圖像。《哀夢影》的一個獨特之處在于先是通過意象所具有的色彩引人注目,再借助不同的色彩營造意境,以此來帶給讀者感官和心靈的審美愉悅。圖像空間中作為客觀實體的意象是以色彩為中介來給人以視覺刺激的。在《也許》中所呈現的空間性特征是顯而易見的,圖像中的色彩是存活在由詩人和讀者的意識再造的空間之中,并以文字符號與意象為載體給人以視覺感受。一個被詩人感覺和體驗到的外在世界,剎那間被轉換成了具有自由與靈動特性的顏色織品。“黃土”、“落紅”、“青山”是大自然特征的物化形態,而“戰場相見”的“友朋”“庭舍相殘”的“兄弟”“喋血宮前”的“君臣”,則在須臾建構了一個借助語言擴充來的語境,讀者可以從這些的意象中閱讀出主體心靈的顫抖。“血”是冷紅色的,這一外在的色彩鮮明的意象一旦與內在的情思結合,即使發射出虛弱的信號和死亡的前兆,卻賦予了色彩一個功能,即令人觸目驚心而印象深刻。在《也許》中,人類的生活由一張白紙逐步演變為一幅色彩斑斕的圖畫,每一種色彩被印刻了詩人的品格和思想,這是詩人的人生體驗與情感融合而出的結晶。也正是詩歌中這些具有色彩的詞語,賦予了《哀夢影》令人久久回味的意蘊。應該說,《哀夢影》中的圖像空間,能夠定格在一幅靜態的畫面中,例如《花溪》中的花溪、羅衣、飛泉、水珠、峰巒、桃花、青山等意象,構成一幅山水圖,極具畫面感;《空談》[3]22中“剪天際的彩云”“山間的明月”“枝頭的朝露”“樂園的花瓣”“青山”“紅玉”“臘梅”等空間意象,呈現出一幅山林晨冬圖,色彩絢麗,馥郁芳香;《解脫》[3]64描寫了“飛泉絕壑”“片片桃花”“一池春水”“池畔綠楊”“酒家”“夕陽”“滿山遍野”的“紅霞”“荷鋤歸去”的“農夫”等空間意象,再借助六言古詩的外殼,呈現出一幅寧靜和諧的鄉村圖景;《自勵》[3]78中“遠處的山峰”“云里的月光”“破瓦頹垣”“北風”“城墻外”的“衰草”等意象,呈現出一幅肅殺的戰前圖像。但是,在將圖像空間定格為靜態畫面的同時,更需要考慮的是它所包含的富于動態意義、意蘊雋永的圖像空間之美,這種動態的圖像空間展現在人們的腦海中,猶如連續的電影畫面不斷延伸,富于詩意地展開一樣,給人以一種持續的美感。例如在《愛的力量》中,“織女守盼銀河,襄王夢醒巫山,洛神隱約波心,嫦娥寂寞廣寒。蝴蝶翩翩花下,游魚嬉戲蓮邊,小溪匯入江河,高峰仰望云天。”[2]29一句詩就是一幅具有動感的圖像,多幅圖像重疊,色調鮮明,并且拓展了這首詩的表現空間。在《桃花》中,一株窗前的粉色桃花、在桃花周圍的一群“游蜂浪蝶”[3]42、停步駐足于桃樹前的“我”等空間意象,以及桃花與“我”的互動,構成了一幅人與自然和睦共存的圖景。由此可見,由色彩切入圖像空間,有助于從視覺感官引起審美興趣,令鮮明的色彩引發讀者的空間想象與聯想的功能,帶給讀者意象之外的獨特美感,古往今來的諸多詩人都借助乎此。如果說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田園意象追求圓融靜逸的色彩,那么現代詩人在調色時注重情感的投入,使色彩和感情相融合,呈現矛盾的心理與情感狀態,并從中架構更具空間性的色彩鮮明的一幅幅圖像。
四、結語:另類抗戰新詩的生成意義
陳銓在《哀夢影》中借助生活空間,如一個接著一個的不同生活場景;意象空間,如“肅殺秋林”的“太陽”、“檐前”“翻飛的蝙蝠”、“剪天際的彩云”;精神空間,如“一個安靜的心靈”[3]53,“像松枝上的白云,像靜夜里的鐘聲”等進行敘事,不僅表現了陳銓對不同層次的空間有著不同的認知、體驗與感受,而且彰顯了《哀夢影》的獨特之處。陳銓正是把自己的所見、所感、所思借助不同的空間進行敘事,而他所挑揀的這些空間盡管不是孤峭奇崛的,卻深深地烙上了他的個性印跡。詩人擁有深邃的精神世界與獨特的生命體驗,他把自己真實的情感與體驗通過外在的形色各異的事物,即“窗外”“屠場”“戰場”等空間意象,借助虛實結合的手法,創作出一首首具有詩人自身風格的詩歌。需要注意的是,《哀夢影》中的地理空間、心理空間和圖像空間呈現,既各有其獨立的意義,有各自富于獨特意味的表現,同時它們之間也并不互相隔絕,而是可以融通的。比如地理空間對于家鄉的眷戀與回憶,也可以出現在心理空間呈現中;而在心理空間所表現的內心意愿的圖景,也可以出現在圖像空間中。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哀夢影》的底色是反對戰爭、渴求和平的。
《哀夢影》盡管是在抗戰背景下寫作的,但卻不是政治諷刺詩、政治抒情詩、長篇敘事詩,它既不似街頭詩、傳單詩以人民大眾為對象,追求詩歌大眾化;也不像七月派的抗戰詩歌,聲嘶力竭,充滿主觀戰斗精神;更不像大多數的重慶抗戰詩歌,充滿“暴風的呼嘯,狂奔的激情,戰斗的吶喊,浮躁而缺乏深沉,整體認同而缺乏個性特征”[8],表達“人民抗戰的激情與頑強的意志”[9]。陳銓也基本不寫侵略者的殘暴、戰斗者的頑強抗爭,《哀夢影》中的政治意識被淡化,陳銓只是在借助它來表達自己的態度,即反對抗戰、祈求和平。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陳銓沒有到前線去體驗生活,也沒有與普通士兵在一起生活,陳銓對戰爭場面的直接描寫,在《哀夢影》的四十八首詩中只占三首,分別是《山頭》[3]69-72《同伴》[3]76-77《戰歌》[3]80-84,并且只是他個人的想象。第二點是《哀夢影》是為紀念亡友所作,“茲仿其意作情詩二十一首,以志哀悼”[3]1,因此,哀悼感傷的氛圍籠罩全詩,如果沒有爆發抗戰,劉夢影或許不會參軍;如果劉夢影沒有在1943 年的夏季參加鄂西會戰,他或許不會這么早就死去。陳銓通過《哀夢影》為他和劉夢影之間的真摯友情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第三點是陳銓寫作《哀夢影》的另一目的主要是期盼人間和平的到來,追求幸福美滿的生活。例如在《恨不得》中,詩人寫道:“恨不得腰橫金劍,斬盡了人間惡魔”,“恨不得萬千羅帕,拭盡了人間淚痕”[3]56,將這兩句詩放在抗戰的背景下,不難發現,這里的“人間惡魔”指的是日本侵略者,腰橫金劍、斬盡惡魔都是為了早日結束戰爭,早日實現世界和平,早日讓人類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不再有悲傷和哭泣;《也許》結尾的四句詩:“人生充滿了轉變,世界飽含著辛酸,恐懼和希望激烈交戰,事實和理想永不相安”[3]41,雖未直接道出戰爭為社會和類人造成的傷害,但卻委婉含蓄地表達了詩人對和平的祈盼;詩人在《戰的哲學》的開頭和結尾都直接寫道:“和平是人類本性,戰爭是天地不仁”[3]67,表達了他對戰爭的控訴和對和平的呼喚。可以說,陳銓在《哀夢影》中展現出他的另一種文學寫作姿態,不再是狂飆突進,也不再是呈現“民族至上、國家至上”這一宏大主題。《哀夢影》更不是林徽因的《茶鋪》,書寫戰時和平生活的民俗風情。陳銓更多的是抒發他自己內心的情感,恰如有學者曾指出:“對于一位滿懷文學想象的思想者,他的思想脈絡內含著他的情感方式,需要我們從文學的情感領悟的角度加以把握。體現著這種情感傾向的陳銓文學,不僅有小說和戲劇,還有詩歌。”[10]129的確,陳銓在《哀夢影》中運用豐富的想象和飛揚的靈感,為詩歌涂上濃郁的個人的情感色彩和理想色彩,呈現出另一種抗戰新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