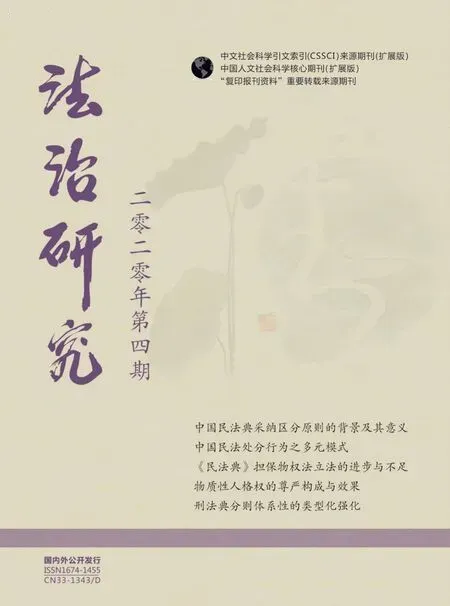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強化
馬榮春
所謂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強化,是指通過刑法立法類型化來強化刑法典分則的體系性,同時也是強化整個刑法典的體系性,它是對刑法科學立法的一個切實響應。
一、刑法典分則體系性類型化強化的標準選擇
(一)“前置法益主導標準”的初步引出
縱觀刑法典分則的章節結構,一直給人一種雜亂之感,特別是通過較為頻繁的刑法修正案而不斷充塞新的罪條之后。而這種雜亂之感實為其體系性問題。如何強化其體系性?刑法立法類型化及其“著力點”是值得關注的思考方向。
現行刑法典分則之所以在整體上給人嚴重欠缺體系性之感,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立法者欠缺類型化立法思維,①馬榮春:《刑法類型化思維:一種“基本的”刑法方法論》,載《法治研究》2013年第12期。而類型化立法思維的切入點即其“著力點”。由于犯罪類型是類型化思維的觀念產物,故又牽扯出犯罪類型的標準問題。而我們將從犯罪類型標準問題的討論中來獲取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及其“著力點”方案或路徑。對于犯罪類型的標準問題,有人在“行為類型說”和“法益類型說”的基礎上提出了所謂“法益標準與行為標準的二元融合說”。具言之,“行為類型說”和“法益類型說”分別堅持“行為類似性”與“法益同一性”的犯罪類型標準。單純以法益侵害作為類型劃分的標準會削弱構成要件的定型機能,以致于籠統地得出“因為侵害同類法益,所以屬于同一犯罪類型”的結論。構成要件本身是犯罪行為的類型化,而犯罪行為的類型化不僅具有規范性評價的指引作用,更具有彰顯“整體形象”的類型意義。但是,“行為類似性”無法回答具有類似性的“貪污”行為和“職務侵占”行為二者為何分立不同的罪名。由此,在“法益同一性”的基礎上,再根據行為的特殊性來獨立設罪,這便形成了犯罪類型的“法益標準與行為標準的二元融合說”②蔡榮:《刑法類型化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19年博士學位論文。。可以肯定的是,犯罪類型標準的選擇肯定是離不開前置法益的,正如臺灣學者指出,法益侵害性是構成犯罪的真正理由,刑法上種種犯罪構成要件的羅列,只不過是為各種法益侵害行為提供具體的認定標準而已。③黃榮堅:《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頁。但是,犯罪類型標準的選擇肯定也離不開犯罪行為本身,正如國外學者指出,立法者描述構成要件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有時會根據外部特征對犯罪行為作詳細的描寫。④[德]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頁。而許多犯罪類型的不法內容不僅是由受保護的行為客體受侵害或者危險決定的,同時也是由行為的方法和樣態決定的;⑤[德]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上),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頁。或如大陸學者指出,刑法典所規定的犯罪類型不僅涉及法益侵害的結果或者危險,還對特殊的行為方式與行為樣態做了描述。⑥陳璇:《結果無價值論與二元論之爭的共識、誤區與發展方向》,載《中外法學》2016年第3期。可見,當前置法益和犯罪行為本身都為犯罪類型的標準選擇所不可或缺,則意味著前置法益和犯罪行為本身在犯罪類型的標準之中是應該并存的,即關于犯罪類型標準的“行為類型說”和“法益類型說”是不相矛盾或不相排斥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法益標準與行為標準的二元融合說”或“行為類似性”與“法益同一性”的“二重性標準說”。客觀地說,犯罪行為本身即其方式或樣態屬于犯罪的現象層面,而現象是具有多樣性和差異性的,故若把犯罪行為本身作為犯罪類型劃分中一個與“前置法益”相并列的標準,則將導致犯罪類型飄忽不定而無從把握。相比之下,作為犯罪現象的“內在本質”,“前置法益侵害性”具有相對的確定性和同一性,故以之為標準的犯罪類型也就具有相對的確定性和同一性。由此,在犯罪類型的標準問題上,我們應確立“以前置法益為主導的標準說”,這意味著法益因素和犯罪行為本身因素在犯罪類型的標準中都得到了肯定,即兩者的合理成分都被采納。然而,這也并非意味著法益因素和犯罪行為本身因素在犯罪類型的標準中“平起平坐”,因為“平起平坐”意味著“分裂性”和“無結構性”,以致于犯罪類型的標準不成其為“標準”。于是,“結構性”及其所能產生的相對確定性和同一性要求著犯罪類型標準的“主導性”。犯罪類型標準的“前置法益主導性”,隱含在犯罪的刑法定義之中。現行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前述規定給出了犯罪的刑法概念。從犯罪的刑法概念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居于刑法典分則“章罪”層次上的犯罪的若干類型,而且看到了犯罪類型通過“主權”“完整和安全”“制度”“秩序”“財產”和“權利”等所表達出來的“前置法益侵害類型性”,而前述每一個“前置法益侵害類型性”在觀念上便對應著一個“前置法益主導性”。“前置法益侵害類型化”和“前置法益主導性”是犯罪類型化和犯罪類型性的根由。
這里要進一步強調的是,為何不采用“刑法法益主導標準說”?答案在于:刑法是法體系中的“后盾之法”和“保障之法”。而若采用“前置法益主導標準說”,則體現著犯罪類型標準的“違法性一元論”與“法秩序統一性論”立場。相反,如果采用“刑法法益主導標準說”,則犯罪類型標準將可能是“違法性二元論”立場,而“違法性二元論”立場將可能使得刑法忘卻自身是“后盾之法”和“保障之法”的“身份”,從而有“專斷刑法”和“權力刑法”之險。
(二)“前置法益主導標準”的進一步論證
犯罪類型標準的“前置法益主導性”是能夠得到“法社會學”和“法教義學”的雙重支撐的。具言之,當犯罪是“蔑視社會秩序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6頁。則犯罪類型也可從社會秩序的蔑視性即社會危險性和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危害性”這里得到說明,正如貝卡里亞就“犯罪的分類”指出的,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是我們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尺”。有些犯罪直接地毀傷社會或社會的代表;有些犯罪從生命、財產或名譽上侵犯公民的個人安全;還有一些犯罪則屬于同公共利益要求每個公民應做和不應做的事情相違背的行為。一切犯罪都是在侵犯社會,但并非都是試圖毀滅社會。其中,叛逆罪屬于第一類犯罪,是最嚴重的犯罪;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屬于第二類犯罪。⑧[意]切薩雷·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頁。由于“社會危害性”隱含或蘊含著“法益侵害性”,故“前置法益主導標準”的“法社會學說明”便隱含或蘊含著“法教義學說明”。
至于“前置法益主導標準”的直接的“法教義學說明”,我們可聯系或觀照刑法典分則結構來進行。具言之,當我們考察和把握犯罪類型的標準問題時,我們不能將目光僅僅停留在個罪上,應該從犯罪類型的“層次”上來考察和把握犯罪類型的標準問題。于是,刑法典分則的章節結構便給了我們啟示:刑法典分則的章、節、條分別對應著“章罪”“節罪”和“條罪”。其中,“條罪”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個罪”,“節罪”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類罪”,“章罪”可稱為“大類罪”。顯然,刑法典分則在從“大類罪”到“類罪”再到“個罪”的結構安排,所突出的是“前置法益類型”,而犯罪行為本身樣態或特征只是從“大類罪”到“類罪”再到“個罪”的順次之中逐漸體現出對犯罪類型的外在性描述。實際上,即便是在“個罪”的層次上,“行為類型”即犯罪行為本身的樣態或特征也未取得犯罪類型標準中的“主導地位”。而犯罪類型標準的“前置法益主導性”,又是與一國刑法的任務或目的緊密相聯系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刑法典分則,其對犯罪的章節條安排不是漫無目的的,它體現了刑法的任務或目的。而一國刑法的任務或目的又是對照前置法益侵害或社會危害性來確定的,正如對犯罪從“侵犯個人法益的犯罪”到“侵犯社會法益的犯罪”再到“侵犯國家法益犯罪”的分則體系安排,體現著有關國家刑法的任務或目的所在。學者將法益分為整體法益、類型法益和具體法益三個層次。⑨張曉虎:《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頁。其實,所謂整體法益是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法益而無法再予分類,而類型法益和具體法益都是可以進行內部分類的。于是,犯罪之所以能夠在事實層面形成經驗類型且在價值層面形成規范類型,是因為犯罪的前置法益侵害性或社會危害性本來就存在類型性,且此類型性又是存在層次性的,即犯罪在刑法典分則章節兩個層面上是可以按照不同標準予以分類的。犯罪的前置法益侵害性或社會危害性的類型性及其層次性在根本上決定了一國刑法典分則的體系結構,而一國刑法的任務或目的又從其分則體系結構中得以映現。刑法典分則體系的體系結構性在映現一國刑法任務或目的的同時,也同時映現了犯罪的刑法分類,即犯罪的刑法類型是以“前置法益類型性”為“主軸”的。學者指出,制定法的任務不是詳細地描述現實,而是正確地去規定、去設計這些現實。⑩吳從周:《論法學上之類型思維》,載《法理學論叢——紀念楊日然教授論文集》,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頁。以“前置法益類型性”為“主軸”即將前置法益作為犯罪類型標準的“主導”,正是刑法典分則體系性安排的基本手法,正如刑法典分則全部條文的排列,應通過對法益分組和分層次來實現章節體系自身的系統性。[11]同注②。而通過對法益分組和分層次,能夠實現受保護的價值的分類和系列化。[12]同注②。犯罪類型標準的“法益主導論”對應著犯罪構成要件解釋的“規范目的論”,而犯罪類型標準的把握不能違背“目的”決定“手段”,而非“手段”決定“目的”。當刑法的規范目的決定刑法的規范手段,而刑法的規范目的又在根本上決定于犯罪的前置法益侵害,則作為刑法的規范手段的刑法立法類型化便通過“前置法益類型化”而實現了刑法立法對犯罪的體系性安排。于是,需要強調的是,“前置法益主導標準”是對“前置法益類型標準”的一種鞏固和強化。易言之,對犯罪類型的標準問題,刑法典分則的體系性問題采用“前置法益主導標準”是刑法類型化和刑法立法類型化的題中之義。而正是“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將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強化落到了實處。
二、刑法典分則體系性類型化強化的標準運用
(一)“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對罪條和罪名的整合作用
犯罪類型標準的“前置法益主導性”有助于消解相關罪條和罪名關系的爭論。讓我們先切入危害國家安全罪的立法來討論問題。如對于刑法第103條、第104條和第105條所分別規定的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暴亂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有人指出,前述三罪可類型化為“內亂罪”,其理由如下:一是三罪都是對國家存在的犯罪,具有法益的同一性;二是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不足以涵蓋所有的破壞憲法統治秩序的行為;三是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與武裝暴亂罪的構成要件存在交叉,而所有武裝暴亂的行為都可以評價為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13]同注②。其實,分裂國家罪可以視為危及“國家存在”的犯罪,但顛覆國家政權罪未必是危及“國家存在”的犯罪,因為這種犯罪旨在更迭國家政權,而武裝叛亂、暴亂罪更未必是危及“國家存在”的犯罪,因為武裝暴亂罪或可能是危及“國家存在”的犯罪,或可能是顛覆或更迭現政權的犯罪,而武裝叛亂罪則是旨在離“國家”而去的犯罪。顯然,按照“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將前述三罪“類型化”為所謂“內亂罪”是有欠妥當的,因為“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反對將前置法益侵害不同的犯罪予以混同,并以此來作出條文編排和罪名設定。由此,與其說將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暴亂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類型化”為“內亂罪”,毋寧是“打包”或“捆綁”為“內亂罪”,但“內亂罪”的罪名在中國也難有刑法規范作為行為規范的積極效果,因為對中國百姓的認知而言,擾亂社會秩序類的犯罪都是“內亂罪”。不過,在肯定危害國家安全這一共性的前提下,現行刑法第103條、第104條和第105條本來似應確定如下順序,即將分裂國家罪規定在前,將顛覆國家政權罪規定在中,將武裝叛亂、暴亂罪規定在后,因為前述順序是一個危害國家安全的由重到輕的順序,亦即一個前置法益侵害的輕重順序。至于“破壞憲法統治秩序”,已經暗含在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和武裝叛亂、暴亂罪之中。
對于現行刑法第110條和第111條所規定的間諜罪和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的立法,有人指出,首先,竊取、刺探、收買可以類型化為“非法獲取”,并且涵攝其他非法獲得國家秘密、情報的行為方式;其次,為境外非法獲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本身就屬于間諜行為;其三,“指示轟擊目標”因過于具體而可將之歸屬于“非法提供情報”這一行為類型。由此,可將兩罪類型化為“間諜罪”,且罪狀表述如下:“(一)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二)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非法獲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14]同注②。應該肯定的是,“指示轟擊目標”是可以“類型化”到“非法提供情報”中去的,而為境外非法獲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本身又是可以“類型化”到間諜行為中去的。因此,論者將間諜罪和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的罪條予以合并且將罪名統稱為“間諜罪”的建議是基本可取的。外在地看,前述罪條合并與罪名統稱使得刑法立法在間諜犯罪這一塊便顯得完整而簡練,從而“局部”地顯現出刑法典分則體系的練達之美;內在地看,前述罪條合并與罪名統稱乃“前置法益主導標準”使然。
“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對罪條和罪名的整合作用,另可從走私犯罪和淫穢犯罪的立法問題中得到例證。如對走私犯罪立法問題,有人指出,應當將“走私武器、彈藥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幣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走私淫穢物品罪”和“走私廢物罪”整合到“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之中,但仍另設“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因為上述罪名都屬于“違反海關法規,走私貨物”的行為類型,即“違反海關法規,走私貨物”是所有走私犯罪的“整體形象”。但就法益保護的同一性而言,普通貨物的走私與“禁止進出口貨物”的走私有所不同,即“走私禁止出口貨物、物品罪”同時侵犯了對禁止走私對象管理秩序的法益保護。再者,只要體現是對“禁止進出口貨物、物品管理秩序”這一法益的保護,無論是“武器、彈藥”,還是“淫穢物品”等都不影響對這一法益侵害的認定,即行為對象的不同既不決定具體犯罪的性質,也不作為對該具體犯罪進行類型歸屬的依據,而僅僅是該具體犯罪成立可選擇的要素。易言之,從保護法益的同一性考慮,有區分“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和“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的必要;而從是否有利于實現法益保護目的而言,將“走私武器、彈藥罪”等罪名整合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貨物、物品罪”一罪,更有利于對國家禁止進口貨物管理秩序的整體性法益的保護。“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的整合既能填補法律漏洞和嚴密刑事法網,也能夠精簡刑法典分則罪名體系和克服“重復性入罪”而造成罪名體系混亂交雜的弊端。[15]同注②。這里還應強調,在“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貨物、物品罪”中,走私武器、彈藥、核材料罪又對應著特殊的前置法益侵害性,且應將其歸入即“類型化”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去。
另外,關于淫穢物品、淫穢音像制品和淫穢表演的刑法立法問題也值得重新考量。有人主張將第364條第1款傳播淫穢物品罪、第364條第2款組織播放淫穢音像制品罪和第365條組織淫穢表演罪合并即“類型化”為“傳播淫穢信息罪”,且理由是:其一,組織播放行為可以類型化為“傳播”行為;其二,淫穢表演相較于淫穢物品僅僅是淫穢信息的載體不同,即前者的載體是物,而后者的載體是人;其三,“組織”的核心意義仍在于對淫穢信息的傳播。[16]同注②。確實,傳播淫穢物品、組織播放淫穢音像制品和淫穢表演,都有“傳播淫穢信息”的功效,而且“淫穢表演”的“傳播淫穢信息”的功效似乎更強。由此,不僅淫穢表演的組織行為應受刑事處罰,而且淫穢表演行為本身似乎也應予以刑事處罰,因為淫穢表演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似乎不亞于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當傳播淫穢物品、組織播放淫穢音像制品和淫穢表演都有“傳播淫穢信息”的功效,則意味著傳播淫穢物品、組織播放淫穢音像制品和淫穢表演對應了同一類型的前置法益侵害或同一性質的社會危害性。由此,基于“前置法益類型化”,將傳播淫穢物品罪、組織播放淫穢音像制品罪和組織淫穢表演罪合并即“類型化”為“傳播淫穢信息罪”是可取的,但其罪狀應重新表述為“通過傳播淫穢物品、組織播放淫穢音像制品和淫穢表演等方式傳播淫穢信息,情節嚴重的”。顯然,經過合并即“類型化”之后的傳播淫穢信息犯罪的罪條將使得現行刑法典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第九節變得更加緊湊而更富條理性和體系性。
“前置法益主導標準”通過罪條與罪名整合來增強刑法典分則體系性,還體現為罪條和罪名的科學吸收。正如我們所知,我國1979年刑法典還在強奸罪之外另行規定了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但1997年刑法典便將奸淫幼女罪的立法轉化為強奸罪立法的一個條款即第236條的第2款。而繼1997年刑法典,2015年11月1日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又將嫖宿幼女罪的立法予以刪除,并且將嫖宿幼女罪的立法轉化到強奸罪立法的“奸淫幼女”一款即第236條第2款之中。其實,從行為的危害和本質上,奸淫幼女犯罪不過是強奸犯罪的一種特殊類型而已,而嫖宿幼女犯罪又不過是奸淫幼女犯罪的一種特殊表現。本文作者曾經指出,“嫖宿不滿14周歲的幼女”具有“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性質,故第360條第2款“嫖宿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規定本應在第236條中作出或直接含于第236條的規定之中,因為嫖宿幼女通常是“時間較長的奸淫幼女”。而正因為忽視或輕視了“嫖宿幼女”的“奸淫幼女”性質,故把嫖宿幼女的罪刑規定在第360條之中不僅違背了罪刑均衡原則,也違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包括保護平等與懲罰平等)原則,而這一點為第236條與第360條的刑罰懸殊所印證。[17]馬榮春:《刑法完善論》,群眾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403頁。既然從行為的危害和本質上,強奸犯罪包含了奸淫幼女犯罪,而奸淫幼女犯罪又包含了嫖宿幼女犯罪,則嫖宿幼女犯罪應“類型化”到奸淫幼女犯罪之中,而奸淫幼女犯罪又應“類型化”到強奸罪之中。可見,1997年新刑法典將奸淫幼女罪的立法由原來的一個獨立的罪條轉化為強奸罪立法的一個條款即第236條第2款,其所體現的便是強奸罪立法中的類型化思維,并且在罪名上是用強奸罪吸收了奸淫幼女罪。而《刑法修正案九》對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刪除和轉化,也體現了強奸罪立法中的類型化思維。經過罪名的科學吸收,強奸犯罪的立法克服了“立法臃腫”而增強了分則個罪立法的精煉性。可見,刑法典及其分則的體系性并非一定體現為增加條文并將之理順,也體現為精簡條文而使之卸掉臃腫。于是,強奸罪立法的先后完善,可視為“前置法益主導標準”通過罪條與罪名整合影響刑法典分則體系性正面適例。
(二)“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對罪條和罪名的體系歸屬作用
“前置法益主導標準”不僅有著對具體的罪條和罪名的直接的整合作用,而且有著對罪條和罪名的直接的體系歸屬作用。如對于現行刑法第282條和第398條分別規定的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國家秘密罪和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過失泄露國家秘密罪,有人提出,出于法益侵害的同一性,應當將第282條和第398條置于“危害國家利益”一章之中,亦即在刑法典分則罪名體系中應該圍繞“國家保密制度”這一法益而作出相應的罪條安排。[18]同注②。正如我們所知,現行刑法第282條和第398條分別屬于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和第九章“瀆職罪”。但現行刑法典中尚未安排“危害國家利益罪”一章,而“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國防利益罪”,甚至貪污罪、瀆職罪都可歸屬于“危害國家利益罪”。雖然現行刑法典尚未或不宜辟出“危害國家利益罪”一章,但論者所提出的問題是有啟發意義的。具言之,將282條所規定的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國家秘密罪置于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確顯不妥,因為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國家秘密罪所針對或主要侵犯的法益應是“國家法益”,而“國家安全”也與時俱進地包含了“國家信息安全”,故將其置于“危害國家安全罪”相對妥當。至于第398條所規定的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過失泄露國家秘密罪,仍放在第九章“瀆職罪”為宜,因為瀆職罪的法益本來就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可見,“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對涉及國家秘密犯罪的章節歸屬問題也可起著根本的說明作用。
再如,現行刑法通過第151條將走私武器、彈藥罪和走私核材料罪置于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第二節“走私罪”中。其實,走私武器、彈藥罪和走私核材料罪所侵犯的“核心法益”即“主導法益”是“公共安全”,故應將其安放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適當位置,即緊隨現有的槍支、彈藥、爆炸物犯罪立法之后。但是,對于現行刑法第127條所規定的盜竊、搶奪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罪和搶劫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罪,有人指出,對盜竊、搶劫、搶奪行為的完全列舉遺漏了其他非法獲取行為而造成處罰范圍不周延,再就是搶劫行為相較于盜竊、搶奪行為具有更高的危險性,但沒有必要單列為一罪,故該條所規定的犯罪應類型化為“非法獲取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罪”[19]同注②。。其實,非法獲取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罪的犯罪手段還可包括“詐騙”,故遺漏“詐騙”是第127條的一個立法漏洞。但仍有必要單列“搶劫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罪”這一罪名,因為該罪名具有明顯的雙重法益侵害性,即該罪所對應的是一個復雜客體,故單列罪名能夠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且能夠更加有力地預防槍支、彈藥、爆炸物、危險物質犯罪。當我們強調復雜客體時,我們便采用了“前置法益主導性”思維。
“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對罪條和罪名的“體系歸屬”作用,還可有諸多反面例證。如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二節“走私罪”中的“走私廢物罪”本應規定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之中的適當位置,或安排在規定“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和“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的第339條之中,且作為其中一款。又如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洗錢罪”本應規定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二節“妨害司法罪”之中的適當位置,即安排在規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第312條之前或之后,也可考慮并入第312條之中且仍然采用“洗錢罪”這一罪名,亦可獨立成條。再如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中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本應規定在刑法典分則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中的適當位置如詐騙罪的條文之后,而這樣安排的理由正如傳銷活動其實是一種騙取財物的行為,只是由于其手段的特殊性而有將其定型化的必要,但其仍然為一種侵犯財產權的犯罪行為。[20]同注②。這里,“侵犯財產權”便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所侵犯的“核心法益”或“主導法益”,正如傳銷活動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原始型傳銷,即以銷售商品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返利的依據;二是詐騙型傳銷,即并非真正的傳銷,只是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返利的依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應是針對后一種傳銷而形成的罪名。而既然刑法典分則條文明確規定了“騙取財物”,則這一要素既不能被解釋者視為多余,也不能被解釋者直接刪除。[21]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36~837頁。另如現行刑法第262條之一規定的“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和第262條之二規定的“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此兩個罪名及其所對應的罪條不應安置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中,因為其所侵犯的“核心法益”即“主導法益”乃社會管理秩序,故本應其安置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最后如傳播性病罪,現行刑法將其罪條置于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第九節“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實際上,傳播性病罪的罪條應被安置在該章第六節“危害公共衛生罪”中,并且在解釋論上,傳播性病罪根本不在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的文義射程之內。可見,前述問題直接關涉刑法典分則,從而是整個刑法典的體系性。
罪條與罪名的“體系歸屬”問題“附帶”出罪條和罪名的所謂位階關系或包容關系問題。而對罪條和罪名的所謂位階關系或包容關系問題的解答,仍可采用“前置法益主導標準”或“前置法益主導性”思維。學者指出,刑法典分則法條本質上具有互斥性,故法條競合屬于“假性競合”。[22]葉良芳:《法條何以會“競合”——一個概念上的澄清》,載《法律科學》2014年第1期。又有學者指出,競合論方案破壞了行為類型(定型)的統一性,甚至引發同一行為類型內部的罪刑失衡,故只能采取互斥論方案。[23]王彥強:《業務侵占:貪污罪的解釋方向》,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5期。對于前述論斷,有人予以反駁,即當以類型的層級性特征重新審視刑法典分則時,則法條之間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具有層級性或包含性。以最為常見的盜竊罪和侵占罪為例,由于盜竊罪的犯罪類型表現為“侵犯占有,據為己有”,而侵占罪的犯罪類型表現為“據為己有”,故盜竊罪與侵占罪之間便形成了位階關系、包容關系。這種從“互斥”到“包容”的關系轉變同樣適用于處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強奸罪”與“強制猥褻罪”、“貪污罪”與“盜竊罪、詐騙罪”之間的關系。而從類型的層級性特征切入,將上述犯罪從互斥關系理解為包含關系,有利于減少各罪之間的排他關系,而具體犯罪之間的包容關系能夠使得罪名體系之間更為協調。通過罪名體系的類型化改造,得以化解法律漏洞、評價不充分、共犯定性等司法適用難題。[24]同注②。當對照刑法典分則的章節條結構,則刑法典分則中跨越“章域”的不同個罪之間,是根本不存在位階或包容關系的,如分裂國家罪與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法典分則同一“章域”乃至同一“節域”內部的不同個罪之間,也是不存在位階或包容關系的,如“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強奸罪”與“強制猥褻罪”之間。在此,僅以“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區別便可說明問題。具言之,雖然二者可歸屬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但二者又存在“質”的區別,即前者所侵犯的是公民的生命法益,而后者所侵犯的是公民的健康法益。可以想見的是,所謂個罪之間是位階或包容關系才真正引起司法實踐無所適從。至于所謂“處罰漏洞”,其真正所指即個案事實不清時的定性疑難,而這首先是個事實認定問題,且可按“疑罪從輕”予以“便宜行事”。可見,我們不能由此無端生出個罪之間存在著所謂位階或包容關系。不過,刑法典分則各章與其內部各節之間、各節與其內部各條之間是大致存在著所謂位階或包容關系的,而前述位階或包容關系正是前置法益的位階或包容關系。而正是前置法益的位階或包容關系在“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的不同順位的“提綱挈領”之下才形成了刑法典分則,從而也是整部刑法典的體系性。學者指出,對于某種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為,如果現行刑法條文已經將其涵括在內,則除非有新的法益保護需要,否則不得增設新罪。[25]葉良芳:《擾亂法庭秩序罪的立法擴張和司法應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第37條為評析對象〉》,載《理論探索》2015年第6期。可見,由于刑法典分則個罪所對應的是前置法益侵害的類型性,故刑法典分則,從而也是整部刑法典的體系性最終還是有賴前置法益的類型性及其體系性作出根本性的說明。而在前述說明過程中,刑法典分則罪條和罪名之間的關系,也就同時或順帶得到了說明。而“前置法益主導標準”正是此說明的切實擔當。
(三)“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對刑法典分則的“章節建制”作用
這里,我們可由法規競合問題來開啟討論。如對于特殊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的立法關系問題,有人指出,在詐騙類型的犯罪中,經濟秩序的破壞也通過對具體犯罪對象財產權的直接侵害造成的,很難說在侵犯財產權利之外,還有獨立于該法益之外的重大法益侵害的存在。因此,于普通詐騙罪之外設立特殊的詐騙罪,是否必要值得反思。[26]同注②。正如我們所知,特殊類型的詐騙罪立法與普通詐騙罪立法之間是一種立法現象,即法規競合或法條競合。實際上,法規競合或法條競合是事物的“特殊”與“一般”的競合。這里,“特殊”與“一般”的競合在事物的表相上是犯罪手段和犯罪領域在“特殊”與“一般”關系之中的競合,而實質上是前置法益侵害在“特殊”與“一般”關系之中的競合即“前置法益侵害競合”。當特殊的法益侵害在一般的法益侵害的基礎上形成了“額外的成份”,而此“額外的成份”需要予以特別保護,則相關罪刑規定便有了“專節”乃至“專章”設置的立法必要。實際上,刑法典分則中的法條競合關系所體現出來的是刑法保護客體或前置法益的類型化,并且是縱向類型化,因為法條競合關系所反映的是前置法益即犯罪客體從“一般”到“特別”的演化。這里,“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對刑法典分則,從而是整個刑法典體系的影響,便通過法規競合及其章節設置問題又得到了一番例證。
“前置法益主導性”不僅是在刑法典分則的章與章之間影響著刑法典分則的體系性,而且會在某一章本身的設置影響著刑法典分則的體系性。如有人主張將第403條“濫用管理公司、證券職務罪”、第404條“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第405條“徇私舞弊發售發票、抵扣稅款、出口退稅罪”、第407條“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第408條“環境監管失職罪”、第408條之一“食品監管瀆職罪”、第409條“傳染病防治失職罪”、第410條“非法批準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第411條“放縱走私罪”、第412條“商檢失職罪”、第413條“動植物檢疫失職罪”、第414條“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罪”、第415條“辦理偷越國(邊)境人員出入境證件罪”“放行偷越國(邊)境人員罪”第416條“不解救被拐賣、被綁架婦女、兒童罪”“阻礙解救被拐賣、被綁架婦女、兒童罪”、第418條“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和第419條“失職造成珍貴文物損毀、流失罪”,全部歸入第397條“濫用職權罪”或“玩忽職守罪”中,或依據侵害法益的同一性而將各個領域的瀆職犯罪分別歸入相應章節之中。將前述諸罪全部歸入第397條“濫用職權罪”或“玩忽職守罪”中,或按犯罪領域分別歸入相應章節,此即論者所說的“兩個方案”。而“兩個方案”的理由是:這些罪名都是特殊的瀆職行為,完全可以被第397條所涵蓋,并且這些罪名都屬于瀆職一個犯罪類型,只是瀆職行為發生的具體領域的不同,故為各行各業的瀆職犯罪單獨設立罪名確無必要。[27]同注②。若是按照論者的主張和思路,則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九章“瀆職罪”就只能保留第397條。若是這樣,則第九章“瀆職罪”也就不成其為一章。正如我們所知,現行刑法典第九章“瀆職罪”的第1條即第397條與該章其余各條是法規競合或法條競合關系,而正是在“一般”與“特殊”的競合之中,第九章“瀆職罪”才成為較豐滿的一章,或至少在“體量”上堪成一章。顯然,按照論者的主張和思路,現行刑法的體系性將受到很大的影響或“折損”。于是,對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九章“瀆職罪”的體系性安排問題,還得回到法益思路上來尋求答案。易言之,按照“前置法益主導性標準”,論者的“兩個方案”都是不可取的。具言之,將前述諸罪全部歸入第397條“濫用職權罪”或“玩忽職守罪”中,這顯然是逆“前置法益類型化”而動;將前述諸罪按犯罪領域分別歸入相應章節,也是逆“前置法益類型化”而動,如將第411條放縱走私罪歸入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第二節“走私罪”中,雖然放縱走私罪也同時侵犯了走私罪所侵犯的法益,但其另有法益侵害,即對公職行為廉潔性的侵害。可見,放縱走私罪因另有法益侵害而與走私罪并未形成所謂“侵害法益的同一性”,且放縱走私罪在“另有法益侵害”之中形成了“前置法益侵害主導性”和“前置法益侵害類型性”。可見,只要肯定犯罪類型標準的“前置法益主導性”,則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九章“瀆職罪”就得保留作為一章的“獨立建制”。由此,刑法典分則的體系性最終是服務于前置法益保護的,故刑法典分則的體系性,最終取決于前置法益保護的需要。但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形成需要主動接受“前置法益主導性”思維的引導,而“前置法益主導標準說”即“前置法益保護論”。
仍由刑法典分則第九章“瀆職罪”的立法問題說開去。有人指出,立法罪名設置標準的不統一,即“一事一罪”的罪名設置模式使得罪名體系顧此失彼、零散孤立。如我國《刑法》第九章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主體劃分依據部門、行業、職責等采用了不同的標準,且原因是刑法典分則第九章的相關條文均來源于單行刑法或附屬刑法,且未在移入刑法典時進行類型化處理,而是直接排列在刑法典分則之中。這就導致了罪名的重復、龐雜以及評價的不充分。而如何將其在數以百計的罪名體系中作出安置,則需要從整體性視角進行類型化處理。[28]同注②。正如我們所知,現行刑法第九章的第1條是關于瀆職罪即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的一般性規定,而該章其余各罪都是瀆職罪的類型化。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將該章第1條關于瀆職罪的一般規定視為“同質抽象”,而其余各罪則為“具象列舉”。易言之,整個第九章就是一個倒置的“具象列舉+同質抽象”的刑法規范模式。其實,當刑法第九章那些具體類型的瀆職罪來源于“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其正是犯罪類型標準的“前置法益主導性”的有力體現。而前述體現及其所對應的瀆職罪立法的類型化,不僅不存在論者所說的罪名體系的顧此失彼、零散孤立等問題,反而是科學合理的。在相當程度上,刑法典分則第九章為我們如何進行刑法典分則立法的類型化,特別是法定犯立法的類型化作出了一種“試驗”。而在此“試驗”中,不僅犯罪類型標準的“前置法益主導性”得到了有力堅持,而且“法秩序一致性”的違法性立場也得到了堅持。因此,如果將刑法第九章的現有罪條即罪名分散到其他各處,那才是“反類型化”的。至于該章所存在的其他問題,并不影響該章現有體系總體安排的科學合理性。
“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對刑法典分則章節建制的影響,還可聯系網絡犯罪予以進一步深化。有人將第285條“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第286條“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第286條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第287條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和第287條之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統括為“網絡犯罪”。由于網絡犯罪在定義和特征上與傳統的犯罪行為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把網絡犯罪歸類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既不利于法律規范的完整性,也不利于對網絡犯罪的認定處罰,故有必要在刑法典中單設“網絡犯罪”章節,以此來彌補網絡犯罪規定的類型性不足。[29]同注②。盡管目前學界對“網絡犯罪”的界定還存在著分歧,但“網絡犯罪”作為一種成型的犯罪現象是不容置疑的。而作為一種成型的犯罪現象,“網絡犯罪”必有其“成型的法益侵害性”,亦即“網絡犯罪”必具有相應的“前置法益侵害類型性”。這就為“網絡犯罪”在刑法典分則體系中的“章節性”準備了事實根據與價值根據。實際上,將“網絡犯罪”規定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暫無不當,不當之處只在于沒有對“網絡犯罪”予以“專節化”,而“專節化”正是“類型化”的一種昭示。隨著“網絡犯罪”理論與實踐的深化,“網絡犯罪”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的“專節化”應該是遲早的事。
“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在宏觀上還可引導“章罪”的體系性安排。有人主張將現行刑法第八章“貪污賄賂罪”中的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通過“類型化”為財產犯罪而歸入第五章“侵犯財產罪”,另將賄賂犯罪(包括受賄罪和行賄罪)歸入第九章“瀆職罪”[30]同注②。。前述主張和思路意在消除“貪污賄賂罪”在現行刑法典中“獨成一章”的體系性地位。其實,相較于一般的財產犯罪,貪污賄賂犯罪也帶有“財產(物)性”,正如我們將貪污俗稱為“官盜”,但貪污賄賂犯罪的犯罪屬性又另有“職務性”;而相較于一般的瀆職犯罪,貪污賄賂犯罪也帶有“職務性”,但貪污賄賂犯罪的犯罪屬性又另有“財產(物)性”。可見,貪污賄賂犯罪是“財產(物)性”和“職務性”“相交集”的犯罪類型。而“財產(物)性”和“職務性”“相交集”正是貪污賄賂罪“前置法益類型性”與“前置法益主導性”的直觀外顯。因此,無論是將現有的貪污賄賂罪立法通過分解而歸入“侵犯財產罪”和“瀆職罪”,還是向“侵犯財產罪”或“瀆職罪”作整體搬遷,都是不適合的。易言之,保留“貪污賄賂罪”的“獨立成章”的地位,仍然是現行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需要。雖然距離第五章“侵犯財產罪”的距離較遠,但“貪污賄賂罪”位于第五章“侵犯財產罪”與第九章“瀆職罪”之間,則多少有點“承上啟下”的意味,而“承上啟下”的意味便是“體系性意味”。
從對罪條與罪名的整合作用到罪條和罪名的“體系歸屬”,再到刑法典分則的“章節建制”,“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對刑法典分則的體系性及整個刑法典的體系性的指導和調適作用,得到了不同層次的實證與體現。
三、現行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檢視與重構
(一)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檢視
1.刑法典分則第二章體系性的類型化檢視。首先,現行刑法典分則應將“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予以分節。由于公共安全涉及諸多方面或領域,故刑法典分則第二章未予分節便顯得較為雜亂,從而缺失體系性。而在將散落于刑法典分則其他各處的,甚至立法新增的以公共安全為侵害客體的罪條收攏之后,則該章將顯得更加雜亂,更無體系性可言。因此,我們有必要按照公共安全所涉及的方面或領域對該章進行分節。第二章體系性的缺失是由立法者缺失“前置法益類型化”和“前置法益主導性”思維所造成的。而若采用“前置法益類型化”和“前置法益主導性”思維,則“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似應按照以下罪名作為節罪名進行分節:“破壞類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險品類危害公共安全罪”、“事故類危害公共安全罪”、“衛生類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劫持類危害公共安全罪”等。
第二章不僅應予分節,而且還應將散落在其他章節的以公共安全為客體的罪條和罪名“移民”到相應的節中或根據需要另外設節,如第六章“破壞社會管理秩序罪”第五節“危害公共衛生罪”應歸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因為所謂公共衛生,實是有關公眾健康和生命的安全而應視為公共安全的一個方面。又如刑法典第338條和第339條也應歸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并將之置于“事故類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節之下,因為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和第339條“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最終危害的仍是公私財產安全和公眾健康與生命安全。由于對此兩種犯罪予以刑法規制的目的自然在于保護公私財產安全和公眾健康、生命安全,故將此兩種犯罪歸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事故類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節之下便順理成章。
2.刑法典分則第三章體系性的類型化檢視。首先,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因強調過多而使章名不僅概括不了節名,反而小于節名。在我國刑法任務的規定中,“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這一表述已經清楚地昭示了我國刑法的社會主義性質。這一性質像靈魂一般貫穿或滲透于整個刑法典包括“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中。而就在我國刑法任務的前述規定之中,“經濟秩序”之前已沒有了“社會主義”四個字的修飾或限制。我們之所以審視“社會主義”這一修飾語,是因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1]《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因此,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名之中,“社會主義”四個字完全顯得多余。易言之,既然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則“社會主義”本來就不用再強調了,況且“市場”本身就隱含著“經濟”問題或“市場”本身就天然地具有“經濟”屬性,故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名之中“經濟”二字也完全顯得多余,即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的章名問題上,只是提出去掉“社會主義”四個字還未能將問題解決得徹底干凈,[32]參見范忠信:《刑法典應力求垂范久遠——論修訂后的〈刑法〉的局限與缺陷》,載胡馳、于志剛主編:《刑法問題與爭鳴》,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頁。而還應去掉“經濟”二字。然而,由于“社會主義”和“經濟”的累贅或多余強調,第三章的章名不僅概括不了其下節名,而且小于有的節名即“擾亂市場秩序罪”,因為“市場秩序”顯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屬概念。可見,“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名應當簡煉為“破壞市場秩序罪”。
在將第三章的章名簡練為“破壞市場秩序罪”之后,則該章第八節的節名“擾亂市場秩序罪”又顯得不妥,因為節名與章名將平起平坐。在本文看來,除了第228條“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應歸入“破壞環境資源犯罪”之中,因為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幾乎都導致對土地資源的濫用和破壞,本節所規定的其他犯罪即第221條“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第222條“虛假廣告罪”、第223條“串通投標罪”、第224條“合同詐騙罪”、第225條“非法經營罪”、第226條“強迫交易罪”、第227條“偽造、倒賣偽造的有價票證罪”、第229條“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和第230條“逃避商檢罪”,都可以概括為“擾亂競爭秩序罪”。需要作進一步說明的是,把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虛假廣告罪、串通投標罪、合同詐騙罪、強迫交易罪視為擾亂競爭秩序的犯罪很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但是,非法經營罪,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偽造、倒賣偽造的有價票證罪和逃避商檢罪與擾亂競爭秩序又有何干系呢?非法經營罪,無論是經營未經許可經營的專賣品或限制品,還是買賣經營證件,都是謀取不正當的市場競爭優勢或競爭條件;無論是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還是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都是虛擬不實的競爭優勢或競爭條件;偽造、倒賣偽造的有價票證罪是直接與合法經營行為進行非法競爭的行為;逃避商檢罪是將可能不被允許進入商業流通的商品即沒有合法競爭資格的商品擠進商業流通而參與競爭。可見,這些犯罪都與競爭秩序直接相關。于是,當第三章采用“破壞市場秩序罪”這一章名之后,該章第八節“擾亂競爭秩序罪”這一節名便是“前置法益類型化”和“前置法益主導性”的思維體現。
另外,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與第五節“金融詐騙罪”的并列也不合邏輯。金融詐騙罪與詐騙罪的關系是法規競合的關系而本來同屬于財產犯罪,但金融詐騙罪另有侵犯客體即金融秩序,故金融詐騙罪才被規定在我們應該將其簡稱為“破壞市場秩序罪”的這一章而非“侵犯財產罪”一章。由于第五節“金融詐騙罪”本來就是破壞金融秩序的犯罪,故其不應與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相并列,而應將此兩節合為一節。由于“秩序”本來就因“管理”而成或“秩序”本來就有“管理”意味,故第四、五兩節合并后的節名宜采“破壞金融秩序罪”。“破壞金融秩序罪”和“金融詐騙罪”的兩節并列,同樣暴露了立法者“前置法益類型化”和“前置法益主導性”的思維欠缺。
3.刑法典分則第四章體系性的類型化檢視。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包含著“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和“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其中,“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走過了從無到有的過程,正如在1978年底至1979年上半年創制現行刑法典的過程中,鑒于“文化大革命”中任意踐踏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慘痛教訓,在立法指導思想上,不但重視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也進一步強調了對公民民主權利的保護,故刑法草案稿第33稿“侵犯人身權利罪”一章的章名被改為“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并被列為現行刑法典分則的第四章。至于為何要把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與侵犯公民民主權利這兩類犯罪規定在一章,這是由于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的條文較少,故列為單章將與其他各章不相協調。另外,民主權利與人身權利聯系密切,把二者合并規定在一章主要是出于立法技術考慮。[33]趙秉志主編:《刑法修改研究綜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頁。其中“現行刑法典”是指79年刑法典。但是,有人明確提出將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列為單章的建議,理由如下:一是對犯罪進行科學分類的需要;二是強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大力保護公民民主權利的迫切需要;三是體現刑法對公民不同類型權利(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財產權利、婚姻家庭權利)的普遍重視與保護需要;四是許多國外刑法典單章規定了“侵犯民主權利罪”。[34]同注[33],第83~84頁。除了前述理由,還有人指出,現行刑法中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的罪名和條文雖然少一些,但不應妨礙其單獨成章,而且如果將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單列一章,還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和可能,增補和充實一些罪名與條文。[35]同注[33],第84~85頁。應該肯定的是,早就提出的“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應單列成章的主張及其理由有一定道理。但基于民主權利與人身權利的緊密關聯性,即二者都屬于公民權利范疇,另有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具有對公民民主權利和人身權利的雙重侵害性,故第四章未作適當分節便映現了立法者“前置法益類型化”和“前置法益主導性”的思維欠缺。而在作出“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和“侵犯公民婚姻家庭權利罪”分節之后,可考慮將“暴行罪”和“恐嚇罪”等增補到“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中,將妨害集會、游行、示威罪和冒名頂替罪(在國家考試和公務職位選拔中)等增補到“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中。總之,第四章也是需要采用“前置法益類型化”和“前置法益主導性”的思維來形成其體系性的。
4.刑法典分則第六章體系性的類型化檢視。首先,“危害公共衛生罪”一節安放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不妥,理由已如前述,在此不贅。再就是,“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一節安放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不妥。環境資源既直接關涉公眾的健康、生命,也直接關涉公私財產利益,還直接關涉社會經濟的發展,故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所侵害的客體或法益是多方面的,甚至是最具公益性的,亦即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的客體有其獨特性即綜合性或包容性。因此,從強化環境保護和環境刑法本身的發展與完善計,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的犯罪應單立一章而不應作為一節“雜燴”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德國等國家將污染環境的犯罪單立一章的立法例值得我們借鑒,[36]參見《德國刑法典》,徐久生、莊敬華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226頁。而國內早有人提出專章設立“破壞自然資源罪”[37]同注[32],第81頁。,理由如下:一是加強國家對自然資源保護的迫切需要;二是完善有關刑法規范的需要;三是便利司法實踐的需要。[38]同注[32],第85~86頁。看來,將“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單列一章確實是必要的,并且“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無論是作為刑法典分則的節名,還是作為刑法典分則的章名,都宜稱之為“破壞環境資源罪”,“保護”二字純屬累贅。
另外,將“妨害司法罪”一節安放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也不妥。
社會管理秩序這一概念有廣狹義之分。所有類型的犯罪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和破壞經濟秩序的犯罪所侵犯的客體都可歸入廣義的社會管理秩序這一概念之中,因為所有類型的犯罪都是擾亂社會管理秩序的行為。顯然,“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社會管理秩序只能作為一個狹義的概念對待,因為在刑法典分則中“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作為一種犯罪類型是與其他犯罪類型相并列的。但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第二節“妨害司法罪”中,諸如第305條“偽證罪”、第306條“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第307條“妨害作證罪”“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第308條“打擊報復證人罪”、第310條“窩藏、包庇罪”、第311條“拒絕提供間諜犯罪證據罪”、第312條“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第313條“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第314條“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都很難說是直接侵犯了社會管理秩序這一客體,而只有第309條“擾亂法庭秩序罪”、第315條“破壞監管秩序罪”、第316條“脫逃罪”“劫奪被押解人員罪”、第317條“組織越獄、暴動越獄、聚眾持械劫獄罪”,才勉強可以說是直接侵犯了社會管理秩序這一客體。可見,現行刑法典分則把“妨害司法罪”安放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并不妥。實際上,“妨害司法罪”這一類罪的客體也是一個綜合性客體,如打擊、報復證人罪直接兼犯了公民人身權利這一客體,而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則直接兼犯了財產權利這一客體。因此,妨害司法罪的客體也有其獨特性即綜合性或包容性。可見,在刑法典分則之中,正如“破壞環境資源罪”,“妨害司法罪”這一節也應獨成一章,正如早就有人提出在刑法典分則中增設“妨害司法活動罪”專章的建議,[39]同注[32],第79頁。且理由如下:一是對有關犯罪進行科學歸類的需要;二是單列專章有助于保障國家司法活動的順利進行和加強法制;三是現代許多國家的刑法中都有妨害司法活動這類犯罪的專門規定。[40]同注[32],第86頁。《德國刑法典》將“未經宣誓的偽證和偽誓犯罪”獨成一章[41]同注[36],第136~137頁。,《日本刑法典》將“脫逃罪”獨成一章和將“藏匿犯人和隱滅證據罪”獨成一章[42]《日本刑法典》,張明楷譯,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6頁。,瑞士刑法典將“妨礙司法的重罪和輕罪”也獨成一章[43]《瑞士聯邦刑法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7~99頁。,這些立法例對我們把握“妨害司法罪”的章節問題應有所啟發。總之,將“妨害司法罪”由一節上升為獨立一章也確有必要,特別是在“法治中國建設”的背景下。
最后,本章有關節名不能統率其下各條,即相關節名不妥。此處所言的相關節名即第七節節名“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和第九節節名“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為何說第七節節名不妥呢?既然是節名,那就能夠統率屬下所有條文。但是,該節之下規定“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的第353條、規定“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第354條和規定“非法提供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罪”的第355條,顯然是該節現有節名所不能統率的,而本節節名應概括為“妨害毒品管制罪”。為何說第九節節名不妥呢?因為規定“組織淫穢表演罪”的第365條是該節節名所不能統率的。其實,第八、九兩節可以概括為“妨害淫亂管制罪”。
5.刑法典分則第七章和第十章體系性的類型化檢視。首先,第七章“危害國防利益罪”和第十章“軍人違反職責罪”不應并列并分開。從現有規定的實際內容來看,危害國防利益的犯罪所侵犯的利益都可歸為軍事利益,而軍人違反職責的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就是軍事利益。由于國防直接是靠軍事來擔負,故基于兩者的相互聯系,“危害國防利益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應合并為“危害軍事罪”,而不是相互并列并隔著第八章“貪污賄賂罪”和第九章“瀆職罪”兩章的距離。為何不將“危害國防利益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合并為“危害國防(利益)罪”呢?因為“國防”或“國防利益”在相當程度上與“國家安全”同義,故前述合并將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罪”和“危害國防(利益)罪”界限模糊不清。其次,由于軍人違反職責特別是軍官違反職責也是一種瀆職,故將“危害國防利益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合并為“危害軍事罪”,也可免去“軍人違反職責罪”和第九章“瀆職罪”的邏輯重疊。最后,第七章與第十章的并列也反映了新刑法典形成過程中的機械照搬。所剩問題是,當我們將第七章“危害國防利益罪”和第十章“軍人違反職責罪”合并為“危害軍事利益罪”一章之后,為體現“危害軍事利益罪”一章的結構性,我們可用“非軍人危害軍事利益罪”和“軍人危害軍事利益罪”來分別統率原由“危害國防利益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所統率的條文。
此外,第七章“危害國防利益罪”和第十章“軍人違反職責罪”的分則位置不應靠后。在整個法律體系之中,刑法是作為最后的手段來調整社會矛盾的。因此,刑法可視為保護最重要或最根本的法益的部門法。與此相對應或相呼應,世界各國刑法典分則的犯罪排列通常是按照犯罪所侵犯法益的重要程度或重要順序即由重到輕予以排列。在我國,國家安全幾乎毫無異議地被普遍接受為社會最高法益,故“危害國家安全罪”當之無愧地被排在了刑法典分則的首位。由于國家安全在相當程度上是靠軍事來維護,故將“危害國防利益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合并而來的“危害軍事罪”排在“危害國家安全罪”之后即排在刑法典分則第二章,是符合我們的價值序位的。有的國家如德國將在內容上與“危害軍事罪”相通的“危害國防的犯罪”排在刑法典分則的靠前位置,對于我們把握“危害軍事罪”的分則位置問題不無啟發。[44]同注[36],第38頁。
由上論述可見,“前置法益類型化”和“前置法益主導性”思維,既是一種分解性思維,也是一種統合性思維。
(二)現行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重構
刑法典分則的體系性,應在類型化之中采用“前置法益主導標準”或“前置法益主導性”思維予以新安排,且此新安排應體現為章節結構的重新規整與排序。關于刑法典分則各章的排序,早就有人指出,調整分則各章犯罪的理由有四:一是基于對各類犯罪總體社會危害性大小的考慮,這是我國刑法典分則排列各類犯罪首要應予考慮的;二是基于對各章彼此間邏輯聯系的考慮,這是刑法典分則體系和結構的科學性也要求考慮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便利司法適用的需要;三是考慮特殊問題的特殊需要,這也是分則體系科學合理和便于司法適用的要求;四是基于同憲法有關規定相協調的考慮,如將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將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和妨害婚姻家庭罪連在一起緊接其后排列。另有人作出補充,即刑法典分則各章次序的排列,不能遵循單一標準,而應綜合考慮諸種因素。[45]同注[33],第87~88頁。在本文看來,綜合考慮“諸種因素”來確定分則各章的排序在總體思路上是對的,但“諸種因素”存在主次之分,或曰“諸種因素”是有“主導因素”的,而所謂各類犯罪總體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不過是“主導因素”的另番詮釋。最終,刑法典分則的章節安排及其體系性,仍須在“前置法益主導標準”之下或在“前置法益主導性”思維之中得以進行和形成。
按照上文對刑法典分則章序方法與標準的粗略把握并結合前文對刑法典分則相關罪章結構的檢視,本文將刑法典分則按章序排列如下: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第二章“危害軍事利益罪”、第三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第六章“破壞環境資源罪”、第七章“破壞市場秩序罪”、第八章“貪污賄賂罪”、第九章“瀆職罪”、第十章“妨害司法罪”、第十一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這里還要作如下具體交代:其一,“危害國家安全罪”所關涉的法益最為重大,故置于第一章當無疑問。由于軍事利益直接支撐著國家安全,故將“危害軍事利益罪”置于“危害國家安全罪”之后。此即“基于對各類犯罪總體社會危害性大小的考慮”。有人曾指出,無論從哪個角度,危害國防利益罪的社會危害性都是僅次于危害國家安全罪的,甚至國防的安全就是國家的安全,故危害國防利益罪應當合并到危害國家安全罪中,或者排在危害國家安全罪之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前。但新刑法卻把危害國防利益罪排在第七章,似乎國防利益還不如公私財產重要。[46]侯國云、梁志敏、張起淮:《論新刑法的進步與失誤——評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載胡馳、于志剛主編:《刑法問題與爭鳴》,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頁。本文贊同這一看法,但就危害國防利益罪與軍人違反職責罪兩者的比較而言,僅次于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應是軍人違反職責罪而非危害國防利益罪,這是由犯罪主體的身份及其犯罪能量的不同所決定的。當我們把軍事利益看作是危害國防利益罪與軍人違反職責罪的共同客體,則可以打個不盡恰當的比喻:軍人違反職責罪對于軍事利益的侵害更是“近水樓臺”。而當我們把危害國防利益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通過共同法益即共同客體予以概括提升后來解決章序問題,則我們的視野將更開闊。其二,環境污染和破壞越來越嚴重,而環境本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且環境權益包含著人身權益、財產權益等成份,故將“破壞環境資源罪”置于“破壞市場秩序罪”之前。這既可以說是“基于對各類犯罪總體社會危害性大小的考慮”,也可以說是“基于對各章彼此間邏輯聯系的考慮”。其三,從所規定的犯罪的實際內容看,“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在整體上所侵犯的利益的刑法地位最輕,故將“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置于末章。這也是直接“基于對各類犯罪總體社會危害性大小的考慮”。
接著上文所確定的章序,則刑法典分則的章節結構可大致顯示如下:
第二編 分則
第一章 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軍事利益罪
第一節 軍人危害軍事利益罪
第三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一節 破壞類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節 危險品類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節 事故類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四節 衛生類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五節 劫持類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第一節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
第二節 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
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綠色發展”成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將“綠色”納入新時期建筑八字方針。在此形勢下,持之以恒、更高標準推動綠色建筑發展成為建設綠色生態文明城市的重要方向。基于此,按照廣州市綠色發展走在國家前列的要求,為進一步提升綠色建筑發展水平,制定了《廣州市“十三五”建筑節能與綠色建筑規劃》,提出到2020年新建建筑全面執行綠色建筑標準,二星級以上綠色建筑占綠色建筑總量的比重達到20%以上,同時創建5個以上綠色生態示范區。
第三節 侵犯公民婚姻家庭權利罪
第五章 侵犯財產罪
第六章 破壞環境資源罪
第七章 破壞市場秩序罪
第一節 危害稅收征管罪
第二節 走私罪
第三節 破壞金融秩序罪
第四節 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
第五節 妨害公司、企業管理秩序罪
第六節 侵犯知識產權罪
第七節 擾亂競爭秩序罪
第八章 貪污賄賂罪
第九章 瀆職罪
第十章 妨害司法罪
第十一章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第一節 妨害公共秩序罪
第二節 妨害國(邊)境管理罪
第三節 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四節 妨害毒品管制罪
第五節 妨害淫亂管制罪
第六節 妨害信息網絡管理罪
從刑法典分則體系性類型化強化的標準選擇到標準運用,再到現行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檢視和重構,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強化首先是個“求真務實”的過程,而“求真務實”的過程就是謀求刑法立法科學性的過程。同時,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強化過程又是一個達致“刑法立法之美”的過程。具言之,從內到外,刑法典分則由條構成節,由節構成章,由章構成篇;而從外到內,刑法典分則分解為若干章,各個章又分解為若干節,各節又分解為若干條。刑法典分則儼然一幢建筑物,其“外觀之美”即“形式之美”可幻化為“形成之美”和“條理之美”、“結構之美”和“體系之美”、“ 呈現之美”與“表達之美”。不僅如此,通過類型化強化,“前置法益主導標準”又賦予刑法典分則體系以“內在之美”即“價值之美”。由此,“外在之美”與“內在之美”便裝飾了刑法分則立法的“大門面”,而此“大門面”直接牽扯著刑法立法的公眾認同,[47]馬榮春:《刑法公眾認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頁。因為“外在之美”和“內在之美”直接增強著刑法作為行為規范的規范效果。而“前置法益類型化”與“前置法益主導性”思維卻是裝飾刑法典分則“外在之美”和“內在之美”的“大手筆”。“真”即“善”,“善”即“美”,故刑法典分則體系性的類型化強化有著“刑法真善美”的科學高度、價值高度和審美高度。刑法典分則的體系性問題是刑法立法科學化的題中之義,而“類型化方法”應視為一種極其重要的“刑法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