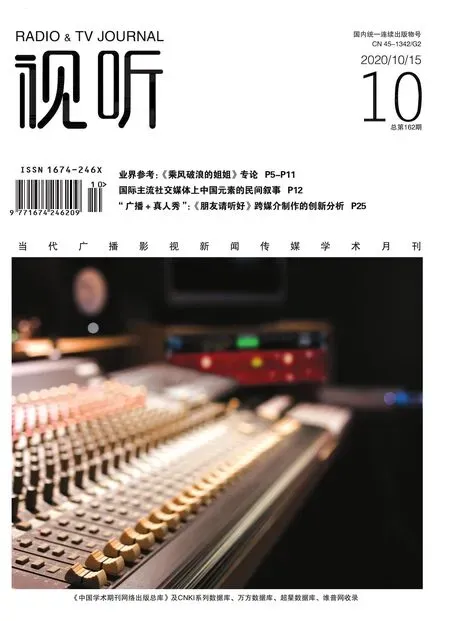《何以為家》:全球視域下家庭倫理的失語和難民問題的癥結
□ 邢德蓮 劉瑋康
《何以為家》是黎巴嫩女導演娜丁·拉巴基執導的一部偽記錄式的現實主義題材影片,自上映以來好評不斷。影片中暴露出的難民問題更是在極大范圍內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和討論。影片以難民問題為切入口,對現實主義進行尖銳批判,呈現眾生相的社會橫切面,也贊揚了那些在絕望困境中生存、努力突破原生家庭限制的人們,充滿了人道主義的光輝。
一、生存與生活模糊的界限——對現實主義的尖銳批評
(一)罪惡和苦難的根源
影片是小主人公贊恩對于父母生而不養的控訴。父母是贊恩悲劇的來源,他們把男孩當成賺錢的工具,把女孩當成抵扣房租的商品,他們不在乎大兒子蹲了監獄,也不在乎小女兒11歲就因為懷孕生子血崩而死,反而信誓旦旦地表示這是為了讓孩子“脫離苦難”。贊恩所起訴的不僅僅是生而不養的父母,更是在起訴這個混亂的世界。在戰爭和貧窮肆虐的國家,人們不為生活,只為生存。贊恩所遭受的苦難,是所有中東難民的真實生活寫照,真正“惡的源頭”不是父母而是戰爭,它是讓這個社會扭曲、讓人們墮落卻無法翻身的根源。人們顧不上生活,因為生存本身就是恩賜。
(二)殘酷現實中家庭倫理的失語錯位
家庭倫理的錯位跟戰亂的社會背景有著根本關系,家庭倫理道德,即整個家庭成員之間關系的原則與規范。贊恩起訴父母是家庭倫理失語的直接表現,但是他不僅起訴了自己的父母,更把話語直指這個混亂的世界。他所遭受的家庭生而不養是全球視域下難民家庭的映照。在戰亂地區,孩子們的不幸、家庭的不幸從來都不稀奇。他在游樂場扒開了女性雕塑的衣服露出雙乳,是他從內心里渴望回歸家庭獲得母愛的心理流露,家庭倫理的失語帶給贊恩的是超乎年齡的成熟和穩重。他毫無怨言地幫助家庭做事掙錢,更在與妹妹的相處中形成了在后天社會中極為難得的同理心和人性的善良。
贊恩的父母生而不養,黑人女人卻展現出了相反的一面,偽造身份偷偷地撫養兒子,這何嘗不是對家庭倫理的諷刺?當女人被關了起來以后,贊恩像嬰兒的哥哥撫養他,更像是一個“母親”,他為了不讓父母賣掉妹妹而跟父母起了爭執,也正因為他心中倫理的天秤,他不忍心將女人的孩子交給人販子。在殘酷的現實中,這不是道德選擇,而是生存選擇。家庭倫理的失語錯位,是社會壓迫的絕對無奈。
二、邊緣人群全力突破階級禁錮——貧窮是最深沉的原罪
(一)社會對人性的碾壓
當一個國家和地區連宗教都無法維護秩序時,當人民失去了精神信仰后,它就真正地進入了一種最原始的混亂。國家的動蕩不安,不足以保護小家,傳統的錯誤思想根深蒂固,贊恩想保護自己的妹妹,但擋不住現實社會的不公,也失去了他這個年齡該有的童真與快樂。受限于傳統觀念和意識形態下的家庭不得不掙扎在溫飽線上,所有的人性都會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低頭。贊恩身上展現的,正是個體處于悲慘境遇中的生存與抉擇中的沖擊力量。
影片中掛滿書包的校車多次出現,暗示我們贊恩的原生生活和他的理想生活之間的界限是無法跨越的。當贊恩最后也不得不用小孩換取生活的理想時,他的臉上不僅僅是抑郁,還有不舍和內疚。犧牲他人的利益來換取自己的自由,贊恩在這一刻會不會想起自己的父母賣掉自己妹妹時的場景?是否也能對父母的處境感同身受?他哭喪的表情下隱藏的是對自我的內疚和不安。人在重壓之下不得不拋棄本性,這就是社會對人性的碾壓。
(二)絕望中的困境與選擇
在烏云籠罩的社會陰影下,擺脫不了難民身份的他們都分別做出了選擇。父母為了生存做出了選擇,戰爭帶來的貧困導致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兒送給房東做老婆。他們就像社會的寄生蟲一樣,處在被社會隨時拋棄的邊緣,他們在苦苦掙扎,生孩子對他們來說,無疑是翻身的一種機會。
贊恩在惡劣的生存條件和不堪的家庭環境下選擇離家出走,打工掙錢,同樣也是孩子的他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照顧黑人婦女孩子的重擔,但是面對生存危機時他還是把這個孩子賣給了人販子。在這種雜亂無序的社會大環境下,他根本就沒有能力去關注每一個可憐的人,他賣掉這個小孩的行為從表面上看和自己的父母賣掉親生女兒的行為一樣,但是追溯至根源,這一切都是在生存和困境中的掙扎下所做的迫不得已的選擇。
以贊恩為代表的難民群體為了擺脫困境冒著生命危險去偷渡,在知道自己要承擔巨大風險的同時還是躍躍欲試,拼命一搏。這是生存的選擇,也是人性的選擇,是社會碾壓了人性,是人只能靠自己來改變命運的絕望的結果。
三、社會運行的規則——無法緩解的絕望和死循環
(一)對混亂失序社會的抗爭
“我要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我”。贊恩將自己視為家庭共同獨立體外的獨立個人,將父母的角色拋擲在傳統價值的背面,人類自然而然的生育繁衍卻是片中流民家庭走向畸變的始作俑者。
性有多裸露,生活就有多貧窮。對于這對父母而言,生殖繁衍是他們的本能,對待孩子的方式來自于民族的傳承和對生活的妥協,討生活、犯罪、暴力,將孩子鎖在家里。這樣麻木的人生狀態和極度貧窮的生存方式,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間循環延續著,這是個可怕的輪回,孩子們的命運也會是如此。贊恩和他的弟弟妹妹們也會組成這樣的家庭。輪回是一個可怕的死循環,仿佛無解。但當他逃離了家這個環境,步入社會以后才發現,他只是從一種絕望走進另一種絕望,離開原生家庭的結果不像他想的那么美好,所以他只能把對未來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人販子口中的那個烏托邦式的國家。
(二)救贖、斗爭在難民題材中的指涉
相對于好萊塢大片的過于煽情,最后孵化出一個英雄主義人物來為難民發聲,幫助他們走出困境,《何以為家》顯得那么蒼白無力。難民的生活是真實又難以擺脫的,他們只能做自己的英雄,他們只能憑借個人力量去和國家、和社會、和命運作斗爭,結果尤如以卵擊石,注定是失敗的,貧窮和苦難終將一代一代延續下去。《何以為家》用平實生動的鏡頭語言記錄了這些難民從一開始便無法擺脫的貧窮,一直到故事接近尾聲他們的命運都不會有根本性的嬗變。
四、隧道盡頭的光芒——繼續前行的力量
(一)從個體到世界的情感訴求
難民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導演并非對父母一味控訴,也并非對孩子一味同情。正如片名,一片混亂,難以解決。但是導演在結局的處理上給予了充分的人文關懷,贊恩的抗爭和命運由于一場審判而改變,到最后有了自己的身份證明,這是在混亂中留下的希望。貧窮和混亂是無力改變的一個事實,但是總要有人去發聲,總要有人讓我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并且去了解難民這個群體。
導演通過電影可以將飾演贊恩的小男孩一家從泥濘般的生活中解救出來,但是仍有數千萬個難民家庭等待救助。希冀未來會有更多的國際組織和政府會為了解決難民兒童的問題而做出更大的努力和嘗試。如果說由媒介與信息主導的當今社會,被無視就是最大的暴力,那么被看見是有可能改變這個世界的第一步。這也是導演充滿考量的地方。
(二)兒童難民問題的癥結
影片結尾的微笑是贊恩和這個世界短暫的對抗成功,每個人都是這個人道主義社會災難性悲劇的受害者,我們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已經泯然眾人。戰區國家中在難民營和無序混亂社區中茍活的孩子,早已經把自己的童真交付給了戰火紛飛的世界。在我們看來微笑是與生俱來的本能,贊恩站在鏡頭前費力微笑,卻仿佛過完了一生。深諳社會運行的規則,卻突破不了階層禁錮,生有何歡?
五、結語
導演通過鏡頭訴說了那些悲痛的歷史記憶,同樣也是對故鄉黎巴嫩的深情低語和對美好明天的殷切盼望。戰爭帶來的生與死是真切又窒息的歷史體驗。贊恩笑了,我們卻哭了,因為一切都還沒有結束。隔著鏡頭,那個世界的苦難和抗爭也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