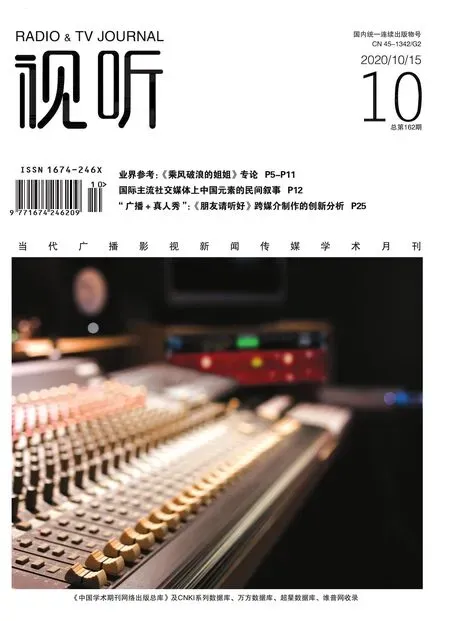韓國電影《寄生蟲》的影像風格分析
□ 唐曉燕
電影《寄生蟲》圍繞住在擁擠不堪半地下室的底層家庭展開,父母失業,兒女輟學,直到兒子的朋友為其帶來一個去富人家當家教的機會,一家四口的命運才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這是一部融合了犯罪驚悚與黑色喜劇于一體的“家庭悲喜劇”,導演奉俊昊嫻熟地運用視聽手段在各種風格類型中自如切換,充分展現了他對于類型片元素強大的掌控力。
一、建筑學式空間造型的構建
電影空間的選擇和建構,既是創作者的話語場域,又是電影文本的敘事載體。縱觀奉俊昊導演以往的幾部作品,可以看出他對于電影敘事空間的作用非常重視。通過“地下室”“審訊室”“下水道”“棚屋”“封閉的列車”等鮮明電影空間的描繪,導演試圖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生活場景進行影像的陌生化處理,從而在這些再造的空間里進行敘事。
《寄生蟲》在這一思路下建立了更封閉的建筑學式的空間改造。電影中的大多數戲份都在室內,甚至被主創自己稱作樓梯電影。從電影的第一個鏡頭開始就出現了半地下室的空間描繪,導演有意通過升降鏡頭引導觀眾的視覺欣賞,幫助觀眾在心中建立敘事與空間環境的關系。
整部電影基本在兩個主要空間里展開:一個是窮人基澤一家的半地下室,一個是富人樸社長的高檔豪宅。前者在下城,后者則在上城。同樣是一家四口,一個家庭住在山上,另一個住在洪水區泛濫的低城區,物理位置首先成為了貧富差距這一嚴肅社會話題的對比與參照。電影開篇,貧困家庭的兒子基宇從下城來到上城給樸社長的女兒當家教,他一路拾級而上,富人家庭奢侈豪華的大房子首先就從氣勢上給了底層窮小子很大的沖擊。影片中還有一處非常有沖擊力又讓人心酸的情節,大暴雨之夜基澤帶著兒女從上城回到下城自己的家,卻發現自家的半地下室已經被洪水淹沒,馬桶里不斷向上噴注著黑水,家具物品都漂浮在洪水中。兒子基宇望著下行臺階上不斷被洪水沖刷著的自己的腳有些發懵。而與此同時,住在上城的富人家庭卻絲毫不受暴雨影響,富二代小兒子任性地在家中露天草坪上搭起美國制造的帳篷體驗人生。對創作者而言,“底層”不僅是居住城市地理空間上的布局差異,而且是通過電影空間搭建起來的與身份尊嚴相關的敘事元素。
當然,隨著劇情推進,片中還出現了富人豪宅中“地上”與“地下”的空間對比。豪宅中的地下室是更陰暗的存在,是先前已經寄生在富人家庭中的傭人及其丈夫的居所。地下室的生活環境比基澤一家的半地下室還要糟糕,暗無天日,它的出現打破了基澤一家苦心構建的寄生關系的平衡,同類之間互相嫉妒互相傷害,引發了脫軌般的相互殘害的結局。到電影結尾,殺人潛逃的基澤再次寄生豪宅的地下室,期待兒子基宇“階級躍升”之后前來救贖自己,于是新一輪對于寄生的期待又重新上演。豪宅、半地下室、不為人知的地下室,如同建筑學一般嚴謹搭建起來的電影空間真實還原了三組家庭的生存空間,想要通過跨越階層而獲得相互寄生的美夢一個個被打破,奉俊昊導演對于階級的分化與批判又有了更深刻的作品表達。
二、電影視覺符號的意象傳達
由于電影的敘事非常依賴影像的直觀呈現,因此諸多的視覺符號都會被電影創作者作為關鍵的細節道具而加以利用。奉俊昊導演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也充分體現出對視覺符號的偏愛,“弱智”“狗”“怪物”“列車”等,通過著重描繪可視化的人或物,使觀眾可以清晰直觀地理解創作者的意圖,不受民族、語言和文化素質的制約。《寄生蟲》中反復出現的石頭盆景、豪宅樓梯甚至人體氣味都是經過巧妙設計的符號意象。
電影開場基宇的同學敏赫登門拜訪,把這一“可以帶來財運和考運的”假山盆景送給了一家人,基宇把石頭拿在手里仔細端詳,認定“很有象征意義”。接下來,這一“道具”就貫穿在整部電影中,可以用來嚇唬家門口小便的男人,也可以作為殺人的工具。在洪水淹沒的家中,漂起的石頭像是一家人泡湯了的寄生美夢;而在電影超現實主義的結尾片段中,被放進河水中的石頭又像極了卸下沉重階級枷鎖的基宇的心。在這一完整且具有流動性的意象表述中,石頭成為了鏡頭語言表達的對象,它既是電影道具又是電影符號,既是細節又是劇情,石頭的“象征意義”不言而喻。
豪宅樓梯的意象也是影像中推動敘事的實在體,而不僅僅是內景擺設,幾個廣角鏡頭表現人物上下樓的過程,就是在視覺化揭示階級固化造成的社會困境。影片多次安排基宇經由富人家庭客廳的上行樓梯到達家教的房間,導演試圖通過空間的角度與構圖來劃分表演區域,從而營造出貧富階層上下分級、窮人想經由“上行通道”寄生富人家庭的隱喻關系。
除此之外,電影還獨具創造性地引入了對“氣味”的描述,盡管嗅覺看不見摸不著,很難通過視聽語言來表達,但它卻成為本片中來界定身份、財富、地位的重要意象和隱形標簽。全片多次提到基澤一家身上有一種氣味,這是一種“地下室的味道”,因此追求上流的氣味成為了基澤一家人努力的目標。無形的氣味是構成貧富差距、階級歧視的重要元素,是窮人父親基澤無法忽視的心結,也是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影片結尾生日派對上,前管家丈夫逃出防空洞,捅殺基婷,嚇暈多松,當社長在取車鑰匙時下意識用手捂住鼻子防止聞到窮人氣味,受到刺激手足無措的基澤終于爆發了,他拿起刀將社長狠狠捅死然后逃到地下室。氣味成為底層人口對上流社會本質上的“原罪”,是階級之間難以撫平的差別和傷疤。
三、光影與色彩營造出的視覺幻象
光影與色彩是電影影像中用于推進敘事、表達情緒的重要手段。光是攝影的基礎,也是人們視覺感受的基礎;影視創作者也會利用人對不同色彩的情緒反應來選擇符合劇情、場景氣氛和人物心情需要的畫面主色。電影《寄生蟲》中,導演奉俊昊不僅利用貧窮家庭以及富有家庭在居住上的高度落差來表現兩者在財富與地位上的懸殊,也非常在意在光線捕捉與色彩對比上反映貧富差距這個議題,“只要你越窮,你能接收到的光線就越少,相對的,你越富有,能沐浴的陽光就越多。”
電影中所有戶外搭建的場景上幾乎都用了自然光,窮人半地下室的小小窗口里昏暗壓抑,而富人豪宅的客廳前卻有一個巨型落地窗,陽光普照。這一暗一明的對比從電影開篇第一個鏡頭開始就貫穿了始終,成為電影影像的有力表達。在電影最后的悲劇結尾中,從地下室走出來的原管家丈夫持刀走向明亮的后院草坪,開始了一場血腥的殺戮。這場戲與一般的驚悚片不同,整個場景的光影以高調光為主,在視覺上這場鬧劇顯得格外刺眼,有更強烈的沖擊力。導演所說的“充滿喜劇色彩的驚悚片”在這一場戲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低調光與光調光的配合,再結合色彩飽和度上的對比差異,共同營造了電影的敘事空間。窮人金基澤的家擁有更多的顏色,色彩基調也是以灰色、綠色、白色為主的冷色調。但這些顏色卻不鮮明,在整個飽和度上是相對較低的,讓人無法明顯觀察到特別突出的顏色,另外這個半地下室也更加擁擠,在整體密度上有明顯的壓迫感。而富人樸社長家豪宅擁有大空間、井然有序的擺設,并且有著明顯可調控的顏色比例,和半地下室形成鮮明的對比。色彩是情緒的直接外在表達,身為觀眾我們會在無形之中就感受到家庭狀況因為經濟條件的不同而有著天與地的差異。
縱觀整部影片,豐富的鏡頭語言把兩級權力關系充分視覺化,并將打造視聽盛宴的場景空間建構、道具符號性、光影視覺感等與“貧富場域”的敘事模式關聯起來。導演奉俊昊對于電影影像風格的準確又獨特的把握,幫助電影《寄生蟲》完成了對好萊塢固有商業片類型的突破與超越,形成了作者電影的獨特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