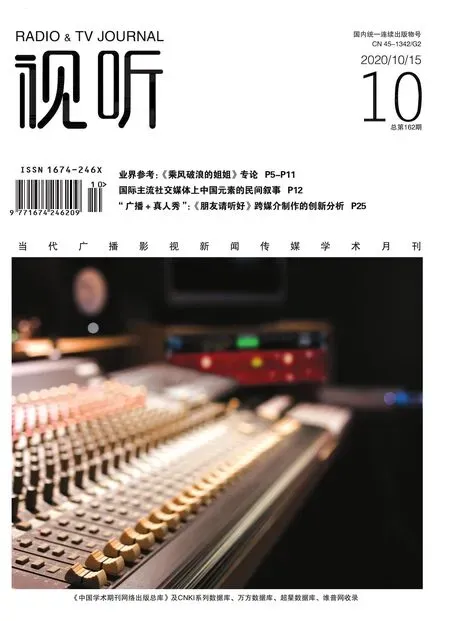電影《蘇州河》的后現代性分析
□ 段雪菲
現代社會出現了多種多樣的文化形式,如偶像劇、商業電影、網絡小說、流行樂曲等,它們占據了市場的主流,與此同時還承擔著特殊的社會功能,即“民眾參與的社會意義的生產和流動”,后現代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思潮或文化形式,它是一個兼具結構性與批判性的理論。茱迪·威廉森曾說,“在我們的文化批評實踐里,存在著偏愛一個文本勝過另一文本的現象,我們已經制造出了自己的經典。盡管高級藝術和低級文化之間的分界已經模糊,我們還是沒有完全放棄藝術的概念”。我們從中可發現,在后現代社會,高雅與通俗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間不再有明顯的分界。在后現代社會,一切似乎都無章可循和變幻莫測。
婁燁在電影《蘇州河》中講述了一個頗具浪漫的愛情故事,但是影片并未給觀眾帶來視覺上的滿足和情節上的期待。觀眾在影片中并未看到緩緩流淌著的美麗的河流,影片中呈現了一個非自然的現實。人類掌握了主動權,居住在河流兩岸的人們控制了河流,由于嚴重污染,蘇州河已不再具有觀賞性,流淌著污濁的渾水。上海是一個兼具中西方特色的國際大都會,在這里,流淌著這樣一條渾濁不堪的河流。城市的發展、經濟的騰飛在都市中處處可見,但是蘇州河卻代表著發展中的城市的真實景象,即人們的生存現狀。導演婁燁拍出了一條流淌著的蘇州河,攝影機搖晃的畫面呈現了蘇州河的真實面貌以及沿岸人們的生存狀態。雖然晃動的畫面使觀者感覺到不適,但是這種擺動與眩暈給觀眾以視覺上的沖擊,引導觀眾進入故事,切身體會主人公的悲歡喜樂。導演婁燁并未遵從影片藝術的說教這種古老的藝術功能,也沒有告知觀眾如何走出迷途,而是通過影片傳達了現代城市青年人的情感狀態與生活現狀。
一、《蘇州河》中的解構主義
在《蘇州河》中,并沒有傳統影片中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只有日常生活中我們能夠見到的普通人。他們沒有做出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舉措,他們僅僅是生活中的人,導演告訴我們生活就是表面光鮮亮麗卻隱藏一條流淌著渾濁污水的蘇州河。《蘇州河》講述了一個關于尋找的浪漫的愛情故事,馬達與牡丹因送貨而相識,后來成為戀人。馬達綁架了牡丹,當牡丹得知被綁架的目的是為了巨額贖金后,萬念俱灰跳入了蘇州河。馬達失去了愛人,與此同時,更失去了自由。馬達出獄后,在蘇州河沿岸尋找牡丹,追尋曾經失落的愛情。在找尋過程中,馬達發現了一個幾乎和牡丹長相一模一樣的女子美美,便將美美當作自己的愛人。在這里,外貌的本真性受到了質疑。鮑德里亞曾提出“鏡像理論”,試圖解釋人們在鏡子中看到的自己并非真實的自己,而只是一個鏡像的呈現。后現代文論家對真實性提出質疑,在婁燁的作品《蘇州河》中,我們同樣發現了后現代主義文論對于我國文化生活形態的滲透。
影片《蘇州河》中,同樣的能指并不代表同樣的所指,即相似的外貌并不等同于同一個人物。后現代主義中的解構主義認為,最初的解構是從語言開始的,通過闡述語言意義的不確定性來進一步闡發解構主義。德里達認為,符號所表現的意思并非兩個符號之間差異的結果,語言并非像索緒爾所描述的那樣是能指與所指恰恰相對應的統一體,每一個符號的意思實際上是因為這個符號不是其他所有的符號,也就是說,符號意思就是在所有符號之間無限的差異中,它只能是潛在的、無休止的相互差異的產物,語言就是一個無限差異、無限循環的系統。德里達提出了延異等幾個概念。延異是在語法差異的一詞的基礎上替換第七個字母E為A而改造得來的,糅合了“差異”和“延遲”這兩個詞義。一方面存在意義存在的差異性,另一方面由于意義的差異而帶來的傳達和理解的推延和阻隔。
當偏執的馬達確定美美并不是牡丹時,又開始繼續尋找牡丹的旅程,最終在一家便利店中找到了牡丹。也許此時觀眾期待影片結局將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但是導演卻沒有給觀眾預期的期待,而是以悲劇收場,馬達與牡丹死于車禍。在電影末尾,美美看到了長相酷似自己的牡丹,導演以此呈現出后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美美離開了蘇州河,留下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局。正如德里達所提出的“延異”,即對于意義的不確定性。德里達認為,詞語永遠沒有一個終極的確定的意義,一個所指指向其它的能值,又由這些個能指指向更多的所指。因此,意義是不確定的。婁燁讓美美得知現實之后,獨自離開,開始她的故事,這同樣是對“延異”的闡述與詮釋。婁燁所設定的不完滿的結局是對傳統電影結局的解構,婁燁告訴觀眾,電影并非都有美好的團圓,悲傷的結局往往發生于現實生活當中,也許更能體現現實。
二、《蘇州河》中的互文性
互文性指的是文本之間的“互文見義”,即文本經常憑借和模仿其他文本,或者無論有意或是無意以其他的方式與其他文本相互聯系。這種借用和影響之間的聯系并不是簡單復制,而是一種動態的拼湊。互文性要以具體的語境為依據,也許是作者刻意而為,也有可能是作者記憶深處的某一個片段。婁燁說,“這些被看成是在‘模仿’中長大的一代人,他們的‘模仿’實際上是真正獨創的。”模仿并非照搬或復制,而是一種經過了創造的再現,能夠在中國的具體社會語境中恰當地應用文本樣式。在電影《蘇州河》中,可以窺探到對《維洛尼卡的雙重生活》這部電影的模仿,這是歐洲著名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在這部電影中,呈現了兩位容貌相似但生活環境不同的女性。波蘭和法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成長環境,不同的社會語境卻造就了兩顆能夠相互感應的心靈。電影《蘇州河》中的牡丹與美美同樣有著驚人相似的外貌,但是二人成長于不同的環境。有著相同外貌的二人看待對方就像一面鏡子一樣審視著自身,因而在電影《蘇州河》中互文式地顯現出《維洛尼卡的雙重生活》的影子。
三、反主流文化
這類題材的電影作品并不是企圖以題材上的禁忌來贏得關注,長久以來,觀眾似乎有一種觀影的盲目性,追尋夢想中色彩斑斕的幸福世界,而這恰恰蒙蔽了灰暗的現實。德里達曾提出“‘揭秘’批評”,他所揭秘或對抗的是人們通常稱之為“信條”或“神話”的觀念,即流行的,已成為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東西。他認為這種神話的產生是由于迷失了事物的歷史本質,即忘掉了事物的構成性,這就使得最后產品成了一種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東西。但是作為藝術家,有責任將現實生活呈現在銀幕上。在婁燁作品中的人物大多處于社會底層,這是一群被所謂主流群體排斥的人,大多數觀影群體的生活環境與這些主人公不同,導致了受眾群體與影片人物的距離感,因此很難獲得認同,即不能滿足觀眾的期待視野。這類作品回避了通俗電影中精致的畫面與浪漫圓滿的期待,而是以電影為媒介講述了國際大都會中青年人真實的生活現狀,觀眾很難找到常規的敘事模式,更多的是一種非線性的敘事手法以及破碎地拼接。冷峻殘酷而又直面現實的影像正沖擊著人們的神經,雖然未能給受眾帶來以往的期待與快感,但使大眾敢于直面現實的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