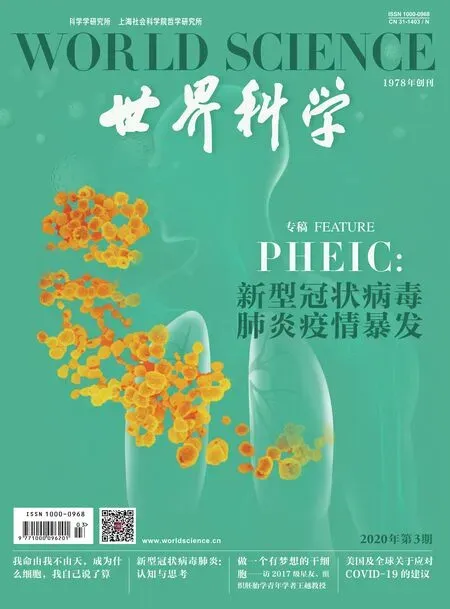對待高風險病毒,如何防患于未然
編譯 莫莊非
非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彼得·達扎克(Peter Daszak)接受了《科學家》雜志肖娜·威廉姆斯(Shawna Williams)的采訪,這位深耕傳染病領域的科學家對中國和其他地區的新型病毒進行了廣泛、大量的研究。此次訪談,他就諸如冠狀病毒等病原體如何跨躍物種傳播以及如何防止下一次大規模流行病暴發的話題發表了觀點。
您能否概述一下冠狀病毒的進化以及它們是如何成功跨物種傳播的?
我們親眼目睹了幾起冠狀病毒從動物(包括牲畜)傳染給人的事件,而研究者也做了大量工作分析這個傳染過程。對于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我們知道關鍵在于確定宿主細胞上的受體,也就是病毒結合并侵入的細胞表面蛋白是什么。如果病毒與我們結合的細胞表面受體,與在蝙蝠、駱駝或豬中結合的相同,那么該病毒入侵我們的風險就存在。
對于SARS冠狀病毒,其對應的細胞表面受體被稱為ACE2,即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我們與蝙蝠都有這個,而SARS病毒也確實在蝙蝠和人類體內都結合了這個受體。而這一次的SARS-CoV-2恰恰也入侵ACE2。雖然,當下對于為什么病毒能夠跨物種傳播有一些線索,但找到ACE2結合并入侵,是其進入人體能力的基礎。
實際上,這些冠狀病毒在野外多樣性豐富。自從SARS暴發以來,我們就一直在研究蝙蝠,因為我們發現它們是SARS的真正儲藏庫,而非最初認為的果子貍。我們發現冠狀病毒的多樣性是如此之大:僅在蝙蝠中就發現了50多種與SARS相關的冠狀病毒。
令人擔憂的是,你可以使用針對SARS研發的疫苗和療法來治療其中某些病毒引發的疾病,但如果這些病毒與蝙蝠攜帶的其他病毒組合在一起出現,療法就失效了。因此,我們一直在說蝙蝠體內的幾種病毒組合是可能帶來危險的。實際上,我們開發過一種針對某個病毒組合的抗體試驗,也去過云南的農村,對生活在蝙蝠聚集地(也是我們發現這組病毒的地方)附近的居民進行了測試。結果我們發現那兒有3%的人感染了這組蝙蝠攜帶的病毒。這表明蝙蝠病毒一直在某個地區蔓延,并以輕度感染(無臨床癥狀)或引發無法明確診斷的呼吸道疾病的方式,侵襲人類。
哪些因素會導致疫情事件擴大,大到像這次武漢的疫情一樣?
這有病毒學方面的原因,也有人口層面的原因。從病毒學角度來看,顯然其中一些病毒與受體結合得不好,沒有導致嚴重感染,但其中一些病毒卻做到了,不僅結合得好,還導致了嚴重感染,不過從這個角度看,其實很難預測疫情。
從人口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如果其中一種病毒進入野生動物市場,它通過某種動物傳染給多人的概率就會明顯增大。以云南的蝙蝠洞為例:人們很少進入洞穴,不過蝙蝠會飛出山洞,在周圍的村莊里捕食昆蟲,如此一來,病毒傳播的輻射面會擴展到數千人。但哪怕如此,病毒在人群中擴散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可是當人們開始在山洞里捕捉蝙蝠,然后將它們帶入市場,那么它們在那兒排出的糞便就會實現真正意義的病毒暴露出來,然后,病毒就可以侵襲果子貍、豬以及人類……另一方面,如果蝙蝠一開始在像養豬場之類的農場附近覓食昆蟲,然后豬或是該農場中的其他一些動物(例如竹鼠)被感染,那么受感染動物的數量一下子就很多了,如果不幸這個病毒還能傳給人,那么向外傳播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此 次SARS-CoV-2與SARS-CoV很相似,這是否有助于我們應對它呢?
在我看來,對SARS-CoV-2進行的系統發育學研究顯示,新病毒與我們預想的沒有太大不同。它是蝙蝠攜帶病毒群的一部分。SARS-CoV曾是該集群中的一個大流行毒株,現在又有了一個新的。我猜測在該群集中還有其他可能導致大流行的病毒。這是一個重要的教訓,雖然我們已經知道有15年之久了。我們應該像激光一樣專注于這個集群,研究這些病毒可能入侵人類的所有可能方式,并努力防止這種溢出。目前最大的威脅是我們還沒有可以抵抗SARS病毒的有效疫苗或有效藥物,更不用說SARS病毒的“親戚”了。
您建議我們應該為那些尚未感染人但存在此類風險的病毒開發藥物嗎?
當然!不過我想說的是,除了將精力集中在一種特定病毒之外,我們還應警惕其整個進化枝,確保這些藥物對整個進化枝都有效。這可能意味著需要對某些單克隆抗體療法或疫苗進行一些調整以使其應用范圍更廣。如果我們花幾億美元研發出SARS疫苗,但發現它不能用于下一個出現的病毒,那么我們不僅浪費了錢,還耽誤了救人。
您想補充什么嗎?
對我們而言,大方針應該是將這些流行病視為公共衛生問題……比方說心臟病,我們知道心臟病的原因,不能等到患上了這個毛病再對其進行治療,而應該改變其生活習慣。而且我認為我們需要在全球范圍內以相同的方式對待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