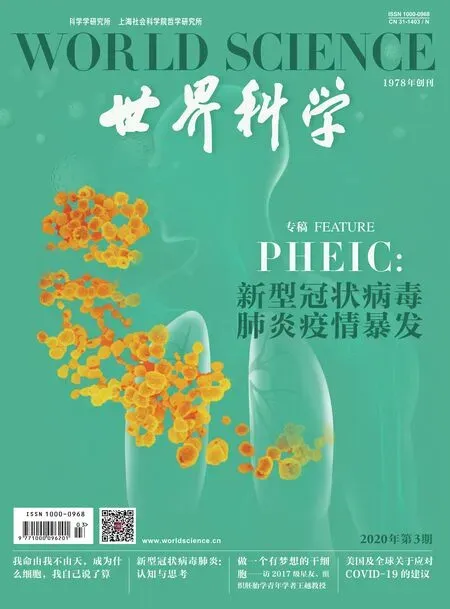化學家能否破解糖的編碼?
編譯 莫莊非
在我們體內,簡單的糖(例如葡萄糖、甘露糖和巖藻糖)連接在一起,形成了復雜的多糖(或者說聚糖),這些多糖修飾著細胞的表面,形成了一層厚厚的“糖衣”,但與基因組和蛋白質組不同,那些“糖衣”中的糖組目前對我們來說仍是待解之謎,部分原因是聚糖的化學結構太過復雜。我們的身體合成了數(shù)千種獨特的聚糖,但是很少有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闡明其結構。與線性組裝的DNA和蛋白質不同,聚糖高度支化,使其難以合成。當然,智慧的化學科學家正幫助我們更趨近于破解糖的編碼。
寡糖主要附著在蛋白質和脂質上,這一事實過去一直被生物學研究忽略。但美國佐治亞大學的吉爾特-簡·布恩斯(Geert-Jan Boons)表示寡糖應該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我認為在過去的十年中,寡糖幾乎參與了機體的每一個健康與疾病的過程。”細胞的糖衣可以提供獨特的細胞條形碼使免疫系統(tǒng)能夠識別其他細胞(包括外來入侵者)。一個公認的事實是,異常的糖基化似乎會推動癌癥發(fā)展,特別是高度唾液酸化作用——因為唾液酸糖含量過高。唾液酸糖連接于聚糖鏈的最外層,主鏈上有9個碳原子。
對于專業(yè)研究者來說,長期研究目標是完整定義糖組學這一概念。所謂糖組學,是研究在細胞或生物體中產(chǎn)生的整套聚糖的結構和功能。但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碳水化合物化學家薩賓·弗利奇(Sabine Flitsch)認為這項工作比定義基因組或蛋白質組更復雜一些,她解釋說道:“糖組不是由基因組直接編碼的,你無法將糖的結構與一種特定的蛋白質(或基因)聯(lián)系起來。糖基化(即聚糖的添加)是一個轉錄后修飾的過程,組裝糖的200多種酶不提供模板。酶與糖核苷酸的可利用性決定了生物合成的結構類型。”
除了不由基因組直接編碼,聚糖數(shù)量過多也是研究的障礙。用10種常見的單糖去組合聚糖,可能的組合結構數(shù)量要比DNA或蛋白質的結構數(shù)量多得多。由6個糖分子組成的六糖可以有1 930億個可能的結構。另外,聚糖的種類很多,包括與氨基酸天冬酰胺連接的N-連接寡糖,與蘇氨酸或絲氨酸連接的O-連接寡糖,以及糖胺聚糖——長鏈的高極性多糖,可作為生物潤滑劑(例如肝素和血液,以及防止血凝塊的血液稀釋劑)。
合成挑戰(zhàn)
從自然界中提取純的聚糖通常是不可能的,因此化學家們需要合成大量可能的聚糖。這并不容易,因為它們有多種異構形式。聚糖有非常多的單糖排列方式和支化結構。異構體可以是基于不同的環(huán)尺寸和不同的取代位置(區(qū)域異構體)的。弗利奇說道:“你還必須正確理解連接的立體化學——是α連接還是β連接,這可能是最大的挑戰(zhàn)之一。”在糖基化中,碳水化合物(糖基供體)與另一個糖(糖基受體)的羥基相連,形成異頭碳,從而允許在兩種可能的構型之間轉化。最終產(chǎn)物可以是α或β構型。弗利奇解釋說:“只有進行大量的保護基化學反應,才能獲得化學選擇性。每個偶聯(lián)步驟需要大約7個化學步驟。”
一種提升速度的方法是使用堅固的支撐架來實現(xiàn)自動化。彼得·西伯格(Peter Seeberger)來自德國波茨坦的馬克斯·普朗克膠體與界面研究所,他于2013年創(chuàng)立了糖宇宙(GlycoUniverse)公司。該公司開發(fā)了一種全自動寡糖合成儀Glyconeer,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已有8臺投入使用。糖宇宙的科學負責人馬里奧·薩爾維切克(Mario Salwiczek)解釋說道:“Glyconeer能固態(tài)合成寡糖,其中訣竅在于第一個結構單元連接到不溶的聚合物上——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聚苯乙烯微珠。好處在于你可以除掉所有尚未反應的反應物或已形成的所有副產(chǎn)物,而不必在每個偶聯(lián)之間進行純化步驟。”
西伯格用這種方法制成的最長糖鏈是線型的50糖寡糖(50-sugar oligosaccharide),更典型的寡糖是6~10個單糖分子脫水縮合而成的。“很明顯,這項技術本身無法解決我們面對的化學問題,”西伯格指出,“一種策略是開發(fā)多種糖的通用結構單元。”布恩斯說:“我們想出的解決方案是巧妙地選擇結構單元。寡糖在結構上非常復雜,但是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以不同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形成某些特定構型。”
布恩斯和其他人已經(jīng)合成出了此類構型的聚糖,它們能通過多種方式進行組裝。他用這種方法合成了由20種二糖制成的合成肝素,而這20種二糖僅僅由6種不同的單糖組裝而成。
生物催化
另一個重要進步是使用了糖基轉移酶,它能將單糖從活化的糖單磷核苷酸或糖二磷核苷酸轉移到寡糖鏈。20世紀80年代,該方法被證明可用于合成復雜的聚糖,其中每個鍵由不同的酶合成。
弗利奇表示:“糖基轉移酶的優(yōu)勢在于,它們可以完全照顧到所有區(qū)域及立體選擇性。它們要用2個通用的結構單元,并以非常特定的方式發(fā)揮組合作用。建構出α-或β-端基異構體取決于核苷酸受體是什么。機器內部的化學合成需要7個步驟,而這個操作其實一步就夠了。化學家可以通過碳水化合物活性酶(CAZy酶)的數(shù)據(jù)庫來輔助設計合成方法。對于這些生物合成所需要的酶,我們已經(jīng)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布恩斯說:“五六年前,這類合成工作基本要靠博士來完成,而現(xiàn)在,我們大家在周末就可以做。不過缺點是,如果你想建構一個非自然的結構,或者具有更多類藥性的結構是存在困難的,因為酶并不擅長。”布恩斯一直努力通過一些化學方法與酶的協(xié)同工作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他僅用10個化學和酶促步驟就合成了具有多達4個不同分支的N-聚糖。
他采用從蛋黃粉中分離出來的對稱雙觸角糖基衍生物作為結構單元;然后,他向其中添加了一個非天然的糖核苷酸供體——5'-二磷酸-N-三氟乙酰基葡萄糖胺,得到一個中間態(tài)結構;當使用酶進一步延長聚糖分支時,非天然分子對酶的作用呈惰性,因此進一步的反應選擇性地發(fā)生在了其他支鏈上;接著,非天然葡萄糖胺被轉化成了其天然對應物,從而允許進一步的酶促反應。布恩斯稱該策略為“打打停停”。他說道:“我們真的相信酶和化學的結合正在革新創(chuàng)造這些分子的過程。”
怎樣分析合成物?
合成聚糖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對其進行分析也至關重要,這不僅有助于定義人類糖組,對于生物制藥也很重要。許多生物藥物是糖基化的,例如促紅細胞生成素(EPO)這一臭名昭著的性能增強藥物。弗利奇說:“如果不對它進行糖基化,它就不會在人類體內活躍。”但分析聚糖結構并不簡單,而且很難復制生物藥物。她補充說:“非專利藥公司非常渴望獲得更好的分析方法。”
大多數(shù)現(xiàn)有的針對聚糖的分析技術都存在問題。當前的方法通常涉及與質譜聯(lián)用的分離技術,但是色譜法設計時要考慮到肽。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的有機化學家凱文·佩吉爾(Kevin Pagel)表示:“糖比肽極性更大,結果,成熟的反相分離技術實際上對糖不起作用。”在單糖本身及其組成的結構中發(fā)現(xiàn)的異構現(xiàn)象(葡萄糖、半乳糖和果糖都通用),有時無法通過質荷比進行質譜分析,NMR也無法區(qū)分立體化學細節(jié)。佩吉爾補充道:“分析簡單的三糖可能非常具有挑戰(zhàn)性。”
N-聚糖更易于表征,但O-連接聚糖問題很大。粘蛋白(mucins)是一種存在于黏液中的,具有很長聚糖鏈的蛋白質,經(jīng)過了密集糖基化且體積很大,它在表征方面也面對著巨大的挑戰(zhàn)。糖胺聚糖也很難表征,這也解釋了肝素分析遇到的問題——2008年,受污染的肝素在全球造成200多人死亡,這是制造商使用了非活性化合物作為替代所導致的,而在常規(guī)測試中,這兩種物質無法被區(qū)分。
弗利奇說:“我們真正想要,也正在努力研發(fā)的是一種可以用于所有聚糖分析的通用技術。一種可能有用的技術是離子遷移譜(IMS)——機場安全部門用它來篩查爆炸物。將它與質譜組合,可以根據(jù)物質的質量、電荷、大小和形狀來區(qū)分氣相離子。佩吉爾解釋說:“不同的異構體通常具有不同的大小和形狀,這使該方法成為表征聚糖的理想選擇。”
離子在弱電場的作用下被引導通過氦氣或氮氣,它們的碰撞速率會發(fā)生變化,較大的橫截面分子會更頻繁地碰撞且漂移時間會更長。IMS與質譜聯(lián)用,可以區(qū)分較小的完整聚糖的不同異構體。
在執(zhí)行離子遷移率測量之前,使用一組有限的標準片段指紋圖譜,對大的聚糖進行片段化可以提供一種與通用測序方法相近的方法。弗利奇說道:“這有點像霰彈槍定序法。”至關重要的是,碳水化合物片段似乎保留了其立體化學的記憶。她補充說:“它看起來會有所不同,具體取決于它是來自α還是β連接——這是測序規(guī)程的又一關鍵步驟。”
另一個重要的進步是紅外多光子離解(IRMPD)光譜。使用高強度激光,通過觀察鍵解離時吸收光子的過程,間接測量紅外光譜。使用質譜測量碎裂產(chǎn)率(fragmentation yield)隨波長的變化,可以得到振動光譜。不過佩吉爾也指出了一個缺點:“在室溫下,所得光譜特征的可診斷性通常很差,因為它們通常很寬泛。”
他接著說道:“我們第一次是在超冷溫度下用糖做實驗。我們獲得了振動指紋,其分辨率非常好,這也使我們能夠弄清聚糖中的每一個結構細節(jié)。”通過冷卻超流體氦液滴中的離子,佩吉爾等人將物質的溫度降至-272.75℃,并使其處于一個極低的能態(tài)。他們明確地區(qū)分出了一系列三糖異構體——在某些情況下,它們的區(qū)別僅在于單個羥基的立體化學性質的不同。
那么結合這些新方法,聚糖測序會成為現(xiàn)實嗎?布恩斯說:“我認為我們已經(jīng)開始具備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綜合能力。”不過佩吉爾依然認為,對完整的人類糖原進行測序可能在20年后還會是一個挑戰(zhàn)。因為與DNA和蛋白質不同,糖組是高度動態(tài)的。弗利奇指出:“人體的糖組之間存在巨大的個體差異。”雖然DNA的差異僅僅是每千個殘基出現(xiàn)一次,但糖組的差異是高度依賴于環(huán)境的。
微陣列
加拿大艾伯塔大學的拉拉·瑪哈爾(Lara Mahal)是聚糖微陣列研究領域的先驅,她對糖組的看法有所不同。瑪哈爾不確定我們是否真的需要它。她說道:“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同行們一直覺得我們需要明確離散結構以及這些結構的每一個細節(jié),但是如果你關注自然,就知道它不在乎是否有一個離散的結構,它在乎的是一組可以實現(xiàn)特定功能的結構。問題在于,我們需要每個單獨的結構嗎?或者我們能夠了解子結構的變化嗎?”
為此,瑪哈爾等人致力于開發(fā)可使用高通量自動化研究糖蛋白相互作用的微陣列。這種陣列將各種聚糖排列在固定于支撐物上的微小斑點中,與聚糖結合蛋白、細胞甚至整個病毒群一起培育。他們使用熒光標簽觀察結合過程。
19世紀初期,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滕·菲茲(Ten Feizi)開發(fā)了第一種固定聚糖的方法。她將脂質接頭連接到聚糖上,形成了“新糖脂”,然后可以將其固定在硝酸纖維素表面上。帝國理工學院糖類微陣列設備負責人劉燕(Yan Liu)說:“采用共價陣列控制載玻片上的聚糖濃度并不容易。”如果聚糖太密集,或聚集方式不對,則結合的條件可能就有問題。借助“新糖脂”,可以使聚糖以非共價鍵結合到基質表面,而且這些聚糖似乎是能夠移動和聚集的——這更好地模仿了細胞表面的聚糖排列。劉燕接著說道:“這種形式對許多類型的內源性和病毒性聚糖結合蛋白非常有用,對抗體也非常敏感。”
連接脂質的第一種方法是伯胺基和聚糖之間的縮合反應,但這會導致核心單糖的開環(huán),對短鏈聚糖是不利的。2007年,劉燕設計了另一種肟連接法。他們對脂質進行了修飾,使其包含一個氨基-氧基基團,該基團經(jīng)偶聯(lián)形成了一個穩(wěn)定的肟鍵(RHC =NOR')。劉燕表示:“基于這種方法,我們通過提供短寡糖和核心支鏈聚糖來進行配體結合研究,從而大大拓寬了基于‘新糖脂’的微陣列系統(tǒng)的范圍。”
帝國理工學院的聚糖庫是歐洲最大的,大約有1 000個序列,可供所有研究人員進行測試,但人類可識別的聚糖可能有7 000種(實際數(shù)量尚不清楚)。劉燕說道:“我認為我們漏掉了很多。另一方面,我們擁有那些在許多識別系統(tǒng)中起著重要作用的聚糖的主要封端基團。”
瑪哈爾采取的方法是使用微陣列查找疾病(包括癌癥)的生物標記。19世紀中期,她開始研發(fā)外源凝集素——結合糖類的植物蛋白——的高通量陣列。瑪哈爾解釋說:“自然界已經(jīng)進化出具有非常特殊的分子識別表面的蛋白質。它們確實擅長識別一些相似的分子結構間的區(qū)別。例如α-2,6鍵與半乳糖鍵接的,與α-2,3鍵與半乳糖鍵接的唾液酸結構間的差異就可被那些蛋白質識別,而且是能夠立即分辨出來,可質譜分析就無法輕易做到這一點。當然,使用這種方法并不能確定精準的結構,但它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確定糖的變化方式的快捷途徑。”
瑪哈爾的研究小組也一直在嘗試了解糖基化在生物學層面是如何被控制的。他們將其與微RNA(miRNA)聯(lián)系在一起。瑪哈爾認為,這種機制控制著引發(fā)糖基化的轉移酶。她說道:“我們試圖找出糖基化酶的完整miRNA調控過程,作為解決其中某些問題的第一步。”
顯然,無論是要弄清糖組,還是搞明白基礎生物學,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弗利奇說道:“我認為碳水化合物化學確實將有機化學推到了極限。”不過瑪哈爾也指出,不要把糖組學看成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我認為糖組學一直存在的問題之一是,人們覺得它很難,而我會挑戰(zhàn)它……實際上,在生物學中又有什么是不復雜的呢?”